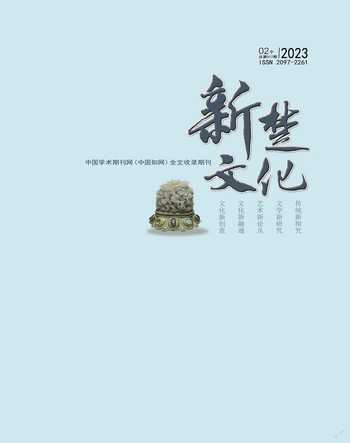論新世紀兒童小說中的留守兒童形象塑造
頡瑛琦
【摘要】新世紀以來,兒童小說在對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上經歷著不斷的探索與變遷。新世紀初,兒童小說圍繞留守兒童成長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采用苦難敘事策略,塑造出一系列問題留守兒童形象,造成留守兒童形象的模式化、同質化傾向。對留守兒童形象的日常化呈現將兒童小說從揭露社會問題、書寫留守兒童苦難生活境遇的表層進入對留守兒童日常生活和心靈世界的深入觀察,有助于塑造出具有獨特個性特征的典型形象。在鄉村振興的時代語境中,兒童小說側重敘寫留守兒童在逆境中的成長與心靈蛻變,彰顯留守兒童獨特的生命意志與精神力量,使得留守兒童形象更為豐富多元。兒童小說應以促成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為價值旨歸,采用多元化的創作方式突破留守兒童形象模式化、同質化的問題,以生動豐滿的人物形象引領少年兒童成長。
【關鍵詞】新世紀;兒童小說;留守兒童形象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05-0024-04
自20世紀末以來,伴隨著中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村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獨特景觀。受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和農民工自身經濟條件的制約,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無法將子女帶在身邊,這些兒童不得不獨自留在農村,或由親友代為監護。
有關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全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97萬人。龐大的留守兒童群體及留守兒童特殊的成長經歷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留守兒童作為一種創作題材逐漸進入兒童文學作家的視野,對農村留守兒童的書寫成為新世紀兒童小說引人注目的創作現象。
兒童小說書寫農村留守兒童的特殊童年經歷和成長體驗,塑造出了眾多留守兒童形象。兒童小說對留守兒童形象的刻畫顯現出兒童文學作家對農村留守兒童生活現狀的密切關注,凝結著兒童文學作家對留守兒童群體的關懷,有著對社會轉型期鄉村童年問題的思考。
一、留守兒童形象的問題式塑造
留守兒童在成長過程中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加之青春期的叛逆、情感的空缺等因素,導致留守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易出現逃學厭學、心理失衡、性早熟、性格偏激、違法犯罪等問題,這不僅是新聞媒體報道的焦點,也是以留守兒童為主人公的兒童小說表現的主要內容。兒童小說圍繞留守兒童成長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采用苦難敘事策略,塑造出一系列問題留守兒童形象,將留守兒童等同于問題兒童,成為兒童小說塑造留守兒童形象的流行法則。
牛車的《空巢》是一部表現三峽庫區留守少年生活的長篇小說,作者揭露了留守生活的艱難與殘酷,書寫留守少年成長歷程中的傷痛體驗。小說塑造了農村留守少年群像,然而這些少年擁有的不再是充滿希望和朝氣的花樣年華,由于缺少父母的陪伴和引導,變得憂郁、迷惘、沉默、頹廢、脆弱、孤獨、無助……這些關鍵詞成為留守少年的共有標簽。王巨成的《穿過憂傷的花季》中的初中女生向華萍因一次醉酒留宿在同學家里而意外懷孕,等待她的是身體上的痛楚和輟學離鄉打工的命運,羅大勇與社會閑散人員結交并參與偷盜,最終死于一場說不清的“意外”。成長中父母的缺席,讓留守少年身陷迷途,也讓他們人生中明媚的花季充滿了無盡的憂傷。在陸梅的《當著落葉紛飛》中,父母長期的缺席導致留守少女沙莎對父母心生怨恨,也讓她的性格逐漸走向偏激,在父母離開后,沙莎開始喜歡收集刀子,冰冷的、鋒利的刀子正如沙莎叛逆的內心,最終沙莎在校外用刀意外傷人,被送進了少管所,里面的少年犯大多是留守兒童,無人照管的留守兒童行走在犯罪的邊緣地帶。齊建水的《笨狗》中的莊大旺與不良少年結識,沉迷于網絡游戲,不惜以偷盜的方式獲取上網的費用。雪燃的《離殤》中的留守兒童因缺少家庭關愛與父母管教,導致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問題頻生。王華性格孤僻、自我封閉,穆青月因過于想念父母而精神失常,李光強性格暴躁,經常打架斗毆……創作者通過對留守兒童形象的問題式塑造,揭示出長期親子分離對留守兒童身心發展造成的傷害,呈現出由留守帶來的童年之殤。
兒童小說對留守兒童形象的問題式塑造更加側重于對留守兒童群像的勾勒,作品中的留守兒童形象總體上呈現出灰暗的色彩,他們或是在現實生活重壓下的早熟、敏感、憂郁、自卑的兒童,或是誤入歧途的問題少年,作品缺乏對留守兒童個體精神、心理、情感的深度挖掘,留守兒童形象顯現出模式化、同質化的傾向。
創作者出于對留守兒童苦難境遇的同情和對留守兒童的人道主義關懷,通過對問題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意圖喚起社會對留守兒童群體的關注。從這一角度講,兒童小說對問題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然而,兒童小說對此類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僅停留在暴露問題、渲染苦難的層面,作品中的留守兒童形象充當的只是各種問題的代言人,“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作為社會問題存在的兒童群體和童年現狀而非作為生命個體的兒童”[1],作品對人物的塑造僅僅止步于對各種成長問題的發掘和呈現,對現實的無力感壓倒了自由無羈、擁有夢想,敢于沖破一切的童年精神。兒童小說對留守兒童形象的問題式塑造,使得童年精神在這些留守兒童形象身上難覓蹤影,除了對留守兒童苦難境遇的同情外,這些留守兒童形象難以有打動人心的力量。
二、留守兒童形象的日常化呈現
新世紀以來,兒童小說對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經歷著不斷的探索與變遷,當留守兒童引發的各類問題已得到各方面的廣泛關注后,許多兒童文學作家試圖擺脫書寫留守兒童苦難生活境遇、塑造問題留守兒童的創作模式,更多地轉向對留守兒童日常生活與精神世界的敘述,由對留守兒童群像的勾勒轉向對留守兒童個體內在精神、情感世界的細致描摹,這成為留守兒童形象建構的另一路徑。
王安憶的長篇小說《上種紅菱下種藕》講述了九歲女孩秧寶寶成長過程中的一段留守生活經歷。秧寶寶的父母同去外地做生意,把她寄養在了退休教師李老師家中,秧寶寶成了“寄人籬下”的留守兒童。作者并沒有刻意渲染秧寶寶與父母離別時的悲情,而是呈現出九歲小女孩在面對生活變動時既落寞又期待的復雜心情。王安憶沒有回避也沒有夸大留守生活會出現的種種負面問題:缺少了父母的監管,秧寶寶會有不認真寫作業的應付了事,會有頭發亂蓬蓬的松懈狀態,想念親人會流眼淚,爸媽元旦沒回來會失落。與此同時,作者也描摹了秧寶寶豐富的內心情感和孩童獨特的處理問題的方式:寄居的不快心情會被外出的新奇沖淡,不開心時會回沈溇老屋看望外公,與好友蔣芽兒在鎮子里的閑逛填滿了秧寶寶孤寂的生活。作品多角度呈現出秧寶寶獨特的個性,使人物形象具有了典型人物應具備的豐富立體的性格特征。殷健靈的《安安》講述了媽媽去大城市打工后,留守兒童安安的生活經歷。殷健靈在談及這部作品的創作時曾說:“這不是一部應時的小說,也無意從社會學層面上剖析‘留守兒童問題。小說反映的是‘這一個典型。”[2]《安安》中媽媽外出打工,使安安只能留在家中與小狗鐵蛋兒相依相伴。鐵蛋兒的慘死讓外婆走進了安安的生活,安安雖然排斥又老又丑的外婆,但外婆對安安的愛還是漸漸打開了她緊鎖的心門,外婆用愛點亮了原本有些灰暗的留守天空,安安也在留守的日子里體會到生活的多重況味。作品聚焦于安安的生活經歷和成長的心路歷程,塑造出了一個看似柔弱,實則勇敢堅強的留守兒童形象。孟憲明《念書的孩子》在對留守兒童開開和爺爺日常生活故事的敘述中塑造了開開這一獨特的留守兒童形象。九歲的開開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精心照顧著年老體弱的爺爺,作品通過對發生在祖孫間日常生活小事的敘述,凸顯出開開樂觀、開朗、懂事的性格特征。但作者并沒有把開開塑造成一個懂事的“小大人”,在孤寂的日子里,開開將小狗看作能夠傾訴心事的好朋友,在與爺爺說的玩笑中透露出開開身上具有的孩子氣的性格特征,使得人物形象更為真實鮮活。敏奇才《月亮和星星》中的圓圓、亮亮姐弟倆與麻眼奶奶留守在鄉,作品通過對鄉村日常生活瑣事的書寫展現出姐弟倆的懂事、能干,雖然他們在小小年紀要像大人一樣操持家務,思謀著本不該他們掛念的事,但他們并不是苦難生活磨礪下“早熟”的兒童,他們以孩童獨有的幻想超越現實生活的苦難,在他們的夢中依然有會笑的月亮、眨眼的星星,抬頭看見的永遠是像娃娃笑臉般紅紅的日頭。秧寶寶、安安、開開、圓圓、亮亮這些留守兒童形象,最獨特的地方就在于他們的真實與自然,生活的窘境讓她們不得不面對留守的生活,這反而讓童年生命充滿韌性,這些作品刻畫出了堅強勇敢、樂觀向上的留守兒童形象,展現出留守兒童具有的美好品德。
對留守兒童形象的日常化呈現將兒童小說從揭露社會問題,書寫留守兒童苦難生活境遇的表層進入對留守兒童現實生活和心靈世界的深入觀察,有助于突破留守兒童形象的模式化傾向,塑造出具有鮮明個性特征的典型兒童形象。
三、成長書寫中的留守兒童形象塑造
現代化進程中城鄉發展的不均衡導致了農村留守兒童的產生。城市的發展不能以犧牲鄉村的利益為代價,留守兒童不能成為城市化進程中“垮掉的一代”。隨著美麗鄉村建設、脫貧攻堅的實施,中國鄉村煥發出新的活力,這成為鄉村題材兒童小說創作重要的時代語境,影響著兒童小說對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兒童小說更側重于表現留守兒童在逆境中的成長與心靈蛻變,力圖塑造出蘊含新時代精神的留守兒童形象,兒童小說中的留守兒童形象展現出多元化的傾向。
曹文軒的《櫻桃小莊》采用“在路上”的敘事模式推動故事情節不斷向前發展,在鄉土之上蓋一座小樓的夢想,驅使爸爸媽媽離開了櫻桃小莊,留下了哥哥麥田、妹妹麥穗和已經老糊涂了的奶奶。奶奶的意外走失,讓麥田、麥穗、一只羊和一只鵝走在了尋找奶奶的路上,對麥田和麥穗來說,這意味著要經歷更多的未知與挑戰,隨著小說情節的展開,麥田、麥穗這兩個留守兒童形象也愈加飽滿。在尋找奶奶的過程中,麥田和麥穗擁有了更多面對生活困境的力量和勇氣,支撐起兄妹二人的除了內心的信念,還有留守生活教會他們的自尊、堅強與相互關愛,他們走在尋找奶奶的路上,他們的身體和心靈也在經歷生活的磨難中成長。舒輝波的《你凝視過我的眼睛嗎?》與一般描寫留守兒童的小說不同的是,作者將小說的敘述空間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留守兒童林國棟在暑假離開家鄉,第一次來到父母打工的城市,父母忙于生計常常忽略了對林國棟的關注,當林國棟目睹了父母在城市的底層生活后,真正體會到了父母的不易,小說通過感人的細節描寫呈現出林國棟豐富的情感世界與積極進取、淳樸善良的性格特征。儲成劍的《少年將要遠行》將對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放置在“成長”這一兒童文學常見的母題之下。小說中的主人公根喜原本生活在一個富裕的家庭中,爸爸做生意被人坑害讓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爸爸媽媽不得不離家去上海打工,根喜只能獨自留守家中。作品在“生活變故——經歷磨煉——蛻變成長”這一敘事模式下書寫根喜的成長體驗,雖遭受了生活的變故,但根喜依舊積極上進,喜歡讀書,有著對自己未來的清晰規劃。留守的日子讓根喜品嘗到生活的酸甜苦辣,生活的歷練讓根喜擁有了獨立生活的能力,也讓根喜有勇氣面對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根喜考上縣城的高中后,向景寬爺爺坦誠地說出了自己當年犯下的錯誤,自信、堅定地走向更加廣闊的未來。作品在對蘊含成長主題故事的敘述中刻畫出根喜樂觀向上、敢于擔當的個性特征。殷健靈的《云頂》敘寫了兩代留守兒童的成長經歷,云頂小學的“童伴媽媽”春曉曾是個留守兒童,表面看起來快樂明朗的春曉,有著不愿回憶的,由留守帶來的童年傷痛,春曉將這份傷痛化為對更多留守兒童的愛,她義無反顧地跟隨丈夫楊果從城市回到村里接管云頂小學,當起了眾多留守兒童的“媽媽”,她用善良、無私的愛溫暖了留守兒童孤寂的童年,守護著留守兒童的成長。在春曉眼中,乖巧的金枝就像小時候的自己,金枝因為知道自己拖欠著學費,敏感的她總是默默地通過幫大人干活來減輕自己心中的不安。在春曉夫婦的呵護下,金枝逐漸擺脫了敏感、憂郁,成為春曉得力的小助手和受孩子們歡迎的陽光可人的小姐姐。春曉的童年有著不幸的留守經歷,然而這段經歷也讓她學會了更好地去關愛他人,春曉將這份愛傳遞給了金枝,金枝在愛與被愛中蓬勃向上、拔節成長。
兒童小說在成長書寫中實現了對留守兒童形象塑造的多元探索,有助于突破留守兒童形象的同質化問題。兒童小說中涌現出一批留守兒童新形象,這些留守兒童形象“非但沒有卑微相,反而有一種生命的‘尊貴感”[3],兒童小說通過對具有獨特生命意志與精神力量的留守兒童形象塑造,改變了以往兒童小說中留守兒童形象灰暗的色調,使得留守兒童形象譜系更為豐富多元。
四、對留守兒童形象塑造的思考
新世紀以來,現實主義兒童文學創作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兒童小說對留守兒童的書寫,有直面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勇氣,是兒童文學現實主義傳統在新世紀的延續,成為新世紀現實主義兒童小說引人注目的創作亮點,開拓了兒童小說的表現疆域,豐富了兒童小說的人物畫廊。然而,兒童小說在留守兒童形象塑造上依然存有改進的空間。
兒童小說對人物形象的塑造離不開故事的參與,在故事的起承轉合中,人物的內心世界和個性特征才能得以更充分的體現。兒童文學作家應深入并走進留守兒童的生活,傾聽他們的心聲,潛心創作,講好中國故事,塑造出真實可信、個性鮮明的留守兒童形象,使少兒讀者能夠獲得心靈的震動和情感的共鳴。
“兒童文學本質上是張揚浪漫主義精神的文學,是一種‘飛起來引人仰望的文學”[4],直面現實,突出作家社會責任意識的現實主義兒童小說在對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上,更多的是“沉下去”的凝視與沉重,少了“飛起來”的俯瞰與輕靈。兒童小說對留守兒童的書寫不僅要“沉下去”關注留守兒童成長的現實境遇,更要“飛起來”去發現和揭示童年最獨特的生命精神,彰顯兒童生命天性中那種“永不被現實所束縛的自由精神”[5],給予兒童應對困境的勇氣和面對生活的希望,以兒童文學的審美想象帶給兒童溫暖與撫慰。
兒童文學不僅需要關注當下,更要指向未來。兒童小說對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應以促成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為價值旨歸,重塑留守兒童的精神世界,以多元化的創作方式突破留守兒童形象模式化、同質化的傾向,塑造出具有新時代精神的留守兒童形象,以生動豐滿的人物形象引領少年兒童成長。
參考文獻:
[1]何家歡.鄉土童年的精神守望——關于當下兒童文學鄉土敘事的思考[J].鴨綠江,2022(11):133.
[2]殷健靈.安安[M].北京:天天出版社,2015:256.
[3]徐妍.殷健靈《云頂》:于云頂處看見人間悲欣[N].文藝報,2022-06-22(3).
[4]王泉根.中國兒童文學概論[M].長沙: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2015:177.
[5]方衛平.中國式童年的藝術表現及其超越——關于當代兒童文學寫作“新現實”的思考[J].南方文壇,2015(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