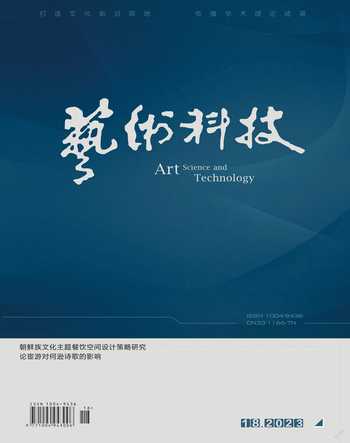“他者”和“自我”的均衡點(diǎn):中外合拍紀(jì)錄片如何構(gòu)建中國(guó)形象
孫紅悅 劉航
摘要:國(guó)家形象是外國(guó)對(duì)本國(guó)的評(píng)價(jià),在中國(guó)日益融入世界的背景下,如何構(gòu)建我國(guó)的國(guó)家形象成為重要的問(wèn)題。對(duì)于國(guó)家形象的塑造,有“自塑”和“他塑”兩種方式。外國(guó)了解中國(guó)形象的渠道,一是西方媒體的“他塑”,二是中國(guó)主流媒體的“自塑”。長(zhǎng)久以來(lái),中國(guó)在國(guó)際傳播中的形象主要依靠“他塑”,這使我國(guó)的國(guó)家形象無(wú)法真正呈現(xiàn),對(duì)中國(guó)形象的塑造產(chǎn)生不利影響。因此,必須加強(qiáng)對(duì)外“自塑”,也要考慮國(guó)外受眾的接受能力。既要牢牢把握塑造國(guó)家形象的主動(dòng)權(quán),又要注重傳播效果。中外合拍紀(jì)錄片作為塑造國(guó)家形象的手段之一,隨著中外交流增多,其在講述中國(guó)故事,塑造中國(guó)形象時(shí),在他者視角和自我表達(dá)上選擇以均衡輸出的方式雙向溝通,在多元互動(dòng)的當(dāng)下,探索中外合拍紀(jì)錄片如何構(gòu)建中國(guó)形象具有極大的意義。文章主要從中外合拍紀(jì)錄片中呈現(xiàn)的民俗風(fēng)情和歷史文化、采用“他者”視角以及現(xiàn)代受眾更易接受的模式使觀眾產(chǎn)生共鳴、視覺(jué)符號(hào)的采用等四個(gè)方面,分析中外合拍紀(jì)錄片如何構(gòu)建中國(guó)形象。并且為日后中外合拍紀(jì)錄片提出建議,即注意多國(guó)發(fā)展,全方位學(xué)習(xí);創(chuàng)新選題,打造多元化的中國(guó);多形式融合,實(shí)現(xiàn)“紀(jì)實(shí)+”。希望中外合拍紀(jì)錄片能更好地實(shí)現(xiàn)對(duì)國(guó)家形象的塑造。
關(guān)鍵詞:他者;自我;中外合拍紀(jì)錄片;中國(guó)形象;形象塑造
中圖分類號(hào):J95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4-9436(2023)18-0-03
黨的二十大報(bào)告指出,加快構(gòu)建中國(guó)話語(yǔ)和中國(guó)敘事體系,講好中國(guó)故事、傳播好中國(guó)聲音,展現(xiàn)可信、可愛(ài)、可敬的中國(guó)形象[1]。中外合拍紀(jì)錄片無(wú)疑成為講好中國(guó)故事的方式之一。改革開(kāi)放后,為了更好地傳播中國(guó)形象,中外合拍紀(jì)錄片應(yīng)運(yùn)而生,在“中國(guó)故事,國(guó)際表達(dá)”理念下,創(chuàng)作出了如《鳥瞰中國(guó)》《美麗中國(guó)》《做客中國(guó)——遇見(jiàn)美好生活》《柴米油鹽之上》等一系列優(yōu)秀作品,打開(kāi)了國(guó)際社會(huì)認(rèn)識(shí)中國(guó)的大門。
在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不斷提升的同時(shí),國(guó)際話語(yǔ)權(quán)卻沒(méi)有得到同步提升,國(guó)家形象的塑造也處于不利階段。利用中外合拍紀(jì)錄片呈現(xiàn)出獨(dú)特的敘事范式,能逐步打破國(guó)外對(duì)中國(guó)的刻板印象。當(dāng)下,中外合拍紀(jì)錄片以什么敘事范式構(gòu)建中國(guó)形象,對(duì)日后中外合拍紀(jì)錄片有何啟示等,都成為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不可回避的難題。
1 中外合拍紀(jì)錄片及“他者”“自我”概述
中外合拍紀(jì)錄片是基于雙方利益針對(duì)某個(gè)拍攝內(nèi)容達(dá)成協(xié)議,共同完成攝制工作,且雙方共享版權(quán),共同承擔(dān)風(fēng)險(xiǎn)。改革開(kāi)放期間,為了增加與國(guó)外的交流,中外合拍紀(jì)錄片一度受到歡迎,且在某種程度上帶動(dòng)了國(guó)內(nèi)相關(guān)紀(jì)錄片的發(fā)展。盡管雙方秉持著公正互利的原則,但是由于在制作和傳播經(jīng)驗(yàn)上的不足,因此合拍過(guò)程中仍是外國(guó)享有最大主動(dòng)權(quán)。隨著中外合作交流的機(jī)會(huì)越來(lái)越多,中外合拍紀(jì)錄片保持著有序的動(dòng)態(tài)發(fā)展,而且在呈現(xiàn)中國(guó)形象上發(fā)生了變化。
“他者”是“自我”存在的前提與參照。法國(guó)存在主義思想家讓·保羅·薩特(Jean Paul Sartre)指出,“他者”是“自我”的先決條件,他人注視我,我才感到自我的存在[2]。中外合拍紀(jì)錄片很難達(dá)到“他者”和“自我”的融合,大部分是“他者”呈現(xiàn),塑造了負(fù)面的中國(guó)形象,這主要是因?yàn)槲鞣絿?guó)家作為外來(lái)者,國(guó)家之間的文化差異使其在塑造中國(guó)形象時(shí),難免出現(xiàn)偏見(jiàn)。除此之外,外國(guó)創(chuàng)作者的主觀性判斷和對(duì)中國(guó)的了解程度也起到重要作用。20世紀(jì)70年代,安東尼奧尼僅在中國(guó)歷時(shí)22天就拍出222小時(shí)的紀(jì)錄片《中國(guó)》就是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當(dāng)下中外合拍紀(jì)錄片呈現(xiàn)了新的敘事范式,不再局限于之前“自塑”的主觀和“他塑”的曲解。由于中國(guó)在國(guó)際上一系列的突出表現(xiàn),因此西方國(guó)家在受邀參與紀(jì)錄片拍攝時(shí),都會(huì)基于鄉(xiāng)土人情、客觀狀況展現(xiàn)真實(shí)的中國(guó)面貌,形成了一個(gè)穩(wěn)定且均衡的“他塑”視角,這為塑造更真實(shí)的中國(guó)形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2 中外合拍紀(jì)錄片如何構(gòu)建中國(guó)形象
2.1 民俗風(fēng)情和文化熏染
紀(jì)錄片具有還原歷史的功能,而中國(guó)作為歷史文化源遠(yuǎn)流長(zhǎng)的大國(guó),將中國(guó)形象傳播到國(guó)際上需要依靠紀(jì)錄片這一媒介來(lái)完成。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能在中國(guó)得到眾人的稱贊和傳頌,這對(duì)外國(guó)人具有極強(qiáng)的吸引力。根據(jù)《中國(guó)國(guó)家形象全球調(diào)查報(bào)告》,在海外民眾對(duì)中國(guó)文化形象的認(rèn)知中,“歷史悠久”和“神秘感”是認(rèn)可度最高的兩個(gè)特征[3]。因此,在中外合拍紀(jì)錄片的前期出現(xiàn)了多種傳統(tǒng)歷史文化題材。
例如,中英合作攝制的《孔子》聚焦到具體的信仰,外國(guó)人雖不了解中國(guó)的社會(huì)理念,但儒家學(xué)說(shuō)中的“仁”“禮”“孝”等理念可謂深入傳播至全球各個(gè)國(guó)家。這就使外國(guó)受眾在觀看時(shí)有了初期的審美期待,對(duì)中國(guó)文化的傳承性有了更深的了解。開(kāi)篇中“回望歷史,或許只有一種方式,那就是一個(gè)人的故事”,紀(jì)錄片通過(guò)個(gè)體命運(yùn)的表達(dá),將這種情感上的聯(lián)系上升到了家國(guó)情懷。且放眼當(dāng)下,這種秩序的建立深深影響到后代幾十億人的生活。紀(jì)錄片以小見(jiàn)大,以個(gè)體命運(yùn)講述時(shí)代的發(fā)展繁榮,關(guān)注文化背后的細(xì)節(jié),在文化的鋪墊中展現(xiàn)大國(guó)情懷。
2.2 適度“他者”視角,化被動(dòng)為主動(dòng)
在過(guò)去合作的案例里,“他者”一直占據(jù)著主動(dòng)權(quán),對(duì)中國(guó)形象進(jìn)行一度的妖魔化塑造,沒(méi)有達(dá)到正向的傳播效果。如20世紀(jì)70年代意大利拍攝的紀(jì)錄片《中國(guó)》,畫面呈現(xiàn)的是當(dāng)時(shí)破舊的村莊,面對(duì)鏡頭不知所措的人,影片的真實(shí)性不容置疑,但因不符合東方傳統(tǒng)的價(jià)值觀而遭到禁播。這實(shí)際上就是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了解甚少的結(jié)果,完全以一個(gè)西方國(guó)家的“他者”視角來(lái)看待,傳播效果大打折扣。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適度的“他者”視角在塑造中國(guó)形象上的確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隨后幾十年,政府和相關(guān)部門開(kāi)始注意到以不同的視角來(lái)講述故事,并開(kāi)始了與國(guó)外紀(jì)錄片的雙向交流和合作。《做客中國(guó)——遇見(jiàn)美好生活》中外國(guó)人以探索的方式游歷中國(guó)各地,他們與中國(guó)各地人民一起勞作、生活,在他們真實(shí)的體驗(yàn)和敘述中,展現(xiàn)發(fā)生在中國(guó)土地上的風(fēng)土人情,從而完成“他塑”視角下“自我形象”的呈現(xiàn)。在國(guó)際視角的解讀中,鏡頭聚焦中國(guó)扶貧工作,這種視角的選取,一方面由于外國(guó)人親自的體驗(yàn),真實(shí)性無(wú)疑,使外國(guó)觀眾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下形勢(shì)有了更真實(shí)的認(rèn)識(shí);另一方面,以國(guó)際視角來(lái)塑造中國(guó)形象,用真實(shí)的鏡頭記錄鄉(xiāng)村地區(qū)的美好生活,詮釋出中國(guó)人民淳樸善良的品質(zhì)和新時(shí)期鄉(xiāng)村地區(qū)的發(fā)展變化。
2.3 真實(shí)記錄過(guò)程,打破“和”的模式
中國(guó)自古以來(lái)講究“以和為貴”,即追求大團(tuán)圓結(jié)局,這與西方的表達(dá)理念有所不同。但現(xiàn)代人的精神需求早已超過(guò)這種“和”的理念,適當(dāng)?shù)拈_(kāi)放式結(jié)局對(duì)“他者”視角而言,有時(shí)會(huì)帶來(lái)更大的思考空間。
在《柴米油鹽之上》中,琳寶這個(gè)人物的呈現(xiàn)引起觀眾的討論,她因自己的樂(lè)觀和努力而收獲幸福,但由于中國(guó)人對(duì)血緣關(guān)系的重視,二婚的丈夫遲遲不肯接受她的兒子,因此最后婚姻再次破碎。這種結(jié)局在中外合拍紀(jì)錄片中很少出現(xiàn),因?yàn)椤昂汀痹趥鹘y(tǒng)的觀影理念內(nèi)根深蒂固,但當(dāng)抹去美化帶來(lái)的濾鏡,直接將現(xiàn)實(shí)搬到熒幕上時(shí),這種打破傳統(tǒng)紀(jì)錄片的結(jié)尾形式在國(guó)內(nèi)更能引起大眾的討論,在國(guó)外更能引起共鳴。并且,外國(guó)更多追求個(gè)人的表現(xiàn),因此鏡頭在對(duì)準(zhǔn)琳寶時(shí),往往更具有吸引力。雖然琳寶的家庭遭遇對(duì)外國(guó)觀眾而言并不是很能理解,但是生活中的破碎感,將她的個(gè)人形象呈現(xiàn)得更為立體化,她肯吃苦,熱愛(ài)生活,這種精神是全世界都能共鳴的。
2.4 用視覺(jué)符號(hào)構(gòu)建大國(guó)實(shí)力
在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愈演愈烈的當(dāng)下,國(guó)家的綜合實(shí)力強(qiáng)弱往往代表有無(wú)發(fā)言權(quán)。為更好地塑造中國(guó)形象,克服文化本源區(qū)別,采用視覺(jué)符號(hào)更有利于雙方的交流。文化認(rèn)同,簡(jiǎn)單來(lái)講是指對(duì)人們之間或個(gè)人同群體之間的共同文化的確認(rèn)[4]。由于本身的文化認(rèn)同和集體差異性,因此外國(guó)人會(huì)用“他者”的目光來(lái)看待中國(guó),而用視覺(jué)符號(hào)來(lái)展現(xiàn)當(dāng)下的中國(guó)文化、中國(guó)故事、中國(guó)發(fā)展往往更直接,成為有效的手段之一。
總結(jié)以往的中外合拍紀(jì)錄片,不難看出,出現(xiàn)最多的視覺(jué)符號(hào)即“路”和“山”,這種橫貫在中國(guó)發(fā)展史上的標(biāo)志,在塑造大國(guó)形象上,往往更具有說(shuō)服力。例如,在《做客中國(guó)——遇見(jiàn)美好生活》中,高鐵沿著鐵軌,飛馳出一條條的路。又如,在《柴米油鹽之上》中,帶領(lǐng)貧困人民走出一座座的山。在這些視覺(jué)符號(hào)的背后,隱藏的是中國(guó)飛速發(fā)展的經(jīng)濟(jì),是中國(guó)綜合實(shí)力的象征,用這種方式來(lái)呈現(xiàn)中國(guó)現(xiàn)狀,意味無(wú)窮。
3 對(duì)后期中外合拍紀(jì)錄片的啟示與建議
3.1 注意多國(guó)發(fā)展,全方位學(xué)習(xí)
中外合拍紀(jì)錄片是傳播中國(guó)文化的重要途徑,也是促進(jìn)中國(guó)向其他國(guó)家學(xué)習(xí)的重要一環(huán),就目前而言,與中國(guó)合作拍攝紀(jì)錄片最多的國(guó)家是日本,其次是英國(guó)和美國(guó)[5]。與此同時(shí),合作攝制的內(nèi)容逐漸從單一發(fā)展為多方向,從起初宣教意味濃重的傳播傳統(tǒng)文化類型到紀(jì)實(shí)美學(xué)的呈現(xiàn),再到當(dāng)下發(fā)展為對(duì)人類共同問(wèn)題的思考。由此可見(jiàn),中外合拍紀(jì)錄片打造了多種類型的紀(jì)錄片,形態(tài)發(fā)展基本成熟。
但大國(guó)理念是否真正傳播,“他者”和“自我”合并塑造的形象是否立體真實(shí),并不在于與其他國(guó)家合作攝制的數(shù)量,而是在和多個(gè)國(guó)家交流溝通中創(chuàng)作更多具有認(rèn)同感的內(nèi)容,從而在國(guó)際上得到認(rèn)可。在華拍攝不僅是單方面?zhèn)鞑ブ袊?guó)文化,更要學(xué)習(xí)其他國(guó)家的傳播策略和發(fā)展理念,如英國(guó)廣播公司(BBC)在本土化和全球化方面的傳播策略。利用全世界共通的話語(yǔ)講述中國(guó)故事,傳播中國(guó)聲音。
3.2 創(chuàng)新選題,打造多元化的中國(guó)
中外合拍紀(jì)錄片始終秉持著“中國(guó)故事,國(guó)際表達(dá)”的理念,而具體到故事,實(shí)則可以理解為紀(jì)錄片選題。為展現(xiàn)更為立體、真實(shí)的中國(guó)形象,紀(jì)錄片的選題尤為重要。雖然當(dāng)下視角由被動(dòng)轉(zhuǎn)為主動(dòng),但是“他者”在觀看紀(jì)錄片時(shí),仍立足本身的文化性來(lái)理解紀(jì)錄片的內(nèi)容,因此在選題呈現(xiàn)上,應(yīng)注意創(chuàng)新且融通。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fā)使全球都陷入了癱瘓之中。圍繞疫情這一選題,中意兩國(guó)合作拍攝《我們?cè)谝黄稹幸鈹y手 同心抗“疫”》,記錄了疫情下中國(guó)與意大利同心抗疫,為“健康絲綢之路”共同奮斗的過(guò)程。該選題接近現(xiàn)實(shí),對(duì)外國(guó)觀眾具有吸引力,也塑造了負(fù)責(zé)、可靠的中國(guó)形象。
反觀其他類型的紀(jì)錄片,如科技、經(jīng)濟(jì)等,在選題呈現(xiàn)上難免打上了“自塑”的標(biāo)簽。中國(guó)的發(fā)展真的如此迅速?中國(guó)人民是否真的富裕?這些外國(guó)觀眾觀看紀(jì)錄片后產(chǎn)生的疑惑,其實(shí)就是對(duì)選題內(nèi)容是否真實(shí)的懷疑。但柯文思鏡頭下的《柴米油鹽之上》就很好地解決了這個(gè)問(wèn)題,在第一集中,幫助農(nóng)民走出大山,邁向城鎮(zhèn)時(shí),雖打著“扶貧”的旗號(hào),但實(shí)質(zhì)上講的是城市和鄉(xiāng)村不斷變化的關(guān)系,這是每個(gè)國(guó)家發(fā)展路上必遇的難題[6]。
3.3 多形式融合,實(shí)現(xiàn)“紀(jì)實(shí)+”
根據(jù)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模式,可以把紀(jì)錄片分為真實(shí)電影和直接電影這兩種,在歷史上,這兩類紀(jì)錄片都有許多經(jīng)典作品。紀(jì)錄片作為大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受眾是廣大的人民群眾,中外合拍紀(jì)錄片更是要將受眾定位為全世界人民。此外,灌輸和說(shuō)教是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的通病,這種創(chuàng)作模式很難讓觀眾接受,依靠這種形式塑造國(guó)家形象是走不通的。因此,在保證紀(jì)錄片本身真實(shí)的基礎(chǔ)上,在形式上稍作創(chuàng)新是必然的。
《世界遺產(chǎn)漫步》就是很好的例子,其用情感對(duì)話代替抒情解說(shuō),主觀視角再現(xiàn)真實(shí)生活,在共情中讓觀眾領(lǐng)悟“小情”和“大美”,全片拋棄以往的解構(gòu)模式,以Vlog的形式促使人們參與到紀(jì)錄片的制作中,從個(gè)人的角度出發(fā),從群體到社會(huì)。這種傳達(dá)方式不僅促使紀(jì)錄片以創(chuàng)新的姿態(tài)發(fā)展,還使國(guó)際社會(huì)對(duì)中國(guó)文化遺產(chǎn)有了由淺到深的認(rèn)識(shí),是一部中外合拍紀(jì)錄片的優(yōu)秀之作。
未來(lái)的中外合拍紀(jì)錄片,更可以和當(dāng)下飛速發(fā)展的互聯(lián)網(wǎng)相結(jié)合,正深受追捧的短視頻已經(jīng)進(jìn)入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領(lǐng)域,如何把這種制作理念應(yīng)用到中外合拍紀(jì)錄片上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4 結(jié)語(yǔ)
紀(jì)錄片作為“國(guó)家相冊(cè)”,是對(duì)外宣傳的重要手段。中外合拍紀(jì)錄片承擔(dān)著傳播中國(guó)文化、塑造中國(guó)形象的使命,在和世界分享中國(guó)故事的同時(shí),紀(jì)錄片以樸實(shí)的話語(yǔ)展現(xiàn)平民百姓生活,用鏡頭內(nèi)容消除對(duì)中國(guó)的偏見(jiàn),以客觀的視角呈現(xiàn)大國(guó)形象。但也需注意,雖然提倡適度的“他者”角度和適中的“自我”塑造,但是在必要的事件上,中國(guó)仍需把握一定的主動(dòng)權(quán),在提升內(nèi)容深度和觀眾審美度上,呈現(xiàn)更多完美的作品。
參考文獻(xiàn):
[1] 王永潔.新時(shí)代講好中國(guó)故事的多邊主義路徑研究:基于智庫(kù)與國(guó)際組織合作開(kāi)展知識(shí)分享的分析[J].北京工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3(6):1-11.
[2] 讓·保羅·薩特.存在與虛無(wú)[M].陳宣良,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289.
[3] 杜平.英國(guó)文學(xué)的異國(guó)情調(diào)和東方形象研究[D].成都:四川大學(xué),2005.
[4] 崔新建.文化認(rèn)同及其根源[J].北京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4(4):102-104,107.
[5] 何春耕,黃誕琦.合拍之旅與探索之變: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中外合拍紀(jì)錄片歷史文化紀(jì)錄片發(fā)展特征探析[J].大眾文藝,2022(10):73-75.
[6] 朱超亞.共同價(jià)值與文明互鑒:2020年以來(lái)中外合拍紀(jì)錄片中國(guó)題材紀(jì)錄片選題研究[J].電影文學(xué),2022(23):78-81.
作者簡(jiǎn)介:孫紅悅(2000—),女,山東泰安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廣播電視學(xué)。
劉航(1999—),男,河南商丘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廣播電視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