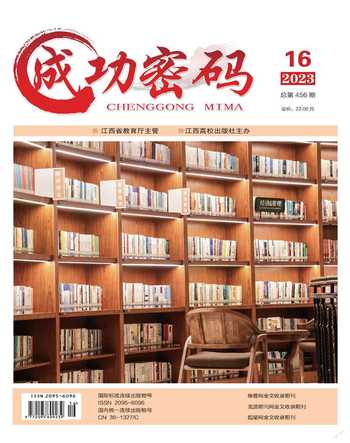張伯端美學思想及其美育價值探研
蘇振宏
張伯端的美學思想是建立在哲學理論與實踐基礎上的對藝術創作的深刻認識和審美精神的總體把握,體現了古代中國人獨特的審美意識與美學觀念。在審美心理層面,張伯端講求靜極生動、自由無待的審美態度與藝術靈感;在藝術創作方面,他主張氤氳朦朧的審美趣味,追求恣意昂揚的藝術生命力。梳理研究張伯端的美學思想,有益于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美育資源,在新時代做好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美育工作。
一、清凈無為:審美態度和藝術靈感之意涵
北宋張伯端宣揚哲學心性理論,提出使心虛靜、返情歸性的理論觀點。映射到美學思維上,張伯端認為清凈純粹的心靈境界與至美至妙的藝術極境是相通相融的,其言“清凈無為,自然現出百般妙用景象”。這一美學觀反映了他對審美心理構建的雙重深刻認識:一是“清凈”,指明“靜極則生動”的心理狀態對內游神思、玄游暢想的重要意義;二是“無為”,強調審美主體自由的顯身敞開以及審美對象以其所是的完整呈現誕育了“心物交融”的藝術靈感和審美境界。
“心”概念是中國傳統哲學心性理論的核心,主張人的一切生命力在“心”的作用下以其可觀察性和可體驗性構成感性經驗,故以心為思維之官。張伯端認為,“心唯靜則不外馳,心唯靜則和,心唯靜則清。”從審美活動的展開來看,“靜極”是詩性直觀的前提,是在審美活動中人交付自身“去成為什么”的“去”得以開啟的心理準備,給內游神思以廣闊的場地;“生動”是審美心理中玄游暢想的依據,是人把自身擺出后彰明“去成為什么”的“成為”得以實現的心靈力量,是推動審美直觀活動的動力。在“靜極則生動”的過程中,純粹清凈的心理狀態使人超出俗見,以一塵不染之心境虛照萬物,為審美活動中的個體構建起滌除玄覽、靜觀深照的精神高度,以擺脫一切經驗和理性的遮蔽,從高視下,全而不偏,破除了所謂的規律性、合理性的審美障礙,最終落實到人的審美活動和藝術活動的穿透力上,獲得一種非生理的、非功利的審美快感,這種審美經驗往往帶有鮮明的直觀性和強烈的豁然貫通之感。讓個體在欣賞美、創造美的同時,領悟生命的自足感與完滿感。
如果說“清凈”是張伯端在內游神思層面對澄心遣欲的抑揚,那么“無為”則體現了他對藝術靈感自由意識的推崇。張伯端強調“無為”的審美取向,提出“但識無為為要妙”,闡述身心獲得絕對自由的“無為”境界的重要性。“無為”在張伯端的美學思想中代表了一種超脫的感知狀態。在這一狀態下,心靈運動被賦予了純粹的自由本性,可以恣情發動、隨意揮毫、自由超邁、率然而生,不依從人的意愿,不尋求特定的物象,不必從邏輯上應然地推出,可以是偶然的、突然的、無法預料的開展。這種自由風貌為藝術靈感的瞬間生成和美感經驗的詩性直觀提供了無限可能。它可以是一種情不自禁、不由自主的凝神觀照,也可以是一種并非刻意封閉或拒絕干擾的心無旁騖,表現為人的一種徹底的、完全的、澄明的敞開。張伯端把這種身心敞開形容為“妙用無窮日慧”。“慧”蘊含著靈感激發、頓然妙悟的意味,表現人(主體)與物(客體)的瞬間契合。這種契合沒有沖突和對立,多為一種愉悅幸福的提升。那突然而至的靈感不是使人失去自我,而是使人獲得了超脫的體驗,即在審美層面,當人以“無為”之心展現其生命活力之時,也正是人在向世界交付、擺出和敞開自己之時。在那一刻,所有意志、理性或利益都被排除在人的意識之外,相應地,周圍的事物也就不會被人自身的主體性或主觀性所扭曲,而能完美呈現。在這種雙向運動中,人既顯現或呈現了自身,也在自身呈現中讓事物的本真得以呈現,體驗到了平時無法體驗的情感,觸及了平時無法觸及的境界,即藝術靈感的生成涌現最終使感受者無間隔地進入審美對象并瞬間洞見其完整本質,兩者之間達成一種親密無間的契合,形成一種內在生命的共鳴,處于一種統一的、渾然未分的整體狀態——這種在心靈中誕育的“心物交融”的藝術靈感和審美境界,源自無為的心靈品格,飽蘊超脫自由的生命氣象。
二、氤氳朦朧:藝術創作和情思構設之表征
從表現主體的審美情感志趣和形象美的人格化內涵方面而言,審美并非只是單純地接受外在對象或感受外在對象,而是表現自己與呈現對象同步發生的顯現、賦形和言說活動。從張伯端的文藝作品來看,他在抒情和表現時更熱衷于構設一些體悟式的、藝術化的、極具朦朧隱蘊意味的符號、形象和意境。這些藝術形象,以特定的極具生命力、表現力的符號作為指征,達成一種確定的、具有意義的形式凝聚。例如,他在詩文中塑造了“黃芽”“白雪”“玉芝”“日紅”“月白”等諸多文學意象,就審美欣賞和創造的經驗依據而言,這些藝術形象展現了張伯端對人的生命力的靈動、自由和絕對自主性的體驗與放大——這些氤氳朦朧之“象”已經不再是事物意義上的對外在世界的構形。它的美學價值并不停留在呈現自然造物的水波光影、云氣升騰或彌漫藹然,而是旨在說明個體卷入了一場審美活動,與外在的山川大地、日月云霞、輕煙薄霧、火燭雪影等感官所把握的對象發生了審美關系,使自身的生機和生命力經由自然對象或欣賞對象獲得外射和替代實現。它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渴望逍遙的情感宣泄的力感,一種不屈服于壓抑的生命力的昂揚,一種使人的絕對無待的逍遙人格顯現出來的汪洋恣意的活力。
同時,張伯端還認為,氤氳朦朧所代表的“美”無法定義也沒有疆界,它的涌流和漫溢不受任何主觀想象的遮蔽,更不應該被客觀形式所概括——它憑借超越必然性和自然的規律成就了無形式的、無限的自在性與完整性。基于這樣的審美觀,張伯端在作品中描繪了很多飄蕩聚合、氤氳繚繞、自由自在的意象群,諸如“醺醺和氣釀春風,一點陽生恍惚中”所描寫的雨露升騰后,融入大地和藹的春風,又化作輕柔細密的光芒,在不經意的瞬息之間灑向晴空萬里,山泉林池,山川大地。這些氤氳意象群體現了張伯端對氣韻的理解、意趣的營造及風致的追求,“聚散變化”作為一種概括表象獲得了審美式、藝術化的詮釋創造,其所展示的審美佳境,既不源于人的理性思維的焦點式透視,也不源于個體力量對自然存在的意志化征服,而表現為人的自由完整的本性得以完滿揭示所產生的歡暢感。
三、價值意義:人格美育和生命美育之構建
在多元文化思潮的沖擊下,新時代美育工作更加需要關注傳統審美觀的傳承教育。張伯端的美學思想內蘊清凈純粹的審美心理,高潔無為的品格意識,自由無拘的精神風尚和敞開暢意的人生態度。這些審美意識和美學觀念不僅彰顯了中國傳統美學的思想深度與理論厚度,還為當代美育教育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和寶貴的精神底蘊,對于開展新時代美育教育具有重要價值。
一是豐富了“人格美育”基本內涵。人格概括為人的內在道德和情感品質。人格美育旨在培養個體良好的品性道德,形成真情美、氣質美、境界美。張伯端美學思想為人格美育的基本內涵提供了有益的思辨路徑,如在增強情感力方面,重視情感的自由表達,推崇內心的坦然和真摯的抒發;在提升審美直覺力方面,強調精神高潔,不受物質干擾和利益驅向;在發展想象力方面,主張對言外之意、象外之蘊的頓悟,加深自我認同等。這些觀念都有益于陶冶情操,以美育德,涵養個體內在的思想道德、倫理觀念和審美境界,形成正確的審美價值觀。二是拓展了“生命美育”的話語體系。生命美育是以生命活動為審美對象的審美教育,強調美的本質應該從人的本質出發,而人的本質就是生命。張伯端美學思想圍繞生命體驗展開闡述,突出主體性和體驗性,重視開發人的藝術感覺,提升人的審美趣味,實現人的自我審美需要,獲得生命的現實意義。這些美學觀念同人的生命教育密切關聯,拓展了生命美育的話語體系,在當代社會依然具有重要的美育價值和現實意義,能夠促使人尊重生命、熱愛生命、珍惜生命、美化生命,最終達到人與自身、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