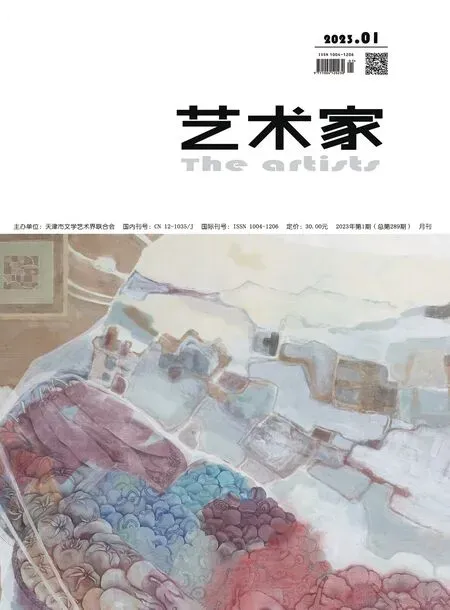沉浸體驗
——從數字景觀到跨越真實
□楊雅迪
數字媒體時代科技與藝術的深度交融,催生了“沉浸式體驗”這一新興的展示形式,豐富了參觀者的情感體驗。從感知形成的過程看,“沉浸感”的形成需要感官、情景和涉身性等多種條件。文章從“數字景觀”到“跨越真實”的視角,論述了“沉浸感”形成的基本原理與機制,并就“沉浸體驗”的新特征與發展趨勢等相關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
隨著數字技術的全域化傳播,社會儼然已被全方位的數字景觀充斥,在吸引大眾沉迷的同時也造成了內心的空虛與無助,正是這種深度的“情感缺失”不斷喚醒人們對具身性體驗復歸的渴望。沉浸式展覽給予觀者第一視角的“超真實”體驗,并在此基礎上與內容及他人進行交互,由此獲得更深層次、更具溫度的情感共鳴與更加愉悅的社交體驗。沉浸式新媒體展覽強調身體在信息傳遞過程中的核心地位,圍繞觀者的感官體驗和行為互動,建立有效的情感引導與認知反饋,構建當代新媒體交互藝術的新生態。
一、數字景觀:影像對真實世界的遮蔽
法國思想者居伊·德波是國際“情境主義”的領袖,其經典著作《景觀社會》對我們認識當代數字媒介實踐具有重要價值。德波認為,在生產技術飛速發展,物質資料不斷堆疊的資本主義后工業社會,影像化、表演化、圖景化的媒介符號已經充斥在社會空間的各個角落,滲透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當代社會儼然轉變為以影像物品生產和物品影像消費為主的“景觀社會”。
(一)影像與生活的分離
景觀已從逐漸喪失實體性的世界中超拔出來,影像世界遮蔽了真實世界的客觀存在。在數媒時代,物理實體的商品演化為由各類數字媒體所打造出來的龐大“影像群”,這些承載著審美性、刺激性、表演性、愉悅性的商品影像以“超真實”的技術手段呈現于受眾眼前,使人們沉浸于此種景象。尤其在虛擬現實技術、數字孿生技術和人工智能的助推下,人的意識沉浸于由真實、技術、物質的材料混合搭建的虛幻場景中,致使影像浮現在真實世界之上,覆蓋并取代了真實的世界。在影像中,我們生活的真實世界逐漸失去了話語權和意義,核心地位被擬像包裝的產物代替,影像世界轉變為“觀看”的主要窗口。
(二)主體與客體的異化
影像景觀將主體與客體的認知關系倒置,控制著大眾的選擇權及被選擇權。景觀是人實踐活動創造出來的內容的表象,但其卻以主體的姿態強化了“人與景”的“分離”關系并反過來支配了人的“看”。德波指出,“景觀不是影像的聚集,而是以影像為中介的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影像景觀成了文化和社會的核心要素和關注焦點。新媒介技術下的社會呈現了一個虛幻的“擬像”世界,人們對于影像的迷戀超出了對于生活本真的探索,從而給予影像以“看”的主動權,并弱化以及壓制著主體“看”時的思考、判斷和話語權,使“看”成了無主體性的被動選擇。
(三)人與人、人與自我的疏離
媒介符號對社會生產、生活的影響日益加深。消費文化、娛樂文化、視覺文化以及新媒體文化已發展為日常生活的軸心,社會空間顯現出影像化的特征,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的關系只有通過媒介、符號、影像、景觀等中介才能實現或表達。景觀使得商品“虛化”成影像,分離了人與真實世界,取代了人對本真世界的體驗與感受。人們僅僅與景觀產生單向度的聯系,被孤獨感和個體化所環繞。景觀以其絢麗化的審美形態、影像化的表達方式,催生人們的虛假消費欲望,即“人們最初的原始需要被接連不斷的偽需要所取代”,而人的真實需求往往在景觀影響的虛假欲望之間不斷抗爭甚至分裂,導致了本我的迷失與淪喪。
二、跨越真實:從情感共振到沉浸體驗
(一)感官共振:從單一感官到交互感知
感官體驗即知覺體驗,在新媒體等技術所營造的虛擬空間的場域環境中,其主要指將視覺、聽覺、觸覺、味覺與嗅覺等知覺器官應用在情感體驗上,從而產生感官共鳴,模糊虛擬與現實,造成心理上的沉浸感。當代藝術創作推崇不同學科與領域之間的融合,音樂、舞蹈、詩歌、視覺藝術、表演等不同藝術形式的結合造就了總體性藝術的時代,此種聯結全部人類感官的藝術突破了原有的創作邊界,更大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完整性。從技術和感知的角度看,沉浸體驗通過VR、AR、MR、AI 等將觀者的行為動作、本體概念投射到數字空間之中。在感知方面,體驗者的本體、行為以及行為效果與空間場所融合在一起,其與空間交互所產生的具身性體驗實現了觀者對展示對象的多維感知。沉浸體驗創造的不僅是單純的圖像與影像空間,還包含主體身心體驗的時空場域,突出了人的主體性,將真實感做到了最大化。
(二)情景重構:從再現真實到再造真實
區別于傳統媒介形式以記錄和復原來再現真實,突出沉浸感的虛擬現實技術是基于現實中的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體驗方式進行模擬,強化再造現實。這種重構推翻了以往的感官認知,營造出跨越時空關系的場景氛圍,將一個虛擬和現實相互滲透的“新現實”展現在觀者面前。波德里亞在《擬仿物與擬像》中提出“符號取代了現實,現實則淪為一個虛擬的環境”,把由擬像構建的新現實稱為“超現實”,而新媒體技術正是利用聯覺方式打造“超現實”時空。沉浸式展示的突出特征在于“空間”再造,在二維或三維物質實體空間的基礎上,將現實存在與數字虛擬相融合,生成了物質與非物質的多維混合體,從而構建起后現代社會藝術創造與現實存在之間的橋梁。
(三)身在其中:從距離認知到沉浸體驗
“沉浸”一詞原指物體進入到液體時被全方位包裹的一種狀態。米哈利·契克森米哈的“心流”理論對其做出了確切解釋:個體將情感、意識與行為完全地投入到某種活動之中,無視外界一切事物的存在,在此沉浸過程中產生歡愉與滿足,當達到最佳體驗狀態,即為心流。而沉浸式展覽則指為了使受眾獲得深度的臨場感與沉浸感,在新媒體技術、計算機以及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支撐下,運用多種媒介和藝術表現方式構建的虛實相融的空間情境,是一種依靠物理設備與數字化內容結合并富有先鋒性與表演性的當代藝術展示形式。
“交流在場”可以理解為通過具身體驗與傳播關系網絡耦合,以實現信息直面交互的沉浸式傳播。梅洛·龐蒂提出具身認知理論,突出人們的不同體驗、感覺、注意、記憶、情緒都是通過身體來實現的。在大眾傳播時代,由于時空上的技術限制,往往大部分傳播都是依靠媒介符號將信息與其他主體聯結,身體很難直接進入傳播關系網絡實現在場交流。而沉浸式傳播的出現使媒介空間更具張力與包容性,通過雜糅復合媒介空間、技術與多元身體形態 (智能身體、人體、意識),感官可以借助想象實現沉浸感,進而打破傳統媒介設定的時空界限,實現交流的在場感。TeamLab 新媒體藝術團隊利用新媒體數字技術,將光影、聲音、影像等元素組合創造出一個具有深度交互性的數字化自然,重置了藝術作品與受眾的關系,讓體驗者在深度的互動與交流中增強體驗的真實感,從而達到沉浸式的夢幻體驗。
三、沉浸體驗的新特征與發展趨勢
(一)媒介擴張:沉浸體驗的實現形式
依照德波景觀社會理論中提及的新聞、宣傳、廣告、娛樂、表演等社會景觀比對,展覽展示幾乎觸及了各個方面,因此,它自身即為制造與傳播景觀的存在。沉浸式展覽同時具有呈現和交流的功能,從此意義上講,它既是傳播信息的載體,也是信息本身;究其本質,沉浸式新媒體展覽是一種跨媒介的信息傳播融合體,它打破了原本時空交流的壁壘,改寫了傳統的敘事方式,營造出符合時代潮流、受眾青睞的主題性藝術展覽。因此,從根本上講,沉浸式展覽是一個龐大的信息制造的傳播機,形式上常常是一個播放影像的巨型平臺及熒幕。
(二)隱形控制:沉浸體驗的新特征
在網絡科技、人工智能與藝術的深度融合下,虛擬現實等技術以絢麗科幻的影像刺激著人的感官,使人只能接受眼前呈現的,失去了人作為主體的個性、自由、創造力與主動性。表面上看,受眾享有絕對的自主權,但是深藏在不干預主義外殼下的是一種隱性的控制和強烈的干預。人們的消費習慣、消費方式以及消費能力已經全部被洞悉,甚至某些展示主題與表演正是在這一洞悉的基礎上精心設計的。
(三)技術進步:顛覆體驗形式
數字技術革命從本質上重新定義了時代,此革命不僅涉及所有文化形態,將科技與藝術深度融合,同時影響到包含藝術生產與藝術展示在內的全部非物質生產領域。這就需要有更具有感染力的“體驗”方式來滿足人們的消費需求,而“沉浸”體驗通過放大媒介的特性,使得信息傳達與交流更高效并富有趣味,極大提升了受眾對作品的理解和情感體驗度。科技的快速迭代正在改變著人的情感體驗方式。信息社會下的人們已經習慣于沉浸在由媒介符號所構成的虛擬環境中。科技感、互動感、沉浸感向受眾呈現出了無比美好的世界,但在一定程度上卻忽略了展示內容的本質——傳達,以及對于受眾情感真實需求的滿足。
四、回歸本真:情感體驗的再認知
居伊·德波的景觀社會理論為我們認知理解消費主義下的媒介環境帶來了深遠啟示,也為我們反思沉浸式藝術展覽的現狀與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
(一)技術導向的負面性
技術革新已經極大地增強了“情感體驗”的真實度。數字媒體時代的技術更迭在不斷吸引大眾視線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技術流與娛樂化傾向。受眾沉浸于體驗的場域中,單純被新奇刺激又絢爛奪目的景象迷惑,被剝奪了抵抗和批判的權利,無法真正地思考展示主題的深層內涵,盲目地追求所謂的體驗感與炫耀欲下拍照打卡帶來的成就感與滿足感,場景主題信息的核心往往被忽視。例如,2015 年英國藝術家創造的“雨屋”令人們蜂擁而至,創作者在作品的天花板上安置了體感器,將觀者的行為路徑進行實時反饋,以實現觀者在雨中穿梭而不被淋濕的體驗。設計者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引發觀者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然而絕大部分觀眾只沉浸于新奇的互動之中,極少去反思作品創作者想要表達的價值觀念。
(二)沉浸體驗的本質思考
新媒體技術的融合使得展示形式衍生出了無限多的可能性,沉浸式展覽憑借其特有的優勢拉近了大眾與藝術之間的距離,為人們帶來了更真切的情感體驗。“藝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盡管藝術的內容和創作手段、形態都來自生活,也受制于技術的表現,但藝術的前瞻性和想象力使得它具備對現實世界進行反思、批判與預測的屬性特征。沉浸式展覽應當在將創作聚焦價值觀念本身的基礎上,嘗試將藝術性、審美性、教育性和價值觀念作為受眾體驗的終極目標,使觀者最大限度地產生對設計者展示主題的共鳴,從而激發觀者長久、連續性的思考,而不只是過度依賴科技設備,將符號影像的新奇感、刺激感作為展示作品的主體,通過正常的主從關系,在無形中影響受眾的行為。
在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盛行的時代,大眾媒介在整體上呈現出了泛娛樂化的趨向,整個社會沉浸在娛樂的幻境中。即便如此,冰冷的機械與自動化程序依然帶給人們一種潛在的孤獨感,人們對真實情感體驗的追求越發強烈,在這種情況下,沉浸式體驗必然會成為主流的傳播方式,建立人與媒介和諧的對話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