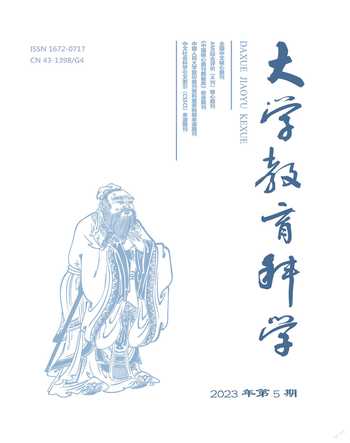論中國電影的自然審美觀



【作者簡介】? 呂培銘,男,山西太原人,北京電影學院中國電影文化研究院博士生,主要從事中國藝術傳統與中國電影敘事美學研究。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2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中國藝術文化傳統在當代中國電影中的價值傳承與創新發展研究”(項目編號:20ZD18)階段性成果。
一、傳統自然審美觀與中國電影的民族性建構
隨著文化強國戰略的不斷深化,如何以中國傳統文藝美學的優質資源來熔鑄中國電影的民族風格,建構帶有中國原創性的電影理論,成為緊迫的時代命題。在中國傳統哲學與審美意識的發展中,“自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中國人的審美經驗在起源和發展上都與中國人的自然觀念有極為密切的關系”[1]。無論是作為美學源流的儒釋道思想、抑或是“意境”“意象”“心游”等審美范疇的生成均在不同程度地指向了自然何以為美的問題,其作為中國美學史“元范疇”[2]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同時,這些自然審美觀念中還承載著中國獨特的文化意識,在天人合一的哲學范式中,“自然”從未外化于人而存在,它從一開始便與作為宇宙生命本體的“道”相連結(老莊),這使其在審美之外又具有形而上的本體化色彩。其次,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自然從不單是人們所利用、征服、改造的對象,它不僅能夠使人獲得精神上的親近,道德上的滿足,還能經由非功利的審美感受而進入美的世界,這是中西方審美觀念的顯著區別。誠如宗白華先生所言:“大自然中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活力,推動無生界以入有機界,從有機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緒、感受,這個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3]
基于這樣的審美事實,當人們試圖以傳統文藝資源切入中國電影的民族化研究時,理應將“自然”作為一個觀察和分析的對象。誕生于西方現代語境下的電影藝術,以逼真的光學透視見長,這就使其在表現自然景觀時擁有得天獨厚的媒介優勢,它不僅能夠全景式再現民族性的地域特色,還能夠通過各種影像技術手段,對自然實現有意味的審美改造。隨著中國電影學派理論建設的持續推進,關乎電影民族化相關話題的研究成果已頗為豐富,但自然的傳統審美經驗及其話語建設卻并未得到充分重視。[4]正因如此,以影像修辭手段來鏈接中國傳統美學觀念,在電影中建構具有民族色彩的自然審美觀,不吝為完善中國電影民族理論的有力視角。
二、中國電影自然審美的思想取向
儒釋道作為中國傳統美學的三大源流,深刻影響著中國傳統自然審美觀念的生成。雖然三家的哲學觀念千差萬別,但在對自然美的關注問題上,卻存在著相當的一致性。當人們將儒釋道所持的自然觀與中國電影的影像修辭手段相結合后不難發現,它們所持的審美觀照方法,恰好對應著中國電影三種截然不同的自然審美取向。
(一)儒家的“德性自然”:比物興德,托物言志
儒家在進行自然審美活動時,傾向于把個人的道德理想向外物加以投射,形成源遠流長的“比德”審美傳統。所謂“比德”是指“將自然物的某些特征比附于人們的某種道德情操”[5],使自然具有人的感情色彩。在文學藝術中,比德傳統最早可追隨到《詩經》中,作品中以自然比物興德的表現手法已初具規模;屈原《離騷》繼承了這一傳統,“香草”“鷙鳥”等自然物象濃墨重彩的刻畫,實則也是表現了作者道德情感的對象化。理論層面,管仲較早關注到了這一問題,它在《管子·小問》中直接提出了“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的理論命題,形成了自然與道德關系的長久討論。對“比德”審美觀影響最大的人物首推孔子,《論語·雍也》中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雖然這句話并未專指“比德”問題,但“智者”“仁者”的分類中卻隱藏著個人精神品質對自然審美的決定性影響,這實際上是首次在美學上提出了人與自然在形式結構上“可以互相感應交流的關系。”[6]總的來說,雖然“比德”觀念帶有一定的原始色彩,但它卻將古代中國人的審美意識推進了一步,由此自然不再是神秘主義的巫術對象,它在與人的道德情感“同形同構”的過程中,開始成為“美”的象征。
在中國電影中,將自然景物與道德情感相“連綴”的比德手法隨處可見。中國電影常通過自然物象的有機選擇、配合以電影化的表現方式來塑造理想人格的“德性主體”。如創作于1931年的《一剪梅》中存在大量以“梅花”為主題的圖案,它既作為一種視覺裝飾元素,同時也是人物性格和道德的象征;在《桃花泣血記》中,導演以“桃花”來類比琳姑堅毅淳樸的道德品格,當母親在家中栽種桃花樹時對幼小的琳姑說:“你將來做人做得好,它開的花必定鮮艷,若是不學好那末…”。長大成人后,當琳姑走投無路不得不用身體換取金錢時,路過桃花林時這句話又在耳邊響起,實現了內心的救贖。
“十七年”時期,中國電影塑造了大量革命理想者的形象,自然景物的“比德”也成為烘托人物性格、謳歌人物精神成長的有力手段。在《青春之歌》中,影片開場便是一個長達2分多鐘的“蓮花”鏡頭,這個段落雖然與其后的故事空間無甚關聯,但隨著劇情推進不難發現,“蓮花”正代表著林道靜堅毅不拔、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品質;類似的例子在凌子風的《中華兒女》中也有所體現,在胡秀之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員的段落中,當胡秀之宣讀完入黨誓詞后,導演緊接著給了四個連續的空鏡頭,它們分別是盛開的鮮花、壯麗的山河、巍峨的山峰、以及奔騰的流水。這些鏡頭不僅再現了祖國的大好山河,同時也是情緒的激蕩和意義的生產[7],它們一方面烘托渲染了神圣的政治氛圍,同時也昭示著人物內心所經歷的洗禮,頗具“托物言志”之感。
值得言說的是,雖然這種創作手法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但畢竟不太符合電影藝術的表現規律。學者李玉華較早地注意到它在電影中的“濫觴”,作者在《詩與電影》一文中談到:常見的情況是電影中主角的“犧牲”總會接一個“冬天古樹”或“瀑布飛濺”的空鏡頭來表達崇高或哀悼、隆重的儀式總會加入一個“滿簇鮮花”的特寫來體現主角對美好的向往,這種類似于文學作品的表達方式“顯得我們的創作思路十分匱乏”。[8]據此,先進的電影工作者們開始注重以電影化的表現手段來建構情景關系,由此衍生出有關電影意象、意境等問題的研討。徐昌霖、林年同、劉成漢等學者均在這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極大地推進了中國電影民族化的理論深度。
(二)老莊的“道法自然”:和諧共生,情景交融
老子是中國哲學史中第一個明確提出“自然”范疇的先哲,他以“自然”作為“道”之依存的邏輯前提,并借由“歸根復命”“復歸于嬰兒”等返璞歸真的思想,為中國“美在自然”審美傳統做出了重大貢獻。《道德經》第二十五章中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里所說的“道法自然”,并不是說在“道”之外還有一個“自然”可供模仿,其真意在于“道以自然為歸,道的本性就是自然。”[9]這一說法在學者蒙培元的看法中也得到了呼應:“在老子看來,道是以‘自然的方式存在的。反過來說,‘自然不是別的,就是道的存在方式或存在狀態。”[10]此后,莊子以一種“無我”的審美關注來面向自然,在天地宇宙的真實存在中親證自由的喜悅,這種“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齊物策略,為中國自然審美觀念的飛躍開啟了新的大門。
總的來說,順應、尊重宇宙自然法則而善待萬物,使萬物各遂其生、各得其所,是老莊自然審美觀的根本立場。具體在電影中,這種觀念首先化為一種天人合一的“生態意識”,這成為諸多電影敘事的母題之一。一般認為,上映于2004年的《可可西里》標志著中國生態電影的正式確立。[11]表面上看,這部作品講述的是民間護衛隊與盜獵分子間的激烈博弈,這構成了影片的主要敘事動力。從更深層來說,它所展現的是正是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導演陸川以紀實化的表現手法真實再現了人類殘酷的殺戮場景,他讓觀眾重審人類中心主義的狂妄傲慢,重建人類對自然的敬畏與尊重,實現中國傳統生態意識中“道”的回歸。類似的觀念在賈樟柯《三峽好人》中也有所體現,在國家快節奏的工業建設之下,人們將個人意志凌駕于自然法則之上,使原本世代生活的土地變成了空洞的廢墟,由此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也逐漸分崩離析。導演正是通過魔幻現實的影像手法,對中國傳統自然觀念的失落表達了自己的嘆惋。
從影像風格上來說,老莊的自然審美觀在電影中還呈現為一種情景相融的美學風格,注重人與自然環境間的悠然和諧,這顯然與西方主客二分的、危機性的自然景觀相區別。如果說愛森斯坦的電影理論立足于矛盾對立統一的辯證法哲學[12],那么中國電影在對蒙太奇技巧進行選擇與取用時,則“更接近于普多夫金的連接組合而不是愛森斯坦的沖突與撞擊”[13],這種注重人物與環境雙向滲透的影像修辭方式,很難說沒有受到老莊自然哲學觀的影響。從這一層面來說,老莊道家恰好成為孔門儒家的對立補充者,[14]它為中國電影提供了情景交融的美學智慧。自此中國電影在處理情景關系時逐漸擺脫了二者間的機械比附,并開始嘗試將“意境”等觀念納入影像深層的自然旨趣當中,使自然與情感的關系變得愈發平等、融洽,如在《林家鋪子》《巴山夜雨》《歸心似箭》《城南舊事》《邊城》《那山那人那狗》等作品中,人們能夠鮮明地感受到中國電影在人與自然的親昵暢達中所呈現的詩情畫意,彰顯著具有民族色彩的意境之美。
(三)禪宗的“心悟自然”:觸目即真,色空之美
禪宗雖是傳統佛學的一支,但究其實質來說,它其實是一種“中國式的精神現象哲學”[15],它的審美觀念褪去了自然物象所有刻意人為的感情色彩,主張“物之存在的意義只在其自身”[16],這便是禪宗“觸目即真”的美學智慧。禪者同樣特別喜歡自然,他們認為自然萬象皆為禪語,主張“悟道之機遍于十方世界”[17]。然而,在禪宗的智慧下,中國傳統自然審美觀念卻發生悄然的改變,“它一改莊子和孔孟們人與自然的親和與融溶關系,自然被心境化了”。[18]著名的“風吹幡動”公案便是此證,六祖慧能之所以能夠將生活中的物理現象闡釋為精神意識問題,其深層原因仍然是導源于一種“境隨心轉”的現象空觀。類似的觀念在禪宗“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的公案中也有所體現,第三階段看似是第一階段的反復,但此時的山水卻只是觀者參悟的心相[19],它雖然保留了事物所有外在的感性細節,但此時認識與分析的視角已不復存在,客觀物象開始從“我執”的牽絆中剝離而出,成為了觀者某種心境的外化。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禪的自然審美經驗徹底破除現象與本質的隔閡,任由自然景觀在“青山自青山,白云即白云”的真實存在中自由舒展,這顯然是一種迥異于傳統儒道觀念的全新美學思路。
具體在中國電影中,“禪”語境之下的“心性”自然擺脫了以往“情境相融的渲染與陪襯,也不再是蒙太奇思維中影像分切的技巧與修辭,其譬喻與聯想的成分已然大幅度地減少了。”[20]以電影中常出現的月亮意象舉例,如果說蔡楚生《一江春水向東流》中月亮的陰晴變化與主人公素芬的情感走向息息相關(賦比興),那么《一輪明月》中的月亮則側重于建構一種不可言宣的悟境。創作者并未以月亮來暗示男女的愛恨離別之情,而是通過一輪明月高懸空中來昭示一種神韻超遠的氛圍,使觀者在靜謐幽遠的月色中收獲禪意化的審美體悟。由此不難看出,“禪觀”化的自然已經開始刻意與影像敘事拉開距離,通過感性細節的反復體認來彰顯其自身的獨特存在。紀錄片《掬水月在手》便是此例,該片以空鏡頭的方式展現了大量自然審美意象,雖然它們與敘事走向無甚關聯,但卻支撐起了全片審美意趣。導演在自然鏡語和敘事內容的“背反”中呈現了一個圓滿具足的生命世界,通過“觸目即真”的呈現方式使“詩境”與“禪境”實現了內在的融合與統一。
同時,禪宗的“心性”智慧在電影中還呈現為一種趨向于“荒寒”的自然意趣,這是其“色空”觀念所影響并決定的。禪宗的頓悟是無相的境界,聲色五彩全部化為一種空的領悟,由此形成了精神意識的絕對冷寂,“荒寒”恰由此而來。朱良志認為,“冷寒為孤立虛空的禪境提供一種氛圍,佛性真如總在這冷寒中展開。”[21]在《靜靜的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岡仁波齊》《一輪明月》等作品中,那些“孤月”“寒雪”“冷水”“冰霜”“幽林”等荒寒意象的運用,其所展現的恰是一種禪意化的自然審美觀。
三、中國電影自然審美的展呈方式
中國電影自然審美觀念不僅與儒釋道哲學息息相關,同時也與中國傳統美學范疇的演化一脈相承。具體來說,“俯仰觀察”“遠望近察”的游觀審美方式形塑中國電影橫移化的鏡頭語言,展現了自然景觀綿延流動的氣韻之美。由《周易》“觀物取象”所奠基的意象傳統深刻影響著中國電影的造型風格,這使其逐漸在自然的“寫實”與“寫意”間摸索出一條具有中國傳統美學色彩的影像造型之路。在“天人感應”的哲學基礎上,中國電影也常注重將影像表達比附于時序的更迭,以民族化的表現方式踐行著“比情自然”的敘事旨趣,這些都是中國電影在傳統美學滋養下所生成的獨特審美觀念。
(一)“游目自然”的鏡語呈現
中國獨特的自然審美方式很大程度是由中國傳統審美視角的選擇取用所決定的。西方繪畫以模仿逼真為首要原則,畫家常從固定的視點來觀察對象,在二維平面上進行三維空間構造,由此形成“陰陽遠近,不差錙黍”[22]的幾何學光影造型。而華夏民族對天地萬物的關照方式卻與西方存在很大的不同。誠如《易經》中說,“無往不復,天地際也”。中國的自然審美從不以固定視角展開,多點移動的觀察方式使我們的眼光在自然萬象中開闔萬里、徜徉流動,由此形成了節奏化、音樂化的“時空合一體”[23],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繪畫從一開始便是“反透視法則”的,它形成了一種被稱之為“游目”“游觀”的審美方式。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說:“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可游者,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為得。”[24]這里所說的“可游”指代的正是一種“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25]的“游觀”視點。
在中國電影中,這種審美觀察方式集中表現為一種橫移化的長鏡頭效果。學者林年同先生曾將這種手卷式“動態連續鏡頭布局”[26]的方式稱之為“鏡游”,展現了中國電影對中國傳統審美關照方式的賡續轉化。歷史地看,這種鏡頭處理方式在早期中國電影中便大量存在,如北京電影學院倪震教授認為,“中國古典繪畫的空間意識和畫面結構,直接影響了早期中國電影的影像結構和鏡語組成。”[27]據此作者考察了早期中國電影的鏡頭規律后發現,在鄭正秋《姊妹花》等作品中,橫移化的場面調度方式幾乎覆蓋了電影大部分的主要情節,在此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天堂春夢》《小城之春》等影片中,這種“平面延展和游動視點”[28]的視覺效果,得到進一步繼承與發揮。鄭君里在談及電影《枯木逢春》的創作經歷時,專門提到自然景物在這部分電影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29]在影片開場描寫解放前夕的生活序幕時,導演從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汲取靈感,創造了一個民族化影像段落:“墳堆、枯柳、死水潭,煙霧沉沉,似乎是瘴氣到處彌漫;一家人被沖散的場面,鏡頭橫移,前景不斷變化,枯樹枝,斷壁頹垣一一從鏡頭面前移過,造成一定氣氛。”[30]這種鏡語呈現不僅將毛澤東的《送瘟神》進行了電影化表達,同時也形象地展現了“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意境。近年來,“游”的自然審美方式在中國電影中的大量運用,如《云水謠》《長江圖》《春江水暖》等等,這些均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學在中國電影中所釋放的巨大價值。
(二)“意象自然”的空間造型
中國古人在面向自然尋求美的感受時,絕不滿足于機械客觀的“傳移模寫”,而是充分發揮著審美主體的情感與想象,在積極的能動創造中完成“物”與“我”的親善與融合。這種審美方式的結晶被稱為“意象”。所謂“意象”是一種“融入了主觀情意的客觀物象”[31],它雖然并未完全脫離客觀事物本身,但已全然具有人的感性色彩,是勾連“寫實”與“寫意”的橋梁。這種方式最早可追溯至《周易》中,《周易·系辭下》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里所說的“仰觀俯察”,正是審美主體以情感為動力,向大千世界加以感悟和取舍的活動[32],換句話說,正是主觀思維意識的有機參與下,才能使客觀物象變為“人心營構之象”,進一步臻于審美的意義世界。
在中國電影民族化理論的建構中,諸多學者均注意到“意象”之于中國電影本體性的美學價值。長期以來,中國電影往往以時間性的敘事見長,其空間造型的意識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均遭到忽視,這在源遠流長的“影戲”傳統中能夠得到充分證實。直到20世紀80年代,在“丟掉戲劇的拐杖”“電影語言現代化”的號召下,電影的空間造型意識被推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此,中國電影人開始逐漸擺脫傳統“戲劇性”的依賴,深入挖掘電影造型功能的潛在價值。直到第五代導演的橫空出世,這種造型表意的影像方式臻于頂峰,電影理論家羅藝軍先生曾將第五代的造型方式稱之為“意象造型”。所謂“意象造型”是一種“介乎具象造型與抽象造型之間,既不脫離物象的固有形態,又力圖超越這種形態,以抒發審美主體對物象的主觀感受和寄富審美主體的意緒為美學原則。”[33]它上承中國傳統意象美學的精髓,下接現代性的電影表現方式,逐漸在“似”與“不似”、“寫實”與“寫意”間摸索出一條獨具中國審美色彩的影像造型之路。
第五代導演們在進行“意象造型”的審美創造時均不約而同地將視角投向了自然,如《一個和八個》的主要場景均是外景,但全片幾乎沒有出現過象征生命的綠色,創作者正是在這種粗獷、荒涼的意象性景觀中,表達了對帝國主義“三光”政策的批判;《黃土地》中占據畫面四分之三的黃土地,在擠壓、窒息的視覺造型中凸顯著導演對農耕文明的批判與思考,張藝謀在《黃土地》的攝影闡述中專門提到了這種造型語言“豎畫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34]的視覺效果。無論《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還是吳子牛的《晚鐘》等電影作品,意象化的自然景觀同樣是中國電影自然審美觀的重要體現。
(三)“比情自然”的敘事旨趣
中國傳統自然觀念認為,外在客觀自然界與人的生命活動間存在著某種聯系,天道與人道的運行圖式互為對照,由此形成“天人感應”的文化傳統。這種觀念可追溯到漢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他借助易學對自然萬象的細致觀察,以陰陽五行觀念推衍出天道與人道間的類比關系,建構出中國傳統“天人和德”(《易傳》)的宇宙本體觀。在董仲舒看來,人如何效法、順應天道的規律是人類存的首要問題,而自然界恰是“人事、天道之間的一種重要中介。”[35]據此,自然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感性色彩,成為溝通天人的樞紐。在美學領域,這種將自然“人情化”“感性化”的觀念形成了中國源遠流長的“比情”審美傳統,它超越了“比德”在道德倫理層面的限制,直接影響了中國美學發展中人與自然間純粹審美關系的生成。
這種自然與情感的關系在時序變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陰陽交替,四時更迭與人性人心保持著某種同類和同構關系。”[36]遵循著這一審美軌跡,中國古代文人逐漸形成了“傷春悲秋”的傳統。受此影響,中國電影在進行影像表達時,也尤其注重將情感比附于自然時序,以民族化的表現方式傳達著“比情自然”的敘事旨趣。例如程步高的《春蠶》、顧長衛的《立春》、費穆的《小城之春》等電影作品均是以時令意象來奠定全片的審美基調。據《小城之春》的編劇李天濟回憶,費穆正是在《蝶戀花》的反復吟詠之中找到了《小城之春》的情緒基礎。雖然作為季節時序的“春”在片中基本屬于“失語”的狀態,它并未有機地參與到主體情節的建構當中,甚至導演對與季節相關的自然物象也并未做任何描寫,但“春”卻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整部電影的幽怨氣氛。導演正是在中國傳統詩詞的浸潤下,以春天的傷感來比興劇中玉紋佳偶難成、青春易逝的哀怨惆悵,傳遞出一股淡淡的感傷之情。
此外,秋天的蕭索也常作為中國電影建構情節、傳遞情感的重要依據。從生命運行的自然規律來看,秋天是草木枯萎、生命由盛轉衰的節點,它映射在人的精神心理當中,必然會帶來一種感傷的情緒,這就為中國敘事傳統的“悲秋”意識奠定了心理基礎,電影《秋決》正是據此而創作的。雖然該片以“秋天行刑”為核心情節,但故事卻始終傳遞著“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命意識。影片結尾,當裴剛在一片肅殺的秋意中被押赴刑場時,女主人公蓮兒已懷有他的骨肉,孕育的新生所意指的正是裴剛道德生命的重生與覺醒,導演正是在這種時序的感傷與生命的傳遞中,實現了對儒家倫理價值的確證與體認。
結語
中國傳統美學中存在著深厚、綿延的自然審美傳統,它不僅在中國美學史中舉足輕重,同時也對中國人審美意識的生成具有深切影響。基于傳統美學的分析視角來進一步厘清中國電影的自然審美觀念,對當代中國電影民族性理論的建構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在未來的發展中,希望中國電影能夠在“倫理化”“文化化”“奇觀化”的創作趨勢后,更多地將中國傳統“自然化”的審美觀念納入影像當中[37],建構出與西方電影不同的審美思路,讓自然重新成為當代人類的棲居之所,彰顯“天人合一”的民族觀念!
參考文獻:
[1][15][18][19]張節末.禪宗美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17,14,14,16.
[2]蔡鍾翔.美在自然[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1.
[3]宗白華.美學與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6.
[4]陳林俠.自然與當下中國電影的審美內涵及其敘述可能[ J ].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3):52-60.
[5]周均平.“比德”“比情”“暢神”——論漢代自然審美觀的發展和突破[ J ].文藝研究,2003(05):51-58.
[6]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先泰兩漢編)[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137.
[7]李鎮.禮樂文化與中國電影美學[ J ].電影藝術,2021(02):17-25.
[8]李玉華.詩與電影——學習札記[ J ].中國電影,1957(01):43-44.
[9]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參照簡帛本最新修訂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175.
[10]蒙培元.人與自然——中國哲學生態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2.
[11]張志慶,門曉璇.21世紀以來中國生態電影的發展[ J ].當代電影,2021(02):153-158.
[12][蘇聯]愛森斯坦.并非冷漠的大自然[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316.
[13]羅藝軍.中國電影與中國文化[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5:16.
[14]李澤厚.華夏美學[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101.
[16]朱良志.中國美學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38.
[17]皮朝綱.靜默的美學[M].成都: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1:124.
[20]王海洲,呂培銘.論中國電影的“禪意”旨趣與美學境界[ J ].東岳論叢,2023(06):70-74.
[21]朱良志.論中國畫的荒寒境界[ J ].文藝研究,1997(04):135-148.
[22][23]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07,129.
[24][25]周積寅.中國畫論輯要[M].南京: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05:255.
[26]林年同.中國電影理論研究中有關古典美學問題的探討[ J ].電影藝術,1985(03):35.
[27][28]倪震.探索的銀幕[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185.
[29][30]鄭君里.畫外音[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79:167,167-168.
[31]蔣紹愚.唐宋詩詞的意象和意境[ J ].文藝研究,2021(05):46-55.
[32]朱志榮.意象創構中的觀物取象[ J ].文學評論,2022(02):41-49.
[33]羅藝軍.第五代與電影意象造型[ J ].當代電影,2005(03):4-10.
[34]羅藝軍.20世紀中國電影理論文選(下)[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3:663.
[35]崔鎖江,白立強.董仲舒自然哲學的四重維度及其對天人感應論的調適[ J ].衡水學院學報,2022(06):53-59.
[36]樊波,常鋒.論中國文化和文藝現象中的時間意識[ J ].藝術廣角,1991(04):91.
[37]陳林俠.自然與當下中國電影的審美內涵及其敘述可能[ J ].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3):5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