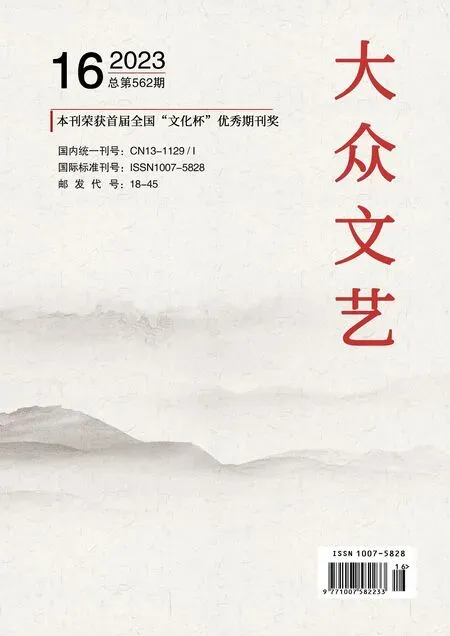伊恩·麥克尤恩前期兒童作品中非常態倫理環境中的倫理身份異化*
許媛媛
(皖西學院 外國語學院,安徽六安 237000)
1978年,《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短篇小說集發表,其中包含《家庭制造》《蝴蝶》等八部短篇小說,后于1978年出版了《水泥花園》和《床笫之間》,因其主題陰暗這三部小說并稱為“驚恐文學三部曲”。筆者認為,主題陰暗僅是麥克尤恩作品假借的表象,表象之下隱喻當代人類生存危機,以及對道德倫理的探討,正如翟世境所言:“他描繪陰沉恐怖的場面,表現心靈與性愛的危機,實在是具有揭示社會痼疾、探討人類生存困境的嚴肅意義。”[1]
麥克尤恩前期作品集中體現了他對家庭倫理、兒童成長等主題的深入挖掘和剖析,其中兒童角色的不幸和災難這一創作特征迭出不窮。作品中兒童的成長軌跡雖有不同,但最終的命運卻大致相同。作品中麥克尤恩構建了一個非常態的倫理環境,家庭和社會環境極為惡劣,兒童成長充斥著壓抑、恐懼,導致其逐步走向倫理悲劇。本文以伊恩·麥克尤恩前期兒童作品《蝴蝶》《家庭制造》《水泥花園》為研究對象,通過對當代英國社會倫理環境、家庭倫理環境等非常態倫理環境的深層挖掘,理清其對兒童倫理選擇和倫理身份異化的作用,由此領悟麥克尤恩對當代家庭倫理的憂慮和審視對待孩子成長的方式,以及健康家庭倫理環境對兒童倫理身份的確定、倫理意識形成的至關重要作用。
一、荒原型社會倫理環境
文學倫理學批評“強調回到歷史的倫理現場,站在當時的倫理立場上解讀和闡釋文學作品,尋找文學產生的客觀倫理原因并解釋其何以成立。”[2]唯有回歸當時的英國社會和小說世界的倫理環境,方能探尋文中主人公倫理選擇錯位和倫理身份異化的根源。
20世紀70~80年代,英國進入動蕩轉型的后工業時代,生態環境被破壞,文化失去規范,貧困與縱欲并存,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人際關系扭曲,整個社會大眾失去信仰。個體成長離不開客觀倫理環境,在這樣信仰缺失、道德衰敗的社會環境中,少年不期望通過誠實勞動來達到奮斗目標。麥克尤恩在《家庭制造》中雖未展現主人公成長的客觀倫理環境,但部分細節可見端倪。“我”和雷德蒙輟學成了無業游民,四處閑逛。“我”的父親在面粉廠工作,每天超負荷工作,回到家身心俱疲卻收入微薄,因為“我”小偷小摸掙得遠比他多,面對父親,“我”是報以嘲笑的態度,“我和雷德蒙喝茶時經常笑話這種對生活的消極背叛……笑話他們為了肯定自己,把一生的低眉折腰看成是美德;”[3]他嘲笑父輩安于天命,只是因為父輩們一星期的艱苦謀生不及他在書店一下午的活掙得多,對于父親和叔叔的禮物也嗤之以鼻。60~70年代的英國信仰缺失,此時“性解放”運動推動了“性自由”等倫理觀念的形成,并通過公共媒介被廣泛而過度地傳播,顛覆了英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和倫理關系。在成人污穢言語的熏陶下,“我”的性意識得到啟蒙,“我意識到自己的童貞,這令我憎惡”[3],社會對性的開放態度加劇了小說中所謂的“處男羞辱”意識。對性禁忌的無知讓“我”陷入了倫理混亂,從而促發亂倫悲劇。“我”誘騙妹妹玩過家家游戲,完成進入成人世界的儀式性的“自我升華”,從文中“瞻仰我的光輝形象”“感覺到的是自豪”“加入人類社會的高級人群當中”[3]等描述,我們逐漸體會到作者對當時英國社會盛行的性解放觀念的嘲諷。
依據聶珍釗先生的“客觀的倫理環境或歷史環境是解釋、闡釋和評價文學的基礎”[2],如若溯源小說主人公的倫理選擇與倫理身份異化根本,有必要從小說世界的倫理環境入手。《蝴蝶》中呈現的是一個被人遺棄的工業廢區,工廠間穿梭著褐色的河水,沒有公園,且大部分工廠已然廢棄,窗戶都沒有,纖道上半天都碰不上人,沒有生機儼然一個精神荒原,目光所及,盡是工業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污染、破敗與蕭條。
重返《水泥花園》的倫理現場,通過體驗小說世界的壓抑和窒息的環境,不難洞悉小說主人公倫理選擇的動因。小說中,“我們的房子又老又大,建得有點像個城堡,厚墻、矮窗。”[4]房子的設定遠離鬧市區,這無疑是一個相對孤立的位置:從外部環境來看,原本他們家的房子立在滿是房子的街上,如今它卻孤零零地立在一片空地上;步入屋內,陳舊、破敗感竄入眼簾:地窖光線陰暗,房門幾乎要從鉸鏈上脫落,花園里野草亂竄,一旁的假山部分倒塌,小池塘也荒廢見底。父母在家庭之外都沒什么真正的朋友,也不允許孩子把朋友帶進家門。在某種層面上廢棄的房子和街道、與朋友絕緣暗示著杰克一家所處的社會倫理結構的損壞。花園、房屋、街道等象征著社會文明和秩序,其廢棄、倒塌隱喻杰克家庭的社會倫理結構的腐化。四處亂竄的野草,意味著杰克等人的獸性因子如野草肆意瘋長而脫離社會秩序的控制。
二、缺失型家庭倫理環境
從文學倫理學關于斯芬克斯因子的相關闡述可見,人的身上同時存在人性因子和獸性因子,成人進行理性的倫理抉擇,往往是后天教化和培養的過程中形成的能夠辨別是非善惡的理性因子的結果,這種后天教化即倫理規訓,或社會文明秩序,造就倫理身份的確定,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子女消退獸性因子(自然天性),塑造其精神天性成為倫理人。“倫理身份的變化往往直接導致倫理混亂,倫理混亂表現為理性的缺乏以及對禁忌的漠視或破壞。倫理混亂無法歸于秩序重構,則形成悲劇文本。”[4]倫理規訓作為兒童成長軌跡中決定性因素,有著重要的倫理身份確定和倫理抉擇引導作用,其主要表現為父母或一方實質上的缺失導致教育與規訓的缺失。家庭倫理規訓的缺失使得青少年不懂基本的社會秩序和規范,易造成他們在步向成人過程中倫理身份混亂而做出錯誤的倫理選擇。
在三部作品中,家庭模式呈現出一種特殊的共性:父親強權或以缺位的方式出現在家庭中,從不教管,而母親似乎久病不起,肉體上羸弱,缺乏權威,孩童被剝奪了正常成長的機會,從而異化成邊緣人。父母或一方實質上的缺失導致倫理規訓與教導的缺失,失去榜樣和引導作用,青少年極易觸碰倫理禁忌不自知,甚至破壞社會的倫理秩序。回顧《蝴蝶》,“我”出生于單親家庭,由于母親與我的面部畸形,沒有朋友,尤其缺乏異形朋友,對他人的看法和態度保持高度警惕,充滿懷疑和不信任。“在警察局里甚至還沒等我作陳述他們就開始懷疑我了”[3],“她們不自然地掃了我一眼。她們懷疑我什么,和其他人一樣”[3],文中的這些主觀臆測使其與社會正常生活漸行漸遠,成為置身事外的邊緣人。同時,在他成長過程中母親未能提供家庭的溫暖和恰當的規訓,造成母親與“我”的疏離,甚至對于母親的離世也無動于衷,躲得遠遠的,且厭惡那些親戚們。母親的離世、父親的缺失使得“我”毫無道德約束,從而造成“我”在空虛發悶的生活中假借“捉蝴蝶”欺騙鄰家女孩企圖猥褻并最終將其溺死。起初,對于女孩的接近“我”只是想找一個可以一起散步的朋友,哪怕只是一個九歲大的孩子,女孩對自己的這種好奇感使“我”得到從未有過的滿足,“她吸引了我,我想要她成為我的朋友”[3],但他的這一想法卻在后繼行為中逐漸扭曲。“說服她和我一起走運河已經變成當務之需,這念頭讓我著魔”[3],原始的獸性因子與良知不斷斗爭,而后逐漸被本能所控制,以運河邊有蝴蝶有船只誘騙簡,導致男孩一次次做出錯誤的倫理選擇,最終迷失人性偏離社會倫理原則,觸犯“戀童”和“弒童”兩重倫理禁忌。作為最后一位見到簡的人,男孩被警察要求去見簡的父母。他精心準備,燙了西服,挑選領帶,噴了香水,卻在臨出門時忽然改變主意,為渴望得到他們的認可而精心裝扮自己感到厭惡,這一系列行為表明“我”知曉文明,但后續行為也顯示“我”并不愿遵循社會普適規范和禮儀。文中他試圖阻止簡逃回家,避免簡將發生的事告知他人,說明潛意識中他是有鑒定道德行為的能力,但從誘騙到性侵再到弒童的過程中,其倫理身份異化,從游離于社會主流文明的邊緣人,變為觸犯倫理禁忌的問題少年。
在成人道路上,父母是子女效仿的道德榜樣,如若父母或一方缺失造成倫理規訓的缺失,無疑效仿和引導,在倫理選擇中理性因子逐漸被自己的原始本能所控制,斯芬克斯因子失去應有的平衡,最終打破倫理禁忌造成倫理悲劇。《水泥花園》中兄弟姐妹由于父母的缺位,使得他們在身份確認過程中缺乏引導,出現姐弟關系畸變為母子關系、姐弟亂倫的倫理混亂現象。并且親子倫理關系關系冷漠,以致孩子對他的死都無所觸動。父親因為心臟病不能干重活,但杰克在搬運水泥時使用伎倆促使“他承擔的重量跟我一模一樣”[5],嘲弄著父親的羸弱,間接地觸發他的病情和死亡,甚至是在父親倒下,他盡管明白此時必須跑過去卻也遲疑許久,沒有立馬呼救,導致錯過搶救時機,間接促成父親的死亡。在成長敏感期遭遇父親身份的突然缺席,緊接著母親身份的空缺,家中無人作為他成長路上的引路人。朱莉在家庭中的身份是母親,妻子,還是姐姐?母親在世時,她有著明晰的倫理身份:女兒和姐姐,卻從她掌管家中事務開始,倫理身份變得模糊,時而表現為家庭的母親,時而是姐姐,三種身份在朱莉身上交織,無力辨別。杰克和朱莉倫理身份的變化直接導致倫理混亂。父母雙亡,原本完整的社會倫理架構倒塌,在進行自我身份確認的過程中失去倫理參照,導致他們在倫理選擇時即道德成熟過程中遇到難題而無人給予引導,其倫理意識無法產生,導致很難完成對自我身份確認的倫理選擇。
親倫關系決定倫理規訓能否實現,親倫關系出現裂痕,則意味著父母之間、親子之間和子女之間的關系處于錯亂的狀態。錯亂或異化的親倫關系,使得青少年游離于道德禁區。《家庭制造》中父親做著十二小時輪班的工作,晚上到家時筋疲力盡,脾氣暴躁,無力管束子女;日常生活中,“我”承擔了一部分照看妹妹的任務,基于此,讀者可以感知這個家庭的倫理道德教育的缺失。故事中兄妹關系冷漠,被迫照看康妮,寧可被綁在柱子上燒死,也不愿參與她的游戲,害怕被朋友看見而恥笑。生活中雷德蒙充當父親的角色“給我啟蒙了成人生活的秘密”[3],我迫切期望自證以擺脫“處男羞辱”,從而做出觸犯倫理禁忌的行為,根本上是其對倫理秩序和規范的無知,這源于親子倫理關系的不和諧導致的倫理規訓的缺位。作為家庭倫理關系的核心,兩性關系和諧平衡至關重要。在麥克尤恩前期作品所描述的家庭環境中,夫妻之間缺乏真摯的情感交流,充斥著冷漠與傷害,丈夫對妻子的身體與語言傷害破壞夫妻感情的同時也破壞了家庭的和諧,而故事中呈現的家庭悲劇無不源于這種家庭成員間的不和諧,使得少年成為家庭的受害者,而夫妻缺乏溝通和理解也是當代社會夫妻倫理關系解體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子女是夫妻之間愛的關系的客觀體現……父母把子女作為他們的愛,即他們的實體性的定在加以愛護。這就是父母撫養和教育子女的義務,或者說子女被撫養和受教育的權利。”[6]早期作品中的青少年自我的社會融入困難,帶有厭世情緒,異化為“邊緣人”,從中我們也可窺探出當代社會被異化的親子關系。親倫關系是家庭倫理環境的產物,奠定兒童倫理身份的確定和正向倫理抉擇,如若家庭倫理規訓缺失,兒童倫理規則無以建立,則引發倫理悲劇。
結語
前期作品中麥克尤恩運用隱晦的敘事刻畫非常態的社會和家庭倫理環境及其對青少年成長的重要性,非常態倫理環境反映了倫理誤導、倫理規訓,通過對上述作品中非常態倫理環境進行分析,還原倫理事件發生的社會、家庭倫理現場,是我們解讀作品中非道德倫理選擇的關鍵。同時作品警示家庭倫理規訓的缺失造就成青少年倫理意識薄弱,無法建構自身倫理規則,導致倫理悲劇,隱喻不斷提高家庭倫理規訓意識的緊迫性與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