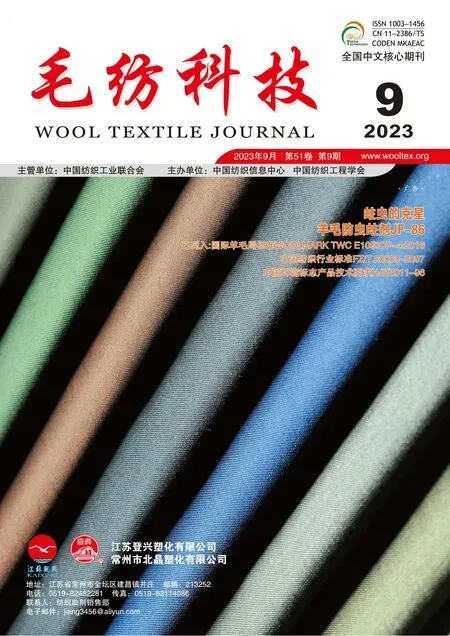回鶻供養人服飾形象比較及其創新設計
王 勃,馬艷輝
(西安工程大學 服裝與藝術設計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8)
回鶻是古絲綢之路沿線最為活躍的少數民族之一,柏孜克里克石窟與莫高窟中遺存著豐富的高昌回鶻與沙州回鶻供養人壁畫。回鶻供養人是指因信仰某種宗教,通過提供資金、物品或勞力,制作圣像、開鑿石窟、修建宗教場所等形式弘揚教義的虔誠信徒的形象。對于柏孜克里克與敦煌莫高窟壁畫中回鶻供養人服飾研究中,原田淑人等[1]、馮·佳班[2]、李肖冰[3]、莫尼爾·瑪瑟爾[4]對柏孜克里克回鶻供養人的服飾進行了描述,但描述重點為冠飾,且只是對于壁畫內容的客觀陳述;謝靜等[5-6]和夏俐[7]對敦煌莫高窟回鶻供養人服飾進行了討論;艾山江·阿不力孜[8]、包銘新[9]、沈雁[10]、呂釗[11]和蔡遠卓等[12]對回鶻服裝從各個部分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整理研究,提供了數字圖像資料,并進行了部分服飾的復原工作;周菁葆[13]、李霞[14]和竺小恩[15]將回鶻民族的服飾與中原、中亞、西亞等地區的服飾進行了比較,但并未從款式、色彩、紋樣等方面進行深入分析;王麗娜[16]僅針對莫高窟61窟女供養人做了文創設計,存在一定局限性。綜上可以看出,學者們對柏孜克里克石窟與敦煌莫高窟壁畫中回鶻供養人服飾的整理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鮮有人對比研究2地回鶻供養人服飾,并在此基礎上做創新設計。
本文通過比對分析柏孜克里克與敦煌壁畫中回鵑供養人的服飾形象,驗證服飾的發展變化與地域性的差別,找尋2地之間的異同,分析其中的原因,并提取其特有的文化元素進行創新設計,以激發當代服飾產品的設計活力,發展回鶻服飾文化。
1 回鶻服飾形象整理
回鶻供養人服飾形象體現了回鶻統治的等級制度、社會文化以及貴族的身份地位等。為直觀對比不同區域回鶻服飾形象的差異,以柏孜克里克石窟和敦煌莫高窟2地回鶻供養人服飾形象為研究對象,梳理現有數據和資料,對回鶻服飾形象進行整理。
公元840年,漠北回鶻汗國滅亡,分3支路西遷:第1支西遷至土魯番盆地,稱高昌回鶻(又稱西州回鶻),經實地考察調研,柏孜克里克中石窟中第9、14、16、17、18、20、22、23、24、27、29、31、32、33、34、38、39、76窟有回鶻貴族供養人服飾形象的壁畫;第2支西遷至現敦煌附近稱沙州回鶻(又稱河西回鶻),莫高窟第22、25、55、61、98、100、108、121、148、152、202、205、237、244、245、275、310、363、399、401、409、418、428、454窟是記載回鶻貴族供養人服飾形象的壁畫。現學術界對第409窟男供養人來自西夏或是回鶻有所爭議,本文以第409窟屬于回鶻這一觀點[17]進行后續分析。第3支西遷至蔥嶺西楚河、七河流域一帶,稱蔥嶺西回鶻(或稱黑汗王朝)[18],但此封建政權并不算回鶻民族的獨立政權,所以本文不將其納入研究范圍。
2 回鶻服飾形象特征差異
對柏孜克里克石窟和敦煌莫高窟2地回鶻男女貴族形象中的服飾形制、色彩、紋樣3方面進行對比分析。
2.1 服飾形制差異
根據2地壁畫中男女貴族供養人服飾形制的差異性對2地男女服飾形制進行整理,回鶻供養人服飾差異對比見表1。

表1 回鶻供養人服飾差異對比Tab.1 A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lothing of the Uighur feeders
2.1.1 男性服裝形制比較
圖1所示為柏孜克里克第20窟,即表1示出的圓領窄袖長袍類形制,此形制一般為回鶻貴族所穿。此種形制2地的區別在于在服裝的質地和圖案以及長袍開叉位置。對于質地方面因沒有實物出土故無法進行比較,圖案問題將在后文詳細論述,長袍開叉位置與繪制手法相關,此處不多論述。其他壁畫遺存如莫高窟第148窟與第409、237窟,柏孜克里克第20、22、24、31窟2地服裝形象相同。

圖1 柏孜克里克第20窟Fig.1 Cave 20 of the Pazikli caves
表1中男裝第2種形制在柏孜克里克石窟與莫高窟的區別在于服飾領襟、袖口、上臂和下擺有飾邊,柏孜克里克石窟服飾裝飾更為豐富。新疆喀什地區博物館收藏有2件服裝實物,形制與此類相近,有學者認為這2件服裝實物出土的地區是喀啦汗王朝所在區域[9],此王朝位于中亞地區,離西亞地區更近,受當地及西亞文化較多。在柏孜克里克第32窟壁畫,發現有西亞貴族回鶻供養人形象,西亞貴族回鶻供養人形象服飾形制為圓領窄袖黑色緊身袍服,兩袖上方中間與前胸與袖口皆鑲有淺色的飾物(見圖2);而柏孜克里克第16窟供養人的服飾形制為圓領袍,領襟、袖口、上臂和下擺有飾邊(見圖3)。可以看出2種服裝形制相同并且其裝飾物所在位置大同小異,但是整體對比發現西亞回鶻供養人服飾較顯貴,其中第32窟回鶻回鶻供養人的身份來自中亞及西亞地區。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在地區受中原、中亞以及西亞文化交流頻繁,而莫高窟地區即敦煌在地理位置上距離中亞及西亞較遠,并且在莫高窟以及敦煌地區并無發現此類形制,說明莫高窟地區受到中亞和西亞文化的影響較少,從而使高昌回鶻產生了區別于沙州回鶻的服裝款式,證實了回鶻民族與外域文化的交流。

圖2 西亞貴族供養人像Fig.2 Portrait of a nobleman offering himself to the nobles of Western Asia

圖3 柏孜克里克第16窟Fig.3 Cave 16 of the Pazikli caves
2.1.2 女性服裝形制比較
由表1可知,柏孜克里克與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回鶻供養人對襟長袍的形制基本是相同的,如柏孜克里克第20窟(見圖4)與莫高窟第61窟(見圖5)展示的形制,柏孜克里克第20窟所展示的人物是回鶻公主,莫高窟第61窟是回鶻夫人,均為貴族服飾。西遷后2地本應會受到當地文化影響產生不同的服裝形制,但是此類服裝形制相同,且對襟長袍這一形制常出現在在北方少數民族,則表明對襟長袍的基本形制在西遷之前就已出現,西遷之后保留了這一形制。對襟長袍的裝飾線這一形制體現在在柏孜克里克第9、16、18、20和39窟,但是莫高窟卻無出現,如“胳膊上飾有一條水平裝飾線,長裙正中有‘十’字交叉裝飾線”[19]。而此類裝飾物與男裝圓領袍有飾邊的裝飾物相似,并且這類具有裝飾線的只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出現,結合上文可以看出柏孜克里克女裝也受到中亞和西亞文化的影響。

圖4 柏孜克里克第20窟Fig.4 Cave 20 of the Pazikli caves

圖5 莫高窟第61窟Fig.5 Cave 61 of the Mogao caves
對襟長袍與交領長袍這2種形制在莫高窟都有出現(見圖5、6),2種區別在于對襟和交領,結合表1可知交領長袍只在莫高窟地區出現,造成此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具體如下:①在身份上,莫高窟108窟第1身與第61窟第1身供養人形象身份為曹議金夫人,是回鶻天公主,第98窟第2身和第61窟第2身為曹議金回嫁給甘州回鶻阿咄欲可汗的女兒,第4、5、6位是甘州回鶻阿咄欲可汗和曹議金女兒所生的3個小公主,其身份都和曹議金有密切關系,即與漢文化接觸的較多,可以看出都是受漢代服飾文化影響較多;②回漢混合裝即頭飾為回鶻樣式,而服裝為漢族樣式,通過調研及查閱文獻發現,回漢混合裝這一服裝搭配在敦煌流行,而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并沒有出現此類搭配,也側面說明了在沙州回鶻受漢文化影響頗深;③交領右衽是漢服的典型特征,但是一些古代少數民族為左衽以及對襟,可以看出應是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
結合以上得出,2地都有部分相同的形制,應是保留了西遷之前服裝款式,而男性供養人的區別差異在服裝裝飾上,女性供養人的差異在于裝飾和穿著方式上,且男女服裝上有飾邊的服飾特征則是柏孜克里克所獨有的,而造成上述差異的原因都是受到當地及周邊文化交流的影響,讓2地服飾產生了差異性。
2.2 服飾色彩差異
從莫高窟與柏孜克里克中各挑選具有代表性的供養人服飾色彩進行對比,以莫高窟第409、148、61、98窟(見圖6、7),柏孜克里克第16、20、31窟(見圖3、8)為例,從中提取出壁畫中供養人服飾的主色彩。通過對比發現,2地的主色彩是紅、青(綠)、藍、黃以及褐色等,差異不明顯,但2地服飾色彩的不同則在于色調的飽和度以及明暗程度,其中莫高窟整體色調飽和度不高,亮度低,中低彩度;而柏孜克里克亮度較高,飽和度也較高。

圖6 莫高窟第98窟Fig.6 Cave 998 of the Mogao caves

圖7 莫高窟409窟Fig.7 Cave 409 of the Mogao caves

圖8 柏孜克里克31窟Fig.8 Cave 31 of the Pazikli caves
就相同點來說,2地服裝的色彩大致相同,這與回鶻自身色彩喜好相關。調研發現回鶻其一崇尚藍色,藍色和綠色常混用[17];其二是紅色,代表喜慶、熱鬧。11世紀《突厥語大詞典》古回鶻諺語:“要想俏,須穿紅,要撒嬌,須著綠”;其三是黃,代表著收獲、高貴、陽光,也把黃色稱作金色[20]。
就不同點來說,2地服裝的色彩差異是受當地文化繪畫方式的影響。首先通過實地調研發現莫高窟的許多壁畫色彩都以中低彩度、中低明度的土紅、石綠、土黃、石青等常用色為主,可以看出莫高窟的大多數石窟所繪制使用的色彩飽和度和亮度與回鶻供養人服飾色彩一致。徐欣[21]通過分析莫高窟第36、61、98、100、146等窟的壁畫作品,也發現莫高窟壁畫色彩以中低彩度、中低明度的土紅、石綠、土黃、石青等常用色為主。其次莫高窟經歷過多個政權(如西夏、吐蕃),受到的文化影響較多;紅、黃服裝色彩更符合西域的特色,西域具有獨特的地理氣候,如風沙多,晝夜溫差大,使得當時的服飾在美觀的同時兼具了御寒防沙等實用性能[22]。
2.3 服飾紋樣差異
根據前期搜集圖像資料并繪制紋樣線稿圖,可知莫高窟男性貴族供養人服飾紋樣以團窠龍紋、女性貴族供養人以花鳥紋、團窠花紋以及連珠紋為主(見圖9),如莫高窟第409、109窟等;而柏孜克里克的回鶻供養人男女供養人都是以植物紋樣為主(見圖10),如柏孜克里克第32窟喜悅公主領口是忍冬紋(也有學者認為是卷草紋[23],本文認可忍冬紋這一觀點),第31窟男供養人的服飾以也花草紋樣為主。可以看出2地紋樣以植物紋樣為主,但莫高窟出現了團窠龍紋。

圖9 莫高窟地區回鶻服飾紋樣Fig.9 Mogao Cave area migratory costume patterns. (a) Dragon pattern;(b)Reunion pattern;(c)Flower and bird pattern;(d)Lianju pattern

圖10 柏孜克里克地區回鶻服飾紋樣Fig.10 Pattern of Uighur dress in Pazikli region. (a) Botanical patterns; (b) Lonicera pattern; (c) Gnomon pattern
2地都有植物紋樣與回鶻崇拜自然、崇拜植物有關。沙州回鶻與高昌回鶻盡管各為獨立政權,但由于各地的回鶻是一個民族,紋樣具有一定共性[24]。差別最明顯之處即莫高窟出現了團窠龍圖案,出現這類情況應是莫高窟受漢文化影響且為了區分于高昌回鶻,具體表現為:①敦煌在回鶻統治時期,主要居民為漢人,受中原漢文化影響較多;②龍文化是漢文化的一種,并且龍紋樣在沙州回鶻的壁畫中頻繁出現,“譬如蟠龍冬案的藻井圖案,在回鶻窟中卻屢見不鮮,14個有藻井圖案的回鶻窟中,就有9個窟是蟠龍藻井圖案,占64%”[25]”,表明回鶻洞窟盛行這種紋樣;③團窠龍紋在莫高窟的使用當中并不少見,而在柏孜克里克回鶻石窟中卻沒有出現,目的是為了區別于高昌回鶻政權;④高昌回鶻的主體居民為回鶻人,紋樣上多使用自身的文化傳統,并無直接吸納龍紋,其衣飾上多團花圖案而無龍紋圖案。沙州回鶻可汗供養像以團龍裝飾,也從側面反映沙州回鶻因長期生活于漢文化當中逐步被漢文化所影響的進程。另外,2地女供養人的紋樣區別在于莫高窟多使用花鳥紋,而柏孜克里克女多使用忍冬紋,這也反映了敦煌莫高窟地區受漢文化影響,因花鳥紋多出現在中原內地女性服飾當中。
3 回鶻文化在服裝中的創新設計
3.1 傳統文化在服裝設計中應用現狀
隨著文化自信熱潮的席卷及國人對服裝審美層次的提高,傳統文化元素在服裝設計中的應用價值也隨之增高。中華傳統文化元素具體形式與內容極為多樣,可應用于服裝設計領域中的傳統文化元素也有著差異性,因此,如何讓傳統文化元素在服裝設計中迸發出應有的活力與價值至關重要。
3.2 應用原則
3.2.1 適配性原則
適配性原則指所選擇和應用的傳統文化元素既要與服裝產品類型相適配,也要與服裝產品設計中的其他元素相適配。傳統文化元素形式多種多樣,不同傳統文化的工藝元素、視覺元素以及材質元素等都有不同的藝術風格。因此,為了讓傳統文化元素發揮應有效果,設計人員就需要圍繞服裝設計主題進行傳統文化元素的選擇,避免盲目應用。
3.2.2 適度性原則
服裝設計是兼顧藝術性和實用性的設計過程,任何一個設計環節都應從整體性進行把控,以設計出被更多消費者所接受的服裝產品。因此,在融入和應用傳統文化元素時,服裝設計人員也應根據服裝產品的實際設計需求,既要避免因傳統文化元素應用太少而導致其藝術特征展現不明顯,也要避免因傳統文化元素應用太多而導致服裝產品整體效果過于混亂[26]。
3.2.3 重視情感體驗與表達
重視情感體驗與表達是藝術所追求的重要目標,沒有情感的藝術是沒有生命力的。藝術通常多為一種向內的形式,而設計恰恰相反,多呈現一種向外的表達。在多元化構造的設計形式中,向內的情感表達與向外的維度延伸應該達到一種原真性的統一[27]。
3.3 應用方法
3.3.1 圖案提取重組及應用
中華傳統文化的圖案豐富多樣,但對于圖案與紋樣元素的運用不應僅僅只將中國元素程式化生產,而是要將中華傳統文化元素滲透進服裝產品中。對傳統文化元素的內在文化意蘊進行深入分析,將傳統文化元素提取出來,在保留傳統文化元素根本文化屬性的基礎上進行再創造,如對圖案的夸張變形,對圖案重組(如二方連續、四方連續等),以將圖案巧妙地與現代服裝融合。
3.3.2 服裝面料的應用
傳統文化元素的服裝設計更要注重服裝面料與工藝的結合,可以進行面料之間的創新實踐,如羊毛與絲綢的結合,或在面料上直接進行3D打印,如運用3D打印技術將刺繡運用到面料上,使得面料本身更富有質感。
3.3.3 色彩的選擇與創新
色彩是服裝設計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應用中國傳統文化元素進行服裝設計的過程中應當加強對傳統色彩的創新設計。充分展開對于多樣化色彩元素的應用,豐富服裝本身的色彩,切實體現色彩之美[28]。有機結合傳統以及現代的色彩元素,保證在服裝設計中既能夠體現現代化的元素,還能具有深厚的傳統色彩文化內涵。
3.3.4 傳統款式的創新設計
傳統服裝的款式有很多,如胡服、漢服等,且傳統服裝款式也隨著朝代的變化隨之變化。但現代的服裝設計并不是復原或者藝術再現,不用完全按照原來的款式去設計,而應該巧妙地將傳統款式運用在現代服裝設計,比如半臂、馬面裙等。
3.4 創新設計
3.4.1 色彩提取
從莫高窟與柏孜克里克壁畫中各挑選出4組比較有代表性的供養人服飾壁畫色彩,并標明RGB色值、HSB值(見圖11)。設計的服裝色彩從以上色彩提取。

圖11 服飾色彩提取Fig.11 Costume color extraction
3.4.2 紋樣提取
搜集5幅具有代表性的圖像資料并繪制紋樣線稿圖(見圖12),將提取的紋樣變形處理,運用到服裝中。

圖12 供養人服飾紋樣提取Fig.12 Donor costume pattern extraction
3.4.3 設計作品
本文系列設計見圖13,將現代服裝設計與回鶻服飾文化元素結合,運用具有代表性的回鶻供養人的服飾紋樣及色彩,將紋樣進行變形重組,以印花及刺繡的工藝進行面料并運用在服飾上,整個系列顏色提取自回鶻供養人服飾標志色彩,色彩純度較低,整體風格沉穩且不失設計感。第1套運用莫高窟第409窟供養人身上的團窠龍紋,同樣將紋樣進行抽象的變化,肚兜運用莫高窟第19窟紋樣款式,將紋樣運用羊毛氈戳戳樂的面料再造手法將圖案立體化;第2套運用莫高窟第148窟供養人身上的團花紋樣,將紋樣變換成印花運用在服飾上;第3套運用莫高窟第98窟供養人身上的團花紋樣,將紋樣適當抽象變形,再結合服飾莫高窟第19窟供養人身上的紋樣,將紋樣變換成印花運用在連衣裙右側;第4套運用莫高窟第148窟及第409窟供養人身上的團花、團龍紋樣,將紋樣使用刺繡工藝運用在服飾上;第5套運用莫高窟第第108窟及莫高窟148窟供養人身上的團花紋樣,將紋樣適當抽象變形,再結合服飾胸口部位款式,使紋樣更加生動視覺上更立體有趣。

圖13 設計作品Fig.13 Design works
4 結束語
通過使用文獻調研、實地考察等研究方法,從柏孜克里克與莫高窟2地的回鶻供養人服飾方面入手,對2地服飾的形制、色彩、紋樣進行比較研究,得出西遷后柏孜克里克與莫高窟2地雖各自為獨立政權,但是大部分服裝還是遵循漠北回鶻時期的制度,部分服裝的形制、色彩、紋樣大同小異。但2地又各自受地域影響,如莫高窟地區受中原地區文化及繪畫方式的影響,色彩更為豐富,紋樣的創新區別于柏孜克里克,而柏孜克里克的回鶻服飾受中亞文化、西亞文化影響更多,部分款式進行了創新,產生差異性。在此基礎上運用回鶻服飾文化元素,提取其服飾色彩以及紋樣,融入到服裝設計當中。以更好地傳承弘揚絲綢之路的文化,加強文化自信,為后續相關創新設計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