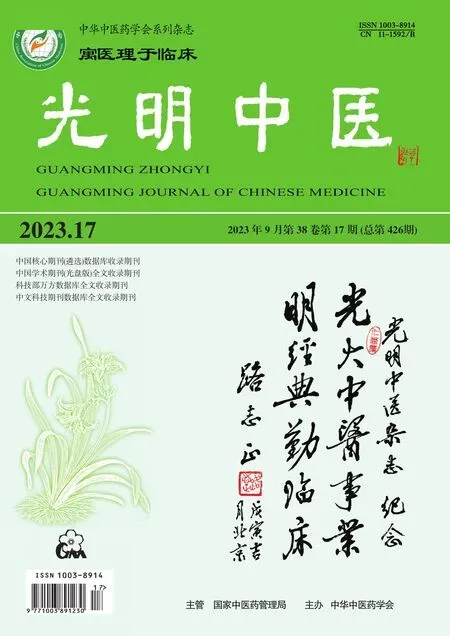經方在基層醫療中的應用
劉燕燕
張仲景之《傷寒雜病論》是中醫學的經典著作,被譽為方書之祖,其最大的貢獻在于確立了一套辨證體系,即六經辨證理論體系。六經辨證源于八綱辨證,胡希恕先生早在20世紀60年代所做的《傷寒論六經論治與八綱的關系》一文中即提出:“六經來自八綱”“無論表、里或半表半里,均有陰陽二類不同的為證反映,三而二之為六,即病之見于證的六種基本類型,亦即所謂六經者是也”[1]。提倡先辨六經、繼辨方證。其所載的100多首方劑以制方規范、結構嚴謹、使用顯效,被世代醫家尊為“眾方之祖”,在臨床中廣為所用。筆者單位所在地區的居民對疾病認識普遍不夠,部分居民檢查依從性較差,且受制于醫院檢查設備不夠齊全等客觀限制,患者的病情有時候未能得到明確的西醫診斷。對于這部分患者,西醫治療上往往采取“大包圍”,依據可能的診斷多方面用藥,有時候診斷未明甚至無從下手。而中醫則可以從患者的癥狀、體征、體質等下手,辨證論治,扶正祛邪,調整人體陰陽,依證處方而取得療效。筆者將在門診遇到的幾例西醫診斷未明確、治療效果欠佳,而用中醫經方辨證論治獲得良效的例子分享如下。
1 桂枝甘草湯治療心悸案
黃某,女,76歲。2021年9月1日就診。主訴:受驚嚇后心悸1 d。患者1 d前受驚嚇后開始出現心悸、心慌感,至外院做心電圖、肌鈣蛋白、心肌酶等檢查未見異常,患者拒絕做心臟彩超、動態心電圖等進一步檢查,西醫診斷“心悸”,予靜脈滴注丹參注射液、口服穩心顆粒后癥狀稍緩解,但次日起床后上述癥狀再次出現,遂來廣州市南沙區第一人民醫院新墾分院門診就診。刻診:心悸心慌,手捂胸前可稍減輕,畏寒,疲倦,舌暗紅,苔薄白,左脈沉細右脈弦。查體:神志清,肺部未聞及干濕啰音,心臟各瓣膜區未聞及明顯雜音,心律齊,心率約76次/min。中醫診斷:心悸,辨證:太陽、少陰合病。治以桂枝甘草湯加減:桂枝24 g,甘草9 g,大棗10 g,龍骨30 g,牡蠣30 g,炮附片9 g(以上中藥均為顆粒劑)。每日1劑,溫水200 ml沖服,共2劑。后患者未再復診。10月11日患者因“腹痛”于門診再次就診,追問上次服藥效果,患者訴服藥后心悸心慌癥狀完全消失未復發。
先辨六經、繼辨方證,這是經方辨證論治的具體實施步驟。惲鐵樵先生[2]曾感嘆:“《傷寒論》第一重要之處為六經,而第一難解之處亦為六經,凡讀《傷寒論》者無不于此致力,凡注《傷寒》者亦無不于此致力”。六經辨證準確,說明其病性與病位明確,繼而再辨具體方證。就此例而言,患者受驚嚇后感心慌心悸,手捂胸前可減輕,與《傷寒論》第64條:“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不謀而合。桂枝甘草湯主治太陽病發汗過多損傷津液,但表未解,機體仍有從表逐邪而出的趨勢,氣上沖心胸而導致心悸。同時患者有疲倦、畏寒、脈沉細的表現,為陷入少陰,故加附片以振陽。患者心悸因受驚嚇得之,《傷寒論》第118條載:“火逆,下之因燒針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故在桂枝甘草湯基礎上加龍骨、牡蠣以重鎮安神、鎮驚而獲得良效。
心悸的發生多因體質虛弱、飲食勞倦、七情所傷、感受外邪及藥食不當等,以致氣血陰陽虧損、心神失養、心主不安,或痰、飲、火、瘀阻滯心脈,擾亂心神。《傷寒論》中的心悸有多種描述,包括心動悸、心下悸、臍下悸、奔豚、欲作奔豚、氣上沖等,而桂枝甘草湯是治療心悸的最簡方,其余治療心悸之方,多在桂枝甘草湯基礎上衍生,如桂枝加桂湯、苓桂術甘湯、苓桂棗甘湯、炙甘草湯等,這些方劑在臨床中都廣為所用。《本經疏證》云桂枝有“通陽”之功,祁爍[3]認為桂枝可通“表里之陽、調和營衛;可通四肢之陽、通利關節;可通上中下三焦臟腑之陽氣、助陽化氣”,桂枝辛溫通達陽氣,配合甘草辛甘化陽,甘溫相得,斯氣血和而悸自平。臨床中有多項研究也明確了桂枝甘草湯及其衍生方在治療心律失常方面的確切療效[4-7]。
2 小建中湯治療腹痛案
馮某,女,63歲。2021年1月22日就診。主訴:反復腹痛1月余。患者1月余前無明顯誘因開始出現腹部疼痛,以臍周及下腹部為主,持續性隱痛,按摩腹部后疼痛可稍減輕,大便正常。舌淡紅,苔白稍厚,脈細。查體:神志清,心肺聽診無異常,腹部平軟,全腹無壓痛及反跳痛,肝脾未觸及,腸鳴音正常。完善消化系彩超、泌尿系彩超、婦科彩超等檢查均未見異常。中醫診斷:腹痛,辨證:太陰病。治以小建中湯加減:桂枝12 g,白芍40 g,大棗10 g,甘草9 g,防風10 g,白術18 g(以上中藥均為顆粒劑),生姜5片,麥芽糖1勺。每日1劑,囑5片生姜煮水半小時后沖顆粒劑,再加1勺麥芽糖,共3劑。2個月后電話隨訪,患者訴服上方后腹痛癥狀消失未復發。
先辨六經繼辨方證。患者以腹痛為主,無鼻塞流涕打噴嚏等表證表現,也無口苦咽干目眩等少陽證表現,故屬里證。患者的腹痛特點表現為持續的隱痛,且按摩腹部后可緩解,結合苔白稍厚脈細,屬虛屬寒,考慮太陰虛寒證,予小建中湯溫中補虛、緩急止痛;患者舌苔白偏厚,予加白術加強祛濕之效,加風藥調暢氣機,加強化濕之功。
小建中湯出自《傷寒雜病論》,“建中”即溫補中焦,王肯堂于《證治準繩》中曰:“脾居四臟之中,生育榮衛,通行津液,一有不調,則失所育所行矣,必以此湯溫健中臟,故名建中”。《傷寒雜病論》多處記載此方,如第100條:“傷寒,陽脈澀,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差,小柴胡湯主之”。《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證并治》第18條:“婦人腹中痛,小建中湯主之”。描述最為全面的是《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第13條,曰:“虛勞里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煩熱,咽干口燥,小建中湯主之”。分析條文可知,小建中湯為治療太陰里虛寒所致諸癥。陳亦人著《傷寒論譯釋》中解方:“以甘藥為主,佐桂枝溫陽益氣之效著,佐芍藥則養血益陰之力強”。再加生姜溫胃散寒,大棗補脾益氣,甘草益氣和中,諸藥共奏溫中補虛、緩急止痛之效。方中飴糖(即麥芽糖)往往讓很多醫者忽略。《藥征》認為“膠飴之功,蓋似甘草及蜜,皆能緩諸急”。曹穎甫《經方實驗錄》更謂:“夫小建中湯之不用飴糖,猶桂枝湯之不用桂枝,有是理乎”,飴糖藥性甘溫,入脾、胃、肺經,具有補中益氣、緩急止痛、潤肺止咳的作用[8]。但是很多時候藥房不能提供飴糖,或者購買困難,袁榮金等[9]認為山藥與麥芽同用可糖化發酵成麥芽糖,并可代替飴糖行使其溫補中臟之功效。
3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治療失眠案
吳某,女,43歲。2021年10月30日首診。主訴:失眠伴心悸2個月余。患者2個月余前開始無明顯誘因出現失眠,心悸,在廣州市南沙區第一人民醫院新墾分院其他醫生處就診,診斷:非器質性失眠癥、焦慮狀態,予阿普唑侖片、氟哌噻噸美力曲辛、天王補心丹等口服。服藥當晚可入睡,但一停藥又會失眠。依賴以上藥物才能入睡,持續2個月,患者不想依賴安眠藥,遂來門診尋求中醫調理。刻診:未服安眠藥時難入睡,眠淺易醒,煩躁,雙眼累,酸澀感,間有心悸,舌淡紅稍暗,苔薄白,脈弦。中醫診斷:不寐,證型:少陽陽明合病夾有痰飲。治以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加減:柴胡12 g,黃芩10 g,法半夏18 g,黨參30 g,大棗10 g,酸棗仁30 g,桂枝20 g,茯苓20 g,牡蠣30 g,龍骨30 g(以上中藥均為顆粒劑)。溫水200 ml沖服,日1次,共3劑。患者擔心單服中藥不能入睡,要求開1周阿普唑侖片備用。囑托患者盡量不用安眠藥。11月2日二診:(服中藥期間未服阿普唑侖片)較前容易入睡,可睡3 h左右,早醒,雙眼仍覺得累,仍間有心悸感,頭暈。繼續予上方加澤瀉(顆粒)30 g。3劑。后未復診。12月7日患者因“腹脹”再次于門診就診,訴服11月2日中藥后,每晚未服安眠藥情況下可間斷睡眠4~5 h,白天精神可,無胸悶,遂未來復診。此次覺腹脹,想繼續吃中藥調理睡眠和腹脹。刻診:腹脹,欲嘔,偶有心悸感,胃口可,大便正常,入睡稍難,可間斷睡眠4~5 h,夢不多。于2診處方中加枳實12 g,厚樸6 g(以上中藥均為顆粒劑)。6劑,仍按上述沖服法。1月后電話隨訪,無腹脹,睡眠尚可,每晚可睡5 h左右。
無鼻塞流涕打噴嚏等表證表現,亦沒有大便異常等里實熱證或太陰虛寒證的表現,考慮其病位主要在半表半里。患者雙眼累、脈弦,五官的不適需考慮少陽證的可能;患者同時有難入睡、易醒、煩躁等陽明氣分熱的表現,考慮少陽陽明合病;同時患者間有心悸,考慮夾有痰飲,方選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因患者大便正常,故方中去大黃。二診患者睡眠有所改善,但仍有心悸、頭暈,考慮痰飲較重,予加澤瀉利水祛痰飲。
關于失眠,中醫古籍很早就有所記載,如《靈樞·大惑論》中記載:“黃帝曰:病而不得臥者,何其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入于陰,常留于陽,留于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蹺盛,不得入于陰則陰氣盛,故目不暝矣”《素問·口問》記載:“陽氣盡,陰氣盛,則目暝;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類證治載·不寐》中提及“陽氣自動而靜,則寐;陰氣自靜而之動,則寤;不寐者,病在陽不交陰也”。因此,中醫認為陽不入陰乃失眠的根本病機。而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可疏通氣機,條達陰陽,使陽入于陰,從而治療失眠。柴胡加龍骨牡蠣湯為小柴胡湯的變方,其中柴胡味苦平,性微寒,氣輕而升浮,味苦而降泄,能條達上下,宣通內外,疏達半表半里之機,使陰陽條達、郁滯疏解,為邪入少陽、樞機不利之主藥;黃芩苦寒性降,《神農本草經》謂其治“諸熱,尤以泄三焦之邪熱為長,則可使三焦通暢,氣道通行[10]。龍骨、牡蠣潛陽入陰、重鎮安神。桂枝走心經,行心血,溫血脈,交通心腎,同時也是定悸要藥。諸藥合用,既有宣暢樞機,和解少陽,疏肝理氣,助厥陰之氣條達,不郁不結之功,又有寧心安神,潛陽入陰之效,服之得以安然入睡。近年來,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在治療失眠方面的臨床應用取得了切實的良效,潘雪等[11]、張蓉等[12]、葉曉縈等[13]的臨床研究均證實了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加減治療失眠療效顯著。同時,很多基礎研究也有了更加明確的治療依據[14-16],且相對于西藥的安眠藥,中藥湯劑不良反應少,是更好的選擇。
4 柴胡陷胸湯治療胸部不適案
郭某,男,70歲。2020年12月11日就診。主訴:反復胸部不適1個月余。患者1個月余前無明顯誘因感胸部不適,無胸痛,伴泛酸,噯氣,惡心感。既往甲亢病史,現穩定,服甲巰咪唑片10 mg,每日2次。曾在廣州市南沙區第一人民醫院新墾分院其他醫生處就診3次,患者拒絕檢查,診斷:反流性食管炎?胸肋關節炎?每次均予抑酸護胃,促胃腸動力和中成藥通血管止痛等治療,用藥后癥狀可稍好轉但次日又會反復。于是至門診就診。刻診:胸部不適感,范圍為全胸,脹悶感,心悸,口干口苦,少許惡心感,已無泛酸噯氣,二便正常。舌暗紅,苔黃稍膩,脈弦。中醫診斷:胸痹,證型:少陽陽明合病。治以柴胡陷胸湯加減:柴胡12 g,黃芩10 g,法半夏18 g,生石膏30 g,大棗10 g,甘草9 g,黨參20 g,茵陳30 g,瓜蔞20 g,黃連6 g,枳實12 g,桂枝20 g(以上中藥均為顆粒劑)。溫水200 ml沖服,每日1次,共3劑。患者服藥后癥狀明顯好轉。12月18日因筆者休息,患者在其他醫生處開了2劑上方鞏固療效。2021年1月15日于門診開甲亢藥物,追問服藥效果,患者稱服中藥后癥狀消失,至今無反復。
無鼻塞流涕打噴嚏等表證表現,亦沒有大便異常等里實熱證或太陰虛寒證的表現,自覺整個胸前區的脹悶不適,考慮病位在半表半里。嶺南經方大家黃仕沛在其《經方亦步亦趨錄》中曾記載:“全胸部的不適屬柴胡證”。該患者同時伴有心悸、惡心感,考慮夾有痰濕;口干口苦,考慮陽明熱證;結合舌脈考慮少陽陽明合病,治以柴胡陷胸湯和解少陽、清陽明痰熱。
柴胡陷胸湯是由《傷寒論》小柴胡湯和小陷胸湯兩方化裁而成,而柴胡陷胸湯出于何時、何書,未曾詳考,陶節庵《傷寒六書篡要辨疑·卷之一》在探討大、小柴胡湯證時云:“若按之心胸雖滿悶不痛,尚為在表,未入乎腑,乃邪氣填乎胸中,小柴胡加枳桔以治其悶,如未效,本方對小陷胸,一服如神”,此即柴胡陷胸湯意。此方兼備二方之長,具有和解兼開降之效,能泄能開,能降能通,具有和解少陽、疏肝理氣、清熱化痰、寬胸散結的功效。程丑夫認為“少陽在表里之間,氣機出入橫逆失常,需條達少陽樞機”,運用小柴胡湯加減治療胸痹[17]。何秀山按“栝蔞(仁)……善滌胸中垢膩,具開膈達膜之專攻,故為少陽結胸之良方,歷試則驗”。何廉臣按“小陷胸湯加枳實,善能疏氣解結,本為寬胸開結之良劑”。 小陷胸湯對治療證屬少陽陽明合病,痰熱互結在心胸的疾病具有良效。農朝雷[18]治療冠心病證屬痰熱內郁、心脈阻塞,應用柴胡陷胸湯加減癥狀緩解明顯;梅國強[19]治療一例萎縮性胃炎、十二指腸球部潰瘍疤痕、充血性糜爛性胃竇炎、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證屬痰熱中阻、少陽經脈不利,8年病史,應用柴胡陷胸湯加減調理7周,癥狀消失;王海博等[20]應用柴胡陷胸湯加減治療膽源性胰腺炎證屬痰熱互結、膽氣不舒,獲得明顯效果。
中醫藥的應用至今有五千多年歷史,是中華民族長期與疾病斗爭的經驗總結,是中華燦爛文化中的瑰寶。在西方醫學發達的今天,中醫中藥仍發揮著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在治療效果方面比西醫更有優勢。而《傷寒雜病論》是中醫四大經典古籍之一,其六經辨證體系科學,無所不包,若正確辨證,依證施方,融會貫通,完全可以在基層臨床的常見病、多發病中獲得良效。應多讀經典,多學經方,為基層的中醫藥事業發展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