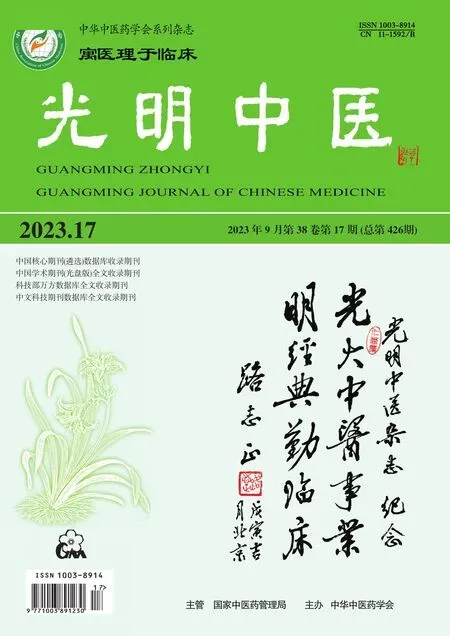中西醫治療原發性三叉神經痛研究進展
王 瑩 王德亮 王 志 熊 暉△
三叉神經痛(Trigeminal neuralgia,TN)是一種臨床常見神經性疾病,起止突然,可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2種。流行病學研究發現,TN的發病率在0.03%~0.3%,平均每年2.7~12.6萬人發病,發病率隨年齡增長而增加[1-3]。TN可在任何年齡發病,其終生患病率在0.16%~0.3%[2,4]。TN對患者心理健康影響極大,患者常伴有焦慮、抑郁、睡眠質量低下等表現。原發性三叉神經痛(Priminary trigeminal neuralgia,PTN)尚無明確病因,但患者人數占TN患者總人數的14%~20%[4]。針對這一問題,本文總結出中西醫治療原發性三叉神經痛相關研究進展,以期為今后臨床治療提供參考。
1 病因
1.1 西醫病因目前普遍認為其病因為神經血管沖突(NVC)導致三叉神經感覺根脫髓鞘[4]。基于上述理論,利用高分辨光纖跟蹤技術檢測TN患者三叉神經白質完整性,可提高對PTN發病機制的理解[5]。深入研究發現中樞端末梢釋放的P物質(SP)與痛覺傳遞有關,降鈣素基因相關肽(CGRP)是向中樞神經系統傳遞痛覺及產生痛覺過敏的必需物質,β-內啡肽可減少或阻斷疼痛信號傳遞,SP、CGRP、β-內啡肽是反映三叉神經疼痛程度的重要指標[6-8]。近年來研究發現,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SE)可作為神經元損傷標志物[9]。最新研究發現血清中NSE水平與三叉神經損傷程度呈正相關,表明TN發病機制與神經元損傷有關[10]。
1.2 中醫病因PTN在中醫屬于“頭痛、面痛”范疇。《證治準繩》記載:“患鼻額間痛或麻痹不仁……連口唇、頰車,發際皆痛……足陽明經受風毒,傳入經絡,血凝滯而不行”,指出此病為風邪作祟累及陽明而發病。又寫道“累歲患頰車痛……如針刺火灼,不可手觸”。此2則醫案詳細記載了“面痛”典型癥狀。風邪侵襲人體,易傷人體上部,侵犯肌表。風邪上擾頭面,則出現“頭痛”“面痛”等癥狀。“蓋諸陽之會,皆在于面……暴痛多實,久痛多虛”(《證治準繩·雜痛》)。風邪侵犯經絡,導致氣血運行不暢,血凝滯而不行,不通則痛。若延誤病情,錯失治療時機,氣血陰陽俱損,面部經脈失于濡養,不榮則痛。
2 治療
2.1 西醫治療
2.1.1 藥物治療卡馬西平(Carbamazepine,CBZ)為抗癲癇藥物的一種,是目前治療PTN臨床一線用藥。給藥后達到有效濃度時能阻滯Na+離子通道,降低細胞興奮性達到緩解疼痛的目的[11]。研究發現,CBZ初始有效率在88.3%,但長期服用或血藥濃度過高可能會引起中樞神經系統、血液或淋巴系統異常,還可能導致皮疹、水鈉潴留或心血管系統疾病等不良反應[11]。奧卡西平(Oxcarbazepine,OCZ)為CBZ的衍生物,藥效與CBZ相似或稍強。給藥后可穩定極度興奮的神經元,從而阻止病灶放電的擴布[11]。不良反應雖較CBZ輕,但仍會引起頭暈、頭痛、多器官過敏等反應。苯妥英鈉為治療PTN二線用藥,給藥后短時間內很快就出現耐受,過量給藥導致血清藥效濃度大幅度增加并產生嚴重毒性,引起精神錯亂、不可逆的小腦功能障礙等。拉莫三嗪是一種Na+阻滯劑和谷氨酸拮抗劑,主要用于CBZ耐藥或不耐受患者,部分患者用藥后會產生運動障礙、記憶力減退等不良反應。
2.1.2 手術治療微血管減壓術(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MVD):1966年Gannetta首次提出MVD的概念,并用顯微神經外科方法治療PTN。顯微鏡下隔離責任血管以減除壓迫消除疼痛來源,術后血清NSE值顯著降低[10]。當硬膜內血管穿透三叉神經根時會增加解壓難度,通過聚四氟乙烯包裹物夾層減壓責任動脈,犧牲、包裹減壓或不處理責任靜脈,疼痛緩解率可達到100%[12]。MVD術后常見的并發癥有腦脊液漏、顱內感染甚至死亡。術前圍手術期評分可作為預測MVD術后結果的有效工具。部分患者可能對潛在的風險排斥手術,但隨著技術革新,整體有效率仍在不斷提升,病死率呈下降趨勢,高齡、兒童患者也可以選擇MVD治療。部分患者MVD術后仍有疼痛,Komatsu等[13]在內鏡下對弓狀小腦上動脈壓迫的三叉神經行“兩步轉位術”,為PTN的治療提供了簡單、可靠的操作方法。術前準確建模或分割或可視化三叉神經及其周圍血管對手術規劃具有重要意義。射頻電凝選擇性損毀術(Radio frequency thermocoagulation,RFT):RFT主要通過使用電極針經皮穿刺進入卵圓孔后,用射頻加熱方法,選擇性的損壞三叉神經痛覺纖維,相對保留觸覺纖維。卵圓孔位于顱中窩內,有下頜神經通過,前方為圓孔后外側為棘孔,旁臨破裂孔頸內動脈在此入顱。卵圓孔入路有效率最高,較高溫度的射頻電極復發率較低,RFT有效率與病灶影響范圍直接相關,明確診斷、精準定位引起面部疼痛的分支是提高手術成功率、減少并發癥的關鍵。隨著DSA、CT導航、立體定向導航等技術的進步,RFT術后并發癥發生率降低。經皮穿刺球囊壓迫(Percutaneous balloon compression,PBC):研究發現,PBC術后NSE值顯著升高,PBC通過穿刺針經皮穿刺卵圓孔后植入球囊導管,膨脹的球囊壓迫神經損傷引起疼痛的纖維,最理想結果為實現“梨形”球囊視覺[10]。研究顯示PBC治療121例術后復發TN總有效率高達94%,術后1年隨訪調查發現僅有4.1%的患者復發,與術前相比患者術后抑郁、焦慮、睡眠狀況等癥狀顯著改善[14]。PBC術后常有感覺減退、咀嚼肌無力等并發癥。研究發現瞬目反射試驗可評估PBC術后三叉神經損傷程度,從而判斷患者預后[15]。伽馬刀(Gamma knife radiosurgery,GKRS):與其他外科手術相比,GKRS是創傷最小、不良作用最少的手術,但GKRS術后起效緩慢,部分患者術后仍需服用藥物緩解。研究顯示,GKRS術后初始成功率為80%~90%,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疼痛又會復發,疼痛緩解時間與靶點定位、照射劑量、照射時間息息相關。明確最佳的靶區定位和放射劑量,可能使GKRS術后效果達到MVD術后水平[16]。
2.2 中醫治療
2.2.1 中藥治療柴碧芳等[17]將PTN患者辨證分為胃火上攻證、肝火上炎證、風寒襲表證、氣滯血瘀證并對證給予中藥治療。3個月后隨訪發現中藥治療PTN有效率為47.6%,無不良反應發生。治療后并未完全治愈的患者疼痛發作頻度較治療前明顯降低,疼痛評級、中醫證候積分等指標也隨之減小。單純使用中藥湯劑治療PTN療效雖不顯著,但無不良反應,值得臨床研究推廣。
2.2.2 針刺療法針刺為中醫外治法的一種,其鎮痛作用顯著,幾乎沒有不良反應。與藥物或手術相比針刺臨床療效更好,治療費用、不良作用遠低于其他2種治療方式[18]。通過針刺面部腧穴或扳機點得氣后行針以調整氣機、疏通氣血。統計學研究顯示針刺扳機點可釋放應激蛋白(SP)、β-內啡肽、5-羥色胺等鎮痛物質,迅速激活下行抑制系統,提高扳機點痛閾值,從而減少疼痛發作次數并提高治愈率[19]。李崖雪等[8]深刺下關穴配合燒山火手法可降低SP、降鈣素基因相關肽(CGRP)含量、增加β-內啡肽含量,從而降低疼痛發作頻次、減輕疼痛程度。
2.2.3 針刺及聯合療法針刺聯合電針:電針作為中醫學與現代技術結合療法,治療PTN效果顯著且安全性高。其治療PTN選穴標準尚不統一,臨床醫生在認識該病的基礎上結合自身臨床實踐制定治療方案,電針參數、時間長短等因素會影響臨床療效[20]。研究發現電針可降低SP含量、升高β-內啡肽含量進而減少疼痛介質釋放從而緩解PTN[7]。閆禹竹等[21]對PTN患者深刺下關聯合耳穴電針治療后,患者疼痛、不適感及不良情緒明顯減輕。針刺聯合中藥:馮閱紅[22]將PTN患者針刺后留針30 min,2次/周,再給予桃仁、紅花、金銀花、連翹、板藍根、大青葉、川芎、石決明等中藥水煎服,1劑/d,2次/d,10 d為1個療程,3個療程后總有效率高達93.02%,遠高于對照組。與單一使用中藥或針刺治療相比,中藥聯合針刺治療PTN效果最佳[17]。中藥和針刺雖存在內服和外治之分,但針藥本體,協同調和氣血經絡,提高臨床療效。針刺聯合穴位注射:馮趙慧子等[23]常規針刺后,留針30 min,1 d/次。再抽取甲鈷胺注射液1 ml、2%利多卡因2 ml穴位注射,2 d/次,4周為1個療程。1個療程后總有效率為97.22%,VAS 評分、疼痛發作頻率、發作持續時間均低于CBZ對照組。針刺聯合穴位注射治療PTN能使藥物直達病灶,短時間內迅速起效。
3 總結
查閱近年來中西醫治療TN相關文獻,藥物治療PTN初始有效率較高,但長期服藥帶來的不良作用甚至遠大于疼痛帶給患者的困擾。藥物不能有效控制疼痛的患者可選擇手術治療,但開放性手術術后并發癥難以避免甚至危及生命。近年來中醫藥的普及推廣,針灸、中藥等治療方法逐漸進入人們視野,雖幾乎沒有不良反應,但單一療法效果不佳,短期內很難緩解患者癥狀。因此,筆者認為,可積極開拓中西醫聯合治療新思路,通過研究PTN發病的分子機制,尋找新分子、細胞靶點,通過中西醫聯合療法調節機體內P物質、CGRP、β-內啡肽等分子水平從而有效緩解患者疼痛,提高臨床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