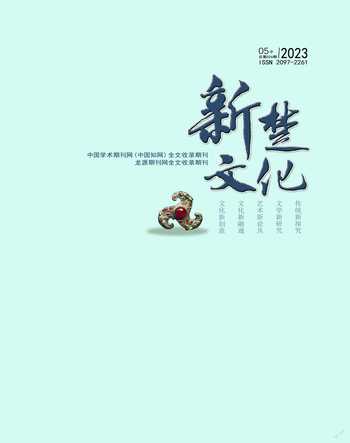非遺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價值與路徑研究
【摘要】布依戲是布依族的特色戲劇,是我國公認的十八種少數民族劇種之一,是我國少數民族戲曲的瑰寶。布依戲至乾隆年間已較為完善,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文化底蘊與藝術底蘊。布依戲的產生和發展體現了民族之間的交融與共生,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發揮了建設共有精神家園、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本文通過探究布依戲當代傳承與發展的路徑,考察其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價值與作用,力求從非遺傳承與發展的角度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時代課題進行解讀。
【關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非物質文化遺產;布依戲
【中圖分類號】J8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14-0052-04
2006年,布依戲正式被我國納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布依戲運用布依族本民族語言進行單語演唱或和漢語進行雙語演唱,通過演員在舞臺上的肢體動作、音樂等表現形式在舞臺呈現出來,凝聚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藝術意蘊,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以及重要的文化價值、藝術價值、歷史價值。正確認識當代布依戲的價值和地位,不僅關系到布依戲的可持續發展,而且有利于挖掘文化旅游資源,實現傳統文化的“活態”創新。
一、布依戲的發展歷程
(一)新中國成立前布依戲的發展情況
布依戲的發展與布依族人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深受人們喜愛。布依戲布包含了民間歌謠、民間故事、舞蹈、文學等要素,在當地又被稱之為“土戲”,用布依語來說是“谷藝”,它是在布依板凳戲、八音坐談戲、布依地戲的基礎上,經過不斷發展、融合逐漸形成的這種表演形式。論其起源具體尚待考究,但據相關的史料記載,大概起源于清朝乾隆時期,《布依族簡史》記載:“在清朝乾隆年間(公元1736-1795年),冊亨州同的秧壩和普安州判(今興義)的巴結,開始編演布依戲,以后推廣其它地區。”[1]距今已有幾百年的歷史。
然而,布依戲的發展看似平和,實則命運多舛。清同治、光緒年間布依戲初步形成,到了乾隆年間,朝廷為了社會穩定與發展大力發揚戲曲藝術,因此我國的戲曲藝術在此期間形成了一次發展高潮。“乾隆十年(1745年),冊亨秧壩開始編演布依戲,之后興義巴結與冊亨乃言、者術、八達、保和等布依戲班紛紛組建。”[2]在此之后,這些搭建的班子就開始了民間演出。“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廣西壯劇戲師黃永貴帶秧白壯戲班到冊亨八達、乃言、板壩等地演出,并交流傳藝。特別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鹽運使在廣西納勞做壽,除集中了當地壯劇戲班外,還邀請了包括云南壯劇、沙戲和貴州布依戲班等共13個,搭起三個高臺,進行了六天六夜的演出活動,觀眾達數千人之多。”[3]此時的布依戲相較之前更加完善,并且形成了自身特色,深受布依族人的喜愛。
民國時期,戰亂頻繁,軍閥割據,布依戲的發展遭受巨大打擊。“1929至1949年,軍閥混戰,地主之間的械斗頻繁,帝國主義的侵略,布依族地區人民生活困苦,布依戲在發展高峰期被迫中斷,停止一切活動。”[4]社會的不穩定導致了布依戲的演員另謀出路,傳承幾乎斷層,同時人們也無過多心力來觀看布依戲,導致“布依戲”幾乎陷入深淵。
(二)新中國成立后布依戲的發展情況
新中國成立之后,布依戲又重新得到發展。20世紀50年代后,中國共產黨對藝術的發展采取“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重視民族文化發展與建設,因此布依戲的發展呈現出繁榮景象。從1953年到1966年,布依戲多個戲班多次進行公演、慰問演出,1956年10月,興義布依戲與冊享布依戲分別以《一女嫁多夫》和《玉堂春》獲獎。
“文革”時期,民族藝術受到影響,布依戲也受到了波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政府鼓勵發展民族民間文藝,“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92年我國市場經濟確立前的這一時期,是冊亨布依戲發展歷史上最興旺的階段”[1]。在此期間,布依戲的整體發展呈現繁榮的狀況。到了現在,我國邁入了新時代,國家重視對鄉村文化的建設,并且鼓勵民族文藝發展,布依戲得到重視,2006年,布依戲成為我國第一批被納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戲曲,更多人因此了解到這種戲曲。
隨著網絡逐漸發達,各種休閑方式令人應接不暇。特別是年輕人群體比較傾向于各種“快餐式文化”,而像布依戲這種傳統戲曲則很難吸引大批觀眾前來觀看。同時,許多布依戲的演員由于年齡較大,又難以找到適合的接班人,可進行表演的演員越來越少,很多劇目逐漸消失,很多表演細節與技巧再也無法看到,使得布依戲的發展面臨著種種危機。
二、布依戲的發展現狀
(一)布依戲劇目的發展現狀
布依戲歷史悠久,編戲的故事來源也眾多。可以按照故事來源將其分類,第一類來源于漢族,以古代歷史故事編寫成劇,此類劇目也被稱之為“正戲”,也可稱之為“移植劇目”。如《轅門斬子》《玉堂春》《包公案》等這些比較著名的歷史故事編寫而成;第二類則帶有布依族的民族色彩,一直以布依族語言來傳唱表演,主要以布依族的民間故事為來源編寫而成,此類劇目被稱之為“雜戲”,較之于“正戲”更顯自由,依靠口口相傳,沒有唱本,如《一女嫁多夫》《王三打鳥》等,以小故事為主;第三類是新編劇,也是以布依族的民間傳說和故事為來源,增加了一些近現代元素,更加新穎,如《趕會》《窮姑爺》《三月三》等,此類劇目也可以與第二類劇目合并在一起,同屬民族劇目;第四類是響應黨的號召而編寫的劇,此類劇目被稱之為“現代劇”,如《光榮應征》《兄妹學文化》等劇目,注重于響應黨的號召、黨的政策,加強民族團結,表現出了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的幸福生活。
1.移植劇目
布依族是一個擅于吸收漢族等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隨著水陸運的開通和商業往來,許多外來文化逐漸走進布依族的生活之中,把一些如“楊家將”“三國”等歷史故事改編成劇,并將這些改編的劇“布依化”。在表演時,唱詞用漢族的語言,旁白采用布依族本民族的語言,表演模式非常獨特。我國著名的歷史故事不計其數,給此類劇目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并以文字劇本的形式流傳下來,所以劇目也偏多,在布依戲劇目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移植劇目以漢族古代歷史故事為依據,進行雙語演出,而且帶有一定的布依族民族特色,使得更多人能夠看懂、聽懂,身臨其境地欣賞布依戲的移植劇目。但移植劇目的發展同樣曲折,乾隆時期,布依族隨著與外界的交流,移植劇目逐漸有了雛形,并不斷發展完善,也得到了其他民族的喜歡。而民國時期,軍閥混戰,一些作品遺失。雖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得到一些改善,但因為各種原因,還是有很多作唱本、劇目被損壞且無法恢復,造成了很多移植劇目的消失。在社會主義新時期,政府重視布依戲的發展與傳承,并將之納入我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但仍有一些移植劇目還是消失了,很是惋惜。
2.民族劇目
民族劇目是布依族本土出現的一種劇目,以攤儀故事、“摩公”的經咒、古歌和民間傳說、故事等為來源,包括了傳統的民族劇目和新編劇目。民族劇目在布依族人們生活中具有很強的代入感,反映了布依族的民間文藝審美觀念,可以稱得上是布依戲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劇目。
民族劇目的傳承相較于移植劇目更加艱難,移植劇目有唱本等進行傳承,即使遭到了毀壞,但仍有一部分保存了下來。但由于布依族沒有本民族的文字,傳承都依賴于演員口口相傳。民國時期,戰亂頻繁,少有人看戲,一部分演員為了生存而放棄了對布依戲的表演,轉行做其他行業,這就使得這種依靠口口相傳的民族劇目傳承出現問題,很多民族劇目遺失。雖然此后布依戲得到恢復重建,開始正常演出,但對于民族劇目來說,恢復之途仍是艱難。
3.現代劇目
現代劇目相較于前兩類劇目的傳承較為完善。現代劇目是新中國成立之后,歌頌祖國,反映布依族人民的社會主義好風氣的劇目,表演時不僅人物形象生動,而且帶有社會主義的積極的進步思想,廣受好評,表演語言在布依族地區為布依語,在漢族地區翻譯成漢語,靈活多變,受眾群體較多。但隨著現代社會的到來,由于人們審美觀念的改變等一些因素,也呈現出低落的狀態。
(二)布依戲表演的發展現狀
1.行當
布依戲發展至今,已形成了較為成熟的行當,各種角色應有盡有,初具“三旦七生”的局面。所謂“三旦七生”是按一定的特征進行劃分,如“旦”一般為女性,老旦是老年婦女;小旦是未婚姑娘和中年婦女,已婚的青年女子也可是小旦;武旦是會一些武藝的女子。“生”一般是男性,文生是知書達理的青年甚至中年男子;小生是樣貌端正的青年、中年男子;大王一般是脾氣不好,甚至相貌丑陋、會一些武功的山大王的男子;小丑是指浪蕩風流的公子,小偷、壞財主、乞丐等也屬于此列,小丑行與其他行不同,主要是詼諧幽默,活躍氛圍;老生是指年齡大的男子,一般是六十歲以上;差官是指官差,身穿官服的一般都可列入其中;武生是指會一些武功的青年、中年男子。
2.步法
布依戲的步法特點鮮明,是由“踩八卦”的步法和“老摩公”的步法為基礎,發展之中融合了布依族的舞獅和“攤舞”的一些動作,從而形成了這種獨具特色的步法。旦角走的是小三角步、緊腿慢步橫移,還有搖擺的高低步,小生、差官中的文官一般走的是三角步,大王走的四方步,武將走的是馬弓步,小丑角在表演中一般起到逗趣的作用,所以三步一跳一轉身,走的是猴步或玩耍步。
布依戲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諺語,“文搖扇,武揮刀”,此藝諺表現出了文武戲角色們表演的特點,表演文戲時,生角一般右手拿著扇子,旦角則左手拿著帕子;表演武戲時,拿著刀、槍、棍、棒進行舞動表演。表演時,舞臺調度是對等相同的,一人進行獨舞,二人進行對舞,三人則對等起舞,人數更多時,則變換位置進行對舞,錯雜有序,觀感更加強烈。
3.武打
布依戲的武打擁有很多的技巧和特點。在武打行當中,如“擋丁”“擋巧”,都是布依戲表演中不斷發展傳承,從而總結下來的“武打”技巧。“擋丁”簡單來說就是打斗中一演員用武器掠過另一演員的頭上,被掠過的演員在掠過時低下頭;“擋巧”就是一方演員用武器扎向另一方演員的腿,被扎的演員用兵器抵擋。除了上述兩種武打技巧,還有“打四門”“上擋下叉”“扎槍”等成熟的武打技巧,這些技巧不僅避免了演員進行打斗表演時受傷,而且令觀眾耳目一新,烘托了打斗氛圍。一些戲隊在武打中,增加了其他類型的武術元素,如棍術、拳術,增加了武打的類型和套路。
三、布依戲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提升民族凝聚力、增強文化認同感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5],并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黨章。布依戲是布依族創造的少數民族傳統文藝的精髓所在,在清朝就得到了官府和商賈的支持;建國之后,隨著“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推行,布依戲更是得到了支持與發展。無論何時,其作品曲目都堅持著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一基本國情,作品中無不展現出維護祖國統一與民族團結;其次,布依戲的發展完善體現出了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經濟上相互交流,形成了“各族一家親”這一看法與觀點;布依戲中采用的歷史典故創作作品,深受人民喜愛,不僅體現了各族人民相互尊重、欣賞、學習的態度,更是體現了各族人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從現代劇目就可看出,布依戲的作品深刻體現出對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我國政府針對少數民族地區提出的一系列民族政策的擁護。傳承布依戲,不僅有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增強文化認同感,更有利于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充分發揮思想的引領作用,在思想上加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以此促進行動上的認同[6]。
(二)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布依族與漢族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布依戲的產生、發展與完善即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實寫照。從移植劇目來講,移植劇目是由于民族之間通商交流交往的過程中產生,隨著盤江水運、陸運的開通和商業往來,許多的外來文化逐漸走進布依族的生活之中。布依戲的班子以漢族的歷史故事為來源從而進行創作,如《穆桂英》《三國》《薛仁貴征東》,都是古典名著和一些膾炙人口的故事,創作出的作品深受人們喜愛,促進了布依族人民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其次從民族劇目來講,同樣體現出了民族間的交往、交融、交流,布依戲的民族劇目是本土產生,但也與漢族密不可分,如《八月十五鬧花燈》這一民族劇目,借鑒了漢族的“八月十五鬧花燈”這一習俗,而創作出這一經典作品;現代劇目則更體現出了兩族人民交往交融,作品內容皆是布依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的幸福生活的真實寫照,如《光榮應征》,熱切地響應了黨和國家的號召。綜合來看,布依戲的產生與漢族是密不可分的,表現出了兩族人民的內在相通性和互動性,而這種相通與互動,促進了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時在彼此交往交流交融中推動著、保護著、傳承著中華民族共有文化遺產。
四、結語
綜上所述,布依戲是我國民族文化瑰寶之一,作為非物質文化,如何使其“活化”展現、創新發展,是當前重點研究方向。保護、傳承與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發揮了重要的價值與作用,更能讓中華民族寶貴的物質精神財富在時代發展中歷久彌新,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匯聚磅礴力量。
參考文獻:
[1]張合胤.冊亨布依戲[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3:8-12.
[2]謝建輝.布依戲發展歷史述略[J].戲劇之家,2018(14):20-21+33.
[3]馮景林.天籟之音——布依族曲藝戲劇文集[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170.
[4]劉玲玲.貴州布依戲研究[D].北京:中央音樂學院,2011.
[4]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0.
[5]黃守斌.城鎮化背景下冊亨布依戲的生存探究[J].興義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22(04):8-12.
作者簡介:
單天宜(1997-),女,滿族,河北承德人,西藏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