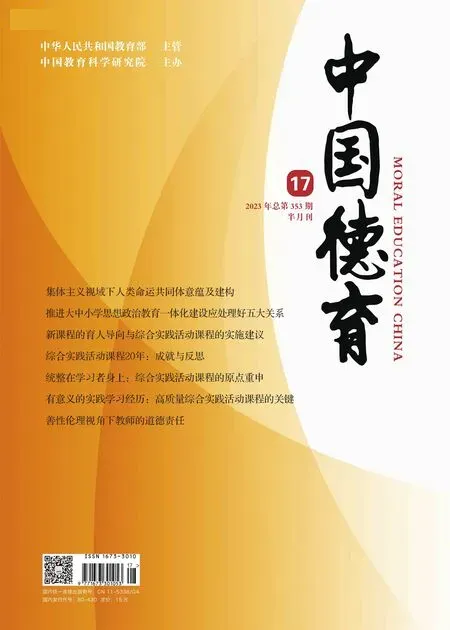善性倫理視角下教師的道德責任*
于智
黨的二十大提出,要培養高素質教師隊伍。高素質的教師意味著教師要具有獨特的育人能力,強烈的責任意識、履責能力及實踐能力等等。同時,一系列與教師相關的政策文件的發布與實施,也明確強調了教師責任的獨特價值和教師履責的重要意義。馬克思指出:“所有道德規范中,責任是個人的道德信念與社會的道德要求結合得最緊密的,也是包含著最多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強制力。”[1]因此,教師履責的過程既是教師“教書育人”“立德樹人”的過程,又是體現教師承擔道德責任的過程。教師對道德責任的履責和盡責可以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道德思想、價值觀念,促成學生行為修養的形成,進而可以快速推進國家公民道德的建設。
育有德之人,需有德之師,德性之源起于善也。善性倫理表示倫理以善為價值尺度,善是個體道德價值的基礎,“善”的理念可以促使人們生成道德動機,做出踐履道德責任的行為。所以教師對道德責任的踐履、對道德價值的追求等皆由“善”而起。“善”也是教師對道德責任的承擔、履行的邏輯起點,可從專業之善、情感之善和實踐之善三個結構方面提升教師的道德責任。
一、教師道德責任的“善”性結構
從古至今,“善”一直是倫理學研究的核心范疇。在古希臘思想家蘇格拉底的善性倫理觀中,“善是一切行為的目的,是最高的道德價值”[2]。柏拉圖認為,“善是每個靈魂都在追求并可以為之做任何事,善也是所有東西所追求的最高目標”[3]。亞里士多德認為,“善是人類的興盛及幸福,要將其付諸實踐”。在中國,“善”始終被認為是有德之人具有的品質,只有有德之人才可以得到民心和天下。儒家的性本善論也認為,人的四端——仁義禮智皆由“善”而發,即人所具有的道德、責任及其義務,本源于人性之“善”。孔子以“善”為基,提出君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以“善”為念,提出“大丈夫”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于是,“善”被認為既是內在的品質,又是外在的道德規范要求;既是一種理性認知,又是一種情感反應態度,是個體知與行的統一。如今“善”也滲透到道德規范體系中,成為各行各業的道德規范與職業精神的基本內容。“人的善總是在于責任”[4],具有“善”品性的人會承擔其所選擇行為所帶來的相應的道德責任。所以在“善”的理念影響下,教師道德責任也具有了獨特的善性特質。
教師道德責任的承擔、踐履來源于教師自身的善,即知善、欲善和行善。若對應于教師的道德責任中,則呈現出專業之善、情感之善和實踐之善的結構特征。教師道德責任的專業之善意味著教師對道德責任的踐履不僅要依靠教師的道德觀念、道德意念,更是要建立在教師德育發展專業化的基礎之上和教師專業道德知識系統的支持之上。
“教師所學習和掌握的專業倫理知識可以激發教師道德行為。”[5]因此,當代教師道德責任的履行與實現需要其具有較為專業的德育知識支持和理性道德反思等,從而確保教師在專業之善的特質下掌握必要德育理論知識,形成正確責任認知,提高直接德育能力,進而做出正確道德選擇和德育行為。
教師道德責任的情感之善意味著教師自身所具有的道德責任情感,“是教師對教師職業所指向的責任對象、所應該擔負的責任、教師實際的履責行為或經歷的責任事件及其結果產生的內心體驗和態度,包括愛、成就感、愧疚感等內心體驗”[6]。教師作為教育主體,在復雜現實的教育教學情境中,無法僅僅依靠外部規約或約定俗成的統一倫理規則去面對和解決專業生活中的道德挑戰,反而更需要依賴于其自身主動、獨立、源源不斷地由內而外地迸發“善”的熱烈情感,使教師自己建立一個對教師自我來說相對穩定的道德信念或準則,從而在此信念或準則下堅定自我,保持正義,避免陷入盲目、空洞與浮華。
教師道德責任的實踐之善意味著教師道德責任的踐履需要教師在教育活動中通過其專業化實踐在目的論意義上完整履行道德責任,實現育人價值,與此同時,在道德責任履行過程中將專業之善轉化為實踐之善。教師由承擔道德責任到履行道德責任的過程中需要將掌握的專業知識、擁有的育人熱情以及內心的良善,有力、高效地外化為教師的善行,并“能夠基于善的理念進行價值判斷并做出‘應該’或‘應當’的行為”[7]。總之,“教師需要有意識和明顯地帶著承諾和決心應用于他們的工作場景之中”[8]。
二、教師道德責任履行的實踐偏離
(一)教師德育專業能力的弱化形成的“平庸之困”,影響責任的踐履
有學者提出:“教師道德品性與專業能力會影響到教師主動履行道德責任的意愿和履行道德責任所能達到的程度。”[9]所以教師德育專業能力是影響教師道德責任履行的重要因素。然而在現實中,教師德育專業能力逐漸被弱化。教師在教育活動中更關注的是自己該怎樣提高學生的成績,忽視甚至缺少教師必需的德育意識。與此同時,教師也缺少有關德育方面的專業知能。由于大部分教師并不是專門的德育教師,他們往往沒有經過專門的德育培訓,工作之余也忽視自身道德專業性知識的學習,從而弱化了其道德教育的能力,同時也轉讓了自身道德教育的權利。此外,由于教師工作內容的復雜性與繁冗性,不僅要履行道德責任,還要在課堂內外處理教學以外的任務,有可能是應對學校及上層領導的工作檢查,有可能是因為職稱評定要填寫各種表格等。繁冗瑣碎事情及各種教學要求常常使教師應接不暇,因而無法全神貫注、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對道德責任的踐履,從而大大降低了履責效率與質量,破壞了道德責任的完整度,導致教師踐履責任時越發趨向“普羅化”。長此以往,教師身陷“平庸之困”。
(二)教師道德責任感淡化產生的“倦怠之慮”,阻礙責任的履行
情感是一個主動建構的過程,責任感是人們內心對責任履行所蘊含的情感態度、信念堅守和理想堅持等一體化融合的精神品性。而教師道德責任感的建構與形成是他們對自身責任履行是否感到滿意、是否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產生的態度體驗,是教師對責任活動的獨特心理感受,可以反映出教師對道德責任價值的認可程度。教師對道德責任的認識越深刻,自我價值的認同就會越高,越會產生積極情感,進而產生令人精神愉悅、工作熱情高漲等正向作用。但是,現代社會在工具理性的主導下,往往把教師關愛學生、投身教育事業等更多地當作一項道德準則來加以要求、限定,導致過于強調教師的道德責任而甚少關注他們的道德情緒感受。“學生德育發展不盡如人意”“教學工作開展不順利”, 以及社會各界對教師的道德高期待等使教師承擔著其他行業無法想象的道德壓力。長久下來,教師極易開始質疑自身的專業身份和工作專業性,進而形成職業道德價值感失落等心理,產生焦慮、憤怒、委屈等消極情緒。同時,學校里的各種行政事務或者學校規定的各種評比、檢查活動等,往往消耗掉教師大量的精力,也常常成為教師“缺席”德育工作的理由。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教師常常以不同方式表達出自己的“心累”與“勞心”。
此外,在理性主義干預下,部分教師將道德責任的履行與自我利益相掛鉤,他們的責任意識、責任情感體現在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傳授學生知識技能,提高學生的成績和能力,從而使自身獲得更高效益。對自身利益的過度計算使他們逐漸成為“理性經濟人”,更為關注由自身外在行為而引發的利益得失,反而忽視了個體內在實質性價值需求,造成教師道德責任感逐漸“物化”,從根本上拋棄了教師自我的情感訴求。因此,在履責時,部分教師表現更多的是選擇性應付或消極應對,面對學生的歡喜或悲傷,他們可能無動于衷乃至表現出厭煩疲倦,將自己隱藏在幕后,只管依據冷冰冰的規則教條做到點到為止,從而嚴重影響到“育人”職責的履行。
(三)教師“遵章守則”形成的“被動之患”,影響履責的實現
教師美其名曰的“遵章守則”,其遵循與服從的僅是“合乎外部給定的責任”,認為“規規矩矩地遵守外部規則就是教師負責任、盡責任的優良表現”。這種被動性的責任意識導致一些教師甘愿成為“差不多教師”,即他們中規中矩,既不逾越底線,又不渴望臻美,遵守著“不遲到、不早退”“安分守己”等外部表層性規章制度要求,堅持著“相安無事”的保守思想,遵循著“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保持著“不爭不搶”的生存狀態,成為奉行普遍化標準和規則的“老實人”。他們用“平庸的‘遵章守則’之善代替了‘追求卓越’之善”[10]。客觀而言,他們并不是人們口中的“壞老師”,但也絕不是“好老師”。事實上,從教師教書育人的本質職責和倫理內涵來看,教師道德責任的履行應是出于自身主動對“善”境界的追求,對內在師道準則尊重與理解的行為。“以善先人者謂之教”,“唯有自律的實踐準則最能夠表達自主的道德人的自由本性”[11]。可見,教師道德責任的實踐之善并不是簡單和表淺的對準則的遵守,對規范的習得,也不是單純認知意識的具備,而是要落實于內生知責、主動履責、積極盡責中的行為實踐。
三、教師道德責任的提升路徑
(一)識善之本,喚醒自我道德責任
教師道德責任的踐履離不開知善、欲善與行善。然而如今我們的知善只是對善的一般性認識,欲善只是情感的單向認同與迸發,行善只是以外在的行為規范約束自己[12],那么,教師如何在教育教學中真正做到“善”,教師如何做才能達到“善”本身?只能由教師個體獨立面對并回答。也就是說,教師主體要真正認識到“教師之善”的本質,方可做到道德責任的自覺踐履。教師主體所面對的“善”,本質是不需要外部規約和評價而道德,而是在復雜現實情境中依賴其主體性的道德判斷與自我選擇,這是需要教師發揮自身強大的主體性功能才能實現的善。然而,現實卻是“大多數人用表面的服從取代了德性”[13]。尼采曾善意地提醒:“人們往往將‘善’當作給定的,事實性的,超越于一切質問之外,然而,倘若在‘善’中亦有某種退化癥狀,同時且有某種危險,某種誘惑,某種毒害,某種麻醉,通過它,當前之生活竟是以未來為代價的呢?”[14]虛偽的主動性很多時候會傷害甚至泯滅德性,甚至成為道德責任踐履的最大障礙。因此,教師必須自我內部喚醒,認識到真正的“善”,從“善”本質出發,擺脫外部施加的規約和對于標準的簡單依賴,確立自我內在的價值原則和道德信念,形成自我道德判斷和選擇的智慧,并以此而道德地行動,履行應然的道德責任。
(二)揚善抑惡,激發自身道德責任情感
“人類社會產生后,隨著道德規范、標準和準則的出現以及各種具體道德情境的刺激,人們逐漸產生并積累了道德生活中的各種情緒體驗,最終形成道德情感。”[15]如何激發教師自身道德責任情感呢?一是基于內部對善的認識而進行的道德反思與個體自覺;二是借助于外部建立健全教師責任機制。道德責任情感是教師對道德責任自覺認同和自愿選擇的前提,缺乏良好道德責任情感的教師,就算能夠依據教育道德原則與規范行事,也必然會出現一些“失善”行為。因此,教師主體需在整體認識善的基礎上,反思個體道德的內在實質性價值需求,需要注意的是主體真正的內在需求,而非外在職業責任的簡單遵循或是社會規約下的道德紅線。只有教師主體做到內部的道德反思與個體認同,才會自覺向善、追善,將道德價值的實現視為自我價值的完善。此外,道德的教師需要道德的制度來成就,教師之善需要制度之善給予保障,外部教師責任機制的建立健全有助于教師激發自身道德責任情感,進而推動教師踐履道德責任,實現完整的“善”。因此,一方面要加強對教師在日常教育生活中道德責任踐履的督導,制定嚴格的教師責任制度以約束不當行為的發生,進一步完善教師責任履行準則、教師責任監督機制和教師問責機制,嚴格實行教師退出制度;另一方面,要重視教師道德情感的訴求,及時滿足教師情感需求,對于盡職盡責的教師實施重獎,增加激勵作用。
(三)以善為基,構建專業支持體系
教師道德責任的踐履即教師之善的現實達成,需要專業意義上的支持體系:一是源于教師自我的專業知能,二是源于外部的專業倫理關系。教師的專業知能便是將善轉變為現實的道德責任的最大依憑。教師在教育教學過程中,需要將教師專業道德置于真實的教育情境中進行理解和定義,并將其與教師的專業知識、專業能力相融合,進行整體把握與分析、全面指導和養成,達到將師德與知識和技能相融合的“整體論”目的,從而突破以往的將師德與知識和能力相割裂的“分離論”師德觀,培育出自覺踐履道德責任、實現“善”本質的完整的“好教師”。教育于多種關系中建立并實現,教師若想在善的基礎上實現道德責任需兼顧各方關系與需求,并贏得各種力量的支持與協作。因此,也需要在多元倫理關系中形成對教師的善,即對教師內在的和所擔負的道德責任的完整理解,重視在師生關系中得到尊重信任,在家校關系中獲得理解支持,在同儕關系中建立認同協作,多方共建道德責任專業支持體系。在支持體系中,教師需贏得“公認”,但這并不意味著是單向性地妥協與迎合,而是基于教師專業倫理原則與道德能力之下的溝通、協調與解決。這種多方共建道德責任支持體系所需的道德素養被美國學者稱為“合作領導力師德”,即努力達成共識、找到互利的解決方式、接受對自己的責任并承擔對他人的責任、保持人際管理方面的韌性、表現出追求卓越的積極熱情和行為。[16]教師通過培養與鍛煉,建成專業的溝通與合作的能力,形成基于道德責任的有效合作的多方倫理關系,營造支持性的積極工作氛圍,推動教師主體做到知善之本,識善之美,行善之樂,在更完整的意義上成為一個有著高尚道德,并能真正踐履道德責任的“好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