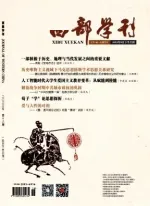努斯鮑姆能力理論及其對家庭正義的發(fā)展
苗雨佳
(黑龍江大學(xué),哈爾濱 150080)
家庭通常作為一個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團(tuán)體,很多時候人們只會聚焦于整體而忽略家庭之中的個人,能力進(jìn)路始終關(guān)注一個問題,即每一個人實際上能夠做什么和能夠成為什么。它尋求一種與人類尊嚴(yán)相匹配的直覺式生活觀念。最為關(guān)鍵的是,能力理論將每一個人看作目的而非手段,人作為人而存在而非作為他者目的的工具而存在。
一、能力理論概述
能力理論(Capability),又稱多元能力理論(Capabilities Approach)。起初是與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的人類發(fā)展報告相聯(lián)系的,能力作為一種比較指標(biāo)出現(xiàn)是由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設(shè)計提出,作為一種經(jīng)濟(jì)項目的關(guān)鍵概念使用,確立一種比較生活品質(zhì)基礎(chǔ)的基本能力框架。努斯鮑姆(1)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女,美國哲學(xué)家。1947年5月6日出生于美國紐約,1969年畢業(yè)于紐約大學(xué),1972年和1975年在哈佛大學(xué)分別獲得碩士和博士學(xué)位。努斯鮑姆認(rèn)為,人類對人的尊嚴(yán)和婦女權(quán)利的共識足以克服文化差異的限制。她的理論強(qiáng)調(diào)文化多元主義教育。2012年5月16日,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評委會宣布,本年度該獎項社會科學(xué)獎由美國哲學(xué)家瑪莎·努斯鮑姆獲得。評委會在公告中說,努斯鮑姆憑借其在人文科學(xué)、法律、政治哲學(xué)以及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道德觀等方面作出的貢獻(xiàn)贏得了評委會的認(rèn)可,報告還稱贊這位女學(xué)者是“當(dāng)代哲學(xué)界最具創(chuàng)新和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的能力理論在森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發(fā)展,通常是一種復(fù)數(shù)的能力(Capabilities),即衡量一個人的生活品質(zhì)的元素是多種多樣的,它們在性質(zhì)上有所區(qū)分,而不能單一地約分為一種一元化的尺度。
從根本上講,能力理論是一種關(guān)于生活品質(zhì)評估和社會正義理論工作的方法。它始終遵循一個原則,即把每一個人當(dāng)作目的,關(guān)注每一個人可以得到的機(jī)會。
二、從“能力”概念到能力的實現(xiàn)
(一)何為能力
能力理論基于能力概念而建構(gòu),能力一詞實質(zhì)上是對一個人能夠做些什么又能夠成為什么的回答,即“一組(通常而言相互聯(lián)系的)選擇和行動的機(jī)會”[1]18。具體來看,能力包括混合能力(combined capabilities)和內(nèi)在能力(internal capabilities)。混合能力是個人能力與社會環(huán)境的綜合,即一個人在其所生活的環(huán)境中所能得到的或被提供的機(jī)會與自由,混合能力的發(fā)展依賴于社會政治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的發(fā)展。內(nèi)在能力,強(qiáng)調(diào)一種個人狀態(tài)的流變,即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其身體狀況、品行品性、學(xué)識智商等都會隨著經(jīng)歷而變動;換言之,內(nèi)在能力是一種后天訓(xùn)練培育而形成的能力,它區(qū)別于天賦素養(yǎng),教育、家庭、社會環(huán)境的支持顯得尤為重要。因而,要確保每一個人的能力發(fā)展,社會的重要任務(wù)之一就是支持人的內(nèi)在能力的發(fā)展。
努斯鮑姆并沒有明確界定混合能力與內(nèi)在能力的分界線,因為一個人總是要經(jīng)由一些實踐才能夠形成一種內(nèi)在能力,同樣,如果失去了實踐的機(jī)會,這種內(nèi)在能力很有可能會喪失。她認(rèn)為“做出這一區(qū)分是一種認(rèn)知探索,可以用來診斷社會的成就和失敗”[1]17。一個社會培養(yǎng)人們的內(nèi)在能力的途徑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包括家庭內(nèi)部給予的情緒價值和物質(zhì)撫養(yǎng)以及學(xué)校教育資源的支持,但是當(dāng)人們擁有內(nèi)在能力時卻并不一定能夠基于內(nèi)在能力進(jìn)行活動。舉例來說,通過普遍的義務(wù)教育,人們得以擁有針對某一社會事件發(fā)表自己的言論的能力,但實際情況是,由于某些需要,社會往往通過壓制言論來否定人們的自由表達(dá)的能力。另一種情況是,社會政治環(huán)境給予了自由表達(dá)的條件,即一個人擁有其實踐內(nèi)在能力的機(jī)會,但是,這個人自身并沒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而也就無所謂發(fā)揮其內(nèi)在能力。
簡單來講,混合能力是內(nèi)在能力與社會條件的綜合,混合能力的實現(xiàn)關(guān)鍵在于社會的各個領(lǐng)域要基于公民們進(jìn)行自由選擇的有效空間。
內(nèi)在能力和混合能力都區(qū)別于天賦素養(yǎng),而“基本能力”(basic capabilities)是個人固有的內(nèi)在潛能,基本能力使得后期的能力發(fā)展與訓(xùn)練成為可能,它是一種初級的能力并不能直接轉(zhuǎn)換為功能發(fā)揮[1]16。盡管基本能力是一種內(nèi)在潛能,但并非完全不受外界環(huán)境的影響,因為在基本能力的延展和塑造過程中,母親的營養(yǎng)、運氣、經(jīng)歷都會產(chǎn)生作用。因而,基本能力并不意味著說所有人的起點線是統(tǒng)一的,每一個人都應(yīng)當(dāng)獲得相同的最低水平線的混合能力;對于基本能力的認(rèn)知應(yīng)該建立在這一基礎(chǔ)上,即每個人都擁有不同水平的基本能力,基本能力水平較高的人,即天資稟賦更高的人并不應(yīng)該得到更為優(yōu)越的對待。相反,基本能力水平較低的人應(yīng)該獲得更多的幫助,只有這樣才能超越國家政策所設(shè)定的能力底線。例如,如果一個人生來就具有認(rèn)知障礙,那么國家有必要強(qiáng)制進(jìn)行特殊干預(yù)以完成教育。
(二)能力的實現(xiàn)
“運作指一種或多種能力的積極實現(xiàn)。”[1]19如果說能力是手段與途徑,那么運作就是最終目標(biāo);能力的獲取是為了能力的發(fā)揮。如果人們擁有能力,但是沒有發(fā)揮的環(huán)境,那么無論個人的能力有多么完善都是無意義的。
從獲取能力到運用能力這個過程中,始終蘊含著一個重要的前提,即選擇的機(jī)會。一個正在忍受饑餓和一個為了身材而節(jié)食的人在獲取營養(yǎng)的問題上采取了相同的實現(xiàn)手段,即有著相同形式的運作。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個人的能力是相同的:節(jié)食的人擁有獲取食物或者放棄進(jìn)食的選擇機(jī)會,而挨餓的人只能有一種別無選擇的結(jié)果。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以運作這一結(jié)果來判斷能力的獲取,因為運作形式相同的結(jié)果下,人們自身的能力卻不一定相同。努斯鮑姆強(qiáng)調(diào),政治的恰當(dāng)目標(biāo)在于能力而非運作,政府應(yīng)當(dāng)為人類自由的活動留下空間。政府為民眾提供充足的營養(yǎng)、教育資源,但并不意味著政府要強(qiáng)制人們選擇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人們應(yīng)當(dāng)有選擇的自由。但是這將導(dǎo)致一種悖論:當(dāng)人們行使這種選擇自由的權(quán)利進(jìn)而放棄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時,卻與核心能力清單中人們應(yīng)當(dāng)擁有健康的身體這一設(shè)定想違背。因而,努斯鮑姆主張,在某種特殊領(lǐng)域,即事關(guān)人們的尊嚴(yán)和平等對待時,政府必須發(fā)揮強(qiáng)制性作用,不應(yīng)當(dāng)放任民眾進(jìn)行選擇。
三、十項核心能力清單:過一種有尊嚴(yán)的生活的能力門檻
能力理論作為一種有關(guān)社會生活品質(zhì)與公平正義有關(guān)的評估性理論,始終圍繞著一個問題,即社會應(yīng)當(dāng)選擇培育、支持哪些能力以建立一個具有最低限度公正的社會環(huán)境。
努斯鮑姆提出要以人性尊嚴(yán)的理念為基礎(chǔ)確立政治原則。其他有關(guān)能力發(fā)展的所有要素都與之相關(guān),但尊嚴(yán)并非是一個明確的概念而是一種直覺觀念。
人應(yīng)當(dāng)是一個具有尊嚴(yán)的自由的存在者,人始終生活在一個與他人合作互惠并為他人所影響的環(huán)境中,因而“真正的人類生活是完全由實踐理性和社會交往這些人類能力所塑造的生活”[2]59。一個人的認(rèn)知能力不僅僅在動物層面運作,在成長過程中得到適當(dāng)?shù)慕逃约白晕冶磉_(dá)都可以與他人建立有價值的聯(lián)系。努斯鮑姆以馬克思的觀點為基礎(chǔ),認(rèn)為某些功能不僅僅要以動物的方式來發(fā)揮,而是要以真正人類的方式來發(fā)揮。人和動物都需要依靠進(jìn)食獲取營養(yǎng),但與動物不同的是,人的飲食行為蘊含著人與人之間社交的需要,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精神需求,不同于動物。更進(jìn)一步講,真正的人類生活需要更廣泛的自由,如言論自由和結(jié)社自由。
能力進(jìn)路追尋這樣一個社會:在其中每個人都受到應(yīng)有的尊重,并且每個人都有能力過上真正意義的人類生活。能力門檻即衡量一個人真正實現(xiàn)人類生活所需要的最低能力標(biāo)準(zhǔn)。從這個意義上講,能力是針對每一個人的,并非為群體、家庭、國家或其他法人群體尋求的[2]60。
因而,作為人類的共同追求,可以說作為門檻的能力清單是能夠得到廣泛的跨文化共識的。但核心能力清單并非一份完備的正義理論,僅僅是為一個社會構(gòu)建最低能力標(biāo)準(zhǔn)提供一個基本坐標(biāo)。
核心人類可行能力包括以下十個方面[1]25。1.生命。健康正常的老去、死亡。2.健康的身體。能夠擁有良好的健康狀況、充足的營養(yǎng)。3.完整的身體。能夠自由行動,身體不被侵犯,自主的生育權(quán)。4.感知、想象和思考。接受充分教育以及科學(xué)訓(xùn)練,能夠運用感知、想象并思考、說理;自我思考并表達(dá)自我,能夠運用自己的思想自由表達(dá);按照自己的方式追尋生命的終極意義。5.情感。對他人產(chǎn)生情感并能接受他人的關(guān)心與愛,能夠體驗到悲傷、歡樂、渴望以及合理的憤怒。不會因為過度恐懼和焦慮,或者因受到虐待或忽視這類創(chuàng)傷性事件而破壞情感的發(fā)展。6.實踐理性。能形成一種善觀念,能夠?qū)ψ约旱娜松媱澯枰耘行苑此?這需要保護(hù)良心自由)。7.依附。能夠與他人緊密生活在一起,認(rèn)同并關(guān)心他人,參與各種形式的社會互動;能夠想象和同情別人的處境;能夠擁有正義和友愛的能力。8.其他物種。能夠關(guān)懷動物、植物和整個自然界,并與之和諧共處。9.玩耍。能夠歡笑、玩耍、享受娛樂活動。10.控制自身所處的環(huán)境。包括政治環(huán)境和物質(zhì)環(huán)境,擁有自主選擇的權(quán)利。
由能力的基本概念我們可以得出,能力理論始終以個人為導(dǎo)向,確保個人能力的獲得與發(fā)展,首先有個體然后才能推演至團(tuán)體。很多人會說在集體之中個人能力能夠得到更好的發(fā)揮,但是這是有前提的,集體由個人會聚而成,集體的發(fā)展一方面取決于目標(biāo)與定位,另一方面來源于每一個個體能力的會聚。盡管人們總是喜歡講自己歸屬于某一個團(tuán)體,并為該團(tuán)體的榮譽而感到自豪,但這種由精神自豪帶來的滿足感偏好與能力理論對個體的關(guān)注并不沖突。如同在家庭之中,盡管每一個人都會為家族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但同時家庭作為一個同質(zhì)性的單位往往使得家庭成員個人的能力得到忽視,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被淹沒于團(tuán)體之中并非合理。
四、能力理論對家庭正義的發(fā)展
我們時常說有家才有國,國是千萬家,因而,家庭這個國家的基本組織單位,就不再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私人探討,而是國家宏觀上的議題。通常意義上,我們所說的家庭由夫妻及其子女組成,男性與女性在法律意義上結(jié)合形成婚姻關(guān)系,并在此基礎(chǔ)上雙方有可能選擇孕育后代。從這一家庭內(nèi)部的基本結(jié)構(gòu)上來看,家庭正義面臨的重要問題即是性別正義問題。
努斯鮑姆在《尋求有尊嚴(yán)的生活:正義的能力理論》一書開篇中例舉了印度女性瓦莎蒂的故事。她指出,女性在家庭內(nèi)受到明顯的不平等待遇。首先,一個作為妻子的女性,其在家庭內(nèi)部的勞動并不被當(dāng)作一項值得認(rèn)同的勞務(wù)付出,因為家務(wù)活動并不能帶來直觀意義上的工資報酬,對于全家的福利而言,女性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被審判為趨近于零。當(dāng)女性在經(jīng)濟(jì)上不受重視,不被認(rèn)為具有經(jīng)濟(jì)價值,這就進(jìn)一步禁錮了其發(fā)展的可能。其次,作為后代即作為女兒的女性,有可能從出生開始就喪失了獲得生命的機(jī)會。印度部分地區(qū)有權(quán)事先知悉胎兒的性別,出現(xiàn)了大量由于性別選擇問題造成的墮胎情況。即便一個女性順利長大,那么她的成長過程也是不平等的,由于性別歧視和貧窮問題的存在,女性并不能得到良好的生存保障--獲得基本的營養(yǎng)狀況和受教育狀況。由于營養(yǎng)不良,女性沒有辦法擁有健康的身體,因而從體能上會造成男女差異的懸殊,這會進(jìn)一步加劇關(guān)于男女之間差異的惡性循環(huán)。由于女性沒有得到學(xué)習(xí)的機(jī)會,因而就無所謂步入社會、就業(yè)與獨立,她的能力沒有得到妥善的培養(yǎng)與發(fā)展。一位女性從一個人的生命伊始就注定無法擺脫依賴于他人或者說依賴于男性的命運。最后,一位女性在家庭內(nèi)部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并非僅僅是個例,更多的問題在于,家庭之中女性的困境是社會環(huán)境壓迫女性的具體展現(xiàn)。單就家庭暴力問題來說,單純的禁止家庭暴力的法令并非一項整全性的手段。它涉及多個領(lǐng)域內(nèi)政府和社會的選擇:不僅要出臺有關(guān)禁止家暴的法令,還應(yīng)該有關(guān)于家庭暴力的教育項目以及關(guān)于家庭創(chuàng)傷的高品質(zhì)治療和康健,這不僅要關(guān)注生理健康的傷害,更要注重情緒健康的影響,“不少人在家庭之中承受著巨大的恐懼,同時又壓抑著自己的憤怒”[1]6;不僅要有法令的文書政策,還要有執(zhí)法系統(tǒng)的落實;不僅要鼓勵人們選擇進(jìn)入婚姻關(guān)系,組建一個家庭,更要保證婚姻關(guān)系中一個人的“退出選擇”和談判能力,女性應(yīng)該具有選擇進(jìn)入婚姻的權(quán)利,同時也應(yīng)該有自由退出的權(quán)利。我們可以看到,沒有直接的政府行為,經(jīng)濟(jì)增長并不會改善不平等現(xiàn)象,也不會推動家庭正義的落實。
從能力理論的十項核心清單可以看到,能力進(jìn)路始終聚焦于家庭之中的每一個人。家庭結(jié)構(gòu)涉及的人類能力包括:生命、健康、完整的身體、擁有尊嚴(yán)和不受侮辱、結(jié)社自由、情緒健康、有機(jī)會與他人結(jié)成有意義的關(guān)系、政治參與能力、擁有財產(chǎn)和外出就業(yè)的能力、為自己著想并形成生活計劃的能力。無論對于男性還是女性,家庭的組織形態(tài)都會對個人能力產(chǎn)生影響,同時這些能力又彼此相聯(lián)。
從清單的具體內(nèi)容來看,核心能力清單第一、二、三項保證了家庭內(nèi)部成員的生命健康,免于家庭暴力的侵害,并且使得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機(jī)會得到充足營養(yǎng)以保證生長發(fā)育;清單的第五、七項使得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維持一種健康良好的關(guān)系,從家庭之中建立的一種關(guān)于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guān)系為每一位家庭成員走向社會打下了基礎(chǔ);清單的第四項保障了家庭內(nèi)的孩童平等的擁有接受教育的權(quán)利。能力清單保障家庭成員的權(quán)利不受侵害的同時也為家庭成員更好地發(fā)展提供了可能。清單中的第六項,人們對自己的生活進(jìn)行批判性反思,對自己的未來能力進(jìn)行發(fā)展規(guī)劃;清單中的第九項,一方面培育孩童的玩耍能力,另一方面也培養(yǎng)人們舒緩情緒的能力,正向促進(jìn)心理健康以及其他能力的發(fā)展。
五、結(jié)束語
盡管我們可以說各個國家和地區(qū)的人們各有各的生活方式,但無法否認(rèn)的是家庭之中的女性的生活模式在很多方面都呈現(xiàn)出相似性--這是因為女性身份引起的一系列問題與歧視。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身體是同一個身體,我們對物質(zhì)、精神的需求都是一樣的,并不會因為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或者政治環(huán)境而產(chǎn)生全然不同的區(qū)別。
總的來說,能力理論承諾跨文化的正義、平等及權(quán)利規(guī)范,而且對地方特殊性和環(huán)境塑造選擇、信念及偏好的諸種方式也具有敏感性。堅持要融入自身運用的語境與歷史之中,只有在一個具體的環(huán)境下,才能做到真正理解事件發(fā)生的脈絡(luò)和某項政策的意義。“理論的部分實踐價值在于它的抽象性和系統(tǒng)性。”[1]33思想和言論是抽象運用的結(jié)果,我們運用文字構(gòu)建理論,理論的抽象性是未來進(jìn)行實踐的基石。能力門檻觀念實質(zhì)上是對政府提出了一種要求,即關(guān)于公民生活質(zhì)量的一種核心憲法原則。因而能力理論并非追求完全的能力平等,它并非一種整全性的分配正義理論。實質(zhì)上,正是由于能力門檻這一觀念,能力理論可以兼容許多達(dá)到這一最低標(biāo)準(zhǔn)之上的多種不同的分配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