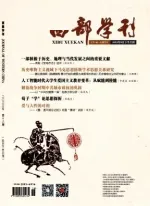從《蕭蕭》到《湘女蕭蕭》:“蕭蕭”故事的版本修改與銀幕呈現
王昭媛 宋 宇
(河北大學 文學院,保定 071002)
《蕭蕭》是沈從文(1)沈從文(1902-1988),男,原名沈岳煥,湖南鳳凰縣人,中國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者。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交界地區。1924年開始進行文學創作,撰寫出版了《蕭蕭》《長河》《邊城》等小說。1931年-1933年在國立青島大學任教,抗戰爆發后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國后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歷史與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國古代服飾研究》。1988年5月10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歲。1929年在中國公學執教期間創作的小說,最初于1930年1月10日發表在《小說月報》第21卷第1號,署名沈從文。后沈從文四易其稿:1936年7月1日發表于《文季月刊》第1卷第2期,7月號,署名沈從文;1936年11月重新修改后,被收入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新與舊》;1957年,面對新的形勢氛圍,小說經沈從文再次修改后被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小說選集》;1983年,經過編校修改,《蕭蕭》被收入廣州市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文集》第六卷。2002年,編輯以1936年11月出版的《新與舊》中的版本為底本,將其收入太原市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全集》第八卷。為閱讀方便,文中將其依次簡稱為初刊本、再刊本、初版本、選集本、文集本和全集本。1986年編劇張弦將小說改編成劇本,由第四代電影導演謝飛(2)謝飛:中國電影導演、編劇、制片人。1942年8月14日出生于陜西省延安市,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1978年,執導個人首部電影《火娃》,從而正式開啟其導演生涯。1986年,執導的劇情片《湘女蕭蕭》獲得第36屆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堂吉訶德獎。1990年,執導的劇情片《本命年》獲得第4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1993年,執導的劇情片《香魂女》獲得第4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1995年,執導的劇情片《黑駿馬》獲得第19屆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2001年,擔任第51屆柏林國際電影節評審團成員。2008年,擔任第32屆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評審團成員。2010年,擔任第4屆亞洲電影大獎評審團成員。2013年,獲得第4屆中國電影導演協會杰出貢獻導演獎。2014年,擔任第8屆FIRST青年電影展評審團主席。2018年,獲得WeLink國際電影節終身成就獎。2019年,獲得第3屆荔枝國際電影節終身榮譽獎。執導,拍攝為電影《湘女蕭蕭》,于1988年在中國大陸上映。
從小說誕生以來,“蕭蕭”的人生故事被不斷改寫,特別是小說被搬上銀幕后,“蕭蕭”故事的創作題旨和敘述方式均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半個多世紀來,“鄉下人”眼中的湘西風景越來越難以自足,現代文明的審視不斷侵入。創作意圖的變化使故事的敘述方式隨之而變,小說初版本多是對“湘西風景”的“現象”還原,接近于客觀的白描敘述,小說的版本修改凸顯了“現代人”的身份介入。到電影中,導演的創作意圖,也就是現代啟蒙話語成為了故事的主導聲音。“鄉下人”與“現代人”這兩種不同視角,促使小說與電影形成了兩種對生命的思考路徑,一個是從情出發而兼顧理,一個則從理出發而注入情。同時,版本的修改與敘述媒介的變化不斷為“蕭蕭”的故事注入新的活力,促使讀者形成了對湘西的多元化的理解和個性化的湘西情結,這成為“蕭蕭”故事能夠長盛不衰,博得眾多讀者喜愛的重要原因。
一、“鄉下人”筆下的湘西世界
1936年沈從文在《習作選集代序》中曾說到:“我實在是個鄉下人……鄉下人永遠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老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1]《從文自傳》中也這樣說到:“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過的蠢事,聽了些平常人不聽過的喊聲,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過的氣味;使我對于城市中人在狹窄庸懦的生活里產生的作人善惡觀念,不能引起多少興味。”[2]58《蕭蕭》中所展現出的湘西世界,實為“鄉下人”眼中的湘西世界。這里的“鄉下人”視角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沈從文以湘西人的視角來看待湘西,二是“鄉下人”的成長經歷使得沈從文“看”的方式有所不同。
首先,“鄉下人”眼中的湘西世界體現在小說的自然環境中。沈從文用散落在敘事中的白描勾勒了一個恬淡自然的鄉村生活圖景,小說中的環境描寫與人物的活動特別是蕭蕭的成長歷程是相互融合的,自然成為孕育蕭蕭的一個重要因素。蕭蕭在“像一株長在園角落不為人注意的蓖麻;大葉大枝,日增茂盛”[3],“又是降霜落雪,又是清明谷雨,都說蕭蕭是大人了”[4]。蕭蕭的成長顯得天然而富有生命力,她是湘西的山水所滋養出的精靈。
自然環境孕育人的成長,人同時也遵從著自然的規則。蕭蕭被花狗引誘而懷孕這一情節是蕭蕭成長的使然,人性欲望的使然,但在沈從文看來,這不僅是在人性發展的維度上對于社會習俗的反抗,同時是對自然規則的另一種順應。在沈從文及湘西的價值觀念中,生育是女性的義務而非權利,蕭蕭的懷孕,既是人為的,也是在履行“自然派定的那份義務”[5]。與此自然倫理相應的,還有一家人對蕭蕭的處置態度。小說的初版本寫到:“這真是了不得的事,一家人皆為這一件事弄亂了”,但是“事情說明白,倒又像不什么要緊,大家反而釋然了”,“丈夫并不愿意蕭蕭去,蕭蕭自己也不愿意去,大家全莫名其妙,像逼到要這樣做,不得不做”[3]。即使在版本修改過程中,對蕭蕭的懲罰被加重為沉潭或發賣。這一細節仍沿用了下來,且選集本中還加上了:“這件事情既經說明白,照鄉下規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緊”,“只是照規矩像逼到要這樣做,不得不做。究竟是誰定的規矩,是周公還是周婆,也沒有人說得清楚”[6]21。選集本在短短的一句話中提到了兩次“規矩”,一個是“鄉下規矩”,另一個顯然代表著封建社會的傳統禮法。兩種“規矩”的交織和碰撞,使小說塑造了一個雜糅了民間樸素觀念與正統儒教的湘西,展現了一種以禮教為表,而根植于生命本位的生存規律。
其次,沈從文以“鄉下人”的眼光看湘西世界,意味著他“看”的方式有所不同。他的“看”和“寫”是對“現象”的還原和再現,如同福樓拜所開啟的“上帝的眼光”。《從文自傳》中寫道:“我永遠不厭倦的是‘看’一切”,“我就是個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象傾心的人。我看一切,卻并不把那個社會價值攙加進去,估定我的愛憎”[2]75。從眼前所見而不是觀念出發,是沈從文感知世界和創造文學的源泉。
正因如此,在《蕭蕭》的初版本中,現象的自由綻放主導著文本,小說中的現象是枝蔓橫生的,其本身就是存在的意義,并不構成情節的鏈條,因此也不直接指向故事的主旨或結局。小說雖然可以概括為描寫了一個鄉下童養媳的悲劇命運,但這種概括是很勉強的,文中描寫了許多與此并不直接相關的“閑筆”,如蕭蕭的夢境:“夢到撿得錢,吃好東西,爬樹,自己變成魚到水中溜扒,或一時仿佛很小很輕,身子飛到天上眾星中……”“天亮了,雖不做夢,卻可以無意中閉眼開眼,看一陣空中黃金顏色變幻無端的葵花”[3],又如一家人乘涼的夏夜:“夏夜光景說來如做夢。坐到院心,揮搖蒲扇,看天上的星同屋角的螢,聽南瓜棚上紡織娘子咯咯咯拖長聲音紡車,禾花風悠悠到臉上,正是讓人在自己方便中說笑話的時候”[3]。這些細節描繪出了蕭蕭日常且具有真實感的生活情態,構成了一種悠遠朦朧的意境。小說雖然蘊藏著沈從文對于落后習俗和湘西現狀的思考,但他卻以平視萬物的心態和不動聲色的旁觀者視角去講述故事,作者的情感和思想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節制,這使得語言所承載的現象本身具有直達文章深層結構的功能,從而產生了“言不盡意”和“意在言外”的效果。在小說的版本修改中,雖然沈從文對文本的介入程度不斷增強,但這種敘事方式一直處于主導地位。
二、“現代人”眼中的湘女故事
沈從文雖然自詡為“鄉下人”,但《蕭蕭》是其離開家鄉六年后創作的作品,此時的他畢竟是一個身處城市中的現代知識分子,不可避免地帶有“現代人”的視角。在電影改編中,城市長大的謝飛導演則完全以現代文明為標桿,形成了現代價值與邊地落后觀念的兩相對照。因此,“蕭蕭”的故事在版本修改與銀幕呈現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現代人”的審視,且這種現代觀念與時代變化密切相關,“蕭蕭”的故事也相應的被賦予了不同的時代內涵。
沈從文的“現代人”視角體現在《蕭蕭》的版本修改過程中。在其四次修改中,最明顯的變化是蕭蕭的身世和結局。關于蕭蕭的身世,在初刊本中,蕭蕭是有母親的,“看到母親傷心哭,眼淚多到豈有此理,這女人她笑”[3]。而從再刊本始,蕭蕭的身世都被改成了從小被寄養到伯父的莊子上,無父無母。沈從文明顯以現代人的身份介入文本,以童養媳為敘事焦點,從故事開頭就賦予了蕭蕭悲劇性的命運。關于蕭蕭的命運,初版本為“蕭蕭當然應當嫁人作二路親了”[3],結局為“到蕭蕭正式同丈夫拜堂,兒子有十歲,已經能看牛,他喊蕭蕭丈夫做大哥,大哥也答應,不生氣”[3]。同樣從再刊本始,蕭蕭的結局都成了沉潭或發賣,并增添了為十二歲的牛兒接親,蕭蕭“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卻在屋前看熱鬧,同十年前抱丈夫一個樣子”[4]的情節。這種改寫強調了蕭蕭的麻木和童養媳命運的重復,是典型的“五四”式的啟蒙話語,包含著魯迅“忠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7]的批判性,使一個靜止自足的湘西被撕開了一道現代文明審視的口子。但聯系上文論述到的,所有版本中都保留著湘西人民的“莫名其妙”和其所信奉的“鄉下規矩”,這一細節帶著為湘西人民開脫的意味,又消解著作者的批判意圖。
選集本是沈從文為適應建國后的道德規范所改寫的,為貼合新的社會環境,作者在結局中改寫了原來的環形結構:當蕭蕭抱著新生的毛毛看新娘子時,她說道:“看看,女學生也來了!明天長大了,我們討個女學生媳婦!”[6]11這預示了童養媳的舊社會將要結束,給予了文本一個開放式的光明結局,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蕭蕭此前懵懂的認知狀態,成為了一個向往“明天”的人。而“明天”一詞在1957年的社會語境中,連接著社會主義式的光明未來,沈從文由此為文本增添了符合時代要求的“現代”內涵。但聯系前文對于女學生的描述:“她們咬人,和作官的一樣,專吃鄉下人,吃人骨頭渣渣也不吐”[6]11,又表現出了敘事者對于女學生態度的前后矛盾。如果說前文代表的是主流聲音對女學生的批判,那結尾處蕭蕭的心聲則暴露出沈從文對新的社會價值的猶疑。
因此,從小說整體來看,有時過于外在的啟蒙意圖與小說的審美意蘊并不相融,顯示出沈從文在自然倫理與現代價值之間的猶疑,也顯示出他對古老湘西在時代中飄搖的焦灼。盡管蕭蕭最終指向的是人性的進步,是民族的改造,但作者卻沒有給出一個堅定的價值判斷與實現路徑。
與小說相比,《湘女蕭蕭》顯現出共通的隱憂與希冀,并給予了確定的價值與路徑。謝飛導演以湘西社會的外來者、現代文明的代表者身份來審視湘西,使其始終處于被改造甚至被摧毀的位置上,并為之提供了一條確切的啟蒙之路。因此,導演以“現代人”的眼光塑造了一個被儒教同化了的湘西世界,以此控訴此種環境下女性的悲慘命運。與小說最大的不同是,電影還講述了其他三位女性的故事:被沉潭的巧秀娘、被遺棄的婆婆及痛失七個子女的婆姨。這些情節如一張大網罩住了蕭蕭未來的多重可能性,暗示著她將逃無可逃:一個比丈夫大十歲的童養媳如若出軌,則有巧秀娘作為前車之鑒,如若能順利與小丈夫圓房,今后也可能如婆婆一樣被遺棄;即便婚姻美滿,邊地殘酷的生存條件是禮教枷鎖之外的另一層寒霜。這很容易讓人想起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魯迅將祥林嫂的悲劇“寫”了出來,而謝飛則將祥林嫂的故事“藏”了起來,《湘女蕭蕭》中蘊含著一個《祝福》中的世界。由此,謝飛實現了他的創作使命--“再造民族靈魂”。
沈從文與謝飛具有相似的“現代人”視角,但從作品風格和敘述方式來看,《蕭蕭》與《湘女蕭蕭》迥然不同,原因不僅在于兩者的“現代人”身份介入程度不同。更在于兩者“看”故事的方式有所不同。
上文提到,沈從文的“看”和“寫”是對“現象”的還原和再現,我國臺灣作家朱天文曾將沈從文的這種觀察視角形象地表述為“天”的眼光[8],這背后是一個像上帝一樣的超然又充滿愛的,細致入微的觀察主體。概而言之,“天”的眼光最大的特點是“遠”,因為足夠遠,才能觀察到散落于各處的紛繁小事,也因為足夠遠,才能不動聲色地將復雜的“現象”組合成一個具有真實感的世界。與沈從文筆下的“現象”無分尊卑相比,謝飛導演則有選擇地“看”。電影的拍攝依靠的是創作團隊理性的思索,情節的銜接與鏡頭的轉換都為導演意圖服務。如果說沈從文講故事的方法像電影的長鏡頭的話,那謝飛導演則將蒙太奇的效果發揮到了極致。蒙太奇的使用讓導演隨時可以介入文本,每一個鏡頭,每一個情節都被納入了故事發展的網絡中,各居其位,一步一步導向主旨,導向結局。與之相應的,導演將鏡頭拉近,再拉近,聚焦于故事的矛盾、高潮與結局,讓觀眾將注意力集中于電影制作者想讓他們看到的東西,而無暇去思考鏡頭外的內容。
《湘女蕭蕭》中蒙太奇的運用鮮明地體現在對電影副線巧秀娘故事的講述中。巧秀娘的故事出自沈從文1946年10月發表的小說《巧秀和冬生》。在原作中,作者營造了由近及遠的幾重世界:置于文章前景的是“我”所描繪的朦朧清冽的雪后圖景和“我”飄渺的意識流動,變動不居的鄉村生活在此意境中緩緩鋪開;隨后,巧秀的出走為平靜的敘述拉開了另一個豁口,從而讓敘述者窺探到了18年前巧秀娘的悲劇,巧秀娘的故事位于敘述的最深處,如夢境般深遠。而在電影中,巧秀娘的悲劇被直接放置于特寫鏡頭下,并與蕭蕭的日常生活并置講述:電影一開頭,蕭蕭與春生間的溫情日常后,鏡頭對準了巧秀娘丈夫的葬禮,特寫鏡頭在蕭蕭與巧秀娘之間來回交替。巧秀娘的第二次出場,再次緊跟蕭蕭看月亮唱童謠的溫情畫面,兩人對話的近距離特寫顯示出巧秀娘對蕭蕭未來的憂慮。蕭蕭懷孕后,電影緊接著上演了喬秀娘被沉潭的情節,鏡頭對男女兩性圍觀者的不同面部表情的特寫,對祭祀儀式和巧秀娘裸體的多次俯拍,造成了強烈的壓迫感。鏡頭語言成為一種強行闖入的統攝性敘事聲音,不由分說地揭露和批判。最后,巧秀娘死去了,但對她的敘述仍沒有結束,她成為一種道德符號,被內化進湘西社會的倫理體系中,又外化為蕭蕭所看的戲劇人物,讓生者不斷感到恐懼與禁錮。通過此種鏡頭語言,電影以“現代人”的視角完成了對“蕭蕭”故事的重新講述。
三、兩種視角下的生命思索
沈從文在1952年赴四川參加土改時,讀《史記》有感而發,談到中國歷史發展的兩條線索--“有情”與“事功”。他說《史記》:“諸書諸表屬事功,諸傳諸記則近于有情。事功為可學,有情則難知!”[9]318。這種“有情”“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別的東西……即必須由痛苦方能成熟積聚的情--這個情即深入體會,深摯的愛,以及透過事功以上的理解與認識”[9]319。《蕭蕭》即是此種“有情”的書寫。
首先,沈從文的“鄉下人”視角為他的“有情”書寫提供了最初的源泉。在鄉下人的眼光中,自然之物給了他發現美的最初的靈感。從山與水,光與色,到有生命的草木蟲魚;從微小生命出現與消逝的瞬間,到江河山川千百年來的流轉,都引起作者的萬千思緒。“自然既極博大,也極殘忍,戰勝一切,孕育眾生,螻蟻,偉人巨匠,一樣在它的懷抱中,和光同塵”[10],作為生命之一種的人,也只是自然之一。沈從文從紛繁復雜的自然中,發現了神秘,發現了美的各種姿態,感受著美與惡的交織,也感受著承載了流動變幻之美的生命。在《美與愛》中,沈從文寫道:“一個人過于愛有生一切時,必因為在一切有生中發現了‘美’,亦即發現了‘神’。必覺得那點光與色,形與線,即足代表一種最高的德性,使人樂于受它的統制,受它的處治”,“生命之最高意義,即此種‘神在生命中’的認識”[11]359。蕭蕭即此種生命之一,在蕭蕭身上,生命的“神性”在于她與生俱來的蓬勃的生命力,在于她與自然天地融為一體的純粹和靈動。蕭蕭的幸與不幸,來自于沈從文對記憶里故鄉的眷戀,對生命“神性”的贊揚與對真實湘西世界的憂慮與哀憫所形成的復雜情感,這形成了獨屬于沈從文的“有情”書寫。
其次,“有情”書寫也是沈從文實現其美育理想的陣地。沈從文在1936年《習作選代序》中寫道:“我知道沒有人把它看成載道作品……先生,你接近我這個作品,也許可以得到一點東西,不拘是什么;或一點憂愁,一點快樂,一點煩惱和惆悵,多少總得到一點點”[1],并說他存心放棄那些想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淚”的讀者。這正符合《蕭蕭》所帶給讀者的印象,并揭示了沈從文對小說創作的另一重追求,那就是以飽含人類深切感情,體現生命最高形式的藝術來凈化和提升國民的靈魂,用一種“愛與美的新宗教”“來煥起更年青一輩做人的熱誠,激發其生命的抽象搜尋,對人類明日未來向上合理的一切設計,都能產生一種崇高莊嚴感情。”[11]362沈從文在多篇文章中也提到對蔡元培“美育代宗教”觀念的崇尚,這種文學主張或者說民族改造理想在小說中的表現便是“抒情”,以情緒來感染以至啟悟讀者,以“有情”的書寫創造對歷史的獨特記錄。
與此種“有情”書寫相比,沈從文與謝飛對“蕭蕭”故事的“現代”審視體現了文學創作的“事功”一面。沈從文的不斷改寫體現出他對“五四”啟蒙精神的回應。謝飛導演面對文革所造成的文化藝術的荒蕪局面和國民靈魂的滿目瘡痍,重拾“五四”精神以對抗現實。相比之下,電影在“事功”的道路上走的更遠。按照此種創作理念,蕭蕭與湘西的自然不再是融洽的,蕭蕭也不再是一個懵懂的少女,導演以現代人的女性觀念塑造了蕭蕭的個體意識。這突出表現在電影對蕭蕭的女性身體和欲望的書寫中,電影“確立了以蕭蕭這個山村少女的性欲的萌動-覺醒-爆發-泯滅為全片的心理活動線”[12],因此濃墨重彩地描寫了蕭蕭和花狗的情愛場景,展現了蕭蕭從被動到主動的過程,因為“這正是她一生中唯一光彩和幸福的時刻。只有在這時候,她才獲得了生命自身所具有的價值,才成為了一個真正的、自由的人”[11]。這種改編直觀化地展現了蕭蕭從孩童成長為成熟的女性,再到泯滅為一個異化者的過程。與沈從文的美育觀念相比,蕭蕭的巨大轉變使得影片更具情感沖擊力,不容分說地向觀眾傳達了必須以現代文明改造湘西社會的價值理念,從而完成了影片所被賦予的教化功能。
四、結束語
沈從文在1961年創作的《抽象的抒情》中這樣總結他的文學創作動力:“生命在發展中,變化是常態,矛盾是常態,毀滅是常態。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轉化為文字,為形象,為音符,為節奏,可望將生命某一種形式,某一種狀態,凝固下來,形成生命另外一種存在和延續,通過長長的時間,通過遙遙的空間,讓另外一時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無有阻隔”[13]。時至今日,《蕭蕭》已走過了將近一百年,仍被眾多讀者津津樂道,實現了沈從文的文學理想。《蕭蕭》不僅還原了沈從文心中的湘西,也讓每個讀者心里形成了個性化的湘西印象。特別是從小說到電影的改編,讓古老的故事重新煥發活力的同時,也帶給了當代讀者/觀影者更多的思考:湘西究竟是一個自足的原始民間群落,還是一個被儒教同化的封建社會,如何看待鄉土社會與現代文明的關系,何以是“自然、健康、優美”的人性?相信在不同時代和地域下的讀者心中,每個人都有一座屬于自己的“希臘小廟”(3)“希臘小廟”:“希臘小廟”一詞出自沈叢文的《習作選集代序》,最直接的理解就是,他的人生、他的文章,不為實物的利益所羈絆,構建的是美麗人性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