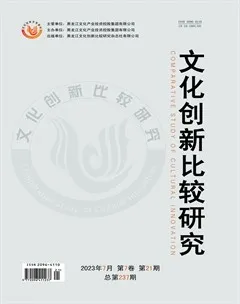“有被X到”結構的構式化演變研究
羅美君,王雪晴
(1.湘潭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湖南湘潭 411105;2.中國傳媒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24)
學界關于“有+NP”的研究起步很早,最初開始 于對“有”字句的研究。關于“有+VP”結構的研究較多集中在對“有”和“VP”性質的探討上,但對“有被X到”結構式構式化歷程還鮮見研究,本文將分析結構式的源形結構,理清結構式構式化的路徑,以求加深對構式“有被X到”的認識。
“有被X到”結構的歷時構式化演變可以追溯到殷商時期,從最初的“有+V/VP”結構,到“有+無被動標記的V/VP”結構,再到“有+有被動標記的V/VP”結構,又經歷了隱退、復現階段,最終演變成一個形義配對的“有被X到”構式,從歷時的角度來看,“有被X到”結構的構式化演變分為以下兩個階段:“有被V到”結構的形成階段;“有被X到”結構的構式化階段。
1 “有被V到”結構的形成
在殷商甲骨文中,同時存在“有+NP”和“有+VP”結構,如:
例(1):辛巳卜,我貞:我有事? (《甲骨文合集》)
例(2):王福勿有伐。 (《甲骨文合集》)
例(1)是“有+NP”結構,“有”表示“確實存在NP”;例(2)是“有+VP”結構,這里“有”無實際意義,主要起強調存在、標記信息焦點的作用,信息焦點就是“有”后面的“VP”。在先秦漢語中,“有+VP”結構內部也存在差異,有些“VP”指稱化了,有些卻沒有,如:
例(3):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 (《左傳》)
例(4):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韓非子》)
例(3)、例(4)畫線部分都屬于“有+VP”結構。 其中,例(3)中的“有”意義較為實在,不可省略,“VP”指稱化了,“豐、省”自指為與“豐、省”相關的事物。但例(4)中的“有”意義較虛,只起強調作用,可以省略,“VP”沒有指稱化,這與甲骨文中的“有+VP”結構一脈相承。蘭碧仙將先秦漢語中的“有+VP”分成了兩類[1]。 一是“VP”發生了自指或轉指的“有1+VP”,“VP”實際上名物化了,因此“有1”還是實義動詞,表“存在”義;二是“VP”沒有指稱化,仍表示動作行為的“有2+VP”,“有2”是虛詞,意義虛化為“強調存在”,能標記焦點、強調動作行為。
在現代漢語中,上述3種結構都存在,“有+NP”結構如“有錢、有機會”,“有1+V/VP”結構如“有個交代、有些喜歡”,“有2+V/VP”結構如“有去過北京、有復習功課”。“有被X到”結構(包括“有被V到”)的“被X到”是謂詞性成分,且結合緊密可視為“VP”,“被X到”沒有指稱化,因此“有被X到”結構屬于“有2+V/VP”結構,如:
例(5):看到這一段感覺自己好像有被冒犯到,聽的耳朵都要起繭子的話……
例(5)畫線部分“有被冒犯到”的“有”強調“被冒犯到”這個行為,“有”與“被冒犯到”結合緊密,且沒有自指或轉指,在句中仍然表示動作行為本身,“有”意義較虛,仍表動作行為本身。我們研究的“有被X到”結構,是“有2+V/VP”結構的子構式,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時代的甲骨文。
“有2”與無被動標記的“V/VP”結合,此時“有2”仍然起到強調存在、標記重點信息的作用,而此時“V/VP”開始含有被動意義,如:
例(6):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
例(6)中“至于犬馬,皆能有養”意思是“但是狗馬都能夠得到飼養”[2],即“但是狗馬都能夠被飼養”,這里的“犬馬”就是受事,句子是無標記的被動句,“有”強調動詞“養”,“有2+V/VP”中的“V/VP”都是無被動標記的“V/VP”,其被動語義的析出依賴于語境提供的信息。
隨著隱性的被動語義被顯性的被動標記“被”所承繼,“有2”開始與有被動標記的“VP”結合,同時無被動標記的“VP”還是可以與“有2”結合。此時兩種情況共存,“有2”的意義和功能都沒有變化,還是表“強調存在”,用來凸顯“有”后的已然焦點信息,例如:
例(7):想念之心,無日有忘。 (《樸通事》)
例(8):芍藥已付春夢遠,楊花有被東風誤。(夏完淳《滿江紅·惆悵》)
例(7)整句的意思是“思念的心,一天都沒有忘記”,“想念之心”是受事,整個句子是無被動標記的被動句;例(8)“楊花有被東風誤”中,“有2”與有被動標記的“V/VP”結合,出現了“有2+被 V/VP”結構,被動語義由顯性的被動標記“被”字來表示,“有”表強調,凸顯“東風誤楊花”這件事已經完成。
明代開始,“有2+被V/VP”結構形成,同時期“到”也融入了被字句,出現了“有2被V到”表層結構形式。元明時期,有很多“到”與被字句結合的例子,如:
例(9):卻說陳武與龐德大戰,后面又無應兵,被龐德趕到峪口,樹林叢密。(羅貫中《三國演義》)
例(10):興終是膽寒,抵敵不住,望澗中而逃;被越吉趕到,一鐵錘打來……(羅貫中《三國演義》)
例(9)的畫線部分的“到”后出現了處所賓語,“到”帶有“位移義”,表示“到達某地”。而例(10)“到”后沒有處所賓語,“到”的“位移義”虛化,表示“動作行為達到某種結果”,“越吉趕關興”這個行為有了結果。從例(9)、例(10)可知,明代被字句中的“到”語義發生了虛化,即從表位移結點虛化為表動作結果,“到”后的處所賓語可以省略。
既然“有2+被V”結構在明代已形成,同時虛化了的“到”也與被字結構組合起來,為什么直到現代漢語中才出現“有2+被V+到”結構形式呢?我們窮盡檢索語料庫,發現明代以后“有2+被V”結構就沒有用例。我們認為阻礙“有2被V到”結構形成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構件“有2”在主流語言中隱退;第二,構件“到”的虛化用法使用頻率不高。首先,構件表完成體的“有2”與專職的體標記完成助詞“了”發生競爭,“有2”在競爭中處于弱勢[3],在主流語言中隱退。筆者認為“有2”隱退的主要原因是,表完成的“了”字自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形成,宋代定型成為完成體標記,在元明時期發展成熟[4]。宋元明時期,“有2”與“了”都可以表示完成。相比于“有2”,“了”表完成體有兩個優勢。其一,就語義關系來看,“了”與完成體的意義相關度更高。“有2”表完成體是借助了動詞“有”的“存在義”,動作行為存在,往往就可以推導出動作行為完成了。而“了”作為動詞時表“完了、終了”義,與完成體的表達有很大的適配性,相關性更高,無需推導就可以表示動作完成。其二,“了”的虛化程度更高,句法特征更單一,信息處理更容易。“有2+V/VP”結構除了表示完成體,還可以表示未然或將然以及表示強調。而“了”只表示實現了的“完成”語法意義,沒有其他的附加意義和功能。表達相同的語義,越簡單、越不需再次分析的結構,越容易被識別,越容易被人們采用,這符合語言的經濟原則。其次,關于構件“到”的虛化用法使用頻率不高。“到”在先秦時期是在句子中獨立做謂語,之后逐漸有了做補語的用法,元明時期“表示動作行為有了結果”的用法開始萌芽。但是,直到近代這種虛化用法才普遍使用[5]。由于“表動作行為結果”的虛化用法不夠普遍,加上“有2”在明代后隱退,“到”融入“有2+被 V”結構的可能性就很小,很難形成“有2被V到”結構式。
“有2被V到”結構的形成雖然被暫時阻礙,但是隨著“有2”在現代漢語中復興,“到”的虛化用法得到高頻使用,“有2被V到”結構式還是在現代漢語中形成了。首先,受到方言接觸和英漢對譯等語言外部因素的影響;其次,語言類推的作用。在東南沿海的粵方言、閩方言中“有2”還保有很強的生命力。主流語言與方言通過人們的交流溝通互相影響,此外還有外來語的促進作用。在漢英翻譯的過程中,含有“have”的句子大多被直譯成“有”,“have”作為實義動詞時被翻譯成“有+NP”結構,而疑問句中的助動詞“have”會被譯為“有沒有+VP”,用“have”回答時可譯為“有2+VP”。如:
例(11):—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publishing a book?你有沒有想過出本書?
—Yes,I have。有想過。(《網上情緣》寧夏文化音像出版社)
事實上,在正反問這一特殊的語法環境中,漢語普通話完成體的表達由不對稱向對稱發展。“有2+V/VP”結構最初就作為完成體的肯定表達在現代漢語中復興[6]。在言語交際中,人們往往借助標記或是重音來突出信息重點,而“有2”結構具有凸顯焦點信息的語用功能,契合了人們的表達需要,促使“有2”在現代漢語中被重新激活。再有,構件“到”的虛化用法已經高頻使用,有利于“有2+被V+到”結構表層形式的形成:
例(12):小懶舒舒服服地睡了個懶覺,雖然中間有被人吵到。
例(12)畫線部分的“有被人吵到”中的“有2”強調動作行為的存在,“到”表示動作有了某種結果。這樣的結構首先在網絡環境中大量使用,隨著大眾傳媒的影響力,“有被V到”結構被大量使用。
2 “有被X到”結構的凝固
“有2被V到”結構形成之后又進一步發展凝固。在結構上,進入此結構式的動詞“V”擴展到心理活動動詞;在意義上,結構式“受到處置”的客觀被動義弱化,主觀評價義增強。構件“有2”還是起到標記焦點信息,強調動作行為的存在的作用,“到”表示“動作行為有了某種結果”。如:
例(13):“第一季的那個小姑娘的最后一幕是真的嚇到我了,講道理我是那種看鬼片都不怎么害怕的(人)。”
“我當時看到這里也有被嚇到。”
例(14):雖然是很老套的劇情,但是有被感動到。
例(13)畫線部分“有被嚇到”中的“嚇”是動作動詞,結構式的主語“我”是受事,此時動作的施事是隱含的“NP”——“那個小姑娘的最后一幕”,在這里構式“受到處置”的被動義還很明顯,動作動詞“嚇”對“我”產生影響,表達了說話者對動作“嚇”的客觀感受。而例(14)中,畫線部分“有被感動到”中的“感動”既可以看成是心理活動動詞,也可以看成是形容詞。當“感動”作心理動詞時,雖然相比于動作動詞其動作性減弱,對隱性受事的影響減弱,“說話人”受到處置的語義也減弱,但是從整個句義上看,我們可以理解為“劇情感動說話人”,此時“說話人”還可以看成是受事。當“感動”理解成形容詞時,從句法層面上看,形容詞只用來說明、描述事物的性狀或特征,起修飾或限制事物的作用,沒有支配能力,不能帶受事賓語,此時“說話人”不能理解成受事。整個句子凸顯隱性說話者的主觀感受,表達說話者對劇情的一種心理主觀評價。形容詞既可以描述事物的性質和狀態,亦可以表達主觀的評價,體現說話人對識解對象、識解方式的主觀感受[7]。當V是心理類動詞時,臨界構式“有2被V(心理類動詞)到”具有了既能表達客觀感受又能表達主觀評價的語用功能。當構件“X”由形容詞填充時,結構式“有被X到”發生進一步構式化演變。構式化是指“新形式—新意義”配對的形成過程,它在構式網絡中形成新的類型節點,這些節點具有新的句法或形態,以及要編碼新的意義[8]。Goldberg一書中對構式做了進一步解釋:構式是業已習得的形式和意義或者話語功能的配對[9]。當具有描述、修飾功能且帶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詞可以用在“有被V到”結構式中動詞V位置上時,該結構式具有評價性語義特征同時被動意義已弱化,我們認為此時“有2被X(形容詞)到”結構的“新形式”與“新意義”(新語用功能)配對,“有2被X (形容詞)到”已是一個構式,如:
例(15):張子楓小時候就那么溫柔可愛,好懂事啊,真的有被甜到。
例(15)畫線部分“有被甜到”的“X”都是形容詞,“有被甜到”的“甜”是說話者對“小時候的張子楓”的主觀感受,而整個短語表達說話者對“張子楓”的一種主觀評價,這種評價側重表達說話者的心理感受,此時“被”動意義弱化。由例(15)可以看出,“有2被A到”已經是一個具有[+評價]語義特征的構式,評價義不能從“有2被A到”結構的構成成分進行簡單的推導。
“有2被X到”構式變項X擴展到名詞、英文詞、網絡流行詞(雖然網絡流行詞也包括名詞、數詞、英文單詞等,但是我們論文的目的是要強調語言的類別,如官方語言、外來用語和網絡語言等,故而把名詞、英文詞以及網絡流行詞作為平行結構,看成變項A可以擴展的語類)等,構式的能產性、圖示性又進一步加強,構式的構式義可以概括為“言者利用X表達對事件(事物)的主觀評價”,如:
例(16):朱亞文出席活動,寸頭造型真的是有被帥到,不愧是行走的荷爾蒙,表示有被A到。
例(16)畫線部分中的變項“X”是英文單詞“alpha”的簡寫“A”。即使不具有[+評價]語義特征的詞也能進入此構式,具有了表達說話者主觀評價的語義,我們認為“有被V到”結構已經完全完成構式化演變。
從“有被X到”結構構式化過程來看,語言現象的演變會受到整個語言系統的影響,完成體標記“了”的主流化使用、語言接觸、外來語的影響以及交際表達的需要都會阻礙或促進語言的演變。正如雷冬平指出構式不是生來如此,其語義也同樣不是生來如此,它不是一種自在存在,而是一種自為存在的意義,它的存在有其形成過程[10]。“有被X到”結構構式化演變也是一種自為存在的過程,有其特殊的演變路徑。
3 結束語
從歷時角度來看,“有被X到”結構的構式化演變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有被V到”結構的形成。源形結構“有2+V/VP”自殷商時期就已有用例,但直至明代才出現“有2+有被動標記的V/VP”結構,與此同時,“到”發生虛化,可用于表達“動作行為達到某種結果”的語義。但此時與“有2”有相同語法功能和語義特征的完成體標記“了”成為主流語言,直到21世紀初,“有被V到”結構在普通話中才得以形成并得到迅速發展。第二個階段是“有被X到”結構構式化階段。當“有2被X到”結構變項X擴展到形容詞、名詞、英文詞、網絡流行語時,并且整個結構式表達“言者利用X表達對事件(事物)的主觀評價”構式義,“有被X到”構式形成。構式的能產性、整體性和不可推導性都進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