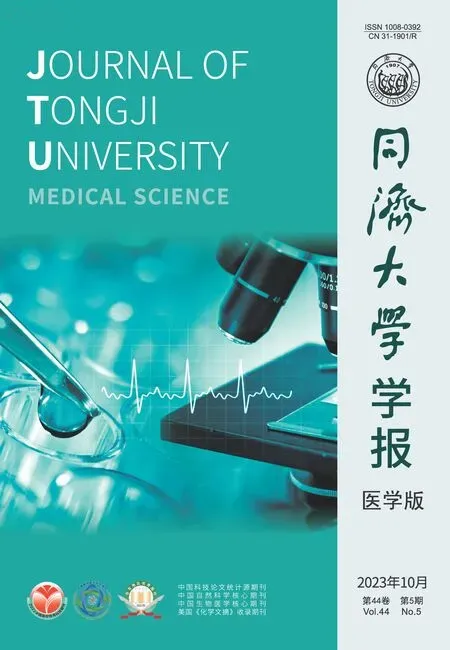父母體重狀況與子代超重/肥胖風險的關聯性分析
游麗娟, 褚陳娟, 喬 荊, 李愛芬
(1. 同濟大學醫學院,上海 200082; 2.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上海兒童醫學中心兒內科,上海 200127; 3. 上海市浦東新區機場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兒保科,上海 201202; 4. 上海市浦東新區川沙華夏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兒保科,上海 201299; 5. 上海市東方醫院吉安醫院兒科,江西 吉安 343000)
兒童肥胖在全球流行,2016年我國9個城市7歲以下兒童單純性肥胖流行現狀及其影響因素調查顯示,7歲以下兒童超重和肥胖總檢出率為8.4%、4.2%[1],2018年中國7個城市學齡前兒童全國調查,結果顯示兒童超重和肥胖的檢出率分別為10.9%和7.9%[2],超重肥胖檢出率呈快速上升趨勢,超重肥胖在我國是個嚴峻的社會公共問題。肥胖父母和兒童聚集在一起很常見,很多研究都明確父母對兒童體重狀態產生重要影響,兒童肥胖的風險在很大程度上受父母體重狀況的影響[3]。一項薈萃研究結果顯示父母體重與兒童體重狀態關聯強度因兒童性別和年齡、親子對類型而不同[4],但目前結論不一致,該關聯可能受父母社會經濟地位影響,故本研究調整相關混雜因素和父母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平均收入和父母的教育水平作為父母社會經濟地位指標)后,探索父母體重狀況與子代超重/肥胖風險的關聯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1.1.1 調查對象 入組標準: 上海市浦東新區2021年3—6月在讀幼兒園兒童,年齡范圍3-7歲,排除標準: (1) 患有嚴重基礎疾病(先天性心臟病、先天性代謝性疾病、先天性遺傳病、惡性腫瘤等);(2) 慢性疾病急性發作期;(3) 患有急性感染性疾病;(4) 因內分泌和代謝病因素引起的肥胖;(5) 有長期服用抗癲癇藥物、糖皮質激素藥物史;(6) 父母患有高血壓、糖尿病、腫瘤等慢性病。征求家長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倫理編號: [2018]體臨審第(010)號)。
1.1.2 抽樣方法 以社區為單位,抽取上海市浦東新區具有地域代表性的跨越外、中、內環3個社區的17家幼兒園,分別為陸家嘴街道(內環代表),川沙華夏社區(中環代表)、機場社區(外環代表)的3個區域。

1.1.4 分組 按照兒童體重狀態分為超重/肥胖組和非超重組。
1.2 方法
1.2.1 兒童身高體重測量 體重使用CTG-60兒童稱測量體重,精確到0.01 kg。測量體重前脫去鞋、帽子和外衣。身高使用貝特斯SZG-180身高坐高計,兒童取立正姿勢,精確到0.1 cm。
1.2.2 問卷調查 采用自行設計的家長問卷,問卷調查兒童出生日期、性別,父母年齡、身高、體重、學歷水平、家庭收入等。
1.2.3 質量控制 工作人員統一培訓,使用幼兒園統一配備設備進行測量,實施過程進行嚴格質量控制,隨機復測5%,復測指標的誤差率不超過5%。
1.2.4 超重/肥胖評定標準 兒童評定根據首都兒科研究所制定的標準,2-18歲兒童肥胖、超重篩查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界值點(kg/m2)來診斷超重和肥胖[5],詳見表4,分為超重/肥胖組和非超重組。父母體重狀況評定依據以下標準: 非超重組(BMI<24 kg/m2)、超重(24 kg/m2≤BMI<28 kg/m2)、肥胖(BMI≥28 kg/m2)[6],分為超重/肥胖組和非超重組。
1.3 統計學處理
2 結 果
2.1 參與調查者基線信息
本研究3個社區3-7歲兒童總數約5 400人,共5 138人參與調查,參與調查率95.1%。收集問卷5 138份,有效問卷5 129份,無效問卷9份(已剔除),問卷有效率99.8%。5 129對父母和子代的基本信息見表1。

表1 參與調查者基線信息
2.2 父母和兒童超重/肥胖檢出情況
兒童超重/肥胖檢出率21.4%(其中超重檢出率13.8%,肥胖檢出率7.6%)。父親超重/肥胖檢出率52.1%(其中超重檢出率39.1%,肥胖率13.0%),母親超重/肥胖檢出率17.5%(其中超重檢出率14.4%,肥胖檢出率3.1%)。
2.3 不同親子對類型父母-子代體重狀態關聯性分析結果
不同親子對類型父母-子代體重狀態關聯性比值比(odds ratio, OR)詳見表2。母親超重/肥胖、父親超重/肥胖、父母親雙方超重/肥胖均為子代超重/肥胖的危險因素,他們所生子代中,女兒超重/肥胖的風險OR值均高于兒子,詳見圖1。與父母雙方非超重相比,父母雙方超重/肥胖所生子代超重/肥胖風險最高,其所生女兒超重/肥胖的風險OR值及95%CI為3.69(2.64-5.15,P<0.001),所生兒子超重/肥胖的風險OR(95%CI)值為2.80(2.09-3.76,P<0.001)。母親超重/肥胖所生子代的風險OR值高于父親超重/肥胖所生子代,見圖2。

圖1 不同親子對體重關聯性OR(95%CI)比較

圖2 不同親子對體重關聯性OR(95%CI)值比較

表2 父母與子代體重狀態的關聯性
2.4 不同年齡段父母-子代體重狀態關聯性分析結果
不同年齡段父母-子代體重狀態關聯性OR值見表3,在不同年齡段中父母親雙方超重/肥胖子代超重/肥胖風險仍最高,所有年齡段中母親超重/肥胖所生子代超重/肥胖風險高于父親超重/肥胖所生子代,在5- 6歲和6- 7歲時其風險OR值逐步接近,詳見圖3。與父母雙方非超重相比,父母雙方超重/肥胖,3- 4歲兒童超重/肥胖風險OR值最高,其OR(95%CI)為4.18(1.65-10.57)P=0.003。與母親非超重相比,母親超重/肥胖時,3- 4歲兒童超重/肥胖風險OR值最高,其OR(95%CI)為2.66(1.27-5.57)P=0.01。與父親非超重相比,父親超重/肥胖時,6- 7歲兒童超重/肥胖風險OR值最高,其OR(95%CI)為1.91(1.41-2.58)(P<0.001)。

圖3 不同年齡段父母-子代體重狀態關聯性OR(95%CI)

表3 不同年齡段父母-子代體重狀態關聯性OR(95%CI)

表4 2 - 18歲兒童肥胖、超重篩查BMI界值點
3 討 論
父母超重/肥胖與兒童超重/肥胖風險關聯性研究結論一直備受爭議,先前Lee等[3]的研究結果顯示父親和母親對子代超重/肥胖風險關聯性沒有任何顯著差異。也有研究認為父親對子代超重/肥胖風險關聯性強于母親[7]。另外,Durmus等[8]的研究認為兒童肥胖與母親體重狀態關聯性強于父親。本研究結果與Durmus等研究結論一致,與父親超重/肥胖相比,母親超重/肥胖所生的兒子和女兒超重/肥胖的風險都更高,3-4歲兒童受影響最大,隨著年齡增加,母親與子代關聯性趨于平穩。此外,我國兒童主要喂養人為母親,兒童的生活飲食習慣更容易受母親影響。母親體重狀態對兒童體重狀態影響已得到很多研究的證實,但父親在兒童早期超重/肥胖風險方面的作用卻被低估了[9]。本研究結果發現,父親超重/肥胖是子代超重/肥胖的危險因素,其子代超重/肥胖風險是父親體重正常的2倍左右。隨著年齡增加,父親與子代的關聯性變得更強。近年來研究證實父親肥胖會通過影響精子中的DNA甲基化編程,而影響下一代的表觀基因組[10]。我團隊還發現父系印記基因可引起的表觀遺傳變化會影響兒童體格發育,引發矮小、肥胖、脂肪肝的發生[11]。所以,以往的各項研究結果不一致基本上是忽略了父親的影響作用造成的。
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父母親雙方都超重/肥胖,其子代超重/肥胖風險是父母雙方非超重的3倍左右。父母親雙方超重/肥胖時,3-4的兒童超重/肥胖風險最高,在4-5歲時風險呈下降趨勢,在4- 7歲期間超重/肥胖的風險隨著年齡增大風險增加,我們的研究結果與Matlosz、Zhang等一致[12-13]。父母與孩子肥胖通常呈聚集性發生,是遺傳和環境的共同作用,日益致胖的環境可能會放大肥胖的遺傳風險[14],同時非致胖環境可以弱化肥胖的遺傳傾向[15-16]。另一項系統分析顯示年齡較大的兒童在體重狀態方面的親子關聯性更強[4],這可能是長時間的共同暴露可能會給孩子和父母的體重留下更明顯的印記,父母和孩子在超重/肥胖關聯的行為特征上可能有更高的相似性[13]。
綜上述,本研究結果支持調整相關混雜因素后,父母超重/肥胖仍然是兒童超重/肥胖的重要危險因素,父母雙方超重/肥胖或母親超重/肥胖對3-4歲兒童影響最大。雖然與父親超重/肥胖相比,母親超重/肥胖所生的子代超重/肥胖的風險更高,但也不能低估父親超重/肥胖的影響。隨著年齡增加,母親與子代關聯性趨于平穩,父親與子代的關聯性變得更強。因此學齡前兒童超重/肥胖預防中,需要考慮兒童的肥胖遺傳背景、性別、年齡等綜合因素,對于具有超重/肥胖遺傳風險的兒童,父母體重管理和改變早期的家庭環境特別重要[17]。本研究為多中心、橫斷面、對照研究,父母的體重為自我報告,但有研究顯示成年人自我報告的體重和測量體重具有高度一致線性[18]。有一定的真實、客觀性。由于本研究缺乏父母孕前體重數據,兒童年齡跨度較小,有一定局限性。未來可對父母和兒童不同生命時期體重狀態相關性進行前瞻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