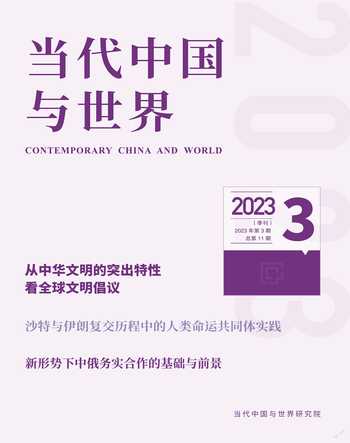從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看全球文明倡議
李國強
【關鍵詞】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全球文明倡議;文化比較;新型文明關系
作為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物質成果和精神成果的總和,文明既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標志,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文明是文化的內在價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化的傳承發展關乎一個國家治理體系的選擇,關乎一個國家治理能力的高下,同時也關乎世界未來的走向。
2023年3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以“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為主要內容的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文明倡議致力于實現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對推動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促進人類文明事業持續進步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首次系統、科學地闡釋了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將其概括為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個突出特性,將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寓于人類文明發展史中,既是對中華文化特質、中華文明精神品格的全面把握和系統揭示,也是立足中國式現代化對開創新文化的深邃思考和恢弘擘畫,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同時,五個突出特性揭示了全球文明倡議的歷史邏輯、夯實了全球文明倡議的歷史根基,為踐行全球文明倡議注入強大動力,為我們深刻把握全球文明倡議的核心要義、精神實質和實踐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是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華民族致力于持續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和世界文明進步事業的必然歸宿。植根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全球文明倡議高度濃縮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充分彰顯出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各國歷史文化的時代價值,順應了當今世界和平發展的客觀要求,為開創世界各國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為打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新世界注入新元素、開辟新路徑、增添新活力。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和平理念是全球文明倡議的源頭活水
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愛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和平、和睦、和諧構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內核。源起于萬年前、率先在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發端的中國農業,不僅對中國歷史的發展、中華民族的成長起到關鍵性作用,而且是奠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平和諧和睦思想理念的重要基礎。以農為本的生產生活方式,培育出以血緣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對家族興旺的責任和對祖先的敬奉,衍生出“敬天法祖”的觀念,逐步萌發出天人合一、講求秩序,貴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的思想元素,“和合”成為流淌在中華民族血液中最樸素的文明基因。
伴隨著農耕文明的日益進步,和合文化漸趨淬煉、持續光大,凝練為中華民族顯著的精神特質,濃縮為中華民族標識性的精神氣度。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德不孤,必有鄰”,奠定了儒家倡導的“仁者愛人”的價值取向;以“道法自然”“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著稱的道家推崇守中致和;以“兼相愛,交相利”為認知的墨家主張非攻尚同;以“謀攻”為主旨的兵家提倡上兵伐謀、非危不戰。先秦諸子百家雖流派不同、觀點迥然,但和合共生卻是存續于諸子百家思想深處的共同特征。
后世歷經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和合文化不斷傳承,日用而不覺。西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郊語》中指出:“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北宋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大志向。
在近代,太平天國建立者認為“天下總一家,凡間皆兄弟”,從而確立了“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目標。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奉為圭臬,主張人類博愛與世界大同。在殊途同歸的氣象中,和平、和諧、和睦成為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永恒價值和至高皈依,形塑了中華民族儒雅、平和、溫良、坦蕩的民族稟賦。
中華民族歷來崇尚“以和邦國”“和而不同”“以和為貴”,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精神積淀,導引著中華民族以“大同世界”為理想,以“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民吾同胞,物吾與也”j為操守,以“尚和合、求大同”“以和邦國”為準則,以“國雖大,好戰必亡”、“化干戈為玉帛”為戒律,以“求同存異”“和諧共生”為與世界相處之道,以實現和平、和睦、和諧為榮,以侵犯他人、謀求霸權為恥,不僅使中華民族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而且始終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彰顯了人類應有的道德取向、價值追求和前進方向,為人類文明進步、為世界和平和睦和諧與繁榮發展提供了正確精神指引。早在公元5世紀,亞美尼亞歷史學家摩西在《亞美尼亞史記》一書中即已盛贊中國“人民富裕,文物昌明,民性溫和,不但可稱為‘和平之友(Friendsofpeace),而實亦為‘生命之友(Friendsoflife)也”。
“四海之內若一家”,親仁善鄰、和衷共濟、和合共生,既是中華民族對待世界的態度,也是中華民族推動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不斷發展的具體實踐。經過幾千年歷史實踐和千錘百煉,和合大同的思想因子早已浸透到中華民族血液中,重誠信、講仁愛、求友善、修和睦的文化特質早已轉化為中華民族的行動自覺,對人類和平的孜孜以求、矢志不渝早已凝結為中華民族的意志品質和堅定信念。1922年,英國哲人羅素在訪問中國回國之后,完成了《中國問題》一書,在書中他高度評價中華文明,認為中國人是一個忍耐、和善、含蓄、灑脫、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歷史上雖然征戰連綿,但老百姓天性是喜好和平的”。他說:“如果在這個世界上有‘驕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國。中國人天生寬容而友愛、以禮待人,希望別人也投桃報李。”n美國《新聞周刊》主編法里德·扎卡里亞在《后美國世界:大國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一書中認為,儒教文明(中華文明)本質上沒有西方基督教文明那種傳教士要向外傳教和擴張的沖動,因而并沒有擴張主義的文化基因。中國儒家哲學的“和平主義”和中國文明并不具侵略性。這一評論是較為公允的。
“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定了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決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
可以說,中華民族以和平為主題主線的天下觀,是全球文明倡議的思想之源、行動之魂,為實現世界持久和平與發展、為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豐厚歷史滋養。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包容特質筑牢全球文明倡議的歷史根基
中華文明是在中華大地上獨立形成的,但它從來不是封閉保守的,相反始終保持著與外部世界的相互聯系、彼此互動和深度交融。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是推動中外文明相互影響、互學互鑒的重要根源。在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看來:儒道和佛道的價值觀更為包容、更為文明、更為平和、更有秩序。
在人類發展史上,文明的雙向互動、相互學習和借鑒幾乎貫穿于歷史發展全過程。中華民族歷來以“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為理念,展現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造就了中華文明求同存異、和合共生、兼收并蓄的博大氣度,標識出何以中國、何以中華民族、何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為中華文明屹立在世界文明之林提供了強大支撐。同時,中華民族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精華,不斷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和創造力,鍛造出中華民族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匯聚成中華民族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思想升華中,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不斷作出原創性貢獻。
公元8世紀前后,東亞國家大規模吸納漢字、儒教、律令制度以及科學技術,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漢文化圈”。以指南針、造紙術、火藥、活字印刷“四大發明”為代表的中華文明向世界廣泛傳播,帶動了世界性變革,推動了歐洲文藝復興,深刻影響了西方社會面貌和歷史進程。羅馬的玻璃器皿和毛織品,印度的寶石、香料,阿拉伯的數字等進入我國,大大豐富了我國物質文化生活。中華民族在為世界文明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同時,世界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持續地為中華文明注入活力因子。
凡是到過敦煌的人,都被莫高窟的壁畫所折服。莫高窟壁畫、彩塑的服飾,既有中原傳統漢服、少數民族衣飾,也有來自中亞、西亞、印度等地的衣裝。這些各具特色的服飾,展現了絲綢之路上千年間各國各民族不同身份的人們的衣裝。敦煌的飲食習俗具有濃郁的漢食胡風特色,來自中亞、西亞、西域的飲食習慣融入敦煌的飲食風俗中。僅在敦煌遺書中出現的食物品種就多達60多種,其中來源于“胡食”的有胡餅、胡桃、胡棗、安石榴、大食瓜、胡酒等等。
歷經將近20個世紀的古代絲綢之路呈現出持續的跨文明交流對話的盛大景象。不同文明交匯在絲綢之路、交融在絲綢之路,各具特色的文化得到廣泛而充分的展示,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建筑藝術,古希臘的哲學、文學和史學,兩河流域的城市建筑、藝術、天文學,等等。儒教、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更是絲綢之路上十分活躍的互動元素,成為不同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代表。
公元前1世紀末佛教傳遍西域各地,公元64年漢明帝派遣12使者前往西域訪求佛法,他們同印度僧人回到洛陽,建造了我國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佛教傳入是外部文化第一次大規模輸入我國,并迅速被我國本土文化改造和吸收,形成漢傳、藏傳和南傳佛教三大派別。經過與儒、道等本土文化的不斷磨合,佛教最終融入中華文化。而印度佛教藝術經過我國藝術家和民間工匠的再創造,形成富有濃郁中國特點的佛教藝術,影響了整個世界佛教。
在唐代,拜火教、摩尼教、景教、猶太教等先后傳入我國,又從我國傳播到其他國家。景教是基督教的分支,從敘利亞傳入我國。公元635年,唐朝政府準許景教徒在長安興建“波斯寺”,景教在中原開枝散葉,呈現出“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與拜火教、摩尼教并稱唐代“三夷教”。
隨著阿拉伯帝國的興起,伊斯蘭教迅速向東傳播。公元651年,大食首次遣使至唐,伊斯蘭教由此傳入我國。元明兩朝伊斯蘭教在我國傳播甚廣,號稱“元時回回遍天下”。從哈里發時代起,伊斯蘭文明在哲學、倫理學、邏輯學、建筑學、醫學和藝術領域的魅力,對我國多民族社會文化生活影響至深。
據統計,唐朝在全國設立的驛站有1639所,僅廣州的外國客商就有12萬人,與唐朝有交往的國家或部族達100多個,南亞、中亞和西亞來唐使團共343次。明朝永樂年間,受鄭和下西洋影響,各國使節來華318次,平均每年15次,最多一次有19個國家朝貢使團同時到達。“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古代中國之所以有龐大的“朋友圈”,得益于開放,受惠于包容。
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涵養著中華民族始終堅守平等、公平、正義的精神高地,持續給人類文明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思想、中國力量,維護了世界文明多樣性,推動人類文明在多元中成長、在多彩中進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蘊含的價值觀,共建“一帶一路”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蘊含的天下觀,全球文明倡議蘊含的文明觀,等等,無不展現出中華文明包容的特質、包容的氣度和包容的胸襟。全球文明倡議不僅是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的有力彰顯,也是人類文明基本內涵的應有之義。
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厚植全球文明倡議的目標方向
中華典籍《尚書》《周易》等,通過對“皇極”“五行”“八卦”等核心概念的闡發,歸納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與時偕行”“天下一統”等思想,展現出中華民族在對自然規律的探求以及對世間萬物相互影響、互相作用的思辨中,將天、地、人融為一體的理性思維,最終塑造出中華民族包容和平、通達適變、多元一體的文明基因。
《左傳》說“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中華民族歷來以“君子和而不同”為信條,以“協和萬邦”為追求,以“天下大同”為志向,凝練出“以和為貴”“萬方融合”的理念。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中華文明始終走在世界各國前列,深刻影響和改變了世界文化格局和人類文明進程。繼張騫“鑿空”之行后,甘英出使大秦,帶來東西方文明的相互貫通。鄭和七下西洋,歷時28年,足跡遍及印度洋、阿拉伯海、紅海和非洲東海岸30多個國家和地區,w鄭和所到之處,沒有占領他國一寸土地,他傳播的是中華文明的思想和理念,留下的是與沿途各國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話。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馬可·波羅到達元大都,在中國游歷17年后寫下《馬可·波羅游記》,激起歐洲人對古老中國的熱烈向往。14世紀初,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從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來到中國,把中華文明的諸多元素介紹到阿拉伯世界。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把中國文化視為文明智慧與道德秩序的典范,帶回了歐洲。18世紀前后,歐洲啟蒙思想家對中華文明推崇倍至,從儒家學說到中國政治制度對近代歐洲影響至深。
世界上其他文明對中華文明也產生了多方面影響,發揮了積極作用。5000年前,發源于西亞地區的農作物小麥和家畜黃牛、綿羊以及銅的冶煉和制作技術傳入我國。4000年前,家馬由歐亞草原傳入我國新疆。距今3300年左右,家馬和馬車經由歐亞草原地帶傳入我國中原地區。唐初“別求新聲于異邦”,z印度、波斯、羅馬、大食音樂傳入中國,蘇莫遮舞、拔頭舞、胡騰舞、胡旋舞等風行長安。明清時期,“中學西傳,西學東漸”,西方傳教士把天文歷算、數學、醫學等知識以及自鳴鐘、火器等制造技術傳入中國。
人類文明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進步的源泉和動力。在歷史長河中,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等交相輝映、熠熠生輝,既展現出各自的歷史文化特色和獨特魅力,又共同譜寫了人類文明史的華麗樂章,共同促進了人類成長進步,成為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
《易傳》指出:“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ヒ世界文明史表明,歷史文化的多樣性,決定著不同國家不同民族選擇自身發展道路的自主性,決定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多樣性。只有從不同歷史文化中汲取有益養分,才能使本國本民族始終保持旺盛的活力、持久的生命力、強大的創造力。
在五千多年文明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尊重不同文化,善待其他文明,以博大的胸懷、海納百川的氣度學習、借鑒、吸收世界其他文明的精華,孕育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化隔閡,以文化互鑒超越文化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的精神品格和鮮明立場,鍛造出“攜手共行天下大道”的深厚情懷。中華文明之所以延續五千多年賡續不絕,之所以能夠以燦爛的文明成果影響世界、貢獻世界,正是因為其價值取向與人類社會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共同價值追求相輔相成,高度一致,始終反映著、代表著、引領著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前進方向。
“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フ文明的差異性決定了人類社會的多元化,文明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不同文明只有相互包容、彼此共存、互學互鑒,才能使世界文明百花園更加姹紫嫣紅、生機盎然,才能使世界在和平、和諧、和睦的道路上行的穩、走的遠。世界上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文明”,也不存在所謂普世性的“優越”文明,不同國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每一種文明都有自己的本色、長處、優點,每一種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都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所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湯因比認為:中國人不以種族主義劃分人群,把天下視為天下人的天下,這種更為高級的公平才是真正的長久之道。這個觀點雖以中國為參照,但是講出了不同文明以多種樣態并存于世的合理內核。
“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ホ對待差異化、多樣性的世界文明,要多一些尊重,少一些傲慢;多一些平等,少一些偏見;多一些取長補短,少一些唯我獨尊。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只有傳承好、發展好自身文明,才能讓古老文明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煥發出蓬勃生機與活力,才能走出符合本國國情、具有自身特色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動輒把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于人,動輒搞意識形態對抗,即是對人類文明的褻瀆,不僅加害于人類文明,而且終將被人類文明所拋棄。
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底蘊厚實全球文明倡議文明觀
“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マ汲取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共同繪就百花齊放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理應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全球文明倡議植根于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思想結晶,是新時代中華民族文明觀的集中體現,不僅科學回答了人類向哪里去的“世界之問”,而且科學回答了人類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美好世界、怎樣建設美好世界的“時代之問”,為世界各國共同開創人類更加光明的未來指明了方向、擘畫了藍圖。
對人類文明的研究和探索,關乎對文明的認知、文明的構建、文明的發展,歷來是世界性話題。在此,我們不妨分析一下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1993年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美國《外交事務》季刊上發表了《文明的沖突?》一文,首次提出“文明沖突”理論,在后續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論著中,亨廷頓對該理論做了進一步闡釋。其觀點集中在《不是文明,又是什么?》《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以及專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歸納起來看,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核心觀點是,冷戰后國際沖突的基本根源已不再是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差異,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沖突”。
在亨廷頓看來,首先,人類在經歷了君主沖突、民族國家沖突和意識形態沖突之后,將進入文明沖突階段。從近代到冷戰期間,國際社會中的經濟利益、意識形態沖突以及引發的戰爭,遮蓋了文明沖突。“冷戰”結束后,文明沖突將重新上升為全球政治沖突的主要根源。其次,文明的差異是歷史產生的,是比政治意識形態及政權等更為根本的差異。隨著不同文明的相互影響加深,強化了人們的文明意識,加劇了文明之間的敵對情緒,這種文化特性和差異不易改變,也難以用妥協的方式解決。最后,文明沖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建立在文明基礎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戰爭的最可靠的保證。亨廷頓認為未來世界沖突的主要原因和最終走向,將取決于文明博弈的結果。
之所以得出以上結論,是因為亨廷頓將文明互動關系作為一個主要范式嫁接到國際政治領域,其理論實質是力圖借用文化學理論與概念,對后冷戰時代的世界格局和沖突形式作出解釋。遺憾的是,在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對外政策影響下,亨廷頓對冷戰后戰爭和沖突原因的歸納脫離了完整的、客觀的歷史背景,對非文明原因導致的戰爭和沖突全然不顧,對中華數千年文明史的認識失之偏頗,不僅主觀臆斷地預設了未來世界的兩大沖突點,即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而且過分夸大文明的差異和分裂作用,對不同文明間的巨大整合作用卻避而不談。
從根本上說,“文明沖突論”把冷戰遺留下的排他性、對抗性、集團性思維模式視為當代國際政治的基本形式,將文明、文化因素視為矛盾的決定性因素,人為將世界解構為西方世界—非西方世界的二元格局,既顯露出理論上的局限性、消極性和破壞性,凸顯出排斥異己文明的西方中心主義,又迎合了美國為霸權主義尋找理論根據的需求,成為美國外交政策制定者們定義后冷戰世界的新理論以及為自身霸權主義辯護的新工具,對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都有極大危害。
歷史是現實的根源,當代人類文明是歷史文明的延續和升華。與所謂“文明沖突論”完全不同的是,全球文明倡議從漫長而多元的人類文明史中走來,從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走來。基于對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科學把握,基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全面揭示,全球文明倡議歸結千古,指向未來,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以及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展現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跨越時空、聯通古今、展望未來中,盡顯卓越價值、發揮非凡作用,賦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鮮活的當代價值和深遠的世界意義。
全球文明倡議堅持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倡導弘揚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為主旨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主張以寬廣胸襟實現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吸收借鑒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主張以文明包容互鑒取代隔閡沖突,主張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于人,不搞意識形態對抗,強調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打破了西方中心論主導的文化霸權話語體系,順應世界歷史發展大勢,符合人類和平發展的夙愿,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新圖景,拓展了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廣闊空間,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了中國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必將對維護全球治理秩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揮出重要作用。
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說到底是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而文明的傳承、發展和創新,既是人類社會永續前行的基本前提,也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的必由之路。我們要立足各國人民的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深入挖掘各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激活文明進步的活水源頭,加強文明對話與交流,深化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推動各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開創世界各國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共同致力于打造同舟共濟、榮辱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世界各國人民追求和平、富強、進步的光榮與夢想。由此而言,全球文明倡議對于推動人類現代化進程、促進人類文明進步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