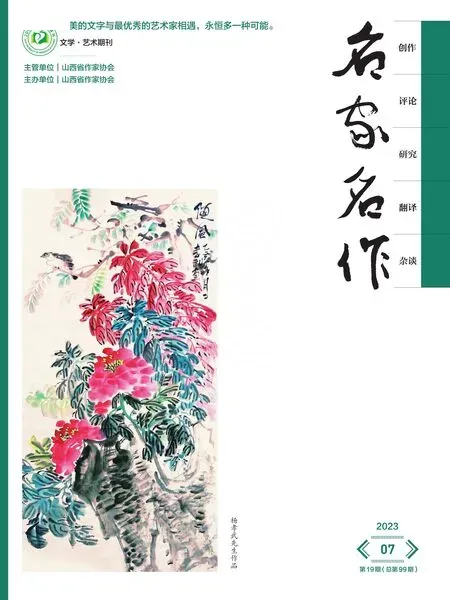論明清傳奇中的信物
李 萌
明清傳奇在中國戲劇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幾百年的發(fā)展歷程中留下了許多廣為流傳的經(jīng)典之作。從諸多明清傳奇作品中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緊緊圍繞著信物展開,甚至很多明清傳奇的劇目名都直接以信物命名,如《玉合記》《瑪瑙簪記》等。信物的使用在古典文學作品中源遠流長,早在《詩經(jīng)》中就已出現(xiàn)“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1]之類的信物贈送行為。《說文解字》中解釋:“信者,誠也。”[2]信物是一種盟證,是彼此對承諾的堅守。信物寄托著深厚的情感,是明清傳奇中重要的言情道具,其在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中更是發(fā)揮著重要的敘事功能。本文旨對明清傳奇中出現(xiàn)的信物的基本特點、情感內(nèi)蘊做以歸納分析,重點探討信物的敘事功能。
一、信物的基本特點
從先秦詩歌、漢樂府、魏晉小說、唐傳奇等各類文學體裁中都可以看到關于信物的描寫,明清傳奇中對信物的描寫更加多樣化,其在敘事、言情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從郭英德先生編著的《明清傳奇綜錄》一書中可知明清傳奇中出現(xiàn)的信物種類豐富、形式多樣。根據(jù)其材質(zhì)的差異大致可分為金玉飾物、絲織物和紙箋類三種信物類型。
明清傳奇中出現(xiàn)的信物種類最多的就是金玉飾物,有金鳳釵、金鑾扣、玉指環(huán)、寶劍、雙魚佩等。金屬玉石具有堅固、貴重等特點,這類信物很多都是家傳寶物,不僅制作精美,而且十分稀有珍貴。《玉劍緣》中淮南人杜器就把家傳的玉劍作為聘禮贈送給自己的心上人珠娘,以家傳寶物作信物相贈彰顯了他們感情的彌足珍貴。《玉釵記》中何文秀與金陵歌妓劉月金交好,在二人分別之際,劉月金將玉釵送給何文秀,作為日后重逢的憑證。何文秀含冤時逢王太師之女瓊珍,瓊珍見何文秀與夢中自己所嫁之人相符,遂欲托付終身,何文秀因此把玉釵轉(zhuǎn)贈給瓊珍。玉釵作為這部傳奇中的信物,牽動著男女主人公的感情。作者也自述為:“全忠全孝全節(jié)義,玉釵始終多情緒。”[3]312《雙魚佩》中柳應龍的魂靈進入想容夢中,二人共題一詞,便互贈玉魚佩以定終身。玉在中國古典文化中具有特殊的象征含義,古人賦予玉溫潤、高潔等美好的象征義,用玉劍、玉釵、玉佩等作為信物,象征著持有信物的雙方之間純潔、美好的真摯情感。
明清傳奇中還有一類信物是個人貼身的絲織物,主要有手巾、束腰絲帶等,古代女子的貼身絲織物大多為自己親手所繡,蘊含著女子的閨房情思。《紫霞巾》中陸生與玉娥化解誤會、互明心意后,玉娥用貼身相帶的紫霞巾與陸生約定為盟。玉娥將紫霞巾贈送給自己心儀的人,表明了對陸生的高度信任,暗含了愿定終生的情意。《白玉鴛鴦絳》中淑兒喜愛楊生俊秀,便把自己的白玉鴛鴦絳贈予楊生,約定二人姻盟。白玉鴛鴦絳是淑兒的貼身束腰絲帶,以此相贈表明了托付終身之意。個人貼身的絲織物雖不如金屬玉石那般價值珍貴,但是以個人貼身的絲織物作為信物,卻更能表明彼此之間親昵的關系。
紙箋類信物也是明清傳奇中出現(xiàn)次數(shù)較多的一類信物,在以紙箋類物品作為信物,通常都會有詩詞附于上面。雙方將詩詞寫在扇子、紙箋等信物上,而且會多次通過詩詞互傳心意。如《玉梅亭》中梅云孫將詩寫在梅家園子的石壁上,林家之女素星偶然看到梅生寫的詩,隨即在扇子上和詩一首。林父看后便邀請梅生在玉梅亭飲酒,隨即把林素星寫的詩扇贈予梅生,作為梅生與素星的婚定盟證。梅生也在扇子上題詩一首,回贈給林素星。《飛丸記》中易弘器在嚴府聚春園游玩時,偶然遇到嚴世番之女玉英,兩人互生情意,弘器有感而發(fā),在紙箋上寫了一首詞。詞箋不小心丟失,被園公拾得送給玉英,玉英和詞后做成丸拋擲下來,土地神又將玉英所作之詞傳予弘器,兩人之間多次用詩詞傳和。詩詞傳和一來一往也是雙方情感逐漸深化的過程,能夠借詩詞傳情的主人公基本都是具有文化底蘊的才子佳人。迫于當時封建制度的束縛,女子不能明確地向自己心儀的人表明心意,詩詞含蓄且能表達真摯的情感,與互生情愫的才子佳人的角色十分符合。
二、使用信物的對象及情感內(nèi)蘊
自古信物多出現(xiàn)在兵亂離亡的大背景下,或是在封建家庭專制的壓迫下,雙方之間不得已贈送信物,作為彼此之間的盟證。能夠作為信物的物件必然具備非凡的價值,信物最主要的作用是傳情達意,在戀人、親人、朋友等親密關系間都會贈送信物,不同的使用對象借信物傳遞的情感也不同。
關于傳奇,有“十部傳奇九相思”的說法,所以在明清傳奇中出現(xiàn)最多的信物為定情信物。定情信物一旦送出,便給互生愛慕的青年男女提供了堅定的情感保障,也預示著即便雙方歷盡千難萬險,最終也會實現(xiàn)大團圓的結(jié)局。《雙翠圓》中金重偶然拾得王翠翹的金釵,在翠翹尋找金釵的過程中,二人結(jié)下姻緣。后金重因叔父之死要與翠翹分別時留金釵為盟。盡管翠翹遇到一系列的坎坷與挫折,但始終沒有違背他們的約定,最終柳暗花明。金釵作為二人感情的盟證,也象征著他們生死不渝的感情。《玉合記》中韓翃對柳氏有愛慕之意,然后就贈送給柳氏玉合,柳氏對韓翃也有思慕之心。二人在戰(zhàn)亂分別相遇時,無法互敘衷情,韓翃便以昔日柳氏所贈題詩之紅綃擲車中,柳氏以帕包玉合投車中韓翃,互示絕情,涕泣而別,最終實現(xiàn)了團聚。“信物饋贈在青年男女之間是完全自由自愿、沒有任何其他附加成分的饋贈接受行為,可以說是最為清新、淳樸、真摯和自由心聲的表達。”[4]定情信物與男女之間的愛情緊密相連,既能定情、傳情,也能表絕情,諸如此類的作品還有《玉搔頭》《江花夢》《易鞋記》等。
目前對明清傳奇中信物的研究多集中在青年男女之間贈送的定情信物,但深入了解明清傳奇作品后不難發(fā)現(xiàn),親人、朋友之間也會贈送信物。親情是永恒的,是割舍不斷的,親人之間贈送的信物連接著至深的血脈親情。如《玉蜻蜓》就是親人之間依靠信物最終得以團聚的經(jīng)典作品,全劇以玉蜻蜓為中心,講述了時行認母、復姓歸宗的故事。作品主要記敘蘇州人申嗣芳與友人同游法華庵,庵尼志貞看到申嗣芳后心生愛慕,在申嗣芳妻張氏歸寧之時,志貞便留申嗣芳在庵中居住。不久,申嗣芳病逝,志貞生下一子,因庵中無法撫養(yǎng)孩子,志貞將一個玉蜻蜓綁在孩子胳膊上,放置在道路旁。玉蜻蜓是志貞留給孩子的信物,也是多年后得以認祖歸宗的依據(jù)。這個孩子被蘇州徐家領養(yǎng)后取名時行,時行長大后知道自己并非徐家親生,又從婢女口中知曉玉蜻蜓一事。時行在尼庵禮佛時遇見志貞,知道志貞為其生母后拿出藏于袖子中的玉蜻蜓,與志貞共同回到了申家。傳奇?zhèn)涫觥耙蝗耸冀K”,十幾年的時間人的容貌會發(fā)生很大的變化,單憑長相很難確定她們的母子關系,但是信物的留存卻是永久的。志貞與時行在不得已分別時以玉蜻蜓這一信物作為日后認親的盟證,信物在此成了延續(xù)親情的紐帶。
朋友之間使用信物作為盟證的傳奇有《埋劍記》《鸚鵡洲》等。《埋劍記》是沈璟汲取唐代小說《吳保安傳》中的英雄事跡創(chuàng)作而成的。吳保安與郭仲翔為同鄉(xiāng),在吳保安沒有官職的時候,郭仲翔力薦吳保安為掌書記。二人結(jié)為兄弟,吳保安將自己的珊瑚鞭贈送給郭仲翔,郭仲翔又把家傳的寶劍作為回禮送給吳保安。這兩個信物都十分珍貴,代表著他們兩人之間的深厚情誼。他們在彼此深陷困難時也是竭盡全力共渡難關,吳保安死后,郭仲翔悲痛欲絕,連同他贈給吳保安的寶劍也一并埋葬,充滿慷慨悲壯之感。珊瑚鞭和寶劍象征著他們之間的情義,郭仲翔埋葬寶劍更是彰顯了他們堅貞不渝、死生如一的交情。
信物饋贈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情感的外露,青年男女、親人、朋友之間贈送信物是他們對彼此之間美好情感的期望和對承諾的堅守。明清傳奇故事中更是借信物彰顯了愛情的堅貞不屈、親情的珍貴無私、友情的慷慨悲壯。信物中蘊含的情感都是十分堅貞的,湯顯祖在《牡丹亭》題記中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皆非情之至也。”[5]信物中蘊含的情感大抵如此。
三、信物在傳奇中的敘事作用
信物作為舞臺道具,在傳奇故事的發(fā)展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戲曲家李漁認為:“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湊成。剪碎易,湊成難,湊成之功全在針線緊密。一節(jié)偶疏,全篇之破綻出矣。每編一折,必須前顧數(shù)折,后顧數(shù)折,顧前者欲其照映,顧后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劇中有名之人,關涉之事,節(jié)節(jié)俱要想到。”[6]在容納著廣闊社會生活和復雜多樣事件的明清傳奇中,信物是牽動事件發(fā)展的關鍵物品,很多構(gòu)思精妙的故事都以信物為中心,而且信物作為重要的線索通常會貫穿全文。
首先,信物在傳奇敘事中具有串聯(lián)故事、促進故事發(fā)展的重要作用。很多明清傳奇中講述的故事跨越時間較久,甚至長達幾十年,有了信物這一媒介,就能夠成功串聯(lián)起故事的發(fā)展,讓復雜紛亂的情節(jié)變得有跡可循。如《易鞋記》《異夢記》中記敘的坎坷波折的故事情節(jié),就通過鞋子、雙魚佩等信物作為線索,串聯(lián)故事情節(jié)。《易鞋記》中程鵬舉被張萬戶拷打,程鵬舉不得已準備逃跑時,他的妻子玉娘將一只鸞鞋相贈,將另外一只鸞鞋自己保存,作為二人日后相見的憑證。多年之后,程鵬舉成為陜西參政,派遣仆人帶著玉娘贈送的這只鸞鞋尋找玉娘,最終依靠這只鸞鞋,二人得以團聚。在傳奇故事中有很多人物都因不得已的外在條件匆匆離別,此時就需要借助信物作為日后相逢的憑證。《瑪瑙簪記》《合桃記》中的瑪瑙簪和合桃作為信物都是雙方各持一個,無論雙方身處何地,依靠信物都能串聯(lián)起故事發(fā)展的兩條線索,最終實現(xiàn)大團圓。信物是雙方之間約定的一種憑證,所以信物在形式上不僅有單個的,也有成雙成對的。
其次,信物是敘事情節(jié)得以轉(zhuǎn)換的重要契機,傳奇故事情節(jié)富于變化,情節(jié)之間通常會出現(xiàn)極大翻轉(zhuǎn),或是悲喜情節(jié)的轉(zhuǎn)變,抑或是人物命運的轉(zhuǎn)變。如《綰春園》中楊鈺、阮蒨筠、崔倩云三人之間的經(jīng)歷,極為曲折,最終借助信物化解誤會,故事情節(jié)出現(xiàn)大翻轉(zhuǎn),男女主人公擁有美好結(jié)局。在楊鈺與蒨筠合巹之夜,兩人通過敘說墜帕始末緣由,楊鈺才知道綾帕是倩云的,意識到自己真正所傾慕的人是倩云。綾帕作為重要的信物,是本部傳奇中故事情節(jié)出現(xiàn)翻轉(zhuǎn)的唯一線索,綾帕的存在使在合巹的最后時刻化解了三人之間的誤會,同時也增加了故事情節(jié)的豐富性與曲折性。最終在阮翊的撮合下,楊鈺與倩云得以在一起。再如《投桃記》中胡桃作為潘用中與黃舜華之間的愛情信物,兩人多次通過投胡桃互表心意。在被人設計離間后,潘用中將半個胡桃還給黃舜華,然后以死明志,黃舜華也決定殉情,在生死存亡之際,判官為二人生死之情而感動,遂為之合桃聯(lián)姻。信物雖小,但在整部傳奇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中的作用卻不可忽視。潘用中與黃舜華借胡桃傳情,以胡桃為證,最終合桃聯(lián)姻,實現(xiàn)了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美好祝愿。
最后,信物的存在是推動傳奇故事發(fā)展的關鍵節(jié)點,它是故事情節(jié)得以展開的重要道具,借助信物能夠推動情節(jié)波瀾起伏,步步深入。“同詩歌、散文比較,傳奇有著小說般容納廣闊生活,結(jié)構(gòu)復雜事件的能力。”[3]113傳奇敘事內(nèi)容廣博,涉及的時間、地點、人物相對比較復雜,想要步步深入敘事,則需要一個關鍵點,而信物作為一種重要的舞臺道具擔負起了這一重任。如《雙螭璧》中裴碩以祖?zhèn)麟p螭璧,一枚予正宗佩于身,另一枚給梅氏。雙璧分散又復合,也由此得知宗文、延宗為兄弟。裴碩將雙螭璧送給侄子裴正和梅氏,整部傳奇開始圍繞雙螭璧展開具體敘事,最終一門榮顯,雙璧復合。再如《墜釵記》中崔嗣宗與何興娘訂婚約時以金鳳釵為憑,十五年后,崔嗣宗在給何興娘上墳時在地上又撿到金鳳釵,開始了人鬼相戀的故事。從《雙螭璧》《墜釵記》這兩部傳奇的劇名便可知雙螭璧和金鳳釵在整部傳奇中的重要性,雙螭璧和金鳳釵在傳奇劇目中作為重要的舞臺道具,它們的存在牽動著故事的后續(xù)發(fā)展,是故事情節(jié)得以深入發(fā)展的關鍵點。
四、結(jié)語
信物作為明清傳奇中的舞臺道具,其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信物作為人物彼此之間的盟證,通常會被寄予美好堅貞的情感。最重要的是,信物在明清傳奇中具有重要的敘事作用,特別是一些傳奇劇目內(nèi)容豐富,人物角色眾多,借助信物鋪陳敘事,從時間、空間上都能夠成功助推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信物的出現(xiàn)更是增加了傳奇的傳奇性與曲折性。傳奇中信物數(shù)量頗豐,但也使很多故事情節(jié)囿于固定模式,即主人公在落難之時被迫分離,最終又依靠信物走向大團圓的美好結(ji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