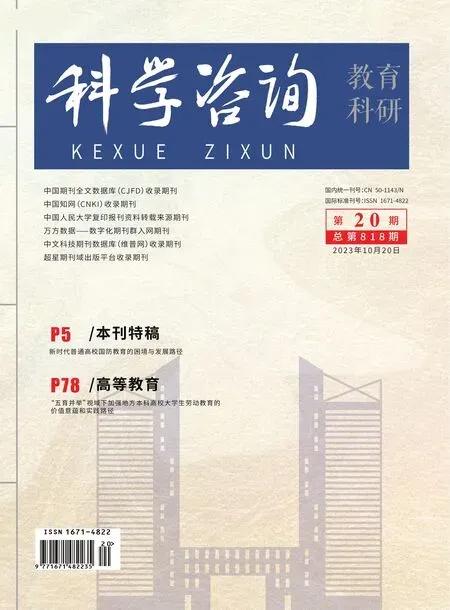高職公共英語分層教學的探索緣起、實踐現狀及未來方向
——基于2012 年至2022 年期刊文獻的綜述研究
趙苗苗,孫治國
(青島工程職業學院,山東青島 266100 )
近年來,隨著高職擴招,生源結構呈現多元化特征。不同生源和專業類別學生的英語水平差異明顯,且分化進一步加強,學業需求也不盡相同。統一的教材和教學進度,相同的課程標準、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單一化的教學模式和大班授課方式,已無法滿足學生的個性化學習需求,對于質量保證,產生巨大挑戰。早在2009年,《高等職業教育英語課程教學要求 (試行) 》就明確要求:“大學英語教學應貫徹分類指導、因材施教的原則。同時,《高等職業教育專科英語課程標準( 2021年版) 》強調“課程內容與專業實踐、職場需求對接”,“創設與行業企業相近的教學情境”。而傳統的“大一統”人才培養方式既不能滿足社會對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培養需求,也難以滿足學生個性化發展需要[1],因此高等職業院校公共英語分層教學改革,勢在必行。
一、研究方法及研究樣本
分層教學是高職院校公共英語教學改革討論的瓶頸困難所在。特別是在當下生源英語基礎普遍存在較大差異的情況下,英語分層教學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對學界的諸多討論也需要進一步梳理。鎖定研究對象后,借助中國知網搜索引擎,分別輸入一級主題“高職”,二級主題“公共英語”和三級主題“分層教學”,按照刊發的時間維度統計,以十年為跨度,共收集了2012年到2022年5月,關于高職公共英語分層教學的相關研究數量共計數225篇,其中核心期刊23篇。研究兼數量研究和內容分析的方法,根據中國知網數據庫中提取的相關文獻和論文,梳理近10年我國高職院校公共英語分層教學的緣起、實踐現狀及未來方向,剖析該領域研究的發展趨勢,為進一步開展教改實踐和完善相關研究,提供堅實的基礎和概括性依據。
二、數量分析
梳理和回顧側重于三個方面:核心期刊間關注度差異、研究年度間差異和研究主體、研究層次分析構成。
(一)核心期刊間關注度分析
十年間,《職業技術教育》對高職公共英語分層教學關注度較高,刊發文獻數4篇;其次是《教育理論與實踐》和《教育與職業》3篇;《職教論壇》和《中國成人教育》2篇,位居第三,剩余《外語界》《外語電化教學》《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等核心期刊相關文章僅1篇。核心期刊發表文獻總量較少,核心期刊之間,在刊載數量,即關注度上,存在明顯差異;職業教育相關核心期刊相對略占優勢,但外語類核心期刊關注度相形見絀,差強人意。
(二)研究年度間差異分析
十年間的整體分布呈現不均衡的特點。如圖1所示,對高職公共英語分層教學關注的最高峰值出現在2016年,其峰值為39篇(單位,下同);2022年(截止到5月)為最低谷值,數值僅為3。第二個峰值出現在2013年,數值為28。另一次級谷值,臨近當下,出現在2021年,數值也僅有6。

圖1 年度間研究數量分析
2016年峰值,至2017年并延伸至2019年三年的平原期,一路急轉直下,跌至谷底,不均衡的年度發表數量分布表明,高職院校公共英語分層教學研究的關注度正在逐漸走低,似乎瓶頸使然。更不盡如人意的是,相較于高職在校生數量不斷攀升的現狀而言,實踐研究總量不足乃至缺位;或者說,與高職在校學生數量的現狀和增加趨勢呈現出極不匹配的背后,不禁發問:這種不匹配的現狀,研究逐漸缺位失當的趨勢是否能夠支撐高職公共英語教育教學的有效性開展?是否能夠適應生源情況的不斷變化、支撐專業培養方案的深化提升?等等諸多問題,都成為實踐者與學界不可回避、又難以簡單回答的問題了。
(三)研究主體與研究層次分析
從研究的層次和研究主體來看,學術期刊210篇,學術論文12篇。高職院校參與度相對而言略占優勢,但總量仍然偏低。聚焦于此的學位論文,集中在碩士層次,雖為數不多,但多為實證研究,也更具實踐參考價值。截至2022年5月,參與高職公共英語分層教學的院校及其發表論文總篇數,排名前三位的是重慶輕工職業學院(5篇)、四川職業技術學院(5篇)和北京農業職業學院(4篇)。排名靠前,也是相對而言,整體量分攤于十年研究統計跨度,則微乎其微。此外,就研究主體而言,應用型本科院校嶄露頭角,例如,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2篇)和烏魯木齊職業大學(2篇);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也有所體現,例如,西北農林科技大學(3篇)、青島大學(2篇)和湖南農業大學(2篇)。非全日制終身教育領域高校——貴州廣播電視大學也參與到研究之列。
三、內容分析
把關鍵詞結合文章的研究內容進行合并歸類后,又做了量化統計,發現國內高職院校對于公共英語分層教學的研究焦點分別是分層教學模式、分層教學內容分析、分層考核評價。
(一)分層教學模式
目前高職院校的公共英語分層教學模式研究的焦點,從宏觀上主要分為顯性分層、隱性分層和混合式三種教學模式。
1.顯性分層
縱觀近十年文獻,顯性分層教學模式研究主要聚焦于“走班制”和分類分層,但多為理論研究,實證研究相對較少。部分院校實行動態的“走班制”,即學生分層、備課分層、教師混層教學和分層評價等。分類分層是指結合專業大類學情特點和人才培養方案,采取分層課程標準、分層課程內容、分層教學設計和分層考核。崔紅等創新性提出“構建“1+X”課程群,分層次、分階段、分專業逐步實踐“CET就業導向+ESP職業取向+國際人文素養”的多元教學層次和類別。[2]顯性分層“僅解決了群體性差異問題,沒有關注分層后班級內部的個體性差異”[3],可能給學生帶來的負面心理效應。同時,顯性分層教學特別是動態“走班制”也給教務系統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2.隱性分層
隱性分層教學則不再依據成績打亂原有的自然班劃分。隱性分層教學的實證研究,多聚焦班內隱性分層、顯性分組和動態調整的動態隱性分層教學模式。其中,OOCIE 隱性分層教學模式,強調從五個維度進行隱性分層,形成循環交替、螺旋上升的教學閉環。[4]此外,教學理論與隱性分層教學的有機結合逐漸受到關注。周卓林等開展了基于項目導向的隱性分層教學模式研究,通過校本教材內容的模塊化、層次化編排,創設以工作場景為載體的職業英語分層學習項目。[5]胡寶菊探索了學生根據任務難度系數自主選擇探究任務、自主分組的班內分層教學模式。[6]顯而易見,隱性分層教學的關鍵在于教師能否對教學內容進行有效整合和重構,確定分層目標,進行分層施教,實施個性化輔導和多維度評價。
3.混合式分層
自2012年起,基于信息化手段和網絡環境的混合式分層教學模式研究呈增長態勢。諸多高職院校開展了基于微課、慕課、云教學平臺、翻轉課堂等混合式分層教學模式實證研究,特別是基于SPOC的分類、分層、分模塊的混合式教學模式受到普遍關注。數字技術賦能高職公共外語分層教學的態勢,改變了傳統隱性和顯性的二元特征,向著混合多元、動態多變方向嬗變。
(二)分層教學內容分析
基于高職公共英語教學開展的諸多內涵因素,分層教學內容方面的實踐和探索主要包括教學內容和教學目標、教學設計和教學方法、教學評價等三個方面。
1.教學內容和教學目標
大部分高職院校針對不同層次學生的學習需求和學習能力,采用教學內容分層,教學目標分類。根據多元化生源和不同教學階段,選擇不同的教材,制訂分類分層課程標準和教學內容。部分有條件的院校結合各專業群的特點和人才培養方案,開發了職業英語或行業英語活頁式校本教材,創建了分類分層的公共英語課程在線教學資源庫。
不同層次學生的教學目標采取不同的教學目標。針對A層次學生教學目標是注重聽說讀寫能力的培養和英語綜合運用能力的提高,為大學英語四級考試和專升本考試做好語言知識和技能儲備。針對B層次的學生,注重培養聽說能力,使之能夠聽懂和進行簡單的日常對話,同時鼓勵學生參加高等學校英語應用能力等級考試。對于C層的學生,聚焦基本詞匯、句型和語法、培養該部分學英語學習興趣和進行必要的學法指導,保證學生順利通過階段性測試和期末考試。
3.教學設計和教學方法
分層教學的關鍵所在是教學設計。諸多院校關注分類分層,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設計。課前,教師通過推送分層學案、分層微課、分層測試和分層討論等引導學生自學。同時,根據教學平臺數據反饋,及時調整教學重難點。課中,設置分層練習、分層任務促進小組成員間的互動交流合作學習。課后,布置多樣化的分層拓展作業,培養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提高英語應用能力。
在教學方法上,基于精準學情分析,采取差異化和多元化的課堂教學方法。大部分研究聚焦任務教學法、項目教學法、交際教學法和行動導向法等在詞匯、閱讀,聽說和寫作分層教學中的應用。
4.教學評價
在考核評價方面,強調采用分層的,動態的,連續的形成性評價和終結性評價相結合。采取測試分層,考核維度分層,強調過程性評價和增值評價。構建“學習—診斷—改進”一體化的英語分層教學與學習評價模式。同時,結合職業院校“崗課賽證”融通育人模式探索,陳永莉探索了基于課證融通,“以考促學”分層教育教學考核新路徑。[7]
四、問題與對策研究
(一)建立生源分類分層機制,實現以學定教分層施教
大部分高職院校已實施公共英語分層教學,各層次的區分度不明顯。部分院校依舊按照高考成績、入校摸底考試成績或生源類別進行強制分層教學,沒有考慮學生的多元化學習需求和職業需求。淡化強制分層,實施柔性分層。基于專業群人才培養需求和學生學習需求,實施專業群內縱向分類、班級內橫向分層的分類分層動態機制。同時,從基礎英語、職場英語和專門用途英語等三個模塊分層分段地設計教學內容。
(二)探索中高職一體化英語課程銜接,構建分層分段式培養模式
目前,中高職院校英語課程人才培養目標不銜接,課程體系不統一。應采取分層分級培養,既不斷層又各有側重的一體化設計思路。一方面,中職英語課程應突出英語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夯實和提高,以破解當前以補修先前知識和技能為主的高職英語教學現狀。另一方面,高職英語課程應結合不同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制訂分層分段式技術技能復合型人才。
五、結束語
職業教育是一種類型教育。在當前產教融合、校企共育的背景下,公共英語作為一門必修課必須與各個專業群的教學有機融合。通過教學團隊分層集備,編制各專業大類的“公共英語”課程標準、課程整體設計和考核方案,實施專業群分類,英語水平分層,使用基于工作場景的情境化教學,任務模塊化和項目化教學,采用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模式,遵循以學定教,以學導教,才能將高職院校公共英語分層教學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