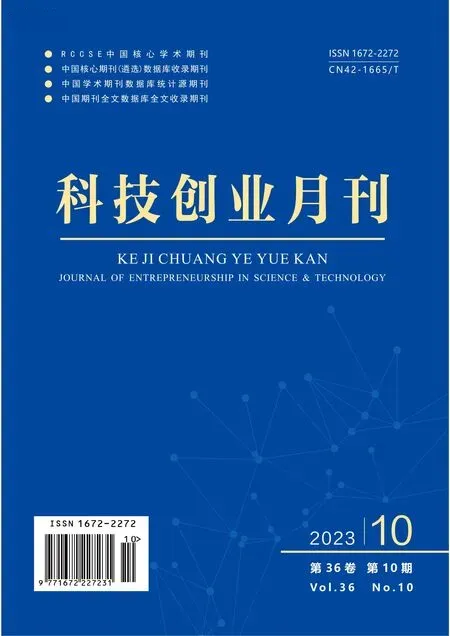國家文化與創業者資本對創業活躍度的組態效應
許志燕
(東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89)
0 引言
創業活躍度作為衡量創業積極水平的重要指標,一直受到創業研究者的關注[1]。不同國家創業活躍度的差異受宏觀經濟發展、制度、文化,以及創業者認知、資源稟賦等微觀層面的影響。越來越多學者開始將國家文化納入創業領域跨國研究的前因。此外,微觀層面的創業者資本對創業活動的影響極為突出。
根據資源基礎理論,資源能塑造對新商業機會的認識與考慮,并為企業家提供完成各種工作的能力,從而直接影響創業者的決策[2]。國家文化和創業者資本可以通過提供資源支持稟賦,系統地促進或抑制個人參與各種創業行動的能力[3-4]。然而,以往關于國家文化、創業者資本影響創業的研究局限于單一層面,將文化和創業者資本視為獨立維度的集合而非相互關聯的復雜模型,忽略兩個層面的多重因素并發對創業的影響,導致結論不一致。
不同于傳統回歸方法關注變量層面的凈效應,定性比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從整體論出發,探究導致特定結果的前因條件組合,適于研究多個層面協同聯動對創業活動的影響機制。鑒于此,本文引入QCA方法,探討分析以下問題:國家文化和創業者資本的各個維度是否構成高創業活躍度的必要條件?國家高創業活躍度存在哪些路徑?多個維度如何相互作用并結合起來影響國家創業活躍度?
1 文獻綜述與模型構建
文化是信念、價值觀和預期行為,它影響人類的思想,并為人們在社會環境中應如何行事提供指導原則[5]。國家文化被認為是影響創業活動涌現和經濟發展的重要非正式制度[6]。一方面,它塑造社會和政治系統的組織,這些組織可以鼓勵或限制創業者行為;另一方面,它也影響個人在冒險、主動性和獨立判斷等的行為與方式,在創業領域,這些行為與方式與創業意愿、機會識別、機會利用以及資源整合密切相關。
本文將霍夫斯泰德的4個文化價值觀維度(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規避、個人主義和男性化)作為測量國家文化的框架,主要出于以下原因:①該框架已被廣泛用于商業實踐,特別是創業活動,與本文研究主題非常吻合;②它是學者廣泛使用的測量維度[7],大多數跨文化研究都使用該文化價值觀框架; ③它為表征文化提供了被普遍接受和定義的術語[8],不同的文化研究維持并擴大該文化類型學,而非與之相矛盾。
研究表明,文化影響著個人資本和創業之間的關系。創業知識溢出理論是創業企業知識生產的主導理論,此理論通過引入創業吸收能力概念得到擴展。這表明,除了知識溢出之外,新企業創建取決于創業者內化知識和創造成功商業想法的能力。有關知識資本和創業資本的研究表明,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促進創業活動[9]。
綜上所述,國家文化與創業者資本對創業活動都有重要作用。但是,現有研究對兩個層面,要素如何聯動影響創業的機制尚不明確。鑒于此,本文整合國家文化與創業者資本兩個層面,探索影響國家創業活躍度的因果復雜機制。構建的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國家文化與創業者資本對創業活躍度的組態效應模型
1.1 國家文化層面
1.1.1 權力距離
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是指組織和機構中權利較小成員接受和期望權利不平等分配的程度[10]。在權利距離較高的社會中,地位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利分配不平等被認為是自然的。在強大等級秩序下,上級在做決策時不需要與下屬商量,下屬參與決策程度低。當權力距離較低時,等級制度趨于扁平,上級與下級之間更加平等,從而出現了更多的聯合決策過程。在這種環境下,人們努力平衡分配,并要求為權利不平等提供理由[11]。
在高權力距離文化中,人們高度重視權利與地位,創業者可能不考慮其他利益相關者(例如員工、投資者、消費者)的需求,以此來最大程度地增加自身的財富、聲望以及社會地位。這種將個人利益凌駕于企業利益之上的做法,將對創業企業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此外,權利距離高的社會中,不同網絡成員之間的信任傾向較低。相反,在不接受權利集中和地位特權的社會中,創業者更熱衷于利用個人資本解決問題、積累資源,他們認為減少不平等的權利分配是可取的。已有研究表明,低權利距離的文化更有利于創業,因為社會對創建創業項目持更開放的態度[12]。
1.1.2 不確定性規避
不同于風險規避,不確定性規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涉及的是社會對不確定性和模糊性的容忍度,被定義為“一種文化的成員對不確定或未知感到威脅的程度”。企業雇傭具有更強的限制性,而自主創業是實現更高自主權和財務回報的機會。
而處于低不確定性規避文化中的人們更習慣沉思、冷靜,所處的環境并不要求他們表達情感。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社會運行規則較少,實踐相比原則更重要。因此,這些國家更善于應對風險,更有可能啟動創業項目。
1.1.3 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與它的對立面——集體主義(Collectivism),是指社會中人們融入群體的程度。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分別涉及“我”和“我們”的自我概念:個人主義意味著“我”,而集體主義則與“我們”聯系在一起。在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個人的經驗、才能、知識和目標是獨一無二的。在這種環境下,人們之間的聯系是松散的,人們優先考慮個人利益而不是集體利益。相反,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人們將自己視為“我們”(例如家庭、工作單位、社區)中的一員,強關系網絡廣泛地建立在群體成員的基礎上。在這種文化中,人們重視長期的群體關系,按照群體規范行事以保持一致性,并將集體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
在創業過程中,個人主義文化意味著工作以合同為基礎,人際關系松散,忠誠度較低[13]。利益相關者很可能用成本收益分析作為衡量個人利益的首要標準,以此來決定是否終止關系[13]。相反,在集體主義文化中,利益相關者,尤其是員工會與公司建立密切的工作關系和高度的參與度,創業者也會考慮他們的需求、愿望和滿意度。
1.1.4 男性化
男性化(Masculinity)和女性化(Femininity)指的是男性價值觀和女性價值觀的程度。男性化文化強調的是獨立思考、自信、成功、果斷、競爭等,它努力建立以目標、任務、績效為導向的社會,并利用正規化的程序和規則來避免群體沖突與混亂。在男性價值觀念下,人們習慣自力更生,追求合作的傾向較低。盡管創業者努力行動,可能對個人成長產生積極影響,但這種行為是基于對眼前利益的渴望,從長遠來看,以自我成功為導向的行為,最終會抑制創業企業發展。
女性化文化基于社會關系,強調的是謙虛、信任、團結、合作、低沖突和社會支持。不同于男性化文化強調自我,女性化考慮的是群體關系,試圖建立個體行為以共同利益為導向的社會。
1.2 創業者資本層面
1.2.1 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理論最初是為了估計員工在人力資本投資中的收入分配,它假設人們從他們的人力資本投資中獲得補償。因此,個人在擁有人力資本情況下,會努力使經濟利益最大化。該理論已被創業研究廣泛采用,這些研究將人力資本納入他們的創業成功預測模型。
人力資本涉及人們的教育、經驗和技能,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創業的關鍵資源。首先,人力資本提高人們發現和開發商業機會的創業能力[14];其次,人力資本可以建立廣泛的知識基礎,使個人能應對突發情況,提高新創企業的生存能力[15];第三,人力資本是實現自身價值增值的先決條件,有助于創業資源進一步優化配置[16]。
1.2.2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是作為個人參與社會結構的功能而發展,這些社會結構由親人、朋友、同事等組成。社會資本反映網絡連接的程度,它描述的是關系資源,能為個人提供信息、合法性、信任和情感支持等[17]。
創業者社會資本的一個重要形式是與其他創業者的網絡聯系,值得注意的是,與其他創業者有聯系網絡的個體往往更具創業精神,因為這些網絡為創業者提供重要的建議。例如,社會資本幫助創業者發現新商機、創造新業務;創業者利用網絡支持、協作和聯盟來建立共識、獲得資源[18]。
2 研究方法
2.1 fsQCA方法
本文選擇fsQCA方法來分析數據,主要基于以下3點原因:①QCA方法基于布爾代數和集合理論,將案例視為條件的組態,來推導特定結果的因果配方[19],有助于揭示因果復雜性現象;②QCA方法綜合定量(變量導向)和定性(案例導向)方法的優點,適合分析中小樣本;③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既能處理類別(Kind)問題,又能處理程度(Degree)問題,考慮到所用樣本數據的連續性特點,選擇fsQCA方法進行探究。
2.2 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來自全球創業觀察(GEM)和霍夫斯泰德文化中心的數據。數據甄選和處理步驟如下:①從2015-2017年APS數據庫篩選創業活躍度、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數據,從霍夫斯泰德文化中心數據庫篩選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規避、個人主義和男性化指標數據;②對兩份數據進行匹配,保留56個案例;剔除沒有連續3年參與調研的國家,最終保留39個案例。
2.3 測量與校準
2.3.1 測量
結果變量。創業活躍度使用全球創業觀察APS中的總早期創業活動(TEA)率來測量,它是指在18~64歲人口中,剛起步的創業者或新企業管理者所占的百分比。
前因條件。國家文化的4個要素:使用霍夫斯泰德文化中心的權力距離(PDI)、不確定性規避(UAI)、個人主義(IDV)和男性化(MAS)4個指標來衡量。
人力資本。使用全球創業觀察APS中的調查項在18~64歲人群中,認為自己具備創建企業所需的技能和知識的百分比測量。
社會資本。使用全球創業觀察APS中的調查項在18~64歲人群中,認識兩年內創業的創業者的百分比來測量。
2.3.2 校準
本文使用直接法進行校準。借鑒已有研究,將樣本描述性統計的下四分位數(25%)、中位數和上四分位數(75%)分別作為結果變量和前因條件完全不隸屬、交叉點與完全隸屬的校準點。各變量的校準閾值和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校準閾值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3 分析結果
3.1 必要條件分析
表2展示了必要條件分析的結果。單個條件必要性的一致性分數均小于0.9,說明不存在產生高創業活躍度和非高創業活躍度的必要前因條件。

表2 必要性檢驗結果
3.2 組態分析
將一致性閾值設置為0.8,案例頻數閾值設置為1,PRI閾值設置為0.7。在反事實分析階段,由于缺乏確切的理論和證據,本研究假設單個要素的存在與否都可影響高和非高創業活躍度。表3展示了QCA的分析結果。

表3 條件組態的充分性分析結果
3.2.1 產生高創業活躍度的組態
低權力距離和低不確定性規避文化下人力資本驅動型。在組態S1中,低權力距離、低不確定性規避和高人力資本為核心條件,個人主義和低社會資本為邊緣條件。屬于這一組態的典型國家是美國。首先,在強調相互依賴、關系平等的低權利距離文化中,不同網絡成員之間的信任傾向較高[13],創業者可以在外界建立廣泛的關系基礎以此獲得外部資源,彌補社會資本不足;其次,高人力資本提供的創業知識保障,加之低不確定性規避文化,使創業者面對未知的創業環境不會感到緊張與焦慮;最后,個人主義文化使得創業者更加自主和獨立,可以自由地做出資源分配的決策[5],而不會受到強大的群體規范的影響和干預。
低不確定性規避和女性化文化下的人力與社會資本驅動型。在組態S2中,低不確定性規避、女性化和高人力資本為核心條件,集體主義和高社會資本為邊緣條件。屬于這一組態的典型國家是印度尼西亞。首先,在女性文化中,通過個人社會網絡的信息共享普遍存在,創業者通過開放溝通獲得外部資源,最終通過合作實現雙贏,這與社會資本產生的信任和互惠相輔相成;其次,鑒于信息和知識在創業過程中的重要性,集體主義背景下的創業者對隱性知識更敏[13],與此同時,人力資本中先驗知識的存在使創業者的警覺性更高,能盡早發現商機;最后,低不確定性規避使創業者更善于應對風險。
高不確定性規避、集體主義和男性化文化下的人力與社會資本驅動型。在組態S3中,高不確定性規避、集體主義、男性化和高人力資本為核心條件,高權力距離和高社會資本為邊緣條件。屬于這一組態的典型國家是哥倫比亞。首先,創業者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挑戰與不確定性,在集體主義環境下,高不確定性規避會促使創業者結成聯盟,以努力減少不確定性,例如,技術聯盟使創業公司能獲得關鍵資源,從而減輕創業企業面臨的持續技術變革挑戰的焦慮;創業團體還可以與政府溝通來解決存在的問題,以降低風險和不確定性[13];其次,男性化文化強調的是自信和成功,創業者會努力行動,不斷豐富人力資本,這將對創業活動產生積極的影響;最后,高權利距離限制創業者與社會中某些人和組織的直接接觸,例如,威權關系的普遍存在,導致國家和地方政府不太愿意與創業公司接觸,這促使創業者只能通過社會資本尋找資源。
3.2.2 產生非高創業活躍度的組態
本文檢驗了導致非高創業活躍度的組態。組態NS1a表明,在高權力距離、低不確定性規避、個人主義和男性化的文化中,缺乏社會資本會導致低創業活躍度。組態NS1b表明,在高權力距離、高不確定性規避、個人主義和男性化的文化中,即使存在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創業活躍度也不會高。組態NS2表明,在低權力距離和個人主義的文化中,缺乏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會導致低創業活躍度。組態NS3a表明,在低權力距離、高不確定性規避和男性化的文化中,缺乏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會導致低創業活躍度。組態NS3b表明,在低權力距離、高不確定性規避、個人主義和男性化的文化中,缺乏人力資本會導致低創業活躍度。組態NS4表明,即使存在社會資本,但在高不確定性規避、集體主義和女性化的文化中,缺乏人力資本也會導致低創業活躍度。
因此,產生高創業活躍度的組態與產生非高創業活躍度的組態存在非對稱性關系。
4 結論、啟示與展望
4.1研究結論
本文圍繞創業活躍度受何種國家文化和創業者資本聯合驅動的問題,以2015-2017年參與全球創業觀察(GEM)和霍夫斯泰德文化中心調研的39個國家為樣本,從制度理論視角和知識資本視角出發,基于組態思維整合國家文化和創業者資本層面的6個前因條件,構建國家文化與創業者資本對創業活躍度的組態效應模型,并應用fsQCA方法探究影響國家創業活躍度的復雜因果機制研究,獲得以下結論。
首先,單個國家文化要素和創業者資本要素不構成高創業活躍度的必要條件,但提高人力資本對產生高創業活躍度發揮著較為普適的作用;其次,3條路徑產生高創業活躍度,分別是低權力距離和低不確定性規避文化下的人力資本驅動型;低不確定性規避和女性化文化下的人力與社會資本驅動型;高不確定性規避、集體主義和男性化文化下的人力與社會資本驅動型;最后,6條路徑導致非高創業活躍度,并與產生高創業活躍度的路徑存在非對稱關系。
4.2 理論貢獻
通過分析國家文化與創業者資本對創業活動的協同聯動機制,不僅發現了產生高創業活躍度路徑,豐富了制度理論和知識資本視角在創業活動中的發現;而且揭示宏觀制度環境與創業者微觀主體聯動影響創業活動的機制,避免以往單一視角研究致使研究結論不一致的困境。
本文采用QCA方法考察國家文化和創業者資本與創業活躍度的關系。充分利用了QCA方法在探究要素間耦合關系的優勢,不僅有助于加深對 “多重并發” “殊途同歸”等復雜因果關系的理解,還為研究文化與創業問題提供借鑒參考。
4.3 實踐啟示
國家文化是長期歷史和社會演化的產物,創業者嵌入在特定的文化氛圍中,應利用適宜的個人資源稟賦來支持創業活動。研究表明,高創業活躍度路徑并不是非高創業活躍度路徑的對立面,單個條件也并不構成高創業活躍度的瓶頸。因此,提升創業活力不能僅僅依靠增加或減少某一個要素,必須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文化情景與個人資本的獨特性,以此提升創業活力。
4.4 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采用來自全球創業觀察(GEM)和霍夫斯泰德文化中心的二手數據,案例數量受限,未來可綜合多種來源的更多數據,擴大案例數量,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有限多樣性問題。
本研究關注的是跨國差異,未來可開展本土化研究。歷史、民族文化以及對外開放政策的差異,導致了我國不同地區文化的多樣性,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分析中國本土文化情境與其他層面協同聯動對創業活動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