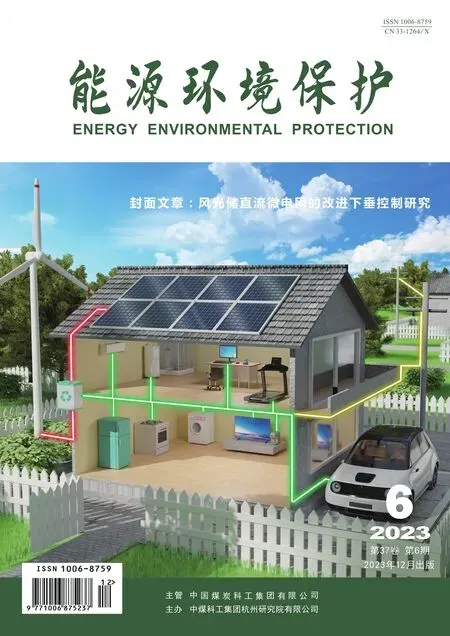水產養殖廢水深度脫氮研究進展
由 昆, 覃發揮, 李 倩, 郭建林, 劉 鷹,肖 艷, 劉德釗, *
(1. 沈陽建筑大學 市政與環境工程學院, 遼寧 沈陽 110168;2. 浙江省淡水水產研究所,浙江 湖州 313001;3. 浙江大學農業生物環境工程研究所, 農業農村部設施農業裝備與信息化重點實驗室, 浙江省農業智能裝備與機器人重點實驗室, 浙江 杭州 310058;4. 中煤科工集團杭州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1201)
0 引 言
進入新世紀,我國水產養殖業迎來了政策利好,現已成為我國漁業生產的主體。據官方最新統計,2022年全國收獲6 800萬余噸水產品,其中八成以上為養殖產出,遠超同期捕撈產品產量。不僅如此,我國水產養殖占地較去年進一步擴大,已達7 107.50千公頃。
水產養殖業每年排放的廢水數以億噸計,因而導致了不容忽視的環境和病害問題。根據《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我國水產養殖業化學需氧量排放量是工業源的0.73倍,達66.60萬噸,總磷排放超過1.6萬噸,同時總氮排放接近10萬噸[1]。養殖廢水帶來的氮污染往往最容易被人們忽視,約75%~80%的剩余餌料、魚蝦類的排泄物等以氨氮和有機氮的形式殘留在養殖水體中[2]。養殖尾水裹挾的污染物尤其是氮元素的過量排放,對水生生態環境具有極大的隱患。此外,養殖水體中以氨氮和亞硝態氮為主要危害源的三態氮對養殖水產品均具有毒性,任其在養殖環境中停留積累,也勢必會降低水產品的品質及產量。因此,為了保障水產養殖業良性、可持續發展和減少對自然環境的危害,必須對養殖水采取合理、經濟可行的處理措施。近年來,循環水養殖(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System,RAS)受到諸多政策利好和扶持,作為未來養殖行業發展的主力軍,其養殖水處理工藝,既反映了該系統的先進性,也是行業健康發展的核心環節。圖1展示了目前常規的循環養殖水處理工藝流程,及三態氮的轉化、排放過程。

圖1 循環水養殖系統水處理工藝Fig. 1 Water treatment process of 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system
常見的機械過濾、泡沫分離、紫外消毒、臭氧凈化、電化學法等物理化學技術,或活性污泥法、生物膜法衍生出的各種工藝都被廣泛應用于水產養殖水凈化領域[3],也可利用濕地生態系統、魚塘水生生態系統以達到凈化效果。在實際生產運行中,往往采用多種不同原理的工藝技術相互組合,對污染物質的去除會更加有效。這其中,生物脫氮由于其成本低、綠色環保、無二次污染等優點被公認為是經濟有效和具有發展前途的方法之一[4]。硝化作用是目前大多數生物濾器的首要設計功能,可將毒性較強的氨氮和亞硝酸鹽氮氧化,然而其產物硝酸鹽在養殖水體中不斷累積,會導致魚類等養殖對象生長減緩等問題[5]。采取養殖水缺氧或厭氧下的脫氧工藝以實現生物反硝化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策略,然而實施此工藝增加了昂貴的設備采購投入、運行及維護成本。因此,如何經濟高效地實現水產養殖水深度脫氮,既是痛點又是行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本文介紹了以下4種常用的生物脫氮技術原理及其在水產養殖水深度脫氮的應用,重點分析了同步硝化反硝化及好氧反硝化理論與實踐,并對前沿技術進行了展望,以期為水產養殖行業廢水深度脫氮提供參考。
1 水產養殖廢水深度脫氮技術原理
目前,水產養殖廢水深度脫氮研究大多還停留在實驗室試驗、小試階段。本節引入了目前常見的幾種深度脫氮技術原理及其應用情況,并簡要分析了其優缺點。
1.1 傳統硝化反硝化
傳統脫氮原理圖如圖2(a)所示。一般理論認為,硝化和反硝化對溶解氧的要求不一致,通常將兩個反應獨立或分隔在溶解氧不同的好氧區和缺/厭氧區分別進行,若反應裝置在時間上滿足周期性好氧和缺氧環境,二者也可序列進行,簡而言之,即硝化、反硝化在同一環境中不能同時發生[6]。基于該理論,朱厲等[7]針對淡水魚塘養殖用水的水質凈化問題,研制出一種一體式厭氧/好氧曝氣生物濾池(Biological Aerated Filter,BAF),總氮脫除達78%以上,養殖水環境可以得到極大地改善。

圖2 水產養殖水深度脫氮技術原理圖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deep denitrification technology for aquaculture wastewater
1.2 好氧反硝化
好氧反硝化菌是ROBERTSON等[8]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最先發現,顛覆了嚴格厭氧菌這一傳統認知。同時,也為富氧水產養殖廢水的反硝化提供了一種新思路。溶解氧不會過分干擾反硝化進程,好氧反硝化便能有效簡化脫氮進程中對氧氣環境的要求[9]。從微觀-微生物的角度分析,是兩種脫氮理論對應的不同優勢菌屬的差異。好氧和缺氧反硝化菌的主要區別在于它們對氧的敏感性。對于缺氧反硝化菌,氧氣的存在會抑制反硝化酶或改變其基因表達,導致反硝化菌活性完全停止,而好氧反硝化菌則不會,圖2(b)從電子傳遞角度描述了二者的區別[10]。圖2(c)及表1從酶作用機理層面表述了好氧反硝化菌深度脫氮的過程。

表1 好氧反硝化反應中的酶和基因[10]
1.3 同步硝化反硝化(SND)

1.4 短程硝化反硝化


宋宏賓等[16]也利用短程硝化反硝化理論建立起一套可編程邏輯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CL)控制的連續流-三級生物膜工藝,以應對水產養殖廢水C/N較低的局面。實驗發現,進水pH 7.5~8.5, 溫度28~32 ℃,溶解氧0.5~1 mg/L,游離氨5~10 mg/L的條件下,不投加任何碳源即可實現低C/N養魚廢水的生物脫氮。此外,該工藝對COD的平均去除率也接近95%,出水各項指標可以達到回用標準。該試驗是水產養殖廢水短程硝化反硝化脫氮的經典案例,為后續研究乃至中試、實際工程應用提供了寶貴的參考價值。

1.5 傳統生物脫氮的優勢及其局限性
傳統生物脫氮技術經過幾十年的研究應用與發展,目前已經比較成熟,脫氮穩定性好,但也有著其局限性。
一般認為反硝化菌為異養型微生物,需要充足的碳源維持其活性。水產養殖廢水通常C/N不高,碳源成為了限制反硝化效率的最重要因素。此外,脫氮過程分成了硝化和反硝化兩個系統,需要的設備龐大,占地面積大,建造成本高,前期投資需求大,工藝流程較長,條件控制也更復雜。目前也有對水產養殖廢水從事傳統生物脫氮的研究,但從成本角度考慮,好氧反硝化及SND更具實際應用價值和研究潛力。
2 SND關鍵影響因素
前文分析指出,由于多種特殊微生物的存在,全程、短程及好氧反硝脫氮皆可能在SND過程中出現,即SND深度脫氮集結了多種脫氮原理及途徑,是實現養殖水脫氮最具研究價值的方式之一。因此,有必要對SND的關鍵影響因素和參與其中的菌屬加以探究、歸納和總結,以更好地為實際應用提供理論依據和指導。溫度、pH、DO和C/N是最直觀的控制因素,它們的最佳控制范圍和參數組合往往需要在實驗和工程實踐中探索確定。
2.1 溫度、pH及游離氨濃度
溫度影響細菌酶的活性,因此能控制SND脫氮速率和效率[17]。通常認為硝化細菌可適應10~35 ℃的溫度范圍[18]。而硝化、反硝化反應的適宜溫度為20~30 ℃,此外,pH的波動會影響細菌對營養物質的吸收程度、改變酶的活性[19]。氨氧化細菌(Ammonia-Oxidizing Bacteria,AOB)和亞硝酸鹽氧化細菌(Nitrite-Oxidizing Bacteria,NOB)一起推動生物硝化過程,如圖2(a),二者統稱為硝化細菌[20]。AOB與NOB的適宜pH分別是7.0~8.5與 6.0~7.5,反硝化細菌(Denitrifying Bacteria,DNB)的最適宜 pH 在7.0~8.5[17]。劉俞辰等[21]在SBBR反應器中研究SND,發現pH為8時脫氮效果最佳。選取不同反應裝置、水質參數的相互組合以及不同的評判指標(脫碳率、脫氮率、SND效率)等,最佳pH往往并不固定。pH還會影響水中游離氨(Free Ammonia,FA)的水平,FA即氣態NH3,會抑制硝化細菌的活性,其中NOB更敏感,當其余條件一定時,提高pH會引起FA濃度升高,進而抑制NOB的活性,阻礙硝酸鹽的生成,利于實現短程硝化[20]。
2.2 DO濃度
硝化及有機物的分解過程需要好氧微生物的參與,要求系統中DO濃度不能太低,否則會導致硝化細菌活性不高、硝化過程緩慢,氨氮無法有效轉化為亞硝酸鹽和硝酸鹽。反之,任由DO濃度升高又會使氧的穿透能力增強,不利于在反應器死角、活性污泥或生物膜內部形成缺氧微環境,DO濃度梯度不明顯;其次,異養型細菌因為溶解氧充足,增殖的過程會加速有機物的消耗,以致反硝化細菌可能會缺乏碳源,活動受限[22]。與此同時,硝化細菌同異養型細菌競爭O2時總處于劣勢,不利于硝化反應。薛武丹等[23]計算了不同DO 濃度下變速氧化溝SND比率的理論值,結果表明,當DO 濃度分別為1.2、1.0、0.8 mg/L 時,理論值均在45%~51%之間,與實測值偏差在10%以內。事實上,采取不同的工藝類型、處理不同成分的水質都會影響到最佳DO濃度范圍的選取,需要在實驗和工程實踐中反復驗證。
2.3 C/N


表2 不同C/N下同步硝化反硝化總氮去除率
總結以上案例,C/N比值往往越高,SND效率也隨之提高;缺氧反硝化和好氧反硝化可以同時發生,也就是說,SND可能伴隨發生好氧反硝化反應,這也與前文的推測相符;即使在一些C/N不高的反應系統中,仍可以通過合理的參數控制,實現很高的SND率,且TN、氨氮等去除效果不差。尤其在水產養殖廢水缺碳的不利局面下,如何實現低投碳量的SND脫氮,值得研究者們積極探索。
不同反應器、進水濃度、控制條件,以及不同評價指標(脫氮率或除碳率),最佳C/N也必然不同,需要在實踐中歸納總結,綜合考慮投加成本和預期目標而定。除了考慮C/N,還要注意廢水中快速降解有機物(RCOD)的含量,即碳源的種類,相同C/N情況下,提高RCOD的含量可以獲得更好的脫氮效果[17]。
2.4 氧化還原電位(ORP)及微生物絮體結構
理論上,ORP的確是同步硝化反硝化的關鍵因子,通常也只是在調控pH、DO等他指標時,觀測到ORP值的變化。因此在設計實驗方案時,一般優先考慮其他因素。
邱靜[22]、周少奇等[6]認為微生物絮體結構也會影響SND進程,對于特定的反應器應有最佳的絮體粒徑、密實度和濃度范圍,便于創造微生物絮體內部合適的好氧區與缺氧區,保證DO和有機碳在絮體內部分布得當,有助于SND的發生。此外,基質傳遞到絮體內部的傳質性能也會因絮體粒徑不同有所差異,然而,在工程應用中不便于通過測定、控制絮體粒徑等來控制SND的脫氮效果[17]。因此,在工程實踐中,往往致力于尋求其他調控方法。
2.5 填料及反應器形式
目前關于SND脫氮工藝的研究,多以活性污泥法、生物膜法的各種衍生工藝開展,如SBR反應器[25,29]、SBBR反應器[28,32]、生物濾池[33]等。MBBR,即移動床生物膜反應器可在無需增加額外占地、不改變原有工藝路線的情況下,實現深度脫氮[34],尤其適用于污水廠提標、提量改造[35],因此成為不少學者們研究的熱點。許多研究都證實了MBBR-SND工藝能夠很好地去除廢水中的氮素,如JIA等[30]、欒志翔等[36]的研究應用。鄒俊良等[37]也曾采用MBBR凈化模擬黃顙魚養殖塘廢水,效果良好,且反應器運行穩定后,在運行初期就發生了SND。同步硝化反硝化工藝的研究多集中于生活、市政及工業廢水領域,如何在水產養殖水處理流程中實現SND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熱點,尤其是MBBR-SND反應器的開發與應用。
除此之外,填料種類也關系著SND的表現效果。王翥田等[38]建立了一套改良A2/O+HYBAS中試裝置以改善出水水質,結果顯示,該工藝運行穩定、實現了SND并提高了系統脫氮能力。鄭麗純[39]研制了一種呈紡錘體型、ABS材質的半懸浮生物填料,并結合該填料特點設計了一種反應器,用于處理人工模擬生活廢水,并成功實現SND。邵留等[40]在生物反應器中投放玉米芯填料,較好地實現了高DO環境下羅非魚循環養殖廢水SND作用,TN去除率達85%以上。
3 SND及好氧反硝化菌群研究進展

目前報道的好氧反硝化菌有很多,如常見的不動桿菌屬、氣單胞菌屬以及副球菌屬等[49]。不僅如此,有許多特殊功能菌也相繼被篩選分離,如耐鹽型[50]、耐低C/N型[51]等。馬青山等[52]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歸納、總結了好氧反硝化細菌的篩選、評價方法。
現今,也有許多研究者把關注點聚焦在水產養殖廢水-好氧反硝化脫氮實際應用方面,相關實踐成果[53-61]見表3,這些從不同養殖水環境中分離得到的好氧反硝化細菌不僅豐富了菌種庫及好氧反硝化理論,未來在水產養殖領域更將有廣闊的應用前景。研究還發現,混合培養的好氧反硝化細菌相比單一和純細菌菌株在分離時間上更具優勢,且由于混合細菌的共存和相互作用等對去除污染往往更有效[62]。遺憾的是,目前研究者對這一類混合細菌去除污染物的性能尚未完全了解,未來,探討其在水產養殖廢水深度脫氮中的表現或可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

表3 好氧反硝化細菌性能表
4 水產養殖廢水深度脫氮實例分析
好氧反硝化菌作為SND脫氮工藝的重要功能菌,促進氨化、硝化和反硝化過程同時在有氧環境中進行。然而SND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影響的復雜過程,需考慮低C/N、低氨氮濃度的特點,開發出適合于水產養殖模式、能穩定高效運行的裝置[5],并合理控制影響參數,才能達到深度脫氮的目的。唐成婷等[63]利用PBS顆粒構建的PBS-SND系統(圖3(a))處理人工模擬養殖廢水,該系統能在低 C/N下高效脫氮,總氮去除率高達99%以上。胡玉等[64]采用PCL顆粒構建了PCL-SND系統(圖3(b)),該系統同樣可以處理低C/N養殖廢水,總氮去除率可達(56.85±2.21)%。向天勇等[65]研究并自制出一種多孔陶粒(再生性能良好),結合該陶粒組建了一套SND反應器(圖3(c))用于模擬淡水養殖廢水的脫氮研究,最終反應器成功啟動。成小婷等[66]將養殖固體廢棄物的發酵產物投放到連續低曝氣的SBR裝置中(圖3(d))處理人工模擬養殖廢水,對TN的去除率約為87%,使用該SBR反應器不僅能穩定地實現SND脫氮,且能資源化利用養殖固體廢棄物,有效避免了污染的發生,并為RAS系統零排放提供支持。

圖3 SND反應器示意圖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SND reactor

5 脫氮前沿技術
5.1 微生物固定化
作為一種細菌富集手段,微生物固定化技術有效克服了實際應用過程中細菌存活率低、高毒性環境中耐受性低等問題,它可以顯著提高菌株密度,毒性耐受性和簡化細菌液的去除,利用自固定或外泌體固定制備出具有特定活動范圍的微生物菌株[69]。
南海水產研究所創新團隊根據DO分配不均理論設計了一種特殊的反硝化膠囊,可置于好氧反應器中實現養殖尾水SND脫氮,總無機氮去除率達到97%,SND率接近99%;這種反硝化膠囊是基于包埋技術的新型固定化方法來制備,經馴化后可直接置入養殖池塘、RAS系統生物濾池或生物絮團中,與好氧硝化細菌協同作用實現SND,完成生物脫氮全過程[70]。陳爽等[71]以粉煤灰、活性底泥、鐵粉和碳酸鈣粉末為原料制作了一種改性粉煤灰陶粒,將有效微生物群落(Effective Microorganisms,EM)固定在此陶粒中形成生物陶粒,其對于模擬水產養殖廢水總氮去除最高可至93.80%,比未固定化EM的純粉煤灰陶粒脫氮效果更佳,且微生物對廢水中氮的去除起了主要貢獻作用。有研究認為,包埋固定復合菌種比單一菌種能更有效處理廢水中多種類污染物,且土著微生物比外來高效微生物更具有適應性,去除能力也更佳[72]。
5.2 微藻處理
微藻植物修復具有去除養分效率高、成本低的特點,具有很大的潛力,最重要的是,微藻生物量可以直接利用或轉化為水產養殖飼料,實現營養物質的閉環循環[73]。通過微藻代謝水產養殖廢水中的有機碳,而亞硝酸鹽和硝酸鹽可被微藻細胞脆化成銨鹽,最后被微藻同化,在實際應用中,可供選擇的藻類較多,諸如小球藻、斜生珊藻等單細胞藻類,利用藻菌共生系統或藻類塘等多種凈化方式改善水質[74]。
劉慶輝等[75]發現綠色巴夫藻對模擬養殖廢水的去氮效果非常好,生長率也很高。呂俊平等[76]發現低起始的生物質接種濃度有利于綠球藻的生長,對養殖廢水中污染物的降解效果也更佳,初始接種濃度為100 mg/L時最為顯著。
5.3 厭氧氨氧化

6 結論與展望
針對水產養殖廢水深度脫氮研究,從幾種新型生物脫氮技術原理及應用情況、影響因素、相關菌種研究進展以及前沿技術等多方面展開論述。
近年來,環保政策持續收緊,各省市相繼出臺、規范化水產養殖行業污染物的排放標準,未來,水產養殖廢水脫氮治理將會愈發重要。傳統的硝化反硝化技術雖然應用較為成熟,但因其諸多局限性,在未來應尋求更經濟高效的脫氮方式。全程/短程硝化反硝化及好氧反硝化可以兩兩或同時在廢水處理系統中發生,在許多案例中都得到驗證,同步硝化反硝化理論很好地揭示了這些現象的內在原理。然而,SND在生活、工業污廢水處理領域的研究應用較多,卻很少在水產養殖廢水處理方面報道,中試及以上規模的更少,且進水多為模擬水產養殖廢水,這與實際廢水在水質、水溫等方面仍有較大差別。因此,為了進一步實現水產養殖廢水深度脫氮的工程化應用,還需要從以下幾方面開展研究:
(1)未來,可以從實際養殖廢水的引入、規模放大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
(2)在SND理論的研究基礎上,從工藝開發方面展開探索。例如,當前針對城市、工業污水脫氮的研究與應用,有許多是通過MBBR工藝來實現的,但水產養殖業的MBBR-SND脫氮案例卻十分有限,未來可以朝這一方向做更多研究。
(3)繼續從水產養殖水體中分離、篩選、鑒定更多類型的HN-AD菌,目前已報道了從多種類型污水分離提取出的好氧反硝化菌,但這些細菌是否適用于水產養殖廢水還有待深入研究。了解不同細菌的脫氮性能有助于在將來的實際應用中選取并接種合適的菌種。
(4)現階段養殖廢水SND案例大多為控制間歇進水,或通過間歇曝氣等方式維持低溶解氧、甚至缺氧狀態,這與實際養殖模式較為不符,而固相反硝化脫氮存在出水有機碳高等弊端,因此,需以連續進水、連續曝氣的工況為出發點,做進一步研究。
(5)碳源短缺一直是制約反硝化進程的難點,可以開展低碳投加策略下的SND相關研究,既保證一定的反硝化效率,同時維持氨氮、亞硝出水的達標排放或循環利用,還能節省碳源投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