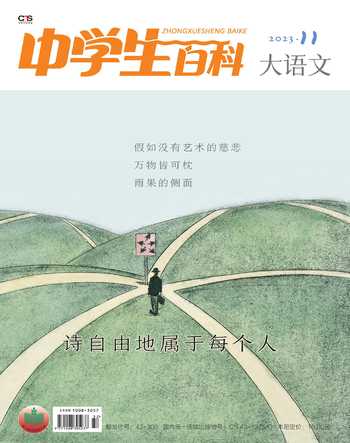偶然遇見王計兵
張夢昕
坐上火車后,我感覺自己像是被擠到了一個小小的角落里:四個人圍坐一張桌子,腿沒法自由地伸展、放松。幾個小時后,火車進站,又涌上來一批乘客。已是傍晚時分,窗外變暗了。收回眺望的眼,我突然很想嘆一口氣。
總在想,如果我生活在電視劇或者游戲里,一定屬于主角故事背景里那種來去匆匆的行人。故事里的他們沒有詳細的人物介紹,資質平平而又忙忙碌碌,存在的意義似乎就是趕路,從這一站到下一站,永遠沒有終點。
打開手機,戴上耳機,邊聽歌邊看新聞。在微微晃動、略顯昏暗的火車車廂里,在抵達目的地之前的這段旅途中,我就這樣毫無準備地認識了“外賣詩人”王計兵。他的出現,打破了我對詩人的刻板印象。
提起醫生,我會想到穿著白大褂、脖子上掛有聽診器的人;說到詩人,我會想起海子印在他的詩集上的樣子,頭發微卷、略長,眼神冷峻。很多人其實和我一樣,習慣按照固有思維對人進行分類,好像醫生生來就是醫生,詩人生來便是詩人。現實并非如此,身份與夢想,從來都不是天生配對的。
王計兵從小熱愛文學,但這種熱愛無法支撐生活。為了生計,他與妻子一同到外地打拼。從事外賣員工作的他把自己定義為“趕時間的人”——每天的大部分時間奔波在路上,送完這單趕下一單。生活的浮浮沉沉與酸甜苦澀,不是短短幾行詩就可以道盡的。但是,詩至少為他掘開了一個可以無限述說的洞口。
生活太過寬廣和包容,容得下任何起承轉合;而在這片廣闊的海洋里,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滴水,很難掀起大的波瀾。我突然就明白了為什么王計兵的故事更讓人動容:并非他實現了與自己身份不相符的夢想,而是即使暫時無法不受限制地、自由地追求隱于內心的微光,也始終沒有放棄自己對詩歌的熱愛。
我們在各自的人生軌道上默默趕路,一言不發地忍受不同的孤獨和痛苦。然而總會有一兩件事讓我們堅信生活不止是雞毛蒜皮和柴米油鹽,如王計兵所說的,詩歌對于他而言,就像是空地里下著的一場大雪,或許它不能改變生活本來的樣貌,卻讓生活的“白”不再是“空白”。在低頭找尋六便士的時間罅隙里,也可以抬頭看看自己的星星和月亮,這才是現實世界里大部分人的生活常態。
抬頭看著車廂里不同的面孔,我知道不能簡單地對他們下定義,因為即使是最平凡最不起眼的人,也有專屬于他的精彩。就像從小就有寫作夢的王計兵,堅硬的現實并沒有讓他放棄“不務正業”的夢想。他揣著一顆始終不變的少年心,穿過重重迷霧,把詩寫在生活的每一頁。詩于他而言,與功名利祿無關,與人情世故無關。詩就是詩本身,又或者說詩就是他自己。他大概沒有想過把詩當作武器,但詩的的確確一直在為他遮擋現實的棱角,對抗生活的瑣碎。
都說少女情懷總是詩,但實際上,每一顆拒絕蒼老的心都是詩最好的棲息地。只要懷有詩心,我們就不必擔心自己不是生活的主角。想到這里,火車即將到站,我看見匆匆下車的人們臉上帶著疲憊。大家都有要奔赴的目的地,也都有正在為之奮斗的目標。恍惚間,我感覺自己像是站在人來人往的廣場中央。
沒有誰是人間畫卷的主角,但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詩,甚至是活成一首詩。這些與我一路同行的人里面,或許就有許多個“王計兵”呢。我們在自己的人生跑道上騎著外賣單車,為了一份份即將超時的訂單在冷熱分明的四季里奔忙,“從空氣里趕出風,從風里趕出刀子,從骨頭里趕出火,從火里趕出水”。
在這一站到下一站的旅程中,我們感受生活的酷熱或涼爽;在喘息擦汗的空隙里,我們抬頭望見一輪虛構的月亮。這是王計兵的故事和他的詩給予我們的最大饋贈。每個人都可以像他一樣,以詩靠近心靈的遠方,又以詩的名義與生活握手言和。“生活給了我多少積雪,我就能遇到多少春天”,這不只是王計兵的詩,也是我們應該寫給人生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