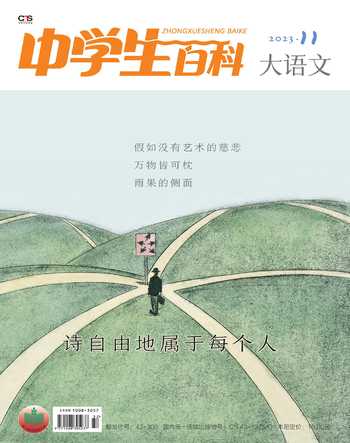李清照的少女時代
張覓
出身于書香門第,家學淵源,再加之從小就博覽群書、見識非凡,李清照少女時代就能寫出令人驚艷的作品來。比如這首傳誦千古的《如夢令》: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這是一首極清新活潑的小令。昨夜狂風大作,暴雨如傾。清照對雨酌酒,不覺微醺,一枕小窗濃睡,次日醒來,天已放亮。侍女正卷起簾子來,雨后清新濕意透進,她不由得牽掛庭院里的海棠,于是問,海棠怎樣了?侍女說,海棠還是那樣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她微微一笑,道,不,雨過之后,應該是紅花稀少了,而綠葉看起來就繁茂了。
以“紅”“綠”做動詞,本已新穎不凡,而清照再以“肥”來形容綠葉繁茂豐盈之態,以“瘦”來描述紅棠凋零殘落之姿,令人眼前一亮,雨后花葉之態宛如在眼前。此句極其別致,是生動的神來之筆。
這首小令中,有白描,有對話,有感嘆,卻不顯堆砌擁擠,足見清照用筆之凝練。仿佛纖手自拈來,空使鵑啼燕妒。
李清照還寫有一首《如夢令》: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常記溪亭日暮”,溪亭,日暮,簡簡單單兩個詞,即勾勒出黃昏斜照水的畫面,以及清照對那個畫面的眷念之意。“沉醉不知歸路”,極愛“沉醉”二字,閨閣少女出游,完全釋放了自己活潑好玩的天性,既是酒醉,也是心醉,沉浸在無憂世界里,渾不知俗世煩憂。“興盡晚回舟”,興盡,盡興而歸,心思是如何甜美而滿足呢?“誤入藕花深處”,誰知就莫眀其妙地進入了一個唯美清新的天地,仿佛從來沒有領略過的美景,在眼前徐徐展開,小舟如葉,輕輕隨碧波而飄蕩,花香浸潤了身上的酒香。“誤入”二字在這里有一種天真明麗的喜悅,正是因為無心邂逅,才更見驚喜。
“爭渡,爭渡”,連用兩個“爭渡”,“爭”字,用筆活潑,讓整句詞都生動起來。“驚起一灘鷗鷺”,鷗鷺受驚,撲棱棱自藕花叢中飛起,掠過天空,畫面頓時增添無限動感。
詞到此戛然而止,但似乎能想象得到芬芳滿溢的粉色藕花叢中,暮靄漸漸彌漫,溫柔的鴿灰色覆蓋,夜色正潮水般涌來,世界忽然如此優美、幽微而神秘。少女烏黑的眸子,亮晶晶的,笑生雙頰,宛然天真的模樣。
李清照賦予這“誤入藕花深處”的少女更多的生命力和生命情態,將年輕時才有的活潑與生機展現得淋漓盡致,滿蘊青春之美,如此空靈,又如此瀟灑。
這樣的景色,會忽然輕輕觸動人心中的一根弦——是什么時候,什么地點,自己也曾有過這樣一份年少時無憂無慮的嬌憨呢?
李清照的兩首《如夢令》都委婉清美,別有一種搖曳不絕的秀麗之姿,描寫的都是她少女時代安逸快活的生活,是她的得意之作。后世一提到《如夢令》,就會想到李清照。
李清照還有一首記少女時代出游的小詞《怨王孫》。明凈清冷的深秋時節,她還要和一群女伴到郊外的湖上來劃船,心情暢快之下,填了一首婉約清新的《怨王孫》:
湖上風來波浩渺,秋已暮、紅稀香少。水光山色與人親,說不盡、無窮好。
蓮子已成荷葉老,青露洗、花汀草。眠沙鷗鷺不回頭,似也恨、人歸早。

正是暮秋時節,晚風吹拂,浩渺的湖面層層漣漪蕩開,仿佛要染濕湖面的殘荷。水光山色如此之美,像是要與人親近。蓮子已成,荷葉已枯,秋色漸老,只有汀邊花草被浸潤秋露,清潤可愛。岸上的水鳥撲棱棱飛開,仿佛是怪游人,怎么回去這么早呀?
這首詞完全展露出無憂無慮的少女心性。她泛舟湖上,那時她的心情是歡快的,總覺得萬物之間有一種和諧的美好。
秋色靜美,在清照的描摹中,暮秋里的風物潔凈而風雅,仿佛成了傾城的出浴女子,美不勝收。只是一首普普通通的記游的小詞,卻給人以一見難忘、清爽宜人之感。
辛棄疾的詞中也有“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的名句。其中情懷,也同于清照的這首詞。
李清照的這些詞作清淺如小溪,不事雕琢,富有一種天然之美。少女原生態的健康活潑的美,如此純凈、清澈、明亮、無邪,像溪流一樣流過心靈,為蒙塵的心洗去污垢,仿佛也被那種忘情的快樂所感染,心情輕舞飛揚。
青春年少時,總是很容易快樂,容易沉醉,不經意間就邂逅了一份難以言語的清美。將那份美好細細封存,放在記憶深處,等到年老時輕輕揭開,那年的風華,那個清晨或者黃昏時的少女情懷,仍然如同初釀的蘋果酒,淺淡芬芳。
這些早期甜蜜無憂的回憶,讓李清照在以后的歲月中每每想起,心生溫暖,唇浮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