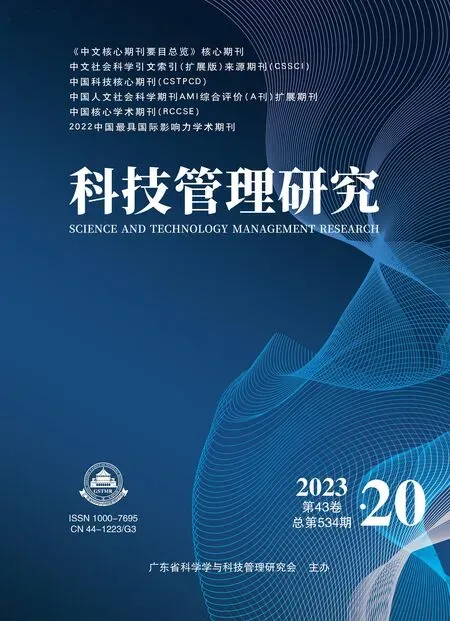省部級科研平臺資源配置效能影響因素以及科研投入要素的閾值效應(yīng)
——以上海市醫(yī)學(xué)領(lǐng)域重點實驗室為例
張文珊,錢軼峰,汪雪玲,賈仁兵,計 菁
(1.上海交通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附屬第九人民醫(yī)院科研處,上海 200011;2.上海交通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附屬第九人民醫(yī)院口腔顱頜面科,上海 200011;3.上海交通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科技發(fā)展處,上海 200025)
省部級科研平臺是地區(qū)科技創(chuàng)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組織高水平科學(xué)技術(shù)研究、培養(yǎng)優(yōu)秀科技創(chuàng)新人才、開展高水平合作交流的創(chuàng)新策源基地。上海市科學(xué)技術(shù)委員會[1]發(fā)布的《上海市重點實驗室建設(shè)與運行管理辦法(修訂稿)》指出,重點實驗室的主要任務(wù)是面向國家與本市重點發(fā)展戰(zhàn)略領(lǐng)域開展基礎(chǔ)研究、應(yīng)用基礎(chǔ)研究和前沿技術(shù)研究,獲取創(chuàng)新成果和自主知識產(chǎn)權(quán),打造創(chuàng)新策源地和人才高地。近年來,我國省部級科研平臺在建設(shè)數(shù)量、質(zhì)量上取得了長足進步,對科研平臺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強。發(fā)展經(jīng)濟學(xué)認(rèn)為,經(jīng)濟增長的主要源泉為科技創(chuàng)新,而科技創(chuàng)新的能力和效率共同決定了科技創(chuàng)新的質(zhì)與量[2]。國家和依托單位對于科研平臺的投入一直處于穩(wěn)步增長,2021 年,全國(未含港澳臺地區(qū),下同)R&D 經(jīng)費支出為27 864 億元,比上年增長14.2%[3]。經(jīng)濟增長理論表明,在技術(shù)水平不變的情況下,任何投入都會存在拐點[4],投入的增長不可能無限增加,終將趨于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區(qū)間。科研平臺作為科技資源的主要承載者,通過優(yōu)化平臺的科技資源配置,尋找和形成投入產(chǎn)出的效能最優(yōu)值,擴大科技創(chuàng)新貢獻,對推動我國的科技創(chuàng)新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通過識別影響醫(yī)學(xué)科研平臺資源配置的因素,采用多視角整合框架和擬合多因素比較分析,探索和發(fā)現(xiàn)科研平臺科技資源配置閾值效應(yīng),以期為上海市醫(yī)學(xué)領(lǐng)域重點實驗室優(yōu)化資源配置提供理論依據(jù)。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調(diào)查對象
截至 2019 年年底,上海市重點實驗室共有 144家,分布于生命、信息、工程、材料、化學(xué)、數(shù)理、地學(xué)等學(xué)科領(lǐng)域,其中生命領(lǐng)域占比最高,為47%,其次是信息(17%)、工程(15%)和材料(9%)領(lǐng)域[5]。2019 年,上海市科委對本市醫(yī)學(xué)領(lǐng)域的29 家重點實驗室進行了建設(shè)發(fā)展績效評估,評估結(jié)果分為4 檔,其中優(yōu)秀的有5 家、良好的有19 家、一般的有3 家、整改的有2 家[6]。考慮到數(shù)據(jù)來源的權(quán)威性、可得性以及代表性,通過上海市科委官方網(wǎng)站披露的數(shù)據(jù)、重點實驗室自建公開網(wǎng)站、國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網(wǎng)站和Web of Science 網(wǎng)站等公開數(shù)據(jù)來源,獲得這29 家重點實驗室在2021 年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2021 年正是“十三五”收官年、“十四五”開局年,當(dāng)年我國發(fā)表高水平國際期刊論文 8.05 萬篇,占世界份額的 35.2%,排在世界第 1 位[7],因此采用當(dāng)年的科研產(chǎn)出數(shù)據(jù)具有代表性。在剔除了缺失值過多的數(shù)據(jù)后,最終將22 家重點實驗室作為研究對象(以下簡稱“樣本”)。樣本數(shù)據(jù)的依托單位覆蓋綜合性醫(yī)院和專科醫(yī)院。根據(jù)評估公示結(jié)果,將樣本分為優(yōu)組和非優(yōu)組,其中優(yōu)組4 家、非優(yōu)組18 家(良好的有15 家、一般的有2 家、整改的有1 家),所選樣本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結(jié)合上海市重點實驗室定位、要求及價值導(dǎo)向,分析實驗室建設(shè)運行實際過程中直接科研投入要素對科研產(chǎn)出的影響,投入方面主要包括人才隊伍、科研項目、科研經(jīng)費等,特別是重點實驗室承擔(dān)國家級科研項目數(shù)量和經(jīng)費數(shù),國家級項目和經(jīng)費占實驗室科研支撐的比例對實驗室可持續(xù)發(fā)展和高人才培養(yǎng)具有的重要作用,因此將國家級項目和經(jīng)費單列考察比較;產(chǎn)出方面主要包括論文產(chǎn)出和專利產(chǎn)出。選取了15 個變量,具體如表1 所示。

表1 樣本基本情況統(tǒng)計
1.2 研究方法
利用線性回歸模型分別對各科研投入要素與科研產(chǎn)出之間的線性關(guān)系進行單因素分析。為了探討自變量和因變量是否存在非線性關(guān)聯(lián),利用限制性立方樣條(restricted cubic spline,RCS)函數(shù)對各項投入與產(chǎn)出之間的非線性關(guān)系進行了擬合,所有變量均以連續(xù)性變量的形式納入模型。樣條函數(shù)本質(zhì)上是一個用于探討自變量和因變量是否存在非線性關(guān)聯(lián)的分段多項式,它一般要求每個分段點上連續(xù)并且二階可導(dǎo)。即,設(shè)自變量數(shù)據(jù)的范圍在區(qū)間[a,b],并根據(jù)需要分成k個段得到:a=t0<t1<…<tk-1<tk=b,在每個區(qū)間 [ti-1,ti)分別用一個多項 Si(x) 式表示,則回歸樣條f(x)=Si(x)在當(dāng)x∈[ti-1,ti),并且f(x)在[a,b]時存在連續(xù)。限制性立方樣條函數(shù)是在樣條函數(shù)的基礎(chǔ)上要求在自變量數(shù)據(jù)范圍兩端的兩個區(qū)間,[t0,t1)和(tk-1,tk]內(nèi)是線性函數(shù),即在第一個節(jié)點前的趨勢和最后一個節(jié)點后的趨勢強制限制為線性,從而更好地對自變量與因變量的關(guān)系進行解釋[8]。在單因素線性回歸與非線性回歸分析的基礎(chǔ)上,還通過廣義可加模型(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GAM)對納入了單因素分析中有意義的變量進行了進一步分析,探索在多因素條件下各項科研活動投入對于科研產(chǎn)出的影響。與一般線性模型相比,廣義可加模型的優(yōu)點是可以通過引入非線性函數(shù),從而對因變量的預(yù)測更加準(zhǔn)確。此外,因為模型是加性的,線性模型的假設(shè)檢驗的方法仍然可以使用。通過廣義可加模型可以同時實現(xiàn)模型的可解釋性(interpretability)、靈活性(flexibility)和正則化(regularization)[9]。最后,利用分段模型對非線性回歸中所發(fā)現(xiàn)的科研要素投入的閾值效應(yīng)進行了進一步的分析與驗證。
2 結(jié)果與分析
2.1 單因素線性回歸分析
如表2 所示,高級職稱人數(shù)、40~60 歲人數(shù)兩個變量與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存在線性關(guān)系,有顯著統(tǒng)計學(xué)差異,博士學(xué)位人數(shù)與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有統(tǒng)計學(xué)差異(見圖1、圖2);而所有投入因素與專利均不存在線性關(guān)系,這與重點實驗室主要開展基礎(chǔ)研究和原始創(chuàng)新相關(guān),專利更偏向于應(yīng)用創(chuàng)新研究。

圖1 樣本中高級職稱人數(shù)與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的線性關(guān)系

表2 樣本中科研要素投入與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的線性關(guān)系
2.2 單因素非線性回歸分析
由于場地面積、總在研項目數(shù)、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等與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不存在顯著的線性關(guān)系,因此利用限制性立方樣條函數(shù)對以上因素與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的非線性關(guān)系進行了探索,如表3 所示。研究發(fā)現(xiàn),以上要素與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之間亦不存在顯著的非線性關(guān)系,然而,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和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之間存在一種倒“U”型的非線性變化趨勢,有且存在一個臨界值拐點(見圖3):當(dāng)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小于該拐點時,經(jīng)費數(shù)的增加可以促進科研論文的產(chǎn)出;當(dāng)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超過該拐點時,科研經(jīng)費的增加將不再對科研論文的產(chǎn)出有正向的刺激作用。

圖3 樣本中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和發(fā)表論文數(shù)的非線性關(guān)系

表3 樣本中科研要素投入與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的非線性關(guān)系
2.3 多因素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索在多因素條件下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對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的影響,將線性關(guān)系中的顯著變量高級職稱人數(shù)、40~60 歲人數(shù)以線性形式,將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以樣條函數(shù)形式同時納入到廣義可加模型(模型1)中進行進一步分析。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在校正人員因素影響的前提下,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和論文產(chǎn)出之間依然存在與單因素分析時類似的非線性關(guān)系。模型1 構(gòu)建如式(1)所示:
式(1)中:β為參數(shù)估計;S為樣條函數(shù)。
2.4 閾值效應(yīng)分析與驗證
為了對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的閾值效應(yīng)進行分析,首先利用模型1 計算得到多因素模型中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對應(yīng)的效應(yīng)值,在此基礎(chǔ)上利用分段回歸模型對其與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的關(guān)系進行了擬合,得出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的閾值為10 110 萬元。在該閾值前,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斜率對應(yīng)的t值為37.13,在該閾值后,斜率對應(yīng)的t值為-8.34,兩者P值均小于0.001。具體見圖4。

圖4 樣本中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對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的閾值效應(yīng)分析
為進一步驗證所發(fā)現(xiàn)的閾值,首先將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高級職稱人數(shù)、40~60 歲人數(shù)以線性形式納入多因素模型,即構(gòu)建模型2 如式(2)所示;再以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的拐點為分界線,將以上因素同時納入分段回歸模型,即構(gòu)建模型3 如式(3)所示。對兩個模型的擬合優(yōu)度進行檢驗的結(jié)果顯示,模型3 的擬合效果顯著優(yōu)于模型2,再次驗證了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對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的閾值效應(yīng)(P=0.05)。
3 討論
3.1 場地面積增加不能帶來產(chǎn)出數(shù)量增加
《上海市重點實驗室建設(shè)與運行管理辦法(修訂稿)》明確規(guī)定實驗室場地面積不得少于1 000 m2[1],在這個基數(shù)之上,通過場地面積和產(chǎn)出的線性回歸可以發(fā)現(xiàn),場地面積的增加對于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變量的線性斜率較為平緩(T=0.645),科研平臺面積大小對論文產(chǎn)出無實際影響。該結(jié)果與白帆等[10]、楊超等[11]、辛督強[12]、羅偉昂等[13]、張燕等[14]、涂繼亮等[15]分別對陜西省某高校、江蘇省某高校、福建省重點實驗室、江西省科技創(chuàng)新平臺和國家重點實驗室等的研究結(jié)果一致,說明科研平臺在場地面積的投入中存在重復(fù)建設(shè)、資源閑置或產(chǎn)能過剩的現(xiàn)象。可能原因是科研平臺作為一個復(fù)雜的多投入多產(chǎn)出系統(tǒng),雖然面積增加意味著可以進行多種科學(xué)實驗,但是更需要對平臺的各項可利用資源進行有效配置才能達(dá)到增加科研產(chǎn)出的作用。
3.2 經(jīng)費增加的閾值效應(yīng)有所減弱
非線性回歸分析和多因素回歸模型顯示,科研平臺經(jīng)費投入的增加對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變量有著顯著的正向刺激作用,但是當(dāng)總研經(jīng)費數(shù)到達(dá)閾值后作用不再明顯,斜率趨于平緩,達(dá)到飽和效應(yīng)階段。這表明,若科研經(jīng)費的擴張無法轉(zhuǎn)變成知識創(chuàng)新和技術(shù)進步,那么其正向刺激作用將會減緩、經(jīng)費使用率降低,極有可能在機會主義行為下產(chǎn)生尋租行為,經(jīng)費投入的閾值效應(yīng)有所減弱。該結(jié)果與趙曉萌等[16]對江蘇省某高校、王立軍[17]對浙江省重點實驗室和朱金龍等[18]對廣東省重點實驗室的研究結(jié)果一致。筆者認(rèn)為出現(xiàn)閾值拐點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經(jīng)費規(guī)模效應(yīng)存在“搭便車”和尋租現(xiàn)象,個人產(chǎn)出貢獻邊際遞減;二是規(guī)模增長的過程還會造成“公共地悲劇”,科研平臺產(chǎn)出貢獻邊際遞減;三是隨著各級各類科研平臺的建設(shè),通過技術(shù)模仿、技術(shù)轉(zhuǎn)移產(chǎn)生的紅利逐漸喪失,當(dāng)規(guī)模擴張后的科研平臺無法促進知識創(chuàng)新,科研經(jīng)費閾值效應(yīng)就會越過拐點,呈邊際遞減態(tài)勢。
3.3 高水平人才帶來的產(chǎn)出效應(yīng)顯著
線性回歸分析結(jié)果顯示,科研平臺的高級職稱人數(shù)和40~60 歲人數(shù)對于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變量有著正向顯著影響。也就是說,隨著人力資源的投入增多,論文的產(chǎn)出也越多。這體現(xiàn)了高水平人才是科研平臺建設(shè)中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表明人力資源配置和人才梯隊搭建對省部級科研平臺的建設(shè)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羅文宇等[19]認(rèn)為優(yōu)秀科技人才流失、科技人才的穩(wěn)定程度不夠?qū)χ攸c實驗室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yuǎn)的影響。童楊等[20]認(rèn)為實施創(chuàng)新驅(qū)動發(fā)展戰(zhàn)略,關(guān)鍵是科技創(chuàng)新,核心是人才,高水平的人才力量決定了科研平臺的未來發(fā)展。這均與齊天等[21]和許敏等[22]對我國高校科研效率、李文輝等[23]和王騰等[24]對我國地方高校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李春等[25]對公立醫(yī)院科研平臺資源配置等研究結(jié)果一致。
4 建議
當(dāng)場地規(guī)模效應(yīng)無法對產(chǎn)出起到顯著促進作用,省部級科研平臺的經(jīng)費優(yōu)勢帶來的閾值效應(yīng)逐漸減弱、趨近拐點時,科研平臺內(nèi)部增長動力不足,將成為我國科學(xué)研究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主要制約。因此,如何推動科研平臺轉(zhuǎn)型,將科研平臺“做寬做長”、做大做強,提升創(chuàng)新效能,成為推動省部級科研平臺可持續(xù)發(fā)展需要思考的問題。
4.1 以超產(chǎn)權(quán)理論改善治理機制,加快建設(shè)大型公共儀器平臺
之所以出現(xiàn)“公共地悲劇”現(xiàn)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產(chǎn)權(quán)的模糊或缺失。在我國,科技資源主要以公有財產(chǎn)形態(tài)出現(xiàn),產(chǎn)權(quán)激勵方面存在不足。英國經(jīng)濟學(xué)家馬丁等[26]提出的超產(chǎn)權(quán)理論認(rèn)為,經(jīng)營業(yè)績主要與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有一定相關(guān)關(guān)系,但沒有必然聯(lián)系,且與行業(yè)市場競爭程度相關(guān)。因此,只有改善治理機制,提高核心競爭力,刺激平臺內(nèi)部增長動力,才能與外部市場競爭環(huán)境相匹配。對于一家依托單位同時擁有多家科研平臺的情況,要打破固化思維,在建設(shè)大型儀器平臺和公共共享平臺時,利用超產(chǎn)權(quán)理論觀點,即任何科研平臺都可以將公共平臺納入自己的面積范圍,自有面積則建設(shè)專業(yè)特色研究平臺,從而實現(xiàn)公共場地和大型儀器的高效使用。通過改善科研平臺治理機制,加強跨平臺、跨領(lǐng)域?qū)W科交叉,將科研平臺橫向拓寬,在合作共享的基礎(chǔ)上突出學(xué)科平臺的優(yōu)勢,發(fā)揮所長,提高科研平臺運轉(zhuǎn)的效能和產(chǎn)出效率,避免“公共地悲劇”。
4.2 創(chuàng)新青年人才評價制度,為青年人才減負(fù)
分析結(jié)果證明,青年人才蘊藏著巨大的創(chuàng)新潛力,能夠挑大梁、當(dāng)主角。優(yōu)秀的人才是實驗室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是核心競爭力,只有不斷完善人才梯隊建設(shè),特別是優(yōu)化40~60 歲優(yōu)秀中青年骨干隊伍和多元化人才配比,最大限度發(fā)揮青年人才的創(chuàng)新潛力,科研平臺才能保持長久的研究活力和激情。科技部、財政部等五部門發(fā)布的《關(guān)于開展減輕青年科研人員負(fù)擔(dān)專項行動的通知》要求幫助青年人才挑大梁、增機會、減考核、保時間、強身心。通過創(chuàng)新青年人才評價制度,在青年人才發(fā)展起步階段為其拓寬人才成長通道,讓優(yōu)秀的青年科研人員能夠嶄露頭角,在中間階段減輕事務(wù)性工作壓力,保證科研時間優(yōu)化[27];在考核方式中建立盡職免予追責(zé)機制,緩解評估周期短且頻繁的問題。通過為青年人才減負(fù),避免智力外流,以達(dá)到提升人力資源效能的管理目的,促進科研平臺縱向做長。
4.3 科研平臺亟待轉(zhuǎn)型
樣本數(shù)據(jù)絕大部分落在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和論文產(chǎn)出的非線性關(guān)系曲線的左支,尚未及拐點,說明這些科研平臺仍可以通過增加科研經(jīng)費數(shù)推動實驗室的產(chǎn)出,但是一些實力強勁的科研平臺已經(jīng)在拐點附近甚至有超越拐點的跡象,標(biāo)志著這些實驗室正處于由產(chǎn)出數(shù)量的高速增長向產(chǎn)出高質(zhì)量發(fā)展轉(zhuǎn)型的重要階段。進入新發(fā)展階段,省部級科研平臺的發(fā)展重心將由規(guī)模擴張、外延發(fā)展轉(zhuǎn)向結(jié)構(gòu)優(yōu)化、內(nèi)涵發(fā)展、質(zhì)量提升[28],平臺主管部門應(yīng)將區(qū)域內(nèi)資源與平臺領(lǐng)域相結(jié)合,使平臺主動承擔(dān)滿足國家重大戰(zhàn)略需求的責(zé)任,從而帶動提升區(qū)域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此外,科研平臺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的培育不能過多依賴于政府的科技資源投入的增長,需要通過調(diào)整平臺的投入結(jié)構(gòu),結(jié)合地區(qū)產(chǎn)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積極謀求與頭部企業(yè)合作,推進區(qū)域產(chǎn)業(yè)發(fā)展,從而帶動科技創(chuàng)新,抑制機會主義行為造成的科技資金隱性流失和低效配置[29],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平臺運轉(zhuǎn)效能,將科研平臺做強做大,達(dá)到科技創(chuàng)新支撐地區(qū)經(jīng)濟與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目的,最終打造高水平自立自強科技創(chuàng)新平臺。
5 結(jié)論
本研究的實證結(jié)果表明,上海市醫(yī)學(xué)領(lǐng)域的22家重點實驗室中,高級職稱人數(shù)、40~60 歲人數(shù)兩個變量與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呈線性顯著相關(guān),實驗室平臺面積大小對平臺產(chǎn)出無實際影響,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和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之間存在一種倒“U”型的非線性變化趨勢,有且存在一個臨界值拐點;科研投入因素對平臺科研產(chǎn)出具有閾值效應(yīng),平臺經(jīng)費投入增加對發(fā)表論文篇數(shù)有著顯著的正向刺激作用,但當(dāng)總在研經(jīng)費數(shù)到達(dá)閾值后其作用不再明顯,達(dá)到飽和效應(yīng)階段。因此,加快建設(shè)大型公共儀器平臺、改善平臺治理機制、創(chuàng)新青年人才評價機制和推動平臺轉(zhuǎn)型,才能有助于科研平臺產(chǎn)出可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
但是,本研究的數(shù)據(jù)范圍僅限于2021 年,未考慮到論文產(chǎn)出具有的時滯性,因此結(jié)論的一般性有待進一步驗證;同時,研究對象僅限于上海市醫(yī)學(xué)領(lǐng)域的重點實驗室,未進行跨地區(qū)調(diào)研,未來需要進一步擴大調(diào)研數(shù)量;此外,研究模型未納入與科研平臺轉(zhuǎn)型相關(guān)的變量,也缺乏對是否轉(zhuǎn)型、怎么量化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的具體研究,后續(xù)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如何識別科研平臺轉(zhuǎn)型的關(guān)鍵變量及其轉(zhuǎn)型量化的標(biāo)準(zhǔn)等。
- 科技管理研究的其它文章
- 現(xiàn)代化技術(shù)賦能高校英語教學(xué)實踐
——評《教育信息化與慕課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 - 高校音樂教育的理論基礎(chǔ)及實踐探索
——評《高校音樂教育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研究》 - 宏觀教育視域下的傳統(tǒng)教學(xué)模式改革與創(chuàng)新
——評《宏觀教育戰(zhàn)略研究的開拓者》 - 攝影藝術(shù)的美學(xué)意蘊及意境營造
——評《攝影藝術(shù)的美學(xué)視角研究》 - 體教結(jié)合理念下高校冰雪體育教學(xué)的創(chuàng)新探討
——評《愛上體育——冰雪運動》 - 高校音樂藝術(shù)教育對大學(xué)生綜合素質(zhì)的培育
——評《高校音樂藝術(shù)教育實踐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