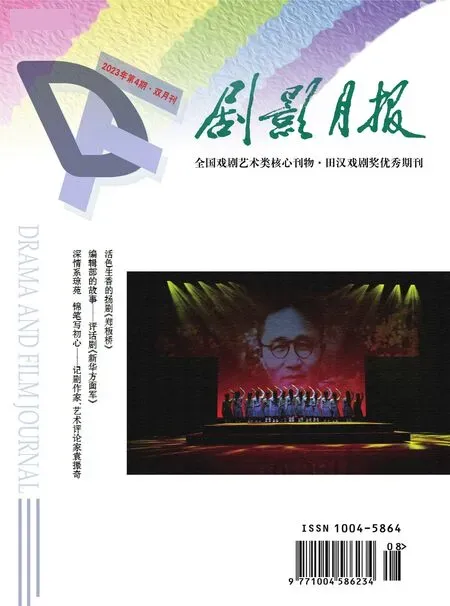以空間視角看《媽媽!》中生命問題的詩意表達
■董逸娟
《媽媽!》于2022年5月上映,是繼《春夢》《春潮》之后楊荔鈉執導的第三部關于女性的影片,由吳彥姝和奚美娟主演,講述了患有阿爾茲海默癥的女兒與母親之間的故事,暗含了家庭與倫理、愛與生命的主題。楊荔鈉導演及其團隊都是女性,以溫情卻不缺乏深意的眼光關注女性生活和社會現實問題。在電影處理時,又將鏡頭聚焦于普通家庭平庸瑣碎的日常生活,以詩意的畫面將故事如流水般緩緩訴說,不高大、不空洞。在電影中,女性的日常生活通過一系列主人公的工作、家庭生活、周邊環境等空間場域的轉換得以展現,關于生命的思考也以一種空間詩意的方式得以探討。法國哲學家亨利·列斐伏爾著重渲染了“空間”這一命題,他的空間思考是基于空間感知、空間想象、空間經驗三層維度為一體的空間觀念,由此構成了關于空間實踐、空間的表象、表征性的空間三位一體的空間辯證法,本文試圖以鏡頭中私人空間、社會空間、自然空間的建構為緯,以列斐伏爾的三元空間辯證法理論為經,對影片中交織的倫理與生命問題進行解讀與回應。
一、私人空間的塑造
(一)離群索居的獨棟小院
在電影中,馮濟真與母親所居住的獨棟小院是故事發生的一個重要空間。從物質空間的性質來看,這所遠離鬧市的小房子是母女兩人簡單的家庭生活環境的真實再現:黑色的鐵門、紅磚砌的圍墻、透明的玻璃門窗、種滿花草的庭院,一切都顯得生機盎然、充滿詩意,營造了一種靜謐美好的視覺效果。從拍攝手法的使用上看,當馮濟真與母親同處于一個場景時,畫面往往以景深鏡頭呈現,或是鏡頭與被拍攝的人物隔著一層門窗,進行遠距離拍攝,不僅豐富了家庭畫面的空間感,也使得這對母女之間的關系看起來更加朦朧且富有詩意。此外,母女兩人遠離人群的居住環境本身就已經為觀眾提供了一個信號:她們的身份與經歷是與普通人不一樣的。隨著影片播放,我們清楚地知道這個家庭與常規家庭相比,是“不完整”的,家中沒有父親,也不存在下一代,母女倆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退休大學教授,她們的生活自足,社會關系簡單,即使馮濟真每天都在做義工,也常常以沉默的方式出鏡。列斐伏爾認為獨棟住宅的居住者往往具有一個想要保護的私人的人格,這種住房常常對應著一個理想,即它包含了保護與孤立的愿望,暗含著認同與自我確認的需要以及獨處的需要。由此,外部的世界與內心世界的矛盾對立賦予了獨棟住宅以意義。
從空間的表征這一層次來看,對于失去父親之后的馮濟真而言,這棟住宅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存在。在電影開頭,馮濟真與母親蔣玉芝的關系是“顛倒”的,母親是被照顧的一方,而馮濟真則沉穩可靠。但馮濟真沒有結婚生子,生活也很節儉,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做義工一事上,沒有額外的社交,可以說是獨來獨往,這些使得她身上包裹了一種孤獨感和壓抑感。直到電影后半部分,觀眾才得以窺見某些原因,馮濟真始終認為自己導致了父親的去世,是有罪的,為此她一生背負著沉重枷鎖,而她的節儉的生活以及做義工都是自我救贖的一種方式。小院的大門與圍墻既是劃分私空間與公共空間的分界線,更是馮濟真為自身筑成的堅硬外殼。這座孤獨詩意的房子是馮濟真精心打造的充滿美好回憶的烏托邦。不管是庭院中被精心照顧的花卉,還是房屋內陳列的父親珍愛的古物,乃至出版父親考古日記的執念,馮濟真對物的投入不僅僅是物理意義上的,更是對安全感和自我救贖等意義與符號的投入。
(二)被門窗框住的房間
門與窗作為內置于家中的物像在電影畫面中經常出現,但導演不僅僅是簡單將其作為一種背景處置,而是充分利用了玻璃門與玻璃窗的透明性質及其邊框在畫面中的空間感,當電影中的人物處于私人空間時,鏡頭常常會透過窗戶拍攝屋內的人物活動。在畫面中我們常常能看到占有很大比例的方方正正的窗沿以及有點模糊的玻璃窗,人物活動所占的比例反而變小,且具有一種朦朧感,由此形成了一個包含著語言符號意義的精神構造與想象的空間,這也正是作為空間主體的導演及其拍攝團隊所特意構建的。采用這樣的手法拍攝時,窗戶內的場景一般都比較溫馨美好,如母親向女兒撒嬌、母女兩人讀書時的歲月靜好、母親安靜的睡顏、周夏耐心地哄孩子睡覺等。這種時候,鏡頭聚焦于窗內人物,周圍的窗楣以及物品會虛化處理,外部畫面色調暗,而內部人物畫面則色調偏暖,畫面整體如同一幅老舊的回憶,而人物被限制在大面積的窗框內部,使得人物距離銀幕更遠,營造了一種極具空間感的詩意畫面。
然而,玻璃窗的功能不止于此。作為一種實實在在的物質,盡管窗外的人能透過窗戶看清屋子內部人物的活動,但卻始終沒辦法穿透這層隔膜真正觸摸美好,窗戶如同一個保護罩,具有一種看見卻不可得的功能。而窗戶內部無疑是馮濟真渴望的美好,這點從她的幻覺場景得以明顯表現:馮濟真多次透過窗戶看到父親教學時的身影以及父親在玻璃門外抽煙賞景的身影。在黑暗的畫框中,小小的屋子透著昏黃的燈光,屋內是曾經擁有的美好,馮濟真作為阿爾茲海默癥患者,最害怕就是遺忘,然而玻璃窗就如同相機的鏡頭,將一切不愿意忘記的回憶都定格在房間里。同時,透過玻璃窗拍攝的小房間也可以看作馮濟真柔軟的內心世界。馮濟真自16 歲就沒有笑過,一生都沉默寡言,背負著沉重的鐐銬艱難生活,這間屋子也是她整理父親考古日記時工作的小屋,可以說匯聚了她所有的執念與思念,是她內心唯一沒有荒蕪的土地,因此色調以暖色來烘托,而外圍模糊、暗調的一切可以看作馮濟真內心一層層裹起來的殼。導演以玻璃窗為媒介,刻意制造了一種明明不在場卻又有極強在場感的第三者視角,借此既拉遠了觀眾與馮濟真內心人格的距離,又創造了一雙虛無的眼睛,這雙眼睛代表著另一個馮濟真的自我觀察與審視。其實不只是窗戶,電影中一切具有映射功能的物質都有類似的作用,如海洋館的玻璃、進入客廳時的玻璃大門以及房間的門框等,以上這些都以規矩的邊框凝固了某些溫馨的畫面,讓這些美好的溫度得以借此綿延。
二、自然空間與公共空間的對立
(一)社會空間的不安與窒息
社會空間作為一個動態、生產性、充滿想象的場域,既不同于直接感知的物質實踐空間以及被語言符號化的精神性空間,但同時又包含前兩者,它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即它要生產的關系使用者與環境之間表現出來的社會關系。“社會空間存在不是物性對象物或空場,而是由人的日常生活行動建構起來的場景存在,它的本質是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互動關系。”表征性的空間作為三元辯證法中第三個維度,是一個被各種權力與規則支配的空間,列斐伏爾通過對公共生活的形式與權力的運作進行探討,揭示社會空間的生活層面。
在電影中,導演有意讓馮濟真面對人群,借助觀眾與鏡頭的他者視角來觀察社會關系下的馮濟真,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是一種對她更為真實的存在狀態的還原。然而在這種社會空間的場域中,馮濟真總是處于某種不自在的狀態,因此與身邊人群相比具有一種格格不入的異樣感。尤其是在構建公交車這個人群混雜的社會空間時,特意用鏡頭的轉換表現了馮濟真眼中的公交車世界,當男人指明手機在她的包里時,觀眾借助馮濟真的視角能清楚地看到公交車上他人的猜忌及男人眼神中的厭惡。在表現這段情節時,鏡頭一度在他者與馮濟真之間反復切換晃動,以此表現出馮濟真內心的慌張無措。在這個過程中,每當鏡頭轉向馮濟真本身時沒有發生虛化且人物所占比例較小,但轉向其他人時,畫面明顯變虛、四周出現了許多光斑且有意放大了人物比例和人物的表情動作,這既可以看作是馮濟真得病的前兆,但更重要的是它以這種方式塑造了一個在社會關系中極度不自信、始終處于弱勢地位的角色。
(二)自然空間的自由與釋放
自然空間的構造是這部電影中除家庭以外的一個重要的故事發生場域,也是馮濟真日常活動的又一重要空間——一片小湖。“在被認識之前,空間就已經存在,在可以被解讀之前,空間就已經生產出來。因此,對空間文本的解讀和解碼,主要目的在于幫助我們認識表象的空間如何向空間的表象的轉變。”當馮濟真出現在湖邊這個自然空間時,往往是獨自一人,如果說家庭是馮濟真的牽掛,那么這處與天地共生的寧靜湖水對她而言則是一個人獨自療愈、尋找救贖的空間。然而自然在整部影片中的表征性意義并不是單一不變的,而是以馮濟真意識清醒與否為分界而發生轉變,導演以馮濟真心理及情緒變化的張力為要素構成了整個表征性自然空間。
在列斐伏爾看來,“空間不是自我的構成性話語,相反它僅是我的身體、是我身體的對應物,是身體的鏡像”。鏡像態的身體揭示了身體和自我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這種鏡像證明了兩者之間的統一性,另一方面也披露出形式與內容之間的對立。通過鏡像,身體和自我毫無保留地展露在對方面前,并且自我把自己從身體中抽離出來,以一種他者的視角來審視自己的身體,從而加深彼此之間的聯系。楊荔鈉將原本就具有鏡像作用的湖水作為馮濟真表露內心的自然空間,借助湖面使得觀眾和馮濟真本身都從身體中抽離出來,從他者的視角將馮濟真的內心狀態變化更加直觀地展現了出來,由此自然空間的表征體系更加完善。
湖水的出現往往伴隨著馮濟真患病后的幻覺,與她的內心狀態互為呼應。湖水作為馮濟真的重要空間第二次出現是在父親的考古日記出版后,鏡頭從長滿雜草與淤泥的湖底緩緩過渡到波光粼粼的湖面,馮濟真穿著裙子坐在船中緩緩入鏡,小船周圍散落著樹葉,由近景到遠景,從仰拍到俯拍,整段畫面只有自然的水聲、風聲,卻將馮濟真內在的釋放表現得淋漓盡致。父親考古日記的出版讓她心中的夙愿得以實現,盤亙在心中的執念與愧疚也逐漸消散,寧靜廣闊、泛著波光的湖面正如馮濟真此刻的狀態:平靜自由,重獲新生,仿佛她真的回到了與父親相處的愉快時光。湖水第三次出現時,她又穿上了碎花裙,撿起落在水面上的落葉,與第一次對湖邊的描寫相呼應,但此時她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有了媽媽的陪伴,然而這段關于人物的場景全都通過湖水的倒影來拍攝,馮濟真蹲在水邊輕聲呼喊“爸爸”,緊接著父親的身影就出現在了水中,一家三口就這樣通過湖水連接在了一起,將自己內心深處的思念反映在了這個自然的空間,在這種現實與虛構之間呈現出了詩意性。在最初,湖水對于馮濟真而言是一片自視為只有自己可以抵達的安全領地,并獨自沉浸其中,成為她逃避外界、尋求救贖的場所,然而逃避總是暫時的,這里仍然有著動蕩與不安侵蝕著她內心的烏托邦。隨著馮濟真心結的解開,對湖水這一空間的描繪由狹窄逐漸變得寬闊,這里真正成了馮濟真純潔的內心世界的代表,在這里她可以不顧復雜的社會關系,不拘束于一方小屋,盡情釋放自己,享受和幻想中的父親在一起相處的時光。三次對湖水這一自然空間的描寫借著對人物自身內在情感的沖突與張力構建起了馮濟真的心理空間體系,也讓觀眾得以意識到精神失常下馮濟真心中真正的所思、所念、所感。通過湖水這一自然空間的表征性走進阿爾茲海默癥患者的內心,讓原本對此一無所知的也無法感同身受的“正常人”借此理解他們,這也正體現了導演關注個體生存境遇、關心社會問題的拍攝初衷。
三、空間與生命的詩意交織
(一)從未遠離的父親
楊荔鈉以詩意的鏡頭構建起了一個又一個不同的空間,但她所聚焦的不僅僅是阿爾茲海默癥這個群體,更是試圖通過鏡頭探討關于生命的終極問題。而這一問題的答案,正可以在馮濟真與父親、母親和周夏這三對關系中得以窺見,可見可感的空間與無形卻充滿力量的生命也得以交融,構成了一個彌散著愛與希望的場。導演將“不在場”的父親解釋為:“影片里的魂魄,沒有他就沒有這對母女,所以他把三個人的關系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影片對馮濟真的塑造是著墨最多的,但在阿爾茲海默癥的癥狀加重之前,觀眾很難從鏡頭中感受到馮濟真身上的煙火氣和人情味,她仿佛是一個“被建構”的存在,觀眾看到的是一個“裝在套子里的人”,尤其在電影前半段,鏡頭所展現出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客觀性的,而很少帶有她個人的真實氣質:我們只知道她每天的最主要工作是整理父親的考古日記,卻不知道她本人喜歡、厭惡什么。父親的自殺讓年幼的馮濟真背負了一生的罪念與愧疚,可謂她個人氣質的直接塑造者。也正因此,馮濟真的每日輾轉的生活空間始終充斥著父親的影子,“日常空間是日常生活所代表的那一類空間,它是表征性的空間,正是身體的獨特實踐產生了這種既不同于自然空間,也不同于心靈空間的日常空間。”以馮濟真無數次的幻視幻聽為媒介,觀眾清晰地知道不管是處于具有烏托邦意義的獨棟小院,還是連接著生死虛妄的湖水,又或是讓人拘謹不安的社會環境,父親所營造的影響與秩序都是無處不在的。對馮濟真而言,盡管父親早已離去,她也從不正面提到自己的父親,但他卻仿佛始終存在于生活的各個角落,父親的愛與遺憾、幼時的美好與過錯始終縈繞在馮濟真所生活的日常空間中。
父親對馮濟真而言是特殊的,雖然她對父親充滿了愛意與敬意,但每當父親的幻影出現時,馮濟真表現出來的行為除了驚喜以外更多的是彌補。電影中有一個父親出現在房間外的庭院中的鏡頭,這時屋內的馮濟真發瘋似的試圖打開房門,這無疑召喚了她內心最深處的恐懼。又如在馮濟真去醫院看病時,鏡頭對著馮濟真,但卻傳來了醫生對另一個病人說的話“天鵝絨、面孔、教堂、紅色、菊花”,而這里提到的每一個詞語都對應著一段與父親有關的記憶:天鵝絨是馮濟真想要送給父親的禮物、面孔指父親的臉、紅色是和父親一起跳舞時的紅裙子和小皮鞋、菊花是父親生前喜歡的花束。盡管父親是“不在場”的,但他串聯起了家庭三人之間的聯系,也是因為他的不在場,馮濟真所有的沉默與孤獨都變得合理化,也間接地使得馮濟真所有的日常生活空間都含有不同于物質實踐的表征意義,而那個關于“我愛你”的暗號則成了失語情境下穿越時空、跨越生死的浪漫表達。
(二)母愛與自然的表達
這部電影與其說是以子女對母親的稱謂為名,不如說是子女對母親發自內心的呼喊,正如導演楊荔鈉在接受訪談時提到的,“如果‘媽媽’不放任何標點符號,它就是一個名詞;如果放上感嘆號,它就是一個情感詞,為母親這個詞匯注入更豐富的情感和力量感,它的意義就不像名詞那么單薄。”雖然電影主要以馮濟真為視角,但毫無疑問全片飽含著濃濃的母女之情,尤其是在馮濟真病癥加重后,母親蔣玉芝對她“母狼護崽”般天然的保護讓整部電影都溢著暖暖的愛意。雖然馮濟真的性格孤僻,在表達愛意時也常常采用隱晦甚至有點強硬的方式,母親反而成了弱小的一方,但正是前期這種顛倒的母女關系的設定,讓蔣玉芝更顯出身為母親為保護孩子而煥發的強大能量。在描述母女關系時,自然作為馮濟真整個人的療愈與救贖空間,同時也成了彰顯兩者之間關系的鏡子,尤其是自然中與水有關的空間成為電影中表達母愛的表征性空間,電影中主要包括三個空間:被雨水洗刷后的庭院、湖水以及大海。在馮濟真與母親坦白了自己的病情后,有一段長達20 秒的關于雨水澆打庭院中花草的空鏡,在這之后,母女兩人的關系再次“反轉”:蔣玉芝再次恢復了照顧者的角色,披上盔甲重新回到保護幼崽的戰場,用自己的光與熱為馮濟真樹立榜樣。這之后的故事發展正與雨水淋過花草后陽光再次照到庭院中的空鏡相呼應,既是她們內心從恐懼沮喪到積極向上的反映,也是遭受疾病摧殘的生命仍然頑強生長的反映。后期隨著馮濟真疾病的不斷惡化,她非理智的一面不斷展現出來,與母親之間的沖突也越來越多。兩人之間的激烈拉扯與母親的崩潰也是發生在下著暴雨的庭院中,馮濟真肆意地躺在椅子上接受著這場來自自然饋贈的雨水的洗禮,而母親面對無法溝通的女兒感到了深深的無力。在這處半開放式的庭院中,在雨水與院中花草的互動中,母親對女兒的照護、包容展露無遺,生命的意義也在母親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超越下得到了新的詮釋。
在故事前半段,湖水一直被馮濟真視為安全、自由的空間,她常常獨自一人出現在這一場所,而母親作為“外來者”與馮濟真一起出現也意味著馮濟真封閉的內心逐漸愿意向母親打開,對父親的愧疚感也逐漸消散。然而湖水對于母親而言似乎是一種沉重的存在,湖面所倒映的目前的面孔充滿了一種沉淀過后的憂思與悲傷——她的丈夫投湖自殺、女兒日漸加重的疾病都成為她無法言說的隱痛。在湖水這個鏡面中,她凝視著自己衰老的面孔,在自然這個靜謐無人的空間中反復咀嚼生命的流逝與歲月留下的無法抹去的刻痕。在電影結尾,母女兩人穿戴整齊,以優雅的姿態走向包容萬物的大海,而這又與馮濟真所言的“媽媽是海,我是一滴水,爸爸是一條不會游泳的鯨魚”重疊。海這個孕育著巨大生命的自然空間正如同母親源源不斷的生命能量與對子女的愛意,溫和地撫慰著疾病折磨下的馮濟真。“大海更像是蔣玉芝和馮濟真這對母女的精神家園,海浪洶涌,人生浪潮,還有母愛的力量都包括其中”,同時,在這個自然形成的廣闊空間下,大海似乎也以一種更廣大的胸懷擁抱著每一個渺小的、微不足道的生命個體,在這里關于生命的終極意義的答案也以開放的方式交付給了每一個愿意傾聽的觀眾。
(三)生命的延續
在電影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女性角色就是周夏,她的出現打破了馮濟真原本循規蹈矩的生活,成為電影中一抹鮮活的色彩。周夏以“犯錯的年輕人”這一形象出場,馮濟真在公交車上與她的對視意味深長,在這之后,馮濟真一次次選擇寬恕,用自己的愛意感化了叛逆的周夏。而對于馮濟真而言,周夏不僅僅是他者的存在,更在她身上看到了曾經犯錯的自己,正如影片中周夏所言“看上去像是你拯救了我,但其實是我成全了你也說不定”。周夏的鮮活、充滿生命力是過去的馮濟真擁有過的能量,也是現在的她最缺失的部分,馮濟真不愿意看到年輕的生命走上歧路,這既是對周夏的救贖,也是對曾經的自己的救贖。在臨近結尾的部分,煥然一新的周夏再次出場,這時她依然充滿活力并且孕育了一個新的生命,當她出現在馮濟真的家中并為馮濟真和蔣玉芝幫忙時,電影響起了輕快的音樂,整個家庭的色彩明顯提亮,畫面中充滿了陽光。
馮濟真的前半生一直將自己封閉在這處象征著美好也包含著罪惡的空間中,父親曾經居住的小屋更是她不愿意輕易打開的私人空間,而鏡頭透過那扇小窗,最終緩緩定格在屋內周夏育兒的畫面上,也意味著原來的執念與愧疚終究逐漸淡去,新的生命將會不斷承載著愛與希望,一直延續下去。在這處原本充斥著昏暗與衰老氣息的封閉空間中,楊荔鈉以最后窗戶內的暖調畫面作為漆黑房間的點綴,以充滿活力與希望的生命作為整個空間生產的輔助,以此進行意識形態的再生產,完善了影像空間生產最為重要的層面。
整部電影以一個又一個空間連接起馮濟真的日常生活,也借此將她的內心世界外化,構建起馮濟真的過往與未來。在空間的轉換下,馮濟真與父親、母親和周夏三人的關系不斷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關于生命問題的終極回答。楊荔鈉導演以細膩真實的鏡頭對準隱藏在社會皮囊之下的問題,畫面中對家庭中日常生活的表現,始終都以人文精神和人道主義為底色,講述個體的生存境遇,成就了一部包裹著濃厚溫暖之情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