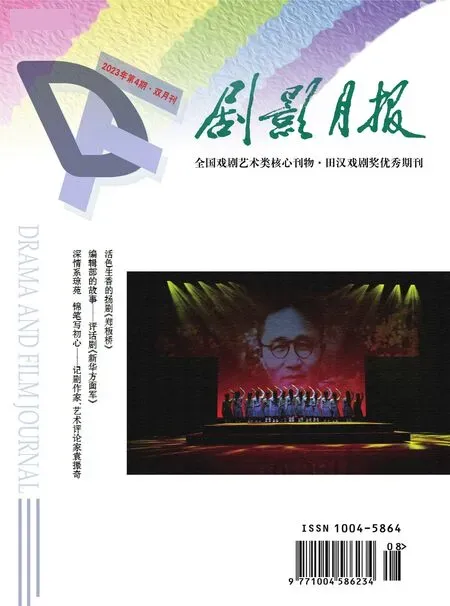“十七年”以來粵劇電影批評形態的嬗變
——從《搜書院》到《白蛇傳·情》
■徐可
粵劇電影《搜書院》由上海電影制片廠攝制于1956年,并于同年上映,是中國第一部彩色有聲粵劇電影,《白蛇傳·情》則是由珠江電影集團有限公司、廣東粵劇院打造的中國首部4K全景聲粵劇電影,于2021年上映。據《粵劇電影史》記載,1966年至2004年的出品粵劇電影作品僅有20部,無論是在出品數量或討論熱度上都始終不及“十七年”黃金時期的經典作品。直至2021年5月20日在全國院線首映的《白蛇傳·情》,作為國內首部4K全景聲粵劇電影,再次將粵劇電影推入一個全新的時代,1956-2021的65年間,粵劇電影在截然不同的創作環境下,發展和進步的并不僅僅是作品本身,隨之而來的還有粵劇電影批評形態的嬗變。
一、從紙質媒體到網絡媒體
十七年時期粵劇電影批評的載體以紙質媒體為主,主要陣地為報紙、雜志或海報等刊物對電影放映的報道和影評,批評載體的路徑相對單一,而《白蛇傳·情》則批評來源廣泛、信息海量。對《白蛇傳·情》的批點評論不僅體現在嗶哩嗶哩bilibili網站上的彈幕,還體現在豆瓣的長評短評、淘票票的分值點評上,以及諸多的自媒體平臺“今日觀影”或“好片安利”的分享型評論上。此外還有短視頻形式的“帶看好片”節目,即博主以個人對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將影片進行重新剪輯并配有解說。當網絡媒體開始取代紙質媒體而成為主要媒體平臺,所改變的并不只是一個載體那么簡單。媒介的改變,同時帶來的是思想結構與認知能力的改變,即尼爾·波滋曼在《娛樂至死》中所提出的“媒介即認識論”,外部原因所造成的批評載體和媒介的改變,隨之而來的也是批評內容和方式的轉變。
“十七年”時期是粵劇電影,甚至整個中國戲曲電影發展的繁榮期,但這一時期的戲曲評論都是高度政治導向和意識形態化的,因而這一時期戲曲評論中最為多見的關鍵詞就是“封建性”和“人民性”。梅蘭芳《動人的喜劇〈搜書院〉》一文中,先是在題材和精神內核上對作品進行肯定,認為其歌頌了受封建勢力壓迫的一個勞動女性的斗爭精神和主持正義、扶弱抗強的正義行為。而后才在故事構造技巧、人物形象塑造和粵劇表演上進行評點。其批評的結論認為,粵劇曾經走上商業化、殖民地化的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經政府的領導,和演員政治水平的提高,清除了表演上那些不好的現象,所以我們在這一出戲里面所看到的乃是氣象一新的民族傳統藝術。正是由于這些大量充斥意識形態的話語,這一時期留下的海量的戲曲評論文獻中,可資今人的資源實際上非常有限。這一特點既是時代的整體批評氛圍所致,亦是作品本身的內容所致。
《白蛇傳·情》的評論則截然不同,無論是思想上還是內容上我們都會看到完全不一樣的關鍵詞。《白蛇傳·情》最為熱門的核心關鍵詞即是“破圈”,“破圈”一詞并非現代語法規范中的詞語,而是網絡流行語,指某個人或作品突破小圈子,被更多的人接納并認可,這一關鍵詞正切合作品在宣發初期的自我定位,即“年輕人的第一部粵劇”。在這場由“破圈”所引發的討論中,對這部粵劇電影的批評不僅有對曾小敏表演功法的討論、對“情”這一思想內核的討論、對戲曲與電影兩種藝術形式之間的討論,還吸引了受眾發散性地討論水墨畫的意境美學、4K全景聲下的視聽感受,以及對傳統戲曲文本中的性別議題的討論等。
從《搜書院》到《白蛇傳·情》的批評、比對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社會對藝術作品批評的眼光從以意識形態為先的立場,轉向更加廣闊的批評空間,觀眾可以同時處于人的立場、文化的立場、科技的立場、藝術本體的立場進行批評。
二、從專業批評到大眾批評
當批評變得“自由”,自由的不僅是批評的語言,還有批評的群體。傅謹認為,戲曲的評論的撰寫主體主要分為注重政治導向與意識形態化、以指導創作為動機的“專家評論”,從戲曲藝術本身討論劇目和表演的“行家評論”,以及以寫作為目的、將評論當作純粹的寫作活動的“作家評論”。但縱觀這些類群可以發現,這一時期的批評是有門檻的,批評的話語權始終掌握和局限在小部分人手上,罕有普通的民眾批評,對一部作品評價的褒獎或批評大多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傳達”。整體而言,批評氛圍相對緊張,批評群體相對集中。而《白蛇傳·情》自出世以來所面臨的是完全不同的批評環境,自媒體時代下,人人都能成為批評者。“淘票票”平臺的數據顯示,“想看用戶”的數據統計中,30歲以下的想看用戶占比高達80.4%。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到,涉及粵劇電影的批評之前,《白蛇傳·情》從觀眾群體層面就開始發生根源性轉變,相比于大眾認知中的近年來戲曲藝術的受眾老齡化甚至面臨斷層危機的現狀,《白蛇傳·情》已經完成了它的初步“破圈”。遍及全網的討論中,批評群體涉及專家學者、演職從業人員、營銷人員、戲曲愛好者、普通觀眾等各個群體。在同樣掀起的討論熱潮中,《白蛇傳·情》區別于《搜書院》自上而下的全民效應,完成了由觀眾自發地、自下而上地觀影與分享的熱潮,使粵劇電影的批評走向大眾化。這一轉變的完成,既需要科技與網絡媒體平臺的賦能,也需要寬松自由的社會批評環境。同時,從批評模式上看,粵劇電影的批評也不再局限為一篇文章或報道式的單向輸出型評論,而是成了集彈幕、評論、點贊、分享為一體的互動型、交流型評論,網絡的世界極盡暢所欲言。然而,辯證地看待這一轉變時,也會發現,當批評群體的范圍擴大、批評的環境變得寬松以后,在海量的信息中,有效、優質的批評則如沙里淘金,批評的大眾化一定程度上伴隨著批評的簡易化、碎片化、低質化。
在面對批評內容的轉向時,不得不關注的是,自“十七年”時期以來中國電影批評界對戲曲電影進行的三次重要的討論,始終圍繞戲曲與電影兩種藝術形式的本體特征進行。電影藝術是舶來品,而戲曲電影則是其與中華民族傳統藝術的碰撞和結合,正是這一嘗試開啟了電影藝術進入中國后在地化的探索。誠然,這一時期的批評探討為戲曲電影的進一步發展做了十分豐富的理論準備,但始終未能真正從實踐層面解決兩種藝術的融合問題。
關于“以影就戲”和“以戲就影”的問題討論同樣出現在《白蛇傳·情》的批評中,可以發現的是,相比于“十七年”時期聚焦于戲曲服從電影還是電影服從戲曲的主次問題討論,當下粵劇電影的評論更傾向于探索和討論此次創作中戲曲與電影之間虛與實的矛盾處理、敘事手法和敘事節奏之間的契合、鏡頭語言對戲曲表演割裂的處理與取舍的問題。如被多次討論的戲曲舞臺是使鶴童頭配白翎,鹿童戴有鹿角,在裝扮上盡力還原鹿、鶴兩種動物在外形上的特征,影片中則以特效的動物原身取代戲曲舞臺上將動物作擬人化的處理,對動物角色的徹底還原,又在之后的打斗過程中使之幻化為人形亮相,完成角色的行動。此外還有諸如此類的多個處理細節都成了《白蛇傳·情》評論中的熱門話題。
三、從引導性批評走向宣傳性批評
“十七年”時期是《搜書院》的熱映時期,傅謹認為,這一時期粵劇電影批評的特點就是強烈的現實觀照,對戲曲作品的創作和演出活動強烈的“指導”意識,在映射觀眾對作品接受程度的同時還作為政治修改意見的指導,從而反作用于內容,推動文本的修改與生成。周恩來曾在《十五貫》座談會中談道:“粵劇也是受了批評以后奮斗出來的,廣東粵劇團代表在中南區會演時受了批評,參加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后,回去就革新。”在這段講話中可以看到,《搜書院》的批評是對其創作和修改具有建設性建議的,而此次大會中對《搜書院》的評點則是來自官方意識形態對作品和劇種改革與進步的肯定,既是肯定其在新中國戲曲改革和建設中取得的成就,更是通過樹立《搜書院》這一成功的范例,為粵劇藝術今后的發展指明方向。
與之不同的是,對于當下的《白蛇傳·情》而言,鋪天蓋地的網絡批評更多的是作用于宣傳,成為作品市場營銷的一種手段,從此間也能看出粵劇電影營銷手段的變化。當作品推廣宣傳的主要載體從報紙雜志和海報場刊轉變為網絡宣傳平臺,對作品的宣發則主要集中在抓人眼球和全平臺覆蓋的推廣軟文中。推廣軟文的撰寫要點在于吸引眼球,要求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引起受眾的觀影興趣,從而成功將讀者導入影院成為電影的觀眾。這一目的導向下的軟文內容無疑將走向同質化,且數目繁多使觀眾難以辨別優劣真假。尤其如微信公眾平臺和知乎等網絡平臺上,甚少能看到中肯的評論,檢索作品關鍵詞后,跳出來的大多都是一些推廣軟文,這些推廣軟文之間亦不斷地相互引用或引用其他平臺的評論來證實這一作品的受歡迎程度。在這一過程中,原本批評的反饋機制功效被削弱,使觀影市場和評論市場中充斥的大多都是內容雷同的推廣軟文。在這一社會批評生態下,批評似乎不僅僅是觀眾對作品喜好接受的映射,而在更大程度上被操縱成了宣傳的工具,用以為票房造勢,這也呈現出網絡媒體對內容發布的不負責任,媒體為作品站臺的現象,實則是一種盲目的行為。
之所以會出現此類“站臺”現象,很大程度是藝術創作的市場化導致的,其背后的內在運營機制是由商業資本控制藝術批評,實則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批評的寬度和廣度。王安奎曾在接受謝雍君的采訪中提道,現在對戲曲批評作用的認識還存在錯位,報刊上發表的戲劇評論,很少是評論家看了戲之后,發自內心的沖動而主動去撰寫的,大多是受到主創單位的邀請而寫的,把評論當成幫助作品獲獎的“附件”。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藝術作品批評的市場化已經初見端倪,而此中所提到的對戲曲批評作用的錯位在當下的《白蛇傳·情》中依然是不可忽視的問題,很大一部分職業寫手并不是在認真負責地評點,而是隨意地撰寫通稿,從而完成宣傳任務和市場效益。從這一層面上看,粵劇電影的批評掙脫了一些束縛,卻不可避免地走向市場化、商業化。
但通過對這一現象的理性分析,可以發現的是,網絡宣傳的風向標實則根源于市場的大眾審美趣味。在《白蛇傳·情》的批評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當代觀眾藝術審美的轉型。當越來越多的寫手和宣發平臺對《白蛇傳·情》的特效、水墨畫、科技感極盡溢美之詞時,折射出的正是當下市場審美對這一類型作品的青睞。因而在《白蛇傳·情》的滿屏夸贊中,盡管能夠看到粵劇電影的批評對作品的功用轉變,但實際上依然在引導著創作者更貼近當下觀眾群體的藝術市場和審美趣味,也為之后的粵劇電影創作和市場指引新的方向。
一部作品的批評史即是一部作品的接受史。安葵認為,戲曲批評應該跟上時代。藝術鑒賞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創作也就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批評自然也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因而,從不同時代的粵劇電影批評中我們所感知到的變化正是粵劇電影本身在藝術形態和市場接受中的變化與發展,從“十七年”時期到當下,從《搜書院》到《白蛇傳·情》的批評形態嬗變中,折射的也正是粵劇電影乃至戲曲電影的發展方向,而當下的批評形態在藝術內容與市場效益間的搖擺,及其將如何反作用于戲曲電影的發展和對藝術作品本身歷史價值的界定,仍需進一步地深入研究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