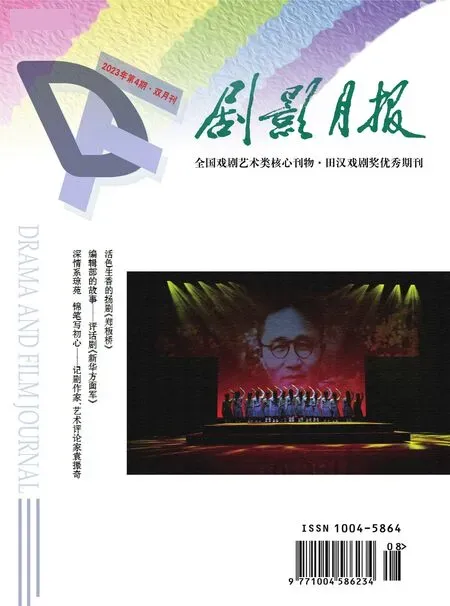優雅的傀儡
——薇拉·齊蒂洛娃電影《雛菊》的木偶美學分析
■段心玫
1966年,捷克女導演薇拉·齊蒂洛娃完成了電影《雛菊》,這部作品不僅作為齊蒂洛娃早期先鋒電影的代表而蜚聲國際,更奠定了她在“捷克新浪潮”電影運動中不可替代的“旗手”地位。《雛菊》以極具風格化和實驗性的視聽語言、充滿隱喻與諷刺的鏡頭表現,以及滑稽與嚴肅并置的哲學表達,成為“捷克新浪潮”乃至世界影史中獨樹一幟的存在。
《雛菊》影片結尾的字幕顯示“這部電影獻給那些精神生活完全混亂的人”。齊蒂洛娃曾表示“《雛菊》是一部告誡年輕人的電影,它批判而非贊揚這兩位少女”,并將《雛菊》自稱為“一部鬧劇式哲學的紀錄片”[1]。《雛菊》的世界是通過兩位少女的形象來建構的,因此國內外學者對薇拉·齊蒂洛娃和《雛菊》的研究視角多集中于女性主義、性別政治及影片的東歐式現代文化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木偶”和“木偶戲”作為《雛菊》的貫穿意象和內在美學手段鮮少被研究者關注,盡管兩位少女“玩偶”“洋娃娃”般的形象在《雛菊》的評論和女性主義研究中常被探討,人們認同“齊蒂洛娃希望將兩個經典的少女形象刻畫成為一種沒有感情的、容易被擺布的、溫馴的玩偶形象”[2],但不同于在易卜生《玩偶之家》中被認為是“受控于男權社會的玩偶”的娜拉,齊蒂洛娃在《雛菊》中塑造的兩個看似易于擺布的“瑪麗”,實際上具有比“玩偶”更特殊、更復雜且超越了女性主義批評范疇的身份屬性——“木偶”“傀儡”以及“木偶師”或許更能定義她們的存在本質,“木偶”并不是對“玩偶”的簡單挪用,而是在齊蒂洛娃獨特的鏡頭語言與木偶戲劇藝術的結合下,開辟出的全新意指空間。
一、被操縱的木偶:《雛菊》的政治隱喻
木偶,即“偶”“傀儡”,美國木偶劇導演比爾·貝爾德在他的《木偶的藝術》中定義“劇場木偶”是“由于人的操作在觀眾面前活動起來的,不屬于動物范疇的人形。”[3]木偶戲劇藝術的研究者通常認為,木偶是人的縮影和變形,它不僅是人類的隱喻,而且通過人與木偶的關系,對人類自身進行了深刻的哲理思考與理性研究。[4]因此,木偶是人的孿生體,是人類靈魂的載體,它向我們傳遞了更為深刻的信息,影射出文明世界中的人及人與他人、與世界的關系。
木偶戲是捷克最重要的傳統藝術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紀,見證了捷克民族的歷史變遷,在統治勢力更迭、國家遭到入侵和吞并時,木偶戲更成為捷克人民保護文化遺產、保存民族語言的重要工具。[5]在斯大林主義限制真人影片內容的時期,木偶從劇場延伸到熒幕,將其政治功能轉移到影像中,產生了大量具有政治諷刺意味的木偶動畫,導致捷克動畫比電影更容易觸碰現實。
木偶本身具有較強的政治意味和后現代隱喻,木偶的面孔似人而非人,專心的神態和僵直的動作讓它具有神秘性。一方面,木偶作為被操縱的對象,具有其獨有的“偶性”(或“傀儡性”),即在偶師的操縱下造成僵死、機械的效果。捷克動畫大師楊·史云梅曾在訪談中強調,木偶根植于他的精神土壤,他認為木偶完美地象征了當代人的性格和生存狀態,這種人在現實中被外界操控的狀態,正如當時捷克現實中的每個人。[6]
《雛菊》作為一部極具前衛性和實驗性的電影,通過一系列的視覺表現手法和敘事技巧,向觀眾呈現出一個充滿反叛和抗議情緒的捷克社會,《雛菊》中的瑪麗就是被外界力量操縱的兩只木偶。影片開頭,固定中景展示兩位穿著比基尼泳衣的少女倚靠木板并排而坐,她們四肢無力、面無表情,兩腿直直叉開,瑪麗一號睜開眼睛,機械地抬起右手伸進鼻孔,接著瑪麗二號拿起小號吹出了一個音節,每當她們二人活動肢體的時候都會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她們的關節仿佛木制門的鐵栓,但身體的其他部位仍然松軟無力,就像沒有繩子牽引的木偶。除了肢體動作,兩位瑪麗時常從面無表情瞬間轉變為哈哈大笑,如同沒有過度表情的木偶。隨著兩位瑪麗接連不斷惡作劇的進行,木偶操縱師的面貌也逐漸浮現,有種不可言說的力量支配她們一步步走向更徹底的墮落:醉酒搗亂、捉弄男人、暴飲暴食、欺詐偷竊、焚燒房屋……直到在無人的宴會廳上演最后的狂歡。這種“操控”的主體不僅有她們自身的食欲、情欲等人類欲望,更有墮落、僵化、無聊的現實世界,我們在這種無法掙脫的“操縱”中能看到現實和政治制約中的個體。
木偶本身沒有生命,是木偶操縱師為它們賦予了聲音和動作,在木偶戲劇舞臺上,木偶操縱師作為演員的主體性地位不斷被強調,新型的木偶表演者摒棄了遮擋在身前的帷幕,成為演出的主體替木偶說話,這種人偶同臺的演出方式沖破了亞里士多德的傳統戲劇模式,轉變為布萊希特史詩劇式的“敘述性木偶戲”,其間離效果更加強調了木偶的政治性。
《雛菊》中,導演齊蒂洛娃作為最顯而易見的木偶操縱師時常在場,無處不在地施加她的力量和意志,在天馬行空的蒙太奇剪輯、濾鏡效果以及復雜的拼貼下,兩位瑪麗木偶本身的表演很難連貫進行,頻繁的跳接鏡頭讓影片的時間、空間失序而隨意,觀眾很難全神貫注地卷入傳統的故事“幻覺”中,反而在導演的有意呈現中不斷被刺激出思考與批判的欲望。影片開頭即是軍樂號聲中,大型機械的鐵輪與齒輪在轉動,隨后接連切換為流彈四射、飛機轟炸等畫面,與結尾吊燈墜落后的畫面相呼應,再結合開場兩位少女經典的“世界在變壞”對話,能夠感知到導演有意以此隱喻一個秩序遭到摧毀、意義無限缺失且道德和價值觀失范的社會,從而引發兩位少女之后不斷挑戰“墮落底線”的焦慮實踐。
因此,齊蒂洛娃和兩位瑪麗構成了一次敘述性木偶戲的表演,木偶在諸多力量的操縱下完成一次政治隱喻,而導演以獨具風格的視聽語言完成后現代批判與暗示。在這次表演中,木偶形象成為表現人與政治、都市文明、機械文明沖突以及個體異化的表征。正如洛特曼對木偶文化演進的描述:“我們的文化意識中形成了兩種傀儡:一種指向安逸的童年世界,另一種則暗示著虛假的生活、僵化的動作、死亡和矛盾。前者關注民俗、童話和原始,后者使人想起機器文明、異化、二重性。”[7]
作為“被操縱的木偶”,兩位瑪麗使《雛菊》具有喜劇與鬧劇的美學特性,旨在打破觀眾的慣性思維,引起他們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使木偶美學呈現出一種游戲性和幽默感,使得電影更具吸引力和趣味性。影片中瑪麗們的行為輕松而滑稽、敢想敢做,她們的面部表情和軀體動作極不協調,產生了強烈的反差、尖銳的矛盾,造成了可笑性和滑稽感,木偶般的演員、面具式的臉孔,以及與她們形象截然相反的瘋狂行為,共同造成了《雛菊》猛烈的視覺沖擊力。
二、被異化的木偶:《雛菊》的雙重假定
如果說“人偶同臺”只是將木偶師請到臺前的木偶戲,那么“人偶結合”則是“人戲”與“偶戲”之外的第三種特殊表演形式。不論是中國還是歐洲,都存在人模仿木偶動作、人變成木偶演出的表演形式。中國福建的高甲戲傀儡丑就是人模仿木偶的典型例子。演員在舞臺上模仿提線傀儡的動作,且形成了成套的表演程式,并由此出現了一個新的行當——傀儡丑。在歐洲,早在20 世紀,戈登·克雷就提出了將演員作為“超級傀儡”的概念,俄羅斯的布拉吉諾劇院也曾上演過人模仿偶從而暗指人被異化成木偶的表演。
從“人偶”到“偶人”,從“真傀儡”到“仿真傀儡”,這種新型木偶戲強化了表演的假定性與劇場性,甚至實現了“倍增”后的雙重假定。洛特曼認為,我們對傀儡戲的認識是在與活人演出的戲劇的相互關系中去理解接受的。因此,如果活的演員扮演人,那么傀儡在舞臺上就是扮演演員,傀儡則成為“扮演的扮演”。如果傀儡在舞臺上是“扮演的扮演”,這種效果為“倍增詩學”,那么真人演員在舞臺上模仿傀儡就成了“扮演的扮演的扮演”,即“再次倍增的詩學”。其舞臺效果對假定性的強調,將進一步地將觀眾與舞臺、角色間離開來,破除幻覺并啟發他們以批判的態度進入思考。
《雛菊》對木偶戲的極致運用就體現在:劇中的兩位瑪麗不僅僅是“被操縱的木偶”,更是“被異化的木偶”,或者說是套著木偶外殼的真人演員,她們同時是被操縱的對象和主體,這種雙重身份的復雜性混淆了觀眾的視聽,也打碎了她們自身的理性與身份認同,人即是偶,偶即是人,時真時假,矛盾而統一。她們與“木偶外殼”時而和平共處,時而激烈對抗。
影片中,兩位少女多次表現出自己的“存在焦慮”——她們究竟是否存在?她們把從雜志上剪下來的紙片人扔進裝滿牛奶的浴缸,瑪麗一號問:“甚至連一個人不再存在也沒關系嗎?”她們對坐在浴缸中展開對話:
你怎知我們是我們?你存在又從何知曉?
因為有你。
是吧,不然你證明不了。我們完全沒有在這里的工作,沒有證據證明我們的存在。
她們彼此成了對方存在的證明。而當她們來到郊外,對著田野里干活的農夫呼叫卻沒有得到注意,在街上行走的時候又與許多騎單車的男人擦肩而過,瑪麗一號若有所思道:“我在想為什么農夫沒有注意到我們”“你知道什么最讓我擔心嗎?就是我們對他來說是不可見的!我們已經蒸發了,為什么他沒有注意到我們?為什么騎單車的人沒有注意到我們?”
她們不斷逾越著日常生活的邊界,試圖尋找自己存在的證明,背后隱含的是對自己主體性的懷疑和探索,就像一只木偶試圖找尋自己生命氣息的存在,而這種哲學式的追問帶來的是一次次主客體權力的扭轉,她們開始用主體的操縱實踐來證明自己作為“活人”的存在。
影片中兩位瑪麗的樂趣之一是捉弄一個又一個男性,她們純潔無知的外表看似被男性客體化的對象,但實際上男性只是她們滿足進食欲望的手段,在瑪麗二號與第一位老男人約會時,瑪麗一號表現出了典型的進攻性,她步步緊逼質問男人、放肆吃喝,消費并審視著對方,男人對瑪麗的這種“操縱權”十分不適,瑪麗反而同時作為木偶師和木偶客體化了對面的男人。而當轉向室內,瑪麗用剪刀把一大堆香腸、雞蛋等食物剪碎,同時對電話里追求者的情話無動于衷,無論這里的香腸是否是男性生殖器官的隱喻,瑪麗果決而暴力的行為活像一個跳脫于故事之外的木偶師,用平靜的目光和“剪”的行為進行自己的木偶表演。
因此,兩位瑪麗的木偶屬性變得愈加復雜,她們同時是木偶和木偶師,包含迎合觀看與破壞觀看的雙重氣質,具有“扮演木偶”和“模仿木偶”的雙重假定性,在前一節所述“被操縱的木偶”之上實現了更復雜的“異化”,蘊藏著強烈的主體意識和反抗性力量。繼承了“人偶結合”的木偶戲,兩位瑪麗模仿木偶的表演帶有鮮明的價值判斷色彩,包含更深刻的哲學思考:人異化為偶的原因不僅僅有政治與機械文明的制約,更有歸屬感被剝蝕的身份危機和精神困境。
作為“被異化的木偶”,兩位瑪麗使《雛菊》具有悲劇和嚴肅劇的美學特性。《木偶劇場心理學》中提到觀眾接受木偶劇的兩種方式:一是把木偶當成無生命的物體,二是把木偶看成活生生的人,而當我們以后者的接受模式看待木偶時,會因為木偶“過于像真實的人類”而產生驚奇感和恐懼感。過于真實的木偶尚且可怖,何況具有真人演員屬性的瑪麗,她們的雙重身份使電影在刺激與熱鬧之外,時常具有迷惘、悲傷的觀感以及嚴肅的批判和思考。
三、優雅的木偶:《雛菊》的道德自由
德國劇作家、小說家、詩人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寫過一篇著名的論述散文《論木偶戲》講述了作者偶遇一位舞蹈家并和他談話,這位舞蹈家經常在集市看那種下等人才看的木偶戲表演,但舞蹈家卻向作者強調“木偶比活人演員更優雅”,“關于優雅,人是比不上木偶的”,他說一個舞蹈家能從木偶那里學到很多東西,兩個人就在這樣的對談中從木偶戲引申到一切藝術的規律和奧秘。
克萊斯特在文章里提問“舞蹈演員沒有手上的操縱線,如何像木偶一樣操縱肢體動作呢?”舞蹈家回答說,木偶師并非需要一個個去擺弄木偶的肢體,而是“每個動作,都有一個重心;把握住木偶的這個內在的重心就足夠了;跟鐘擺似的四肢,不用去動它,它自己就會機械地做出動作”。除了木偶師只將心靈落在簡單的“重心”之外,文中認為木偶具有人類無法企及的自然和真實,木偶只會以最真實的方式行動,從不存在意志和行動之間的脫節,而人類總會因為克服不了身體和心靈的矛盾而顯得矯揉造作,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精神,精神就不會出錯”。
克萊斯特強調,恰恰是“理性”和“智慧”的能力使我們被逐出了伊甸園,而只有“再吃一口智慧樹上的果子”——對知識和理性否定之否定,才能使我們再次重返天堂。這與《雛菊》中兩位瑪麗的行為不謀而合,她們作為兩只木偶,擁有普通人不具備的純真和直接,具有《論木偶戲》文中的“優雅性”,她們摒棄了良心和罪惡感,喪失了理性和判斷力,她們的“意志”和“行動”之間就像木偶一樣沒有任何脫節,所有的道德規范和社會期待只是她們的玩物,但她們重返的“天堂”并不是克萊斯特所指藝術上的純粹與美,而是一種免于被懲罰、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道德空間。
影片場景不斷在河邊、房間、餐廳、洗手間、站臺間跳躍,時間也在不規律的時鐘嘀嗒聲中呈非線性狀態,導演有意塑造了一個非正常世界,而兩位瑪麗似乎擁有隨意掌控這個世界時間、空間的能力。不僅如此,她們的飲食、睡眠、沐浴等生活作息并不規律,她們沒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卻永遠以光鮮亮麗的姿態出現,在兩人互相用剪刀攻擊對方的片段里,她們的身體就像木偶的身體一樣,可以在沒有痛苦或后果的情況下被拆卸和改造。在這些前提下,一切對她們的道德要求和審判都是空虛的,道德本身也是可戲謔的,更不必提供解決方案,在道德空間里她們只是死去的木偶,只關注一個“重心”的木偶。
利用這種道德自由,導演可以將兩位瑪麗的“墮落”推向極致,呈現出秩序崩壞的種種后果,她們的能動性可以改變世界但不受任何懲罰,并且將觀看電影的觀眾也拉入其中成為共犯,我們正在看瑪麗的“墮落”,而自己也作為旁觀者觀看著這場奇觀,欣賞她們的破壞性行為做出的“貢獻”。就像在木偶劇場里,觀眾需要主動將明顯分離的木偶和木偶師的表演統一成一體,《雛菊》也因觀眾的參與而更加完整。另外,在當時捷克嚴格的政治審查和官方控制下,這種道德上的自由空間也在一定程度上為齊蒂洛娃提供了保護,盡管《雛菊》仍因“浪費食物”的罪名被禁映,但齊蒂洛娃也在之后的致總統信中為自己辯解:《雛菊》是對兩位女孩抱有批評態度的道德劇,它展示了邪惡不一定會在戰爭造成的破壞狂歡中表現出來,更隱藏在日常生活的惡作劇中。[8]
作為“優雅的木偶”,兩位瑪麗讓《雛菊》的滑稽與嚴肅得以統一,她們沒有任何負擔和任務,以木偶的優雅性邀請觀眾自由地感受和判斷,她們可以帶來歡樂、幽默和滑稽,也能讓人聯想起廣闊人生的悲劇,感受到現代性焦慮和對既有文化、道德框架的不滿意、不信任。這種雜糅的觀感就是齊蒂洛娃獨具個人風格的電影實驗,也是她所描述的“一部鬧劇式哲學的紀錄片”。
洛特曼在《文化體系中的傀儡》一文中說:“在一種文化體系中,一個給定的概念原有的作用越是具有本質意義,它隱喻的意義也越豐富,這種意義可以非常富于侵略性,有時甚至可以用來形容一切事物。傀儡就是這樣一種根本性的概念。”[4]這段話指出,具有豐富的隱喻意義的木偶在文學藝術中具有十分廣闊的應用空間。他接著寫道:“生與死、復活與僵化、靈活與機械、虛偽的生活與真誠的生活之間的對立在當代藝術中得到如此廣泛與多樣的反映,以至于越來越明顯。”這是木偶哲學的基本內容,也是本文分析《雛菊》木偶美學的根基。
木偶美學是導演齊蒂洛娃獨特的詩性智慧,木偶構成了薇拉·齊蒂洛娃電影《雛菊》的核心隱喻,也實現了整部影片的核心美學效果。“被操縱的木偶”體現了瑪麗作為被操縱對象的政治意味,使《雛菊》具有喜劇與鬧劇的美學特性;“被異化的木偶”描述了瑪麗主體與客體身份統一的復雜性,使《雛菊》具有悲劇和嚴肅劇的美學特性;“優雅的木偶”指涉影片構建的特殊道德空間,讓《雛菊》的游戲性與嚴肅性得以統一,賦予其悲喜交融、平靜自由的美學特征。木偶美學的建構不僅讓《雛菊》更切中作者的生命體驗,更突顯了作品的詩性智慧,也更能切近文藝本體,更好地揭示齊蒂洛娃的創作規律,齊蒂洛娃也以此完成了這部生動而多義的影片,啟發我們思考個體存在、人類境遇和更深入的現代性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