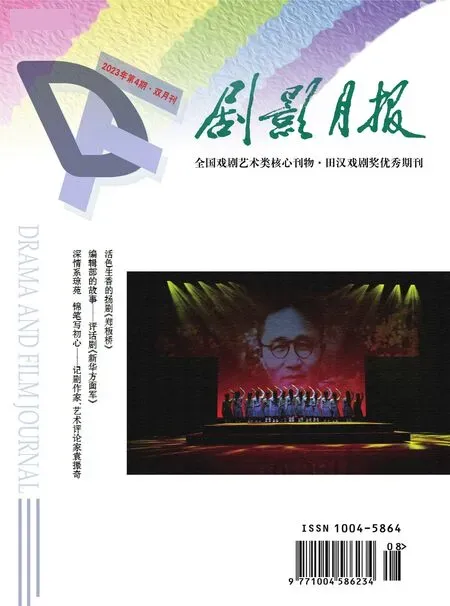淺析東亞語境下的電影美學新趨勢
——以電影《分手的決心》為例
■聶君伊 唐國棟
電影《分手的決心》將身體欲望的凝視演變成一種對“情緒”欲望的展示,全片圍繞愛,卻言不提愛,更像是一種“更無言語空相覷”[1]的情景,愛意蘊含在人物的內在之中,影片將愛割裂成前后兩段,用懸疑的方式連接成一個整體的悲劇。該片不同于大部分愛情電影,影片展現出導演內在對原始欲望的思考。宋瑞萊和奇道秀之間的關系是“所有欲”,和林浩信的關系是“貪欲”和張海俊的關系是“情欲”。本片回歸到人類的本質屬性,結合東方傳統含蓄內斂的品質,將情欲進一步升華,從而實現了東方傳統美學與西方現代美學的有力結合。
一、對形式美的藝術追求
(一)外在之形色美
電影畫面是根據拍攝題材和主題思想的要求,對環境、人物進行合理的分配布置,形成一種和諧完整,具有藝術美感的畫面。畫面能夠客觀地記錄場景中出現的人和發生的事。“電影畫面首先是現實主義的,或者更確切地說,它擁有現實的全部(或幾乎是全部)外在表現。”[2]因此畫面具備了形式美的部分構成要素,即作為基礎的形與色。通過導演對畫面布局和色彩的精雕細琢,實現了從三維立體到二維平面的個性轉變,從而展示電影的外在美感。
“形的審美特征要從其造型元素的審美特征去理解。”[3]在電影藝術中,可以通過鏡頭變換來刻畫造型。采用仰俯拍交代人物強弱感和身份地位轉變,通過影片人物前后兩種攝影技法,展示人物落差。通過直線和曲線展現男性和女性的形體特征,刻畫人物性格,同時直線和曲線交雜,在視覺上形成錯亂感,為影片懸疑鋪墊了外在“形”美。越軸鏡頭展示空間錯亂非現實的美感。在《分手的決心》中,宋瑞萊催眠張海俊時采用了越軸,這種空間錯亂感加上“同呼吸”暗示著兩人不可言說的關系。服裝造型上張海俊是具有呆板性的,西裝領帶迎合著女性觀眾對男性的審美,也符合人物呆板的特征。風格多變的宋瑞萊迎合著男性觀眾對女性的喜愛,也為女性角色增添了一層神秘感。
馬克思認為“色彩的感覺是一般美感中最大眾化的形式”[4]。不同的色彩能夠給人帶來不同的心理感受。《分手的決心》選用了冷色調來體現影片意蘊深遠,文化氣息嚴肅莊重。影調采用黑藍色系,對影片進行憂郁情感的鋪陳。通過陰郁色彩基調渲染了悲情故事結局、東方傳統對情愛的隱晦氛圍,以及成人視角對欲望的索求。同時色彩升華了影片的莊重感,營造了影片的懸疑氣息。色彩基調為影片更好地講故事、渲染影片懸疑悲情基調奠定了外在“色”的美感。黑色憂郁美學釋放壓抑的情緒,悲情浪漫主義緊緊貼合悲劇核心,是色的盛宴。色是光之子,光是色之母,在光影上,男主在發現女主是兇手時,同樣的室內燈光下女主臉上是有光的,男主是無光的處境,男主因為自己陷入感情旋渦做出錯誤判斷,進入崩潰狀態,女主被男主保護自己的行為而打動,迎來光輝。簡單的雙人對話用光影緩解了觀眾視覺疲勞,增加了畫面美感,也暗示著女性在劇情發展中將要引導男性。
(二)情與欲的無言之美
愛情與欲望是一種無言之美。“本來愛情完全是一種心靈的感應,其深刻處是老子所謂不可道不可名的。”[5]愛情是互相吸引,在吸引之中產生了“探索欲”“情欲”等系列欲望,欲望催化了愛情的發展,升華了對內在美的展示。《分手的決心》在“情”和“欲”的心理層面做了很大的鋪墊,影片展示了一種不言不語的愛。愛情既抽象又具體,言語難以形容情的深意。荷爾蒙使得戀愛者無限制地放大對方的優點,忽略對方的缺點,做出非理性判斷,在此語境下戀愛者認為自己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在《分手的決心》中,導演通過鏡頭語言隔閡著張海俊和他的兩個搭檔,通過二分構圖、背對背爬山等攝影技法暗示張海俊和吳秀完意見不一,結果必將分離。吳秀完懷疑宋瑞萊,張海俊卻“迷戀”于宋瑞萊的氣質,選擇相信宋瑞萊,做出非理性判斷。在張海俊和呂妍秀搭檔中,通過車內、車外營造巨大冰冷框架的隔閡,隔開兩人的默契,呂秀妍無條件地相信宋瑞萊,張海俊則極力地想要克制愛欲,保持理智,選擇不相信宋瑞萊,再次出現錯誤判斷。兩次非理性判斷都源于“愛”的變故,劇中對愛的展示融入了人物性格,通過人物行動向觀眾傳達了無言的愛,那些輕而易舉就能產生的默契,那些為了見對方找出的各種荒唐理由是“無言”的最好表達。 欲望的目的性催化了感性的進程。欲望會使人充滿幻想,像朱塞佩·托納多雷的《西西里的美麗傳說》、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等這些作品將人的幻想實體化,把人內心的世界物象化,創造出幻想的一種真實觸感,從而達到欲望影視化的目的。其理論依據是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中夢是欲望的滿足,“夢的內容是在于欲望的滿足,其動機在于某種愿望”[6]。《分手的決心》中,張海俊通過望遠鏡充當幻想框架進入宋瑞萊的生活世界,替她接煙灰,嗅她的味道,滿足自己的“偷窺欲”和“愛欲”。影片通過這種表現方式,展現了張海俊的內心世界,通過具有真實觸感的場景滿足了他的一系列欲望,所以他在這樣不舒適的環境下睡了個好覺。多巴胺是快樂因素,對睡眠、失戀有調節作用。張海俊患有失眠癥,來源于張海俊對“犯罪欲”的渴望,從而實現自負的斷案能力。在他發現宋瑞萊是兇手的時候,他選擇了自我的“崩潰”來包庇女主。
二、對意象美的詩意表達
(一)意與象的東方古典之美
中國古典美學藝術表現注重“象”對“意”的傳達。《易傳》中的《系辭》首次明確提出“象”與“意”的關系,“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以盡意”東方藝術不受實體形象的限制。繪畫上不同于西方現實主義,西方注重現實場景、人物的刻畫。中國卻是單一的黑白配色,不合實際的畫面比例,畫面出現大量留白,將蘊意留給觀賞者思考感悟,注重思維意蘊的留存。影視作品不同于繪畫形式的表現,“象”更為具體,通過具體的事物,傳達影片人物的關系和電影內涵。《分手的決心》中,男主與女主通過擊鼓,表達一種愛情互相回擊、你退我進的晦澀情感。影片圍繞《論語》“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而展開,展現出一種儒家山水觀,孔子在對山水的審美中,抓住了水動山靜的特性,將知者比擬成水,體現思維的活躍,將仁者比擬成山,體現安于禮義。其本質上,山、水都是“象”,各有各的物質形態。而知和仁是抽象概念的哲學思維,沒有具體的形象,只憑語言的表述顯然蒼白無力,只有借助“象”才能進一步解答深意,電影通過山水意象傳達著對情的兩種態度,從而深化了影片主題。“詩人于想象之外又必有情感。分想作用和聯想作用只能解釋某意象的發生如何可能,不能解釋作者在許多可能的意象之中進行的選擇。”[7]“意”能破“象”,當言不能盡意、像不能足意時,就會用“意”破“象”。《分手的決心》很好地結合了東方含蓄傳統的藝術審美,用“情”這種心理結構搭建橋梁,破除觀眾對人物外在的“形象”理解,將情的展示由淺到深層層遞進式地傳達到觀眾的思維神經,表達情的高尚和中國古典美學的特殊韻味。
中國古代文化的主干是儒道釋,中國古典美學思想依托著中國古代文化。儒道釋三種思想共同點都關注個人的發展,歷史上出現了“三教合一”的現象,儒家之“中庸”,道家之“自然”以及釋家之“禪意”,三家融合創造出了中國獨特的古典美學范疇。“意”與“象”在“儒”“道”“釋”三家并立融合的趨勢下,后人進一步融會闡釋創造出了“意境”等審美理念。意境的特點是景中含情、情中藏景、情景交融,具備象能傳意,意能映像的思維;作者在文藝作品中將“意”寓于形象之中,借景抒情表達自身的思想感情。《分手的決心》吸收了中國古典美學的意境,影片注重對意境的刻畫,塑造了三個大方向的意境,“霧”“雨”“雪”,用霧的壓抑刻畫人物的迷茫,秋雨的綿柔刻畫情的纏綿,雪的潔白寒冷刻畫“分手”的悲劇浪漫。“藝術意境的創構,是使客觀景物作我主觀情思的象征。”[8]影視作品的意境非因景而生情的,它是導演的刻意布置,因有情而顯景,因有景地刻畫情才更易表達,更易釋放。
(二)山與海的東方內韻
“藝術家以心靈映射萬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現的是主觀的生命情調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9]山與海的關系也是一種人與人的關系。山與海有著兩種關系,一種是橫向的地理分界關系,一種是縱向的包含突破關系。橫向關系即為視覺能夠探查的山海分界線,縱向關系即為視覺不能完全探查的分界線,山突破海便成了山,海淹沒山便成了海。中國儒家和道家對待山水有各自的哲學,儒家更推崇山的品格,儒家思想沉穩敦厚,像山一樣不輕易受外界影響動搖,道家更推崇水的品格,道家思想自由,像水一樣海納百川,即所謂的上善若水。《分手的決心》展現了韓國對山水的理解,體現了人物內在的“山水”和人物關系的“山水”,其根源離不開深厚的中國哲學。《山海經》其地理學內涵是第一位的,它記錄了山與海的地理特征,影片圍繞山海的奇幻誕生,展示了男女各自突破,相愛相隔的內涵。
影片在劇中人物名字上做了很嚴謹的鋪墊。張海俊是劇中男主角,他名字里帶有海,海是大海,指代的是水;宋瑞萊是劇中女主角,她名字里帶有瑞,瑞是美玉,也是石頭,所指代的是山。從兩人第一次吃壽司開始,魚形的醬料和山水相融的壽司盒就展示出山海的奇妙關系。張海俊象征著水,所以他隨身攜帶的物品與水有關,潤濕眼睛的眼藥水,補水的護手霜和潤唇膏,以及遮蔽太陽光線的墨鏡。他在影片中的形象更像是要突破海的山,鏡頭仰拍塑造高大形象,人物性格沉穩,對宋瑞萊有莫名的向往,他對愛的表示直接、明了。宋瑞萊象征著山,海水會不斷侵蝕海岸,因此她需要遠離水,她的特征是粗糙的手、防水的創可貼,以及護工物品具有防水性。她在影片中更像是被海淹沒的山,她不僅害怕高,而且服裝幽藍,居住環境幽藍。被張海俊的愛所“侵蝕”,愛上了象征水的張海俊,對張海俊的愛婉轉纏綿。
電影結束以瑞萊的死,海俊尋找瑞萊結束,很具有以“意”破“象”性,縱向上海俊突破了海變成了海上山。海水推平了山,瑞萊被大海淹沒,變成了海下山。兩人終于實現了各自的突破,但也意味著兩人在縱向上被海水隔絕。橫向上山與海的界限模糊又分明,海水侵蝕著山,卻始終無法突破山的阻隔,山被海侵蝕著,漸漸融為海的部分。兩人的關系終究有一層看不見的界線,這層界線限制著兩人情得如愿,即便海水波濤洶涌,與萬丈高山相比還是相形見絀。
三、同根同源的美學新發展
中、韓兩國的美學基礎具有同源性。根據《朝鮮簡史》記載,在公元一世紀初儒學就傳入當時的朝鮮,隨著兩國文化交流日益密切,韓國文人對儒學不斷深入探討研究,儒學在韓國逐漸成為主流思想文化。訓民正音出現之前,韓國幾乎是使用漢字進行史料記載和文化交流傳播的。在文化和漢字的共同影響下,營造了相似的文化氛圍,構筑了共同的東亞美感。在儒學觀念的引導下,中、韓兩國都注重“中庸”之美。
中庸是人生修養的道德哲學,也是道德行為的最高標準;中庸之道其理論基礎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人自覺修養達到像天一樣善良美好。在這種修身理性思維的引導下,東亞電影在細節處理上基本具有同種屬性。“克己復禮為仁”要求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言行舉止合乎禮節,從而達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原則。“正因為重視的不是認識表象,而是情感感受,于是,與中國哲學思想相一致,中國美學的著眼點更多不是對象、實體,而是功能、關系、韻律。”[10]因此中、韓極其注重含蓄內斂的表達,使人物內在與外在相互調和,達到其視覺和藝術上的雙重美感。
儒家文化有很強的包容性,為中華文化融入世界、吸收西方審美理念創造了不斷提升的空間。中庸講究中和之美,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即便是悲劇,往往也以“大團圓”結局,如中國戲劇《牡丹亭》《竇娥冤》《西廂記》等,朝鮮唱劇《沈清傳》,韓國古典名著《興夫傳》。隨著西方世界打開東方世界的大門,傳來了一系列新的審美理念,西方美學理論與中國審美精神結合,形成了全新的美學觀。朱光潛在《美是情趣與意象的契合》一書中認為“美不僅在物,亦不僅在心,它在心與物的關系上面”[11],對東亞美學進行了全新的詮釋。
《分手的決心》是東西方美學交互下的一種表征,兼具了商業性與藝術性,是樸贊郁導演的一部力作。電影以儒學山水觀開題,情欲色彩為主線,自我克制為約束,懸疑劇情為線索,將東方內斂品質與西方懸疑色彩相結合,悲劇的結局打破了大眾對大團圓的美好結局期待,留下了更具深意的內涵。儒學審美精神遠不止此,其深層含義還需要更進一步挖掘,中西結合的電影美學潛力巨大,需要導演和學術專家共同探究,演員進一步體會文化深入角色,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更優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