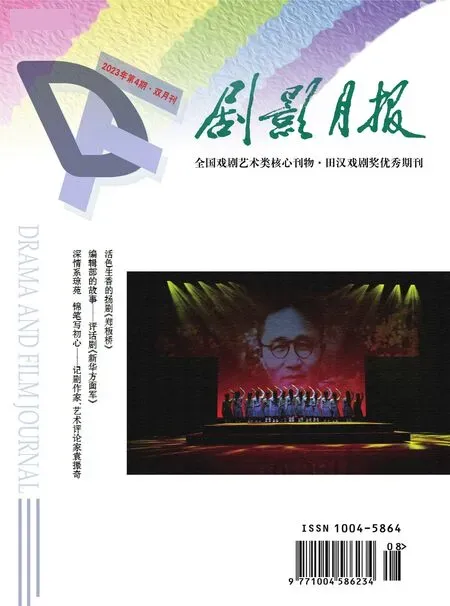跨文化管理與“他者”敘事
——以紀(jì)錄片《美國工廠》為例
■周鈺婷
2019年8月,由史蒂夫·博格納和茱莉婭·賴克特導(dǎo)演的紀(jì)錄片《美國工廠》在美國上映。創(chuàng)作者們以“他者”的視角,用記錄影像的方式提供了一個跨文化管理的典型案例,其展現(xiàn)的新時代勞資矛盾、跨國企業(yè)管理、社區(qū)關(guān)系、工會斗爭、人機沖突等課題,都值得我們深入解讀。在世界局勢風(fēng)云突變和我國推行“一帶一路”倡議的時代背景下,《美國工廠》有著特別的現(xiàn)實意義,其不僅可以幫助中國企業(yè)走出國門、高效管理,也可以為我國的海外形象傳播塑造提供借鑒。
一、來自美國的“他者”敘事
作為一部紀(jì)錄片,《美國工廠》堪稱成功,在第92屆奧斯卡頒獎儀式上,該片獲得了“最佳紀(jì)錄長片獎”,其在中美兩國均獲得了廣泛關(guān)注和相對正面的評價。在片中,中美企業(yè)在管理經(jīng)營、價值文化、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的沖突,則成為影片的最主要看點,借由工會斗爭、勞資糾紛、人機矛盾等線索徐徐展開。
(一)“他者”視角下的影像關(guān)注
《美國工廠》記錄的是中國民企福耀公司赴美建廠的過程,但其制作發(fā)行則是由美國團隊完成的,導(dǎo)演史蒂夫·博格納和茱莉婭·賴克特早在該片之前就已持續(xù)關(guān)注美國產(chǎn)業(yè)衰退的問題,他們的前作,攝制于2009 年的《最后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chǎn)》,也同樣關(guān)注了美國“鐵銹帶”的工業(yè)衰退現(xiàn)象,而如果說該片展現(xiàn)的是汽車產(chǎn)業(yè)的萎縮,那么《美國工廠》則表現(xiàn)了一種轉(zhuǎn)變頹勢的可能性,改變這一切的外來力量正是中國的福耀公司,影片對于外來資本如何作用于曾經(jīng)讓美國人深以為傲的汽車產(chǎn)業(yè)進(jìn)行了審慎的觀察。
《美國工廠》的制片由美國前總統(tǒng)奧巴馬及其夫人創(chuàng)辦的高地制片公司承攬,美國流媒體巨頭奈飛公司負(fù)責(zé)發(fā)行,可以認(rèn)為,該紀(jì)錄片的主創(chuàng)由美國團隊擔(dān)綱,而該片的政治背景和行業(yè)認(rèn)可則證明了它基本可以代表美國的主流視角,也由此可知,工業(yè)的衰退成了大眾關(guān)注的對象,而外來資本如何作用于美國工業(yè)則成了一個敏感話題。實際上,類似的影像作品絕非孤例,此前,史蒂夫·博格納和茱莉婭·賴克特就曾創(chuàng)作過《最后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chǎn)》,聚焦于龐大的通用集團是如何走向蕭條的;而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也在2017年攝制了類似題材的紀(jì)錄片《美國:制造希望》,二者都將鏡頭對準(zhǔn)美國的“汽車城”底特律,揭露了“鐵銹帶”制造業(yè)的殘酷現(xiàn)狀。
對于美方而言,福耀玻璃公司和其所代表的中國企業(yè)資本是一種“他者”,《美國工廠》正是代表美方一種謹(jǐn)慎而冷靜的關(guān)注和認(rèn)知。早在愛德華·沃德爾·薩義德等人的東方主義理論中,東方就以一種西方想象中、落后而待拯救的“他者”形象出現(xiàn)。而在后全球化時代的今天,當(dāng)中國資本成為美國產(chǎn)業(yè)的“闖入者”出現(xiàn)時,如何對其解讀不僅關(guān)系到外在視角的觀察記錄,還意味著對其“自身”的體認(rèn)。誠如約翰·伯格所言:“我們從不單單注視一件東西;我們總是在審度物我之間的關(guān)系”,當(dāng)我們分析《美國工廠》的意義建構(gòu)時,也可在片中解讀美方如何看待他們與世界的關(guān)系,可以說,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rèn)識到了其本土制造業(yè)的萎縮,他們也希望這樣的頹勢可以得到遏制,與此同時,任何可能的改變,特別是來自外來資本的介入,又會引起所有人的警惕。
(二)多重開放的意義建構(gòu)
作為一部題材涉及中美兩國的企業(yè)、文化、政治等命題的紀(jì)錄片,《美國工廠》用巧妙的影像手法來維持作品意義的開放性。雖然主創(chuàng)團隊是美國班底,但該片卻并未在價值觀上有明顯的偏向,而是用克制內(nèi)斂的方式展開影像敘事,從而保證了它相對客觀的風(fēng)格。正如德國學(xué)者羅伯特·堯斯等人在接受美學(xué)理論中所提出來的那樣,該紀(jì)錄片較好地維持了一種意義上的“開放性”,創(chuàng)作者并不直接介入和過多評判表現(xiàn)的對象,而是組織陳述事實之后,將解讀思考的空間更多地留給了觀眾。
在作品整體風(fēng)格上,《美國工廠》依循了直接電影的創(chuàng)作手法,創(chuàng)作者就像“墻壁上的蒼蠅”一般旁觀事件的進(jìn)程。全片沒有解說詞,只用簡單字幕交代必要的背景信息,從而進(jìn)一步地消隱創(chuàng)作者的主觀立場。在攝制技巧上,隱性采訪貫穿全片,創(chuàng)作者并不在提問上進(jìn)行過多引導(dǎo),沒有咄咄逼人、針鋒相對的逼問,沒有制造噱頭、奪人眼球的爭吵,而是給兩國相關(guān)人員平等的發(fā)言權(quán),其外在形態(tài)更類似于中立的新聞紀(jì)實,讓雙方充分各抒己見,從而使觀眾更加接近事實真相,形成自己的觀點。
在涉及大量可能的分歧和異見時,該片采取的客觀紀(jì)實手法不僅保證了影像意義的開放多元,還避免了可能出現(xiàn)的紛爭與偏見。對雙方的管理層和工作人員,采訪者始終隱于鏡頭之后,未對任何人主動進(jìn)行評價,也沒有刻意丑化和美化,這就讓觀眾有足夠的空間去思考中美雙方的優(yōu)劣異同。通過記錄影像的組織,片方將工會之爭、勞資矛盾、技術(shù)更替,乃至中美文化差異、理念分歧等問題都擺在臺前,以期引起人們的充分重視。
(三)個人視角下的時代浪潮
本片聚焦了一個后全球化時代極具代表性的商業(yè)案例,但故事的講述則更多是從個人視角來展開的,導(dǎo)演并未采取傳統(tǒng)紀(jì)錄片常用的“解說+畫面”的方式,而是通過一個個具體而微的人來展開各自的生活,其中包含中美雙方的不同工作人員,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串聯(lián)起全片,使《美國工廠》這部作品更具溫度。由此,觀眾所了解的事件不再只是一個圍繞中美勞資展開的宏大事件,而是深入不同層級的參與者那里,探尋這樣的時代背景給每個人帶來的影響與改變。
與很多紀(jì)錄片的常見做法不同的是,《美國工廠》并未選擇幾個代表人物并持續(xù)跟蹤拍攝,而是不停變換視角,以足夠多的記錄對象塑造出中美雙方工作人員的群像,讓該片有了較強的代表性和說服力,足以反映時代的浪潮。在拍攝對象的選擇上,創(chuàng)作者充分考慮到多樣性和差異性:首先,給中美兩國參與者同等的發(fā)言機會,擺明雙方的不同態(tài)度,各抒己見;其次,采訪記錄了不同層級和位置的工作者,包含企業(yè)的基層、中層、高層人物等;最后,相對立體全面地呈現(xiàn)了不同觀點,對于中方的管理方式,反對與贊成的聲音兼而有之。通過這樣“多聲部”的刻畫,充分證明了中方跨國管理的復(fù)雜與不易,也展現(xiàn)出美方夾雜著期待與懷疑的糾結(jié)心態(tài)。
二、全球化市場的美國工業(yè)衰退
全球化浪潮深刻地改變了世界,隨之而來的是資本在全球范圍內(nèi)的流動和高效配置,分工協(xié)作在更廣的空間范圍內(nèi)得以開展,不同國家和地區(qū)承擔(dān)著生產(chǎn)與消費行為等各自任務(wù)。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我國曾廣泛承接世界范圍內(nèi)的低端產(chǎn)業(yè),從事大量的勞動密集型工作,而美國則長期處于全球產(chǎn)業(yè)鏈的頂端,其低端產(chǎn)業(yè)也逐漸遷往國外。正因為此,《美國工廠》這部紀(jì)錄片才更具有特別的象征意義:它揭露了美國產(chǎn)業(yè)空心化的困境,表現(xiàn)了汽車工人在通用汽車公司等大集團衰敗之后的困境,而在此階段入局的福耀玻璃公司,又無疑承擔(dān)了一個破局者的身份,成為當(dāng)?shù)仄嚠a(chǎn)業(yè)的出路和希望。
(一)批判視角下的美國工會
工會矛盾是《美國工廠》里的敘事重點之一,創(chuàng)作者記錄了中美雙方對工會的不同態(tài)度,引人思考。圍繞工會展開的斗爭與博弈占據(jù)了影片的較長篇幅,其中既包含了勞資矛盾,也有著社會共識、文化差異的因素,紀(jì)錄片廣泛地收取了各方的聲音,呈現(xiàn)了一定的批判視角。記錄影像中,早在2016年福耀工廠的開工儀式上,俄亥俄州的參議員就在發(fā)言中公開肯定了工會的意義,指出該地有著工會斗爭的悠久歷史,為原本喜慶的典禮帶去一絲不和諧。對此,中方的意見很明確,曹德旺直接表示:“工會進(jìn)來,我關(guān)門不做了。”之所以圍繞工會產(chǎn)生了如此多的矛盾,與人們對其的不同認(rèn)識相關(guān)。于很多傳統(tǒng)美國人而言,工會是保護(hù)工人權(quán)益的組織,它可以團結(jié)起松散的個體工人,合力避免資本家的過度剝削。但隨著工會的發(fā)展嬗變,它的初衷也在逐漸變質(zhì),包括中方和部分美國人相信,工會阻斷了管理層與員工的直接交流,并可能降低工作效率。過于強勢的工會可能導(dǎo)致生產(chǎn)活動的中斷,一些不合理的斗爭也會影響正常的生產(chǎn)秩序,紀(jì)錄片中就表現(xiàn)了UAW(全美汽車工人聯(lián)合會)組織下的員工,打著支持成立工會的標(biāo)牌在廠房中宣傳的場面。工會矛盾的敘事以2017年由美國國家勞資關(guān)系委員會(NLRB)在當(dāng)?shù)亟M織的一場投票畫上了句點,這場票選決定了是否要在當(dāng)?shù)氐母RS成立工會。最后,在1500余名工人的投票中,以868票反對、444票贊成的絕對比例宣告了工會力量的失敗。其背后的原因或許和當(dāng)?shù)亻L期產(chǎn)業(yè)蕭條與就業(yè)遇冷密不可分,也和人們對工會弊端的認(rèn)識直接相關(guān)。紀(jì)錄片雖然沒有直接發(fā)聲對工會進(jìn)行評價,但通過較長的篇幅表明了俄亥俄州的汽車工人面臨的糾結(jié)選擇:一方面,選擇工會,或許代表著更好的權(quán)益保障,卻可能降低生產(chǎn)效率,乃至失去工作機會;另一方面,沒有了工會,工作強度可能有所增加,薪資待遇等也不如往常,卻保住了工作。這樣的糾結(jié)在當(dāng)代產(chǎn)業(yè)空心化的美國可謂極具代表性。
(二)中美空間的并置于對照
在表現(xiàn)資本和文化交流的同時,紀(jì)錄片也將中美兩國的空間進(jìn)行了并置與對照,擴展了該片的視野,給觀眾以更多的思考。在20世紀(jì)后半葉逐漸成熟的空間學(xué)說中,西方學(xué)者逐漸理解了空間在物質(zhì)性之外的社會和精神屬性,它不再被視為一成不變的“容器”,而是被理解成社會關(guān)系的集合體,它有著豐富的意涵。誠如法國學(xué)者列斐伏爾所言:“空間里彌漫著社會關(guān)系;它不僅被社會關(guān)系支持,也生產(chǎn)社會關(guān)系和被社會關(guān)系所生產(chǎn)。”作為一部講述跨文化管理的紀(jì)錄片,《美國工廠》中的空間構(gòu)成更富研究價值。
紀(jì)錄片最重要的空間是美國的福耀莫瑞恩工廠,它位于俄亥俄州的代頓小鎮(zhèn),該地是萊特兄弟的故鄉(xiāng),并繼而成為美國的重要航空工業(yè)聚集地。隨后,通用公司在此建立了規(guī)模龐大的廠區(qū),養(yǎng)活了當(dāng)?shù)爻汕先f的產(chǎn)業(yè)工人。航空工業(yè)和雪佛蘭汽車曾經(jīng)是代頓小鎮(zhèn)的象征,但2008年的金融危機終止了這里的繁榮景象,通用公司因此破產(chǎn),大量工人隨之失業(yè),同樣受到?jīng)_擊的還有當(dāng)?shù)卣鼈円驗槭ザ愒炊萑肜Ь场?梢哉f,在紀(jì)錄片中,代頓小鎮(zhèn)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空間,更是當(dāng)代美國本土產(chǎn)業(yè)的一個縮影,它集合了時間、經(jīng)濟、文化等諸多元素。當(dāng)福耀公司來到代頓小鎮(zhèn)建廠時,作為資方,某種程度上它被視為當(dāng)?shù)毓I(yè)現(xiàn)狀的拯救者,當(dāng)?shù)卣粌H給予公司以財政補貼、稅務(wù)減免等福利,更是將廠區(qū)旁的一條道路命名為“福耀大道”,此種榮譽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對地理空間的重命名代表一種改變,成為代頓小鎮(zhèn)汽車工業(yè)變革的風(fēng)向標(biāo)。
除了美國工廠,該片還記錄了位于中國福建省福清市的福耀集團總部,鏡頭跟隨一批受邀來參觀的美國代表,探訪了廠區(qū)內(nèi)的中國式管理,見到了高效的流水線,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在美國人看來并不合理的細(xì)節(jié)。創(chuàng)作者以冷靜旁觀的態(tài)度展現(xiàn)了他們眼中的中國工廠,其中既有對工作效率的肯定,也有對集體主義的一絲不解。除了廠區(qū),鏡頭還拍攝了曹德旺去到的寺廟,對于大部分美國觀眾而言,這個集合了中式文化和宗教的空間是陌生而神秘的,從而也代表著雙方認(rèn)識論和價值觀上的差異,這從側(cè)面證明了跨文化管理的復(fù)雜性。
(三)技術(shù)更替的危機
《美國工廠》的結(jié)尾留下了一個伏筆,即福耀公司將逐漸引進(jìn)智能化的生產(chǎn)流水線,機器會逐步替代廠房里的工人。可想而知,人機矛盾會成為未來代頓小鎮(zhèn)繞不開的難題,至此,紀(jì)錄片又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悖論:一方面,美國一直以高科技的引領(lǐng)者自居,于常理而言,他們應(yīng)該歡迎這種新技術(shù),以推動汽車產(chǎn)業(yè)的快速發(fā)展;但另一方面,當(dāng)?shù)赜钟兄罅康拇龢I(yè)者,智能化流水線的引進(jìn)將會進(jìn)一步縮減用工需求,不利于當(dāng)?shù)氐木蜆I(yè)市場。
科技因素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量,也是跨文化管理中的主要考量。印度裔美國學(xué)者阿爾君·阿帕杜萊明確指出,當(dāng)代全球化的進(jìn)程伴隨著各地域、各維度的互動,在其著作《消散的現(xiàn)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維度》中,他將之劃分為媒體景觀、族群景觀、意識形態(tài)景觀、金融景觀和科技景觀,他認(rèn)為,全球化往往不是一帆風(fēng)順的,總是會伴隨著各種各樣的摩擦,在《美國工廠》中,早已熟悉傳統(tǒng)汽車流水線的美國工人群體,如何應(yīng)對新的生產(chǎn)技術(shù)和更少的用工量,并且管理者又是來自中方,這在行為和心態(tài)上都有著復(fù)雜的適應(yīng)過程,這也是一個極有價值的記錄樣本。
三、管理中的文化維度差異
紀(jì)錄片《美國工廠》極具代表性地闡釋了當(dāng)代跨國、跨文化管理中的困境和出路,其中包含對公司形象、國家形象、文化形態(tài)的認(rèn)知與建構(gòu)。對此,我們可以借鑒荷蘭學(xué)者吉爾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理論.除此之外,荷蘭學(xué)者馮·特姆彭納斯和英國學(xué)者查爾斯·漢普頓-特納共同提出的七大文化維度學(xué)說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
《美國工廠》中所表現(xiàn)出的中美雙方的差異與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的屬性偏向有直接聯(lián)系,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理論中,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代表著人們“人們關(guān)心群體成員和群體目標(biāo)(集體主義)或者自己和個人目標(biāo)的程度(個體主義)”,在他的評分計算中,美國人在個體主義一項得分排在世界最高,這代表著人們注重個體的得失勝過對集體的關(guān)注。而中方在同樣環(huán)境下更重視集體利益,個體的犧牲精神也是中方一直強調(diào)的。這些在紀(jì)錄片中都得以表現(xiàn)。
作為一部由美國人主創(chuàng)的作品,《美國工廠》對中方的集體主義精神著墨頗多,來自“他者”的視角呈現(xiàn)出審慎的態(tài)度,這與片中記錄的美國人身上的個體主義有著明顯區(qū)別。片中出現(xiàn)的一名王姓員工,自從18 歲以來就在福耀工作,他服從了公司外派美國的分配,并無怨言,采訪中他也表達(dá)了對公司深厚的感情,并坦言熱愛自己的工作。類似于他這樣的員工成為中方集體主義的縮影,他們有著服從和自我犧牲的精神,“以廠為家”的理念成為共識。另外,美國代表在探訪位于福建的福耀總部時,也對工廠的半軍事化管理感到驚訝,而當(dāng)美國管理者想把這個模式搬回莫瑞恩工廠時,卻遭遇了失敗:想讓美國工人列隊報數(shù),卻發(fā)現(xiàn)無人響應(yīng)。這些區(qū)別主要來自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不同,也來自兩國文化習(xí)慣、價值觀等的長期浸潤,從中我們可以感受跨文化管理的不易之處。
(二)不確定性規(guī)避
不確定性規(guī)避是霍氏文化維度理論中又一在紀(jì)錄片中有明顯差異的維度,它指的是人們在面臨模糊性、不確定性以及風(fēng)險時的接受程度。在這個指標(biāo)低時,人們更容易接受風(fēng)險,愿意對成功有更多付出,在面臨未知與挑戰(zhàn)時也更容易適應(yīng)。而當(dāng)不確定性規(guī)避較高時,人們則更習(xí)慣于穩(wěn)定規(guī)律的工作生活,因此,也需要管理者給予更多的安全感與確定性。在跨文化管理中,被管理者的不確定性規(guī)避是需要事先調(diào)研的因素,并根據(jù)其高低來制定相應(yīng)的管理策略,這樣才能更好地調(diào)動工作人員的積極性。
《美國工廠》對不確定性規(guī)避這個維度的表現(xiàn)上有著值得關(guān)注的新動向。長期以來,美國人一直被認(rèn)為是低不確定性規(guī)避的,“在不確定性規(guī)避弱的國家(如美國)中,人們更喜歡自由,流動性更大,組織內(nèi)部的大范圍變革往往被人們理解并接受”,但在該片中,經(jīng)歷過金融風(fēng)暴和工業(yè)衰退之后,代頓小鎮(zhèn)的美國工人卻表現(xiàn)出了不同的特質(zhì),工會爭端顯示了他們對于風(fēng)險的厭惡:試圖讓福耀工廠維持通用公司原有的工作模式和薪資待遇,而中方管理方式的不同則給他們帶去了諸多不適應(yīng)。與此同時,中方員工的低不確定性規(guī)避卻展露明顯,在很多工人看來,規(guī)則是靈活的,是可以人為把握的,片中出現(xiàn)了很多令美方驚訝的細(xì)節(jié):叉車工被要求一次運載規(guī)定兩倍的貨物、一些員工在清理玻璃時并未戴上手套,這些細(xì)節(jié)表現(xiàn)了中國工人為了提高工作效率,也在面對一定的風(fēng)險,但同時也顯示了他們較好的主觀能動性。
(三)長期導(dǎo)向和短期導(dǎo)向
在霍夫斯泰德的理論中,長期導(dǎo)向和短期導(dǎo)向代表著某種文化語境中的人們在作出決定時,是更加注重短期收益還是更加注重長期發(fā)展。長期導(dǎo)向往往更需要人們具有勤儉、付出的精神,著眼于未來,為風(fēng)險做好預(yù)案。而短期導(dǎo)向則偏向于當(dāng)下感受,要求在較短時間內(nèi)有可見的收益,其管理中的考核也著重在短期內(nèi)的付出與回報。中國文化中一直有著居安思危的傳統(tǒng),人們重視長遠(yuǎn)的發(fā)展,養(yǎng)成了吃苦耐勞、勤儉持家、自強不息的品質(zhì),在管理和工作中也同樣如此。
紀(jì)錄片中表現(xiàn)的一批美國工人很多是短期導(dǎo)向的,他們對于未來往往并未做太多規(guī)劃。其中的名叫尚尼的藍(lán)領(lǐng)在采訪時就說:“那時(金融危機前)我的孩子想要一雙球鞋我就會去買,現(xiàn)在不能這樣隨性了,我們失去了房子和車。”由此可見她在家庭經(jīng)濟上并沒有長遠(yuǎn)思路,消費主要為滿足一時之需。類似的還有叉車工吉爾,她在通用公司關(guān)閉后失去了自己的住房,只能借住在朋友的地下室內(nèi),而當(dāng)吉爾在福耀上班后,才又可以租住在公寓里。這些都表明工人們普遍缺乏應(yīng)對未來風(fēng)險的防備,是短期導(dǎo)向的。類似這樣的情況并非個案,《美國工廠》通過記錄這群美國藍(lán)領(lǐng)工人,也表現(xiàn)出對他們短期導(dǎo)向的憂慮。
《美國工廠》代表著后全球化時代美國主流視野對中國福耀公司,也是對中國工業(yè)的一種審視,該片用相對紀(jì)實中立的態(tài)度表現(xiàn)了跨文化管理中的種種現(xiàn)象,群像式地刻畫了中美雙方的參與者,避免了直接的評判。在當(dāng)下中國企業(yè)大量在海外發(fā)展的背景下,該片有著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