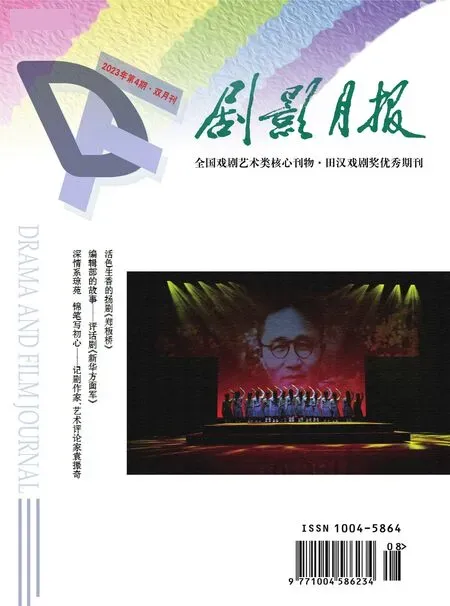淺談戲曲的歌舞演故事
■劉覓瀅
以歌舞演故事,是前人對中國戲曲的明確定義,也是人們對中國戲曲長期形成的共識。在中國戲曲的實踐中,通過歌舞性與戲劇性的結合表現神話故事、社會生活、英雄傳奇,完全符合“以歌舞演故事”的美學本性。《白蛇傳》中的水漫金山,蝦兵蟹將的總動員,忠奸邪惡的大比拼,天上人間的搏斗,讓一個神話擁有震撼心靈的場面,也擁有地動山搖的力量。在這個神話故事,愛情的力量宛若夢幻,一個不太接地氣的神仙故事,因此觸到心靈的柔軟部分。《情探》原本是一個男人榮華富貴后拋棄糟糠之妻、妻子死后復仇的故事。然而,田漢富有想象力的劇本,一旦被演員激情地載歌載舞的表演在舞臺上盡情發揮,那種情感的激蕩讓人內心波濤洶涌。程硯秋曾說過:“演任何劇都要含有要求提高人類生活目標的意義。”恰如《竇娥冤》是關漢卿的偉大作品。作者如果僅僅寫出竇娥在蒙冤喪命之際,感嘆命運之悲慘,也就會缺少足夠的戲劇性的情節張力。關漢卿讓竇娥發出:“大旱三年,血飛白綾,六月飛雪的刑前三愿,真的是感天動地。”的吶喊當最后的三愿在吶喊中狂舞,對黑暗的控訴,便具有抗爭者的行動力——而且是非凡的行動力,足以造成山崩地裂的行動力。悲劇主題,也強化了一個弱女子赴湯蹈火、不可摧毀的意志力。當然,歌舞在故事中的推動作用是多方面的。這種作用往往不是小家子氣的潤滑點綴,而多半是畫龍點睛式的,烘托高潮的輝煌和絢爛。
通過歌舞塑造人物是中國戲曲的主要特色。但是服務于人物的歌舞絕不是大路貨的東西,它必須是獨特的人物的靈魂舞蹈,是由獨特的性格產生的獨特的行動。不妨看看那些優秀戲曲作品中歌舞是如何讓人物神采飛揚,變成彩繪和雕塑的。膾炙人口的京劇《拾玉鐲》幾乎完全由真實、生動的細節編織成情節的花環,這花環上的花朵在歌舞中可謂花枝招展、搖曳多姿。它展現了少女孫玉姣對生活的熱愛,對愛情的渴望,以及初遇異性的欣喜、嬌羞、心靈悸動。她開門、關門、放雞、數雞、穿針納鞋、拾鐲、藏鐲等一連串的細節,生動細膩地描繪了孫玉姣的性格特點及感情特征。江蘇省京劇院的京劇《駱駝祥子》,看文本并沒有特別的引人之處。但最后產生的舞臺效果卻讓人們興奮不已。從京城到鄉下縣城,從專家到百姓人家,可謂贊不絕口。這樣的轟動效應與黃孝慈、陳霖蒼二位表演藝術家精彩的舞臺呈現有著至關重要的關系。這個戲可以說是無中生有地創造了拉黃包車的身段,而且是那么富有形式美和表現力,完全刷新了中國戲曲的舞臺語言。就個人條件,陳霖蒼演祥子已不是最佳年齡、最佳身材,但是他把握住了人物的靈魂、體態行為,在舞臺夸張和生活真實之間,找到了最接近黃包車夫生命狀態的歌舞化舞臺語言,從而使駱駝祥子的形象與電影、話劇迥然不同自成一格,同時以京劇藝術的鮮明特色,活泛了小說的人物風貌。古裝戲里有一些劇本也許并不是最佳作品,但有一些人物卻讓人們印象深刻。這得力于表演藝術家們運用歌舞的語言,賦予人物的心靈以風采和神韻。如周信芳的《徐策跑城》,那種不屈不撓、一往無前的精神在他舞蹈化的動作中,在須髯的飄動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現代戲創作中,包括頗多爭議的"樣板戲",在英雄人物的表現中,對于如何以歌舞塑造人物靈魂,也還是有一些成功的探索。如楊子榮的《打虎上山》和解放軍小分隊的滑雪進軍的場面,舞蹈很壯美。無論是人物的服飾還是身段動作,都給人一種強烈的現實感。它們并非傳統程式,是從現實生活中滑雪運動的姿態動作提煉而來,而從這種表現形式以及審美特點來看,它又與傳統程式有著內在聯系。在現代戲曲創作過程中,舞臺時空得到了全新的開拓。有些作品對舞蹈演故事的戲曲特色進行了富有創意的開拓,如漢劇《彈吉它的姑娘》,寫一個殯葬女工的愛情遭遇,其中有一段戲,是幾個男青年出于不同的心理打電話給姑娘的情節。演出中編創了一段打電話的舞蹈,讓習以為常的生活動作變得輕靈優美,并由此展開了多層次的舞臺空間、與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
當然,在實踐過程中,也有一些歌舞演故事的誤區,比如,在戲劇元素稀薄、矛盾沖突缺乏、看點亮點較少的情況下,某些作品為了吸引觀眾,以歌舞穿插其中。譬如:用歌舞表現抗洪救災,表現沖鋒陷陣,表現歡天喜地。而這些歌舞既非情節發展的需要,也非人物塑造的必需手段,不是喧賓奪主,便是畫蛇添足。這類歌舞往往會打亂整個演出節奏,破壞演出的整體效果。比如,有些老導演善于讓滿臺演出都歌舞化。這一方面說明,導演因為當過演員,拿得出演員的活兒,可以示范講解,讓演員不至手足無措;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導演還是對本子缺少足夠的信心,他需要用夸張的歌舞表演、繁雜的舞臺場面,讓自己內心的不安得到掩飾和消解。他在舞臺上設計的動作,相當一部分就是為歌舞而歌舞、以套路做戲路,整個演出表面上行云流水,實際上只能浮光掠影地走過場。比如,有時為了視覺沖擊力、心靈震撼力,需要把歌舞場面做得壯觀宏大。但是戲曲演出中這類場面是否是越大越好?目前的市場運作水平,已經出現多至六七十人的舞蹈場面。首先,這是需要花錢去經營打造的;其次,就算在資金投入和人員組織方面沒有問題,也容易破壞本身的劇場整體。宏大壯觀的舞臺場面固然是資源共享的優化結果,但土豪金式的擺闊卻是冗雜多余的破壞因素——不可缺少的豪華歌舞確實可以支持,但雞肋式的歌舞,“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或者有些歌舞成為大年三十晚上的兔子,“有它不多,無它不少。”
傳統戲曲的創作觀念,往往強調內容決定形式,形式規制內容,其實形式有時是可以變為內容的。在新戲《徐虎的故事》中,三個報修箱擬人化,以三個年輕女孩來表演,貫穿全劇,她們與主人公徐虎對話、碰撞、積極互動,是載歌載舞的生動與有滋有味的思考有機結合,有意味的形式成為內容的轉化和變異。從劇情設計開始,有表演發揮空間的歌舞表演,適合為表導演提供二度創作的情節和場面。在現代揚劇《皮九辣子》中,有一場墻里墻外戲,皮九和顧二嫂互相試探心意,從顧二嫂干活常用的小凳、竹竿,到皮九遺落的紐扣,環境、心境、道具都為歌舞演故事提供了足夠的條件,歌舞也聯絡起諸多要素,形成精彩的戲劇場面。探索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時代結合,讓歌舞更具有穿透心靈的力量。錫劇《孔繁森》是歌頌英雄人物的一個現代戲,主要事跡當然不可能脫離新聞報道,但能否通過想象力讓人物的靈魂如飛天一般,手持彩練當空舞?而這種想象的舞臺體現,不是說教的、空泛的,應該是飽滿的、樸實的。劇中有一個情節,孔繁森深入群眾走訪藏民,夜宿雪山時發生了嚴重的高原缺氧現象。他身心疲憊,感覺天昏地轉,人幾乎不行了,便寫下遺囑,準備直面死神。就在這個昏昏沉沉的時候,他產生了幻覺:年近百歲的老母親來看他了。老母親是自己推著輪椅來的,母親走下輪椅,聽兒子敘述,給兒子打氣鼓勁。兒子說,媽,我不行了,我就要倒在這高山上了。母親說,起來,兒子,那么多藏民同胞盼著你吶。最后是母親把拐杖遞給孔繁森,讓他扶著坐到輪椅上。于是在風雪高原上,出現了這樣激動人心的一幕:百歲老母推著坐在輪椅上的兒子,前進在茫茫雪原的長路上,一段心曲伴舞,讓人心生感動。
國外的音樂劇與中國戲曲在歌舞演故事的命題上,應該有一些共同的東西。從當年的《貓》《悲慘世界》到如今的《人鬼情未了》,都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現代舞、音樂說唱、街舞等在音樂劇中的廣泛應用,同樣會啟迪多維的創作方式,讓更多的當代歌舞與傳統戲曲融匯滲透,解構和重建。更多地了解當代文學藝術在繪畫、音樂、舞蹈、文學戲劇等諸多方面的最新成果,尤其是跨界的創意,新鮮的手段,乃至天馬行空的思維,能夠讓民族的創作風采更迷人,創作眼界更高遠,創作情懷更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