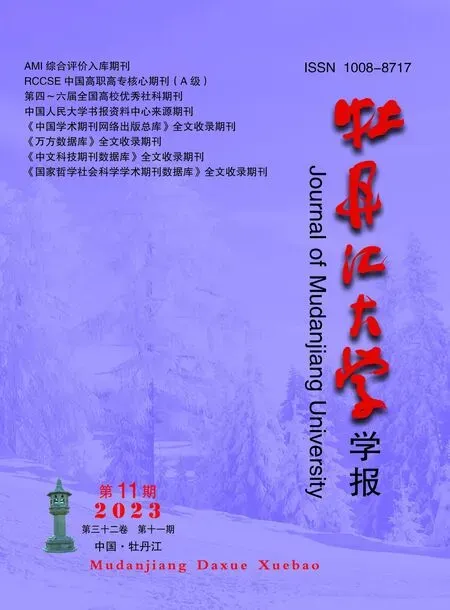時代脈搏的反映者
——程造之現代長篇小說創作論
董卉川 趙藝佳
(青島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程造之,1914年7月出生于江蘇省崇明縣(今上海市崇明區),原名程兆翔,筆名有韶紫等。20世紀三四十年代,程造之創作了被后世譽為“抗戰三部曲”的三部長篇小說《沃野》《地下》《烽火天涯》,涉及各個階層的人物,摹寫廣闊的社會生活,反映人物的悲劇命運,為時代留下了一份生動的見證。程造之的文學創作成就并沒有受到充分的重視,長時期以來他成了文學史上的“失蹤者”,被學界忽略。程造之的現代小說表現出對時代脈搏的精準把握,“文藝作品要反映出時代的脈搏,我想,青年時期的我沒有辜負了時代對我的要求吧”[1]。他以鮮明自覺的現實主義立場記錄社會眾生相,具有史詩的品質。程造之的現代長篇小說在反映時代的同時,又呈現出對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碰撞、交融下生成的畸形社會的批判與哲理深思,既與時代緊密結合,由時代出發,又不囿于時代,具有跨越時代的鮮明特性。
一、抗戰時期鄉土世界的全景繪制
程造之的現代長篇小說具有廣闊的社會視野,構造了一個完整的鄉土世界,繪制了抗戰時代鄉土世界的世相全貌,展現了大變革、大動蕩時代下,現代工業文明與原始農耕文明的碰撞。他以敏銳的眼光、犀利的筆觸,描寫和揭露了鄉村中的種種社會問題。
《地下》《沃野》是劇情相連的兩部長篇小說,全方位地反映了抗戰時期蘇北鄉村——蘇北鹽墾區人民的游擊戰爭、墾荒歷史和社會世相,共同構成了一部完整的“蘇北現代鹽墾史”①。
面對敵人的侵略,大旺村、白狼村等蘇北地區的農民自發組成游擊隊,與敵人作戰,用生命捍衛家園尤其是土地。在農耕文明中,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大旺村的土地被侵略者占領毀壞后,鹽墾區廣闊的、未開墾的“沃野”給了他們延續生命的希望,“那咸的而肥沃的黑土,正表明她是有著無限的精力,可以滋長出無限養育人類胃袋的莊稼,小麥呀,蠶豆呀,葡萄呀,……怎么數得清!當然,她現在還沒有被人動過,好像以前一徑給人家瞧不起,或是忘記了的一樣。那就是處女一般待人開發的原野呵。”[2]378小說中將農民對鹽土的改良利用進行了細致描繪,“天氣好到極點。泥土給犁耙一割開,經不住太陽的蒸曬到傍晚,白皚皚的鹽花就曬出來了。夜里下起雨來,鹽屑沖到開好的引溝里去。明天太陽又把鹽花曬出來了。但鹽花會一天天少下去的”[3]29,由此再現了蘇北鹽墾區的墾殖方式,“開溝排鹽和引淡沖洗,也是改良利用鹽土的基本措施。當陸地脫離海水影響之后,在自然情況下,雖亦能逐漸脫鹽,但歷時較久,不合于積極發揮土地生產潛力、促進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的要求。如經開溝蓄淡,引水洗鹽等的技術作用,就可以大大提早實現改良利用的要求”[4]95。
小說在展現農民與土地血肉相連的同時,也揭示了現代工業文明對原始農耕文明的入侵和影響。“鹽墾區委員會”在本質上依然是“若干地主的聯合租棧”[4]54,卻也形成了現代企業的雛形,“先將什么會的名義改組為公司……什么是都應該科學化一點。像這樣蠻荒的鹽田,一方面用著人力,一方面我們想起俄羅斯的進步了,去買幾部曳引機來……管理方法總之盡可能要科學化……我們應該開設義務小學二所……我們應該四面八方地去經營。不要死著眼在一點上。”[3]64-65客觀上推動了鹽墾區經濟的發展。鹽墾區委員會設立了石灰廠、磚廠、草紙廠,分別被命名為鹽墾區第一、第二、第三工廠。鹽墾區委員會在工廠實行日夜兩班的現代化作息制度,并從鹽墾區墾殖的農民中招聘工人,從而使農民的社會身份發生了變化,在工廠做工的鹽墾區農民,上工時的身份是工人,放工后的身份則是農民。
程造之細致描繪了抗戰爆發后鄉村衰敗、混亂、蕭條的現實境況,以及農民的悲慘命運,揭示了造成上述社會問題的根源所在,既是侵略者的暴行所致,更源于人性的丑惡、人類的互害。
《地下》《沃野》中有幾路游擊隊伍,除了“老獨”“羅三”率領的隊伍一心抗日,“關德”“鋼絲馬甲”“潘大成”“朱古律”等人的隊伍均是以抗日為名,實則行使綁票勒索、殺人越貨的勾當。《沃野》中,“關德”和“鋼絲馬甲”的隊伍不約而同的先后綁架了鹽墾區委員會的委員長“國柱”。為了爭奪鹽墾區的控制權,“抗日隊伍”內部和“抗日隊伍”之間經常發生火并。《烽火天涯》雖描寫了抗戰時期都市上流階層的全貌,但也涉及了南京淪陷后南京農村的某些世相。南京淪陷后,“吳昔更”“魏福基”加入了當地百姓和未能及時撤退的軍隊組織的游擊隊,在南京周邊的鄉村同侵略者展開了游擊戰。由此揭露了同一游擊隊內和不同游擊隊之間的爭權奪利、互相傾軋。各個游擊隊相繼成立后,隊伍內部的成員為了得到隊長職位,彼此勾心斗角、心懷鬼胎。各個游擊隊均妄圖一家獨大,彼此落井下石、相互吞并。在現代文明的入侵下,鄉土世界那純樸的自然文明與傳統的倫理道德已被破壞殆盡,人性被金錢腐蝕,金錢成為主宰一切的源泉。丑陋的國民性依然根深蒂固。
程造之以溫厚的歷史意識,為蘇北鹽墾史作一忠實描繪,通過游擊戰爭、墾荒歷史和社會世相全面呈現了抗戰時期的壯闊畫卷。他以敏銳的嗅覺探尋、揭露鄉村中的種種社會問題,揭示現代文明沖擊下人性的異化,懷抱啟蒙精神對國民性進行批判。
二、抗戰時期社會群像的深度塑造
程造之秉持記錄時代、書寫時代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以深入沉潛的姿態,觀照各個階層、階級,上至達官顯貴,下至販夫走卒,無不網羅其中。在他的筆下,既有理想主義的民族資本家,也有唯利是圖的地主鄉紳;既有麻木愚昧的舊農民,也有逐漸覺醒成長的新農民;既有進步的時代青年,也有無法抵抗誘惑而墮落的新女性;既有上流社會人士,也有小知識分子……程造之塑造了眾多生動的人物形象,繪制出時代人物的精神圖譜。
《地下》《沃野》中的“龐國柱”是民族資本家的代表,人如其名,他是鹽墾區的柱石,雖有資本家追逐利益的天性,也有著強烈的愛國心與責任感,具有較為高尚的人格。侵略者毀滅了大旺村等村落后,他積極聯絡并請求各村的地主鄉紳向難民們發放賑災糧食;他組建了“鹽墾區委員會”,引入現代化的企業制度,建立工廠,發展經濟;他提出“教育普及,男女平權”的口號,積極籌建學校;他面對土匪漢奸的綁架禁錮和攫取鹽墾區股份的無恥要求,寧死不屈。他是一個絕對的理想主義者,認為只要用心做事,就能成功,“環境?敲碎它呀。困難?在國柱的字典里根本沒有這兩個字。國柱先生是一位道地的實行家。說起‘做’,就非得做不可。”[3]49理想終敗給了殘酷的現實,他辛苦籌建的鹽墾區先被“關德”的隊伍占領,后又被“鋼絲馬甲”的隊伍霸占,反抗的“龐國柱”竟被“朱古律”鋸掉了一條腿。“龐國柱”的父親“龐學潛”則是老式封建地主鄉紳的代表。“龐學潛”痛恨侵略者,主要源于他在大旺村的產業被侵略者毀滅。他卻不敢反抗侵略者,也不敢反抗侵蝕自己利益的土匪漢奸,害怕財產將在反抗中毀于一旦。他利用自己鹽墾區委員會委員的身份,貪污公款、中飽私囊、唯利是圖,只求自己家業的壯大。
《沃野》中的“李三斗”是中國老派農民的典型——強悍倔強與善良質樸,迷信愚昧與英勇無畏,粗魯沖動與吃苦耐勞的結合。“李三斗”偏愛長子“壽發”,對小兒子“阿榮”終日惡語相向,源于愛妻生產“阿榮”時不幸離世,便認為“阿榮”是災星,克死了愛妻。當“阿榮”被土匪漢奸抓住后,“李三斗”竟下跪為兒子求情。他有著中國農民吃苦耐勞的傳統精神,“自己耕起田來,從沒哼過一聲吃力,打戰爭中跋涉過來,骨力益發堅硬了。就是做活的時候干不上來,自己相信他還跟兒子們勁道不差到哪兒。”[3]21
“阿榮”“雅蘭”是青年農民的代表,面對資本文明的入侵,他們不再安于現狀,與土地分離。“阿榮”不像父兄“李三斗”“壽發”那樣依戀土地,這也是李家父子矛盾的根源所在。“阿榮”在“雅蘭”的介紹幫助下成了鹽墾區的一名工人,最終脫離了土地。“雅蘭”曾獨自一人到城市的紗廠做工,抗戰爆發后,紗廠被炸毀,她又回到鄉村。城市的經歷使她懂得了“資產革命”與“階級斗爭”,“女性獨立”與“男女平等”,初步具有了新女性的時代精神。“阿榮”最初有著農民階層的某些局限性,懦弱自私、眼光窄狹,囿于小我之中,只希冀賺錢娶妻。在現代文明、時代精神的影響下,他逐漸成長成熟并覺醒,后來主動加入游擊隊,想要在動蕩的大時代中成就一番事業。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曾主動帶領鹽墾區婦女到委員會示威,要求委員們在新成立的工廠中為女性安排崗位,喊出過“教育普及,男女平權”的口號,作為大旺村乃至鹽墾區最早覺醒的青年女性代表的“雅蘭”,最終竟迷失于資本文明之中,為了金錢、為了享樂,甘心做了土匪漢奸“高皇經”的姘頭,自甘墮落,被眾人唾棄。
在《烽火天涯》中,程造之力圖描摹抗戰時期都市青年的人生之路,“真正有靈有肉的青年,在這大時代里許多動態”[5]2。女主人公“慧平”性格倔強、要強、敏感,甚至偏執,源于她自幼喪父喪母、寄人籬下的不幸身世。她的靈魂是孤獨的,渴望被愛,且富有愛國心。她開始時對外貌出眾、出身軍人世家的“王亮公”充滿幻想,到達南京通過接觸后,卻發現自己的未婚夫空有一副漂亮的皮囊,卻沒有一顆上陣殺敵、保家衛國的雄心,因此失望至極。她反而對相貌平平、家境貧寒卻與自己靈魂相近的“吳昔更”傾慕不已。兩個青年人在淞滬會戰爆發后相繼投身前線。南京淪陷后,“吳昔更”還加入了當地百姓和未能及時撤退的軍隊組織的游擊隊。“雯官”“竟新”是“慧平”的表妹、表弟,二人在愛國青年“蔣東平”的鼓舞下相繼投身革命事業。在小說最后,“雯官”在戰地醫院被敵機炸死,將自己年輕的生命獻給了抗戰事業。“趙也誠”是一位三十歲左右的護士,她原本是一個享樂主義者,享受被男人追逐的感覺。抗戰爆發后,在時代洪流的沖擊下,她逐漸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態度,發揮自己的專長做起了戰地護士,為抗戰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烽火天涯》中“長輩們”的角色塑造也極為出彩。作為官方高層的“上官伯周”有著復雜的人物性格。一方面,他想借侄女“慧平”和“王亮公”的婚事,同“王宇”結為姻親,鞏固雙方的關系;另一方面,卻對“王亮公”的荒唐行徑,尤其是大發國難財的貪污行為感到憤怒與鄙視。一方面,他想憑借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王宇”在軍方的勢力,在政壇大展拳腳;另一方面,在得到撤職的訓令后,卻沒有因仕途的斷送而感到憤懣郁結,反而變得輕松灑脫,“賦得歸去來兮,十多年宦途可算得了一個結束,我再也不要去鉆營,謀官,自己本來‘兩袖清風’家中薄有田產……君以喻于義,小人喻以利,我非王宇,可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5]424-425。在“上官伯周”的書房中始終放著一張插著國旗和日本旗的地圖,供他每日觀察與思考戰事走向。被撤職后,他依然關心時局,依然在思考戰爭的發展變化。作為軍方高層的“王宇”,則是抗戰時期投機分子的代表。抗戰到底的主張只是為了奉迎上峰、迎合民眾,是他求得仕途的一種手段與謀略。在“上官伯周”得勢時,“王宇”極盡拉攏收買之能事,當“上官伯周”失勢后,則竭力撇清二者關系。抗戰爆發后,他指使“王亮公”的副官“區振山”謊報牧馬營軍糧遭受轟炸燒毀,實則偷運轉賣。撤退到武漢后,故技重施,指使“區振山”克扣、倒賣軍糧,中飽私囊。通過對“王宇”形象的塑造,批判了抗戰時期政府、軍方上層的丑惡世相。
通過對“上官伯周”與“王宇”家庭生活的描寫,展現了艱苦的抗戰時期,政府、軍方高層紙醉金迷、夜夜笙歌的丑陋世相。“上官伯周”在南京城內的月桂巷和郊區的湯山均有府邸別墅,湯山還有一處面積極大的馬場和草場。撤退到武漢后,他又在法租界租賃了極其奢華的別墅,排場依舊。“王亮公”用倒賣軍糧來的錢在武漢迎紫街為舞女“江夢茵”租了一所半西式的二層洋房,二人過著花天酒地的日子。見微知著,可推斷“王宇”的奢靡人生。青年一代中,“上官伯周”的二女兒“淑賢”,“上官伯周”的年輕姨太“費嫻如”,“費嫻如”的表弟“封修士”,“王亮公”的副官“區振山”,“王亮公”的情人“江夢茵”等,均是都市中享樂主義、利己主義的墮落代表。與都市上流社會奢靡享樂的生活相比,都市中的小知識分子階層更顯卑微與黯淡,民生的凋敝、社會的黑暗,使他們勉力掙扎,卻仍然無法抵抗殘酷社會的壓迫。
在程造之的筆下,各色社會人物上演各自的命運,演繹出一出出時代的傳奇。升騰向上的進步青年,紙醉金迷的達官顯貴,迷途忘返的女性,愚昧麻木的民眾……在這一幅長長的人物畫卷中,可見程造之的才氣與野心,他以塑造人物群像的方式,為時代留下了獨特的見證。
三、抗戰時期社會悲劇的哲理沉思
程造之的現代長篇小說多呈現抗戰時期的社會悲劇,但他并沒有將社會悲劇的生成簡單歸結為戰爭,而是以辯證的理性思維、超越時代的深閎眼光,對戰爭、生命、命運、人生、人性進行深刻的哲理沉思。在創作過程中,他將理性沉思轉化為哲理化的語言,“敘述多過描寫”[2]5,灌注于文本之內。
《地下》多處描寫了大旺村及周邊鄉村女性的悲慘命運。程造之以粗糲、血腥的原生態語言,呈現女性被欺侮、被殘害的慘狀,施害者無疑是侵略者,但程造之借角色之口發出了深邃的哲理沉思,“女人為什么總是這樣易于遭難呢?”[2]284這是一個超越歷史、跨越時代的哲理命題、命運拷問。在戰爭中,男人同樣在遭受劫難、面臨死亡,“男人也不一樣在遭難么”[2]284。但程造之的視角更為深刻獨到,更具人文關懷,更富宏大視野,指向了“女性”。此處的“女性”已經不僅僅是抗戰時期的女性,更是一個包含古往今來、超越國界的名詞。睿智、理性的作者化身文本中粗魯、愚昧的角色,將自我的沉思呈現在讀者面前,“不,男人們有槍。沒有槍,也有力量。可是女人是不能的,連抵抗的方法都沒有的。”[2]284戰爭毀滅了家園,毀滅了大旺村村民的生活,在冬日,人們饑寒交迫、流離失所、與親人陰陽永隔。在呈現人間慘劇的同時,程造之再次化身文本中的角色,反思戰爭的緣由,揭露人類可怖的欲望和野心,“不好的事情都是野心的人弄出來的。本來沒有你爭我奪的事,因為只是想弄得自己舒服,自己快活享受,叫苦難讓別人去吃,天下壞了,越過越糟了”[2]290。在《沃野》中,鹽墾區建設失敗的社會悲劇與侵略者無關,恰是源于人類的欲望野心——土匪漢奸的屢次侵占,鹽墾區內部的一盤散沙、各懷鬼胎。《沃野》的語言相較《地下》更富詩意哲理、更加幽婉折繞,“但一經戰爭,從上到下便開始毀滅了,已往血汗的灌溉統歸于無用。那就像洪水的泛濫一樣,經過此番洗滌,人們回到原始去了”[3]7,宗教寓言與時代現實相結合,更好地承載和表現了作者深刻的理性沉思,揭示了戰爭的恐怖、現實的悲慘。
程造之的現代長篇小說雖以抗戰為時代背景,卻不囿于描寫戰爭,因此,程造之筆下女性的悲劇命運實際與戰爭無關。《烽火天涯》的女主人公“慧平”有著倔強、要強的性格和現代女性的獨立精神,她屢次違背伯父的意志,放棄了代表權勢、金錢、美貌的“王亮公”,與出身卑微的“吳昔更”相戀,并離開伯父的庇佑。但現實的困境——金錢,使“慧平”不得不再次回到伯父家中,屈從了與“王亮公”結婚的父母之命。倔強的“慧平”依然拒絕與“王亮公”同房,“王亮公”因情生妒,槍擊“吳昔更”,反被對方所傷,令“王宇”大怒,趕走了“慧平”,伯父也與“慧平”斷絕了關系。現實的困境——金錢再次使“慧平”陷入了困境,她即將臨盆,卻身無分文,幸得“趙也誠”的相助得以平安產子。此時的“慧平”終被現實擊敗,放棄了倔強和理想,給同在醫院中接受治療的“王亮公”寫了一封發自肺腑的書信,“她為著你的神經錯亂,暗暗的抱憾而心痛欲絕呢!從你的氣憤出走,并日和吳的決斗,使我深深的痛悔,深深的感覺你并非全無良心……我的心碎完了,但預備為著你而復活起來!我覺得生活感受威脅,枯燥,乏味!我今日才知道吳并不十全十美,而且他毫無信義……亮公,你能寬容我嗎,你能饒恕這個曾和你朋友同居已經作了母親的罪人嗎?”[5]472-473希望并懇求得到他的原諒。這封書信是一個象征,象征了以“慧平”為代表的都市女性的社會悲劇——在金錢的壓迫下,對現實的妥協、對自我理想的放棄。作者是借男女感情問題——未婚先孕,來探索社會問題。
程造之對于世界的理解不脫離悲觀的本色,因此筆下浮現出一幕一幕慘狀、一出一出悲劇。他以深邃的思索面對紛繁的世界,對戰爭、生命、命運、人生、人性進行深刻的哲理探尋,彰顯出思想的深度和廣度。在程造之那里,悲劇成為人的存在本質,這種悲觀主義色彩既是時代的使然,也是個人哲學的外化顯現。
結語
長久以來,程造之的小說一直被學界忽視。他的長篇創作,個人特色鮮明,深刻、全面、細致刻畫了抗戰時期的眾生相,透視社會問題的千姿百態,書寫民族戰爭中大眾的艱難覺醒。程造之飽蘸深厚蘊藉的情感,繪制時代的萬千世相,塑造多彩的人物群像,以強烈的人文關懷呵護人性之真、批判人性之惡,對時代、人生等重大命題抒發深沉的哲思。程造之的現代長篇小說立意深刻、題材廣泛、風格多樣、技藝奇巧,為現代文學貢獻出別樣的審美經驗,實屬有待開掘的一座文學富礦。對程造之現代長篇小說創作的綜合闡釋,鉤沉程造之的現代長篇小說,不僅能還原他的文學創作風貌,重審他的文學史地位,對于現代文學來說,程造之的重新“發現”,亦是一種有益的補充。
注釋:
①“鹽墾”一詞最早出現于清朝末年,大約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通海墾牧公司成立。蘇北鹽墾區是我國著名的棉區之一,也是江蘇省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其開發有著上千年的歷史。蘇北鹽墾區主要位于江蘇省東北部,東濱黃海、西界范公堤、南起呂四、北至陳家巷。包有濱海、射陽、大豐、如東、阜寧、鹽城、東臺、海安、南通、海門、啟東等地。在近代,蘇北鹽墾區歷經了兩次飛躍式的發展。一是在清末時期,張騫等人在通、泰兩地設立了大豫、大豐、大賁、華成等大量的墾牧、墾植、墾鹽公司,盛極一時。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帝國主義列強無暇東顧,民族工業進一步崛起,對棉花需求日益增長,促使蘇北鹽墾區迅速成為我國重要產棉區之一。而在新文學的創作中,較少有反映蘇北鹽墾區的小說作品,長篇小說更是罕見,程造之的《地下》《沃野》填補了這一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