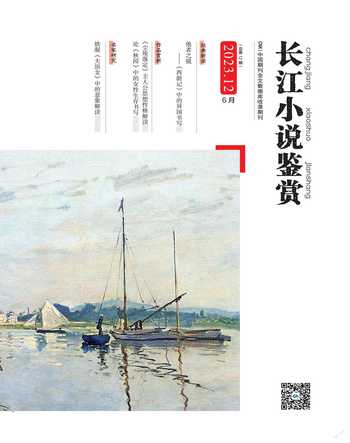《島》中的疾病隱喻書寫
李文娟 齊雪艷
[摘? 要] 作為維多利亞·希斯洛普的處女作,《島》一經出版就登上了英國各大圖書暢銷榜的榜首。在科學技術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時代,麻風病被強加上許多超出自身的含義,本文擬通過分析《島》中承受著心理與身體雙重傷害的麻風病患者戰勝麻風病、重返健康的過程,揭示麻風病被人們隱喻化、污名化的現實,鼓勵疾病患者要正視自身的生理疾病,以積極的心態看待疾病與外界社會。
[關鍵詞] 麻風病? 疾病隱喻? 去隱喻化
[中圖分類號] I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12-0055-04
《島》是一個明顯反映疾病隱喻化的文本,維多利亞·希斯洛普圍繞以麻風島聞名的斯皮納龍格和與其隔海相望的普通村莊布拉卡兩個地點展開敘述,暗示麻風病被強加上許多超越生理層面的意義。這種隱喻無論是對患者本身還是對社會外界都產生了極大影響。作者揭示將麻風病等同于“罪惡”“不潔凈”“上帝的懲罰”“死亡”“羞恥”等現象,批評人們將安置麻風病人的斯皮納龍格島稱為“活死人之地”的行為。住在島上的麻風病人也曾因為疾病的隱喻化與污名化而喪失了基本的人權,被隔絕在主流群體之外,成為毫無價值的人,承受著身體和心理的雙重傷害。
一、麻風病的隱喻化與污名化
關于麻風病及其隱喻的記載最早可以追溯到圣經,在圣經當中,被發現患有麻風的人,首先會被牧師判定為不潔凈的,然后被脫去衣服、剃掉頭發,驅逐出族群或部落。除了不潔凈,圣經還將麻風病人判定為丑怪、邪惡、骯臟的,因此歐洲社會對麻風病人普遍采取歧視、排斥,甚至是驅逐的態度[1]。不僅如此,“在《舊約》里,表面的潔凈與否對應著內心的純潔程度。”[2]“圣經中常把得了麻風病的人稱為‘基督的窮人,麻風病人潰爛的外表成了他們腐化了的靈魂的反映。”[3]雖然將麻風病人傷口的潰爛程度作為判定患病者靈魂腐化程度的標準很荒謬,但圣經對歐洲人的影響是巨大的,滲透到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文學文化、政治、藝術、哲學等領域都有它的影子。所以,圣經中麻風病人“不潔凈”“有罪”“邪惡”的隱喻意義先入為主地激起了主流群體對麻風病及麻風病患者的厭棄。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麻風病患者是做了罪惡的事情才會被上帝懲罰。
由于早期科學技術的不發達,人們難以解釋未知事物的原理,便將麻風病當作是上帝的懲罰。到了近現代這種情況也并未好轉,人們雖然已經不再迷信,但此時的科學技術仍處于萌芽和發展階段,因此,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克里特島,麻風病仍然是醫學尚未解決的難題,人們應對麻風病的唯一方法就是將患者隔離。人們的心理因素對病情的痊愈也會產生影響:當時的人們對麻風病的知識普及和認知還不夠,并沒有真正地了解麻風病,只知道麻風病具有傳染性、傷口十分恐怖且現代醫學無能為力。所以麻風病人終將走向死亡。出于對生命安全的擔憂,人們將麻風病患者看作“生活在身邊的瘟神”,主觀臆斷其可怕程度,厭惡、排斥他們,用盡一切辦法遠離麻風病患者。在小說《島》中,當瑪麗婭在醫院檢查確定自己患上麻風病時,克里提斯醫生提醒瑪麗婭:“除了那些跟你最親密的人之外,你盡可能不要告訴別人。人們對麻風病還有偏見,他們會以為只要與病人同處一室就會傳染上。”[4]由此可見人們對于麻風病的了解之淺薄、誤解之深刻。“瘟神”“死亡”“傳染源”等新的隱喻不僅加重了麻風病人的痛苦與不幸,使他們認為自己是被上帝拋棄的人,還從心理和精神上讓他們覺得患有麻風病是一種羞恥,是一種懲罰。
二、疾病導致的空間分隔
伊蓮妮是布拉卡最受尊重的人之一,她是一位好老師、好母親、好妻子。但感染麻風病使一切都改變了,她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學生、兩個年幼的女兒和辛勤勞苦的丈夫。不只是伊蓮妮,所有的麻風病患者都要遠離人群,到專門的區域進行隔離。這種空間分隔的方式最早見于圣經,在圣經的《利未記》中有過記載:“規定麻風病患者必須被置于群體之外,因為他們的不潔可能會危害神圣,將他人引向罪或者玷污神圣之地。”[5]在麻風病人是“不潔凈的”“有罪的”的看法基礎上,圣經認為,污穢的麻風病人有可能會玷污神圣之地、危害神靈,還會將“潔凈”的人引誘上邪惡之路,所以為了保護其他人和神靈,必須要將“污穢”的麻風病患者趕出主流群體外。馬海德先生在研究麻風病的書中寫道,“現代考古學者在其廢墟中挖掘出很多瓦片,上有‘楔形文字,其中有令麻風病人遷出城外的法律條文。”[6]由此可見,這種將麻風病患者趕離主流社會之外的做法很早就有了,屬于最初的隔離方式。
近現代以后,醫學發展逐漸專業化,人們建造了專門性的麻風病醫院或病房以確保麻風病人的可控性,防止其他人被傳染。斯皮納龍格島就是類似的隔離區,它專門用來安置必須遠離主流群體生活的麻風病患者,將麻風病人固定在一個對于主流社會相對安全的區域內。斯皮納龍格遠離陸地,被海域隔絕,住所全部由石頭墻圍起來,只留一扇不起眼的小門,由此與主流群體之間產生了生存空間的割裂。這種隔離方式使得無數患者家庭支離破碎、忍受分別之苦。空間的分割使得被孤立在正常生活空間之外的麻風病人在心理上受到極大的傷害。斯皮納龍格的島上空間與布拉卡的陸地空間隔海相望,他們的距離近到島上的麻風病患者可以看到對面人們的日常生活。“斯皮納龍格被賦予了禁忌和絕望的含義;而克里特島在斯皮納龍格的反襯之下,則代表了健康和生機。”[7]雖然斯皮納龍格島和布拉卡同處于一片天空之下,但卻形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兩種情景、兩個空間的鮮明對比使麻風患者產生被群體排斥、拋棄的感覺,成為健康王國以外的他者。這種低落情緒所引發的消極心理是麻風病人配合治療疾病、重獲健康的巨大絆腳石。所以,麻風病患者因為外界的排斥而產生的心理傷害遠比疾病給他們帶來的身體折磨更為嚴重,這使他們喪失了求生的欲望,不相信自己可以重回健康王國,更不相信自己能重新被主流群體所接納。
迪米特里患麻風之后離開了父母,獨自去往斯皮納龍格。雖然對于小孩子來說父母是無可替代的存在,但比起憐憫,人們更加在意的是他麻風患者的身份。雖然登島之前他的母親曾傷心欲絕、放聲大哭,他的父親也懷著悲痛又沉重的心情,可麻風病人待在被孤立的疾病空間之后,久而久之就會慢慢被自己的親人淡忘,最后在情感和現實生活中實現完全的隔絕與孤立。所以當迪米特里住進斯皮納龍格以后,處于兩個對立空間的血親再也沒有互相聯系過。而伊蓮妮因為丈夫負責向島上輸送物資,所以一直與島外的空間有著密切聯系,她每周都可以見到丈夫、與女兒通信、了解家里的情況,因此伊蓮妮的空間與精神世界并沒有實現真正的隔離。
其實麻風病人并非不可以與人接觸來往,麻風病的傳染有一個長期而直接的過程,如果不長期接觸患者的衣物或皮膚,注意日常防護,戴好口罩,病菌就不會傳染到健康人的身上,簡單的見面并不會造成疾病的傳播,但人們還是像驚弓之鳥一樣提防麻風病患者,堅決將其孤立在遠離大陸與人群的地方。
三、疾病導致的權力漠視
麻風病患者在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問題上面臨許多的困難。一旦被確診,麻風病人就成為被遺棄了的“非人”,他們在患病的同時被剝奪了一切權力,其基本的生命保障權都受到了漠視,每一次試圖重獲權利的反抗都會被當作是少數群體的造反運動,最終換來更加徹底的權力剝奪和殘酷懲罰。外界收走了斯皮納龍格人作為公民的一切權利,或者說,在他們成為麻風病人之后,他們已經不是社會主流群體眼中的公民了。在佩特羅斯·肯圖馬里斯擔任島主之前,島上的麻風病患者都面臨十分窘迫的生存難題。首先是用水問題,島上唯一的水源是山腳下的蓄水池,住在島上的人每天都需要自己提著水桶去山下取水,并且這種水源的供應受氣候和環境的影響是很不穩定的,時不時便面臨缺水的問題。其次是用電,島上的發電機只運行了三周就壞掉了,上級直接忽視島民們的維修請求,導致島上居民的用電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然后還有生存空間問題,在空間有限且固定的斯皮納龍格,政府不斷遣送麻風病人入島,房屋基本上被住滿。除此以外島上的醫療條件也十分有限,島上之前是沒有醫院和醫生的,但作為患者往往最需要的就是醫生,麻風病人需要醫生的治療和護士的照料,并且需要藥品清洗傷口。教育問題也十分棘手,斯皮納龍格島有十幾個孩子都到了啟蒙的年紀,卻整天無所事事,他們需要接受正規的教育,但島上的女教師克里斯蒂娜并不能滿足實際需求,她散漫松懈、獨斷專行,孩子們并不能從她那里學到真正的知識。
不論是農夫、貧民還是律師、教師、編輯、工程師、醫生,但凡與麻風病有關的人,都會被剝奪作為正常公民的權利,變成主流群體嫌棄和排斥的對象。雅典市的麻風病患者幾經輾轉后被捆綁著雙手第一次出現在斯皮納龍格,他們衣衫襤褸、面容枯槁,一度給人一種活不下來的錯覺。可見,即使是最講究文明的雅典人,在患上麻風病之后也沒有任何權利可言,他們像動物一樣被主流群體奪去自由與人權,驅逐出境。在被轉移到斯皮納龍格島之前,他們一直被關在像監獄一樣的雅典麻風病醫院里,吃的是附近監獄剩下的殘羹,穿的是從大醫院里死人身上扒下的舊衣服。在社會主流群體眼中,麻風病患者是比已死之人還要無足輕重的生命體。雅典麻風病患者試圖采取知識分子式的文明抵抗方式,他們起草信件輾轉送給政府里的朋友和官員并發動絕食抗議時,卻被當局視為威脅和暴亂分子,并對其強權壓制。政府不但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處境和條件,反而下定決心要將這些有著“反動因子”的麻風病患者驅逐出去。于是這些來自各行各業、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被主流群體“二次拋棄”:從自由體面的主流社會輾轉到似監獄的麻風病醫院,又從麻風病醫院被送到異域的荒島。
從權力角度來講,統治階級把患者當作一種威脅,認為他們會危害到現有社會統治秩序的穩定,引發社會騷亂,為社會治理帶來不安定的隱患,因此他們采取了他們認為最可靠的方式,通過強權壓制,將麻風病人與外界普通人的一切聯系都阻斷,剝奪他們享有的權利,將其置于徹底孤立無援的境地,隔絕在麻風病的世界,讓病人不得不接受患病就要死亡的思想,加速其走向死亡的進程,這在本質上是對麻風病患者的權力壓制。
四、疾病導致的錯誤價值判斷
當戰爭和麻風病隨著時間慢慢退出主流視野,斯皮納龍格逐漸成為獵奇的代名詞,人們對于這座島和曾經生活在這里的麻風病人僅僅懷有一種“殘忍的好奇”,而對曾經在島上的麻風病人的生存境遇毫不關心。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曾經說過:“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于健康王國,另一重則屬于疾病王國。盡管我們都只樂于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么一段時間,我們每個人都被迫承認我們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8]暫時身處健康王國的人們與深陷疾病王國的人們存在著巨大的情感隔膜,他們不愿意甚至想不到要去了解一個麻風病人的痛苦與遭遇。布拉卡的人民和斯皮納龍格島上的麻風病患者形成了一種無聲地看與被看的關系,它代表著整個主流社會與麻風病人群體的關系。每個身處健康王國的人身邊都可以見到處于疾病王國統治下的公民,但健康王國的人更多的是像看客一樣漠視著疾病王國里受苦的人。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曾提到,政府會把神智有障礙的人逮捕起來,將其統一趕到一艘任其漂流的船上,而船上那些沒有生存能力的失智者也只能聽天由命。“疾病盡管是一種生理現象,但在生理的痛苦、心理的重壓中卻分明有著人類社會與文化的折光,負載著一定的道德批評和價值判斷。”[9]《島》中的麻風病人在被強行帶到斯皮納龍格之后也面臨著聽天由命的困境。主流群體做出的價值判斷是:麻風病人是無價值且危險的,麻風病隱喻著死亡,麻風病患者對于物質和基本生活條件改善的渴望是沒有意義的,他們終究要走向死亡,不斷補給物資給將死之人是一種浪費。這種價值判斷使得麻風病患者有時也陷入一種自我懷疑中——肯圖馬里斯也曾思考過:自己努力改變這座島的生存環境,為大家謀取更多利益的意義在哪?因為“社會外界對疾病的情感態度是基于對特定疾病的道德認識和評判而體現出來。”[10]
五、去隱喻化后的理想王國
如果說前期的斯皮納龍格是朝不保夕的“麻風病人的棄島”,那么后期它就是麻風病患者的理想王國。歷屆島主不斷為麻風病人爭取更光明的未來。肯圖馬里斯在任期間不僅為患者爭取到水源供應,還獲得了政府的資助,在斯皮納龍格建立了醫院和房屋,每個麻風病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賺錢,島上的居民每月還能獲得補助。而接任的尼可斯·帕帕蒂米特里奧同樣認真負責,他在任期間不僅幫島民解決了用電的問題,還帶領雅典各行各業的麻風病患者投入島上的建設,麻風島上開始有了酒館、咖啡廳、電影院、條件正規的醫院和學校,一切都與外界無異,人們有了新的生活,忙碌充實了麻風病患者的身心,他們不再一直怨天尤人,也不再沉浸于被拋棄和病痛的折磨中。
醫生作為重要一環對于患者的作用十分重要,尤其當醫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麻風病人與其他病人時,會在極大程度上減輕麻風病人的羞恥感,使他們愿意配合治療。在拉帕基斯成為島上的固定醫師之后,整個島上的麻風病患者士氣大漲,他們對于自己所患的疾病更加了解。拉帕基斯醫生督促他們注意作息、保持傷口清潔,教他們有益于健康的鍛煉方式,真切地關心他們。但在拉帕基斯醫生來到島上以前,所有麻風病人的情緒都是很消極的,每個人都在盡可能地保持沉默,拉帕基斯醫生在照顧他們身體的同時,也細心地關照著麻風病人的情緒。還有克里提斯醫生,他積極參與各種治療麻風病的活動和試驗,日復一日地為麻風病人奔走,鼓勵他們,給他們帶去治愈的希望,最后成功治愈了斯皮納龍格島上所有的麻風病人。
可見,良好的生活環境和心理狀態對于麻風病人極其重要,甚至可以延長他們的生命,緩解他們遭受的痛苦,如果社會能夠屏除偏見,還原疾病原本的面目,給予麻風病患者應有的尊重,正常對待他們,那么病人就會更加積極主動地去面對疾病、接受治療。所以,我們要加強人們對于麻風病的了解,進一步科普關于麻風病的一切知識,讓人們明白它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疾病,從而將人們從恐懼中拉回現實,還原疾病本來的面目,使人們在現實世界而不是在自己無限的臆想世界里認識麻風病。
六、結語
疾病是什么?亨利·歐內斯特·西格里斯特在《疾病的文化史》一書中講道:“疾病是一個與生命歷史同樣古老的話題,作為一個生物過程伴隨人類始終。”[11]所以,生命必然伴隨著疾病而存在,無論是動物、植物、微生物還是人,只要還具有生命特征,就無法擺脫疾病的侵襲。不可否認的是,所有的病不論多么難以治愈,都屬于疾病的一種,而人人都有患上某種疾病的可能。因此,疾病是人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們應該正視疾病,而不是將其妖魔化,消除人類自己制造出來的隱喻陰霾,摒棄偏見,給予患者應有的權利和尊重,正視并幫助他們。
參考文獻
[1] 谷操.驅逐與救助:中世紀西歐的麻風病[D].南京:南京大學,2016.
[2] 陳倩.被顛覆的隱喻:麻風主題的當代闡釋——以希斯洛普的《島》為核心[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1).
[3] Brody S N.The disease of the soul:leprosy in medieval literature[J]. Speculum,1977(3).
[4] 希斯洛普.島[M].陳新宇,譯.海口:南海出版社,2020.
[5]? ?Bryon G L.Pestilence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M].New York:Routledge,2004.
[6]? ?馬海德.麻風防治手冊[M].南京:江蘇科技出版社,1989.
[7]? ?張春燕.“島”之意象的內涵分析:對維多利亞·希斯洛普小說《島》的解讀[J].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21).
[8]? ?桑塔格.疾病的隱喻[M].陳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9]? ?韓冷.京派小說的疾病隱喻[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9(4).
[10]? 孫雯波,胡凱.疾病的隱喻與疾病道德化[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0(6).
[11]? 歐內斯特.疾病的文化史[M].秦傳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特約編輯 孫麗娜)
作者簡介:李文娟,伊犁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指導教師:齊雪艷,伊犁師范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比較文化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