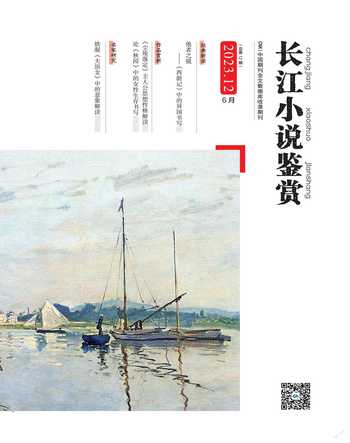從“凝視理論”看果戈理的《肖像》
[摘? 要] 果戈理的《肖像》通過敘述高利貸者用金錢誘人墮落、毀滅的故事,塑造了一個魔鬼般的高利貸者形象,高利貸者死后,其靈魂附身在肖像中,用一雙鬼魅的眼睛引誘人墜入罪惡的深淵,從而實現靈魂的復活與永生。從西方凝視理論的權力機制和論述話語來看,果戈理的《肖像》中的高利貸者用罪惡之眼凝視魔鬼世界與現實世界,“眼睛”既是高利貸者游走在這兩個世界的媒介,也是實現這兩個世界中欲望、力量、金錢讓渡的工具。小說通過“看”與“被看”以及“凝視”與“被凝視”的動作,表明視覺權力機制之間的復雜關系,揭示了《肖像》中凝視、金錢、欲望所具有的毀滅性力量。
[關鍵詞] 凝視? 果戈理 《肖像》? 眼睛
[中圖分類號] I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12-0059-04
“凝視”是20世紀后半葉以來西方文論和文化批評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凝視指攜帶著權力運作和欲望糾結以及身份意識的觀看方法,觀者多是“看”的主體,也是權力的主體和欲望的主體,被觀者多是“被看”的對象,也是權力的對象,可欲和所欲的對象[1]。
在西方文論和文化研究中,凝視已經成為重要的關鍵詞,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批評范式和研究方法。拉康對“眼睛”與發出“凝視”的對象進行界定、分離,初步發展了“凝視”理論[1]。他認為眼睛是主體性的,凝視是客體性的,但是在“看”的復雜過程中,凝視因附著來自主客體發出的權利、欲望等復雜因素而讓人難以理清凝視所承載的主客體關系。在視覺理論的觀照下,“看”這一常規的動作呈現出多層次的意蘊。首先,在“看”這個動作發出時,主客體身份得以確認,但是在持續性的“看”的過程中,主客體身份可逆,因為該過程隱含著情感的轉換。其次,“看”這一視覺過程隱含著主客體之間復雜的情感,主體在“看”的目光中投射著開心、害怕、誘惑等情感[1]。最后,在“看”的過程中,“被看”的對象面對“看”的動作主體的情感做出相應的情感回應,并實現主客體的逆轉。拉康認為,最能顯現欲望的器官之一就是眼睛[1],眼睛在完成凝視這一動作時實際上已經完成了權力、欲望的選擇。眼睛會讓最滿足主體欲望的客體進入注視視野,在此過程中,凝視的目光里表達了在現存秩序中難以實現的愿望,主體借此進入想象與幻想的世界[5]。
在《肖像》中,“眼睛”是高利貸者實現靈魂復活的幸福通道,也是他凝視內部、外部世界,通過視覺權利誘捕、控制獵物,實現永生的工具。
一、肖像中“凝視”機制的產生、運作
果戈理非同尋常的童年經歷、亞健康的身體狀況、信仰東正教的家庭氛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在寫作方面的思想觀念、藝術技巧。在人類的早期文明中,人們認為自己身體的各個部分都與其主體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即使自己身體的某個部分與主體相分離,其功能并沒有減弱、消失,仍保持與主體的聯系,他們認為自己身體的各個部分都具有不可侵犯的神性[2]。果戈理深受母親的影響,神經敏感脆弱的特質使他更能接受宗教神話,他認為基督教是罪惡的宗教,他還接受了波蘭天主教有關魔鬼和魔法的部分。在烏克蘭民間傳說的影響下,果戈理認為魔鬼會引誘人犯罪墮落[3]。在這些眾多因素的影響下,果戈理的作品中出現了大量的“魔鬼”。果戈理筆下的魔鬼總是帶有某種神秘的、超自然的強大力量,《肖像》中的高利貸者就是魔鬼的化身,他用魔鬼般的罪惡之眼凝視著周圍的一切,用“凝視”控制、摧毀一切沉迷于金錢欲望中的人。
《肖像》共兩部,為了方便闡述因果,故事采用倒敘的方式從第二部高利貸者的產生展開。一些藝術收藏家正在競買一幅畫藝精湛的肖像畫,這幅畫最吸引人的是肖像的眼睛,傳神到仿佛人們看一眼就會被吸走靈魂、墜入無盡的深淵。高利貸者作為惡魔的化身,其肉身死去,靈魂卻不滅,他的靈魂隱藏在肖像之中,用來自地獄般的眼睛凝視著世間形形色色的人物,織就誘人的罪惡之網捕獲獵物以求永生。在《肖像》中,關于“眼睛”的描寫出現了二十多次,表現了果戈理對金錢至上的風氣的思考和批判。
《肖像》產生于死寂、貧窮的柯洛姆納,這里沒有生氣,也沒有將來,“你一踏上柯洛姆納的街道,你就會覺得所有年輕的欲望和沖動都離開了你。”[4]他們的欲望都因生活的瑣碎與精神的無聊而沉寂,唯有足夠多的金錢能給這死水般的生活激起水花。《肖像》中的高利貸者就產生在這樣的需求中,他是這些高利貸者里最不平凡的一個。他的不平凡表現在:(一)這個高利貸者有著異常可怕的面容。“高高的、幾乎是不尋常的身材,黧黑的、瘦削的、曬焦的臉,臉上一種異常可怕的神色,目光如火的大眼睛,垂掛的濃密的眉毛,使他顯得跟京城里所有灰色的居民們迥然不同。”[4]可怕的不僅是他的外貌,更為可怕的是他擁有一個非同尋常的內心世界。(二)他擁有無窮盡的金錢,他慷慨借錢給所有需要的人,并利用一套奇怪的利息計算方式,源源不斷地獲得錢財。與此同時,在高利貸者這里獲得金錢的人也都得到不幸的命運結局,例如,高尚美好、真誠聰穎的青年才俊從高利貸者這里接受財富之后變得殘酷暴虐,并在瘋癲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縱觀所有向高利貸者借錢后悲慘死去的人,他們的悲劇結局背后都隱藏著高利貸者的一套運轉機制:高利貸者用“眼睛”審判、誘惑、控制他所選中的目標,讓他們被凝視所攜帶的權力、力量擊潰,在金錢所帶來的狂喜中沉醉不已,逐步喪失天賦才能、道德人品,走向自我的沉淪與毀滅。
高利貸者先是通過“眼睛”觀察周圍的一切事物,通過凝視對所有反向凝視他的人物進行判斷,選定他的誘捕對象;然后,他用能滿足他人需求的金錢進行試探,此刻的金錢變成了凝視機制運轉的齒輪,高利貸者借助金錢這個工具對富有才能、品行良好但急需錢財的人進行誘惑。
金錢集合了享樂、權力、名聲、財富等各種欲望,高利貸者的可怕之處在于他是欲望的使者,人們從他的眼神中能夠看見自己墮入欲望深淵的不幸命運。可即便看見自己的可怕命運,他們在短暫的掙扎過后依舊如飛蛾撲火般投入金錢的欲望深淵。高利貸者在這些屈從于凝視下的被看者眼中滿足了自己得以永生的欲望,凝視操控下的命運齒輪緩緩運轉起來了。
二、“凝視”的在場與不在場
人們終于注意到這個眼中充滿欲望的魔鬼般的人物,但他終究不是魔鬼,金錢的無限性與生命的有限性催生了高利貸者隨意操控金錢的欲望。如引言所說,凝視的“動作發出——過程完成”這一過程本身就纏繞著權力、欲望、力量,這一過程的特殊性在于凝視的可逆。《肖像》中高利貸者的凝視雜糅著這些復雜關系,具體可將主客體對欲望的想象區分為不在場凝視與互為凝視主體的在場凝視。但通過對《肖像》的分析,在場凝視與不在場凝視之間并沒有嚴格的界限,在某些場景中,不在場可在短時間內轉化為在場,這取決于人物的心理狀態、眼神動作的變化。
肖像從產生起就展現出強大的震懾力量,它深刻揭示了“凝視”操控下被看者的無力抵抗,被統攝者的悲慘結局也由此注定。“這雙眼睛包含著這么多的力量……只要畫筆一接觸到這雙眼睛,他的心里就涌出來一種古怪的憎惡,一種不可理解的重壓之感……終于他再也受不住了……第二天,第三天,這種情緒更加強烈起來。他害怕極了。”[4]畫家并未向高利貸者借錢,卻在高利貸者極具威懾力的注視下,敗下陣來,他在沒有給高利貸者畫完肖像之前就潰敗了。畫家在高利貸者的魔鬼“凝視”下深陷墮落的深淵,天賦才能被腐蝕,人也變得瘋狂。《肖像》中,魔鬼的力量是抽象式的超自然力量,并通過“凝視”的權力機制呈現出來,借助金錢這個實質性工具控制被凝視者,實現高利貸者永生的愿望。
畫家和高利貸者之間產生了不在場的凝視,高利貸者對永生的極度渴望與畫家對功成名就的欲望相互映照。在畫家未替他繪制肖像時,高利貸者必定在腦海中憧憬過擁有不死不滅的靈魂與隨之而來的無盡金錢;而畫家渴望的是能獲得無盡的靈感,保持高超的繪畫技藝,成為眾人和他自己眼中的完美畫家。“他撲到他的腳邊去,懇求一定給畫完這幅肖像,說是這關系他的命運和他的一生;他已經用畫筆抓住了他的生動的容貌;只要忠實地畫出來,他的生命,由于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就會保存在這幅肖像里;因此他就不會完全死掉;他一定得繼續活在世上。”[4]高利貸者把欲望的目光投向了能畫出人物靈魂的畫家,此時的畫家對高利貸者而言處于凝視的欲望表層,畫家為高利貸者作畫是因為沉迷于高利貸者的強烈欲望所散發出的熾熱之光。畫家從高利貸者的凝視中找到了心目中完美的魔鬼形象,并通過高超的繪畫技藝畫出高利貸者的靈魂所在。畫家在為高利貸者作畫之時,高利貸者、畫家、肖像三者之間形成一個欲望、情感、權力雜糅的中心并通過畫家的繪畫實現了三種要素的流動。
恰爾特科夫是一個貧窮的畫家,他住在一個簡陋的出租屋中,居住環境惡劣,面臨著因無力繳納房租即將流落街頭的命運。“他吃力地、氣喘吁吁地爬上潑著污水、留著貓犬爪痕的樓梯。”“……然后一歪身坐在一只狹小的沙發上,這只沙發已經不能說是蒙著皮,皮也早已離開銅釘……蠟燭沒有了……他說,要是再不付房錢,就讓咱們搬家;他們明天還要來呢。”[4]現在恰爾特科夫最缺的就是金錢,雖然他的教授告誡他要警惕金錢對天賦才華的腐蝕,但面臨被迫搬走的困境讓他無暇顧及教授的告誡,金錢是恰爾特科夫欲望、想象和生存的來源。戴錦華在《電影理論與批評》中曾論述道:“凝視本身就帶有想象與幻想,這些都是欲望的投射,觀看主體希望沿著缺席(欲望對象的匱乏)到達在場(欲望的滿足),但是我們所能達到的只是欲望本身——那個掏空了的現實的填充物。”[5]肖像被放置在畫店時,高利貸者的凝視空間相較于被買回家中無疑是被壓縮了的,他用鬼魅的眼睛挑選著滿足他欲望的人,直到恰爾特科夫從他那里獲得金錢,他的凝視都可以視為不在場的凝視。恰爾特科夫拿到金圓時的內心獨白展現了他對金錢的渴望:“過去他睜著艷羨的眼睛望著,咽著唾沫遠遠地欣賞著的一切東西,現在他都有力量買到了……穿上時髦的燕尾服,長期素食之后開一次葷,租上一幢漂亮住宅,立刻上戲院去,上點心鋪去,上……”[4]所有這些幻想都能在金錢的操控下得到滿足,恰爾特科夫內心的欲望在未得到實現前一直處于缺席狀態。得到金錢的恰爾特科夫立馬將自己裝扮了一番,搬進了豪華的住宅,金錢讓他在報紙媒體的宣傳下變得聲名顯赫……他從前的所有幻想都得到了實現。
三、“凝視”的雙向流動
在視覺文化研究的語境中,“凝視的概念描述的是一種和眼睛、視覺相關的權力運作方式。……它的目的是探索和掌控。……當我們凝視某物時,我們的目的就是控制他們”[6]。《肖像》中,高利貸者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觀看、審判、控制著其他被看者,但它并非一直處于主體的地位,被看者在與觀看者發出的目光對視時實際上也實現了二者主客體身份的逆轉,被看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抗著觀看者的權力控制。恰爾特科夫從用被單蒙住肖像不敢看到他不覺得害怕這個過程,“看”的力量對比使他生出微弱的反抗之心,但這反抗在絕對的控制力量面前必然潰敗,他的屈服是在意料之中的[7]。《肖像》的特殊之處在于:高利貸者的“凝視”是抽象的,它主要是通過“金圓”這個具體的事物來實現對恰爾特科夫、P公爵的絕對控制,即抽象與具象同時發揮作用。
恰爾特科夫是個頗具天賦的畫家,但是貧窮阻礙了他才能的完全發揮。金錢是恰爾特科夫展示才能、名聲大噪的成功階梯,也是他維持生活的必要條件。高利貸者擁有無盡的金錢,他需要恰爾特科夫交付靈魂來獲得其想要的一切,恰爾特科夫對高利貸者“凝視”的心理流變暗含了他對“凝視”權力運作機制的對抗結果。
恰爾特科夫買下肖像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一是恰爾特科夫對魔鬼身上散發出的神秘力量的好奇。“……面貌似乎是在痙攣的瞬間畫的,并且不像是北方的神氣。炎熱的南方在臉上刻著痕跡”[4]。二是畫家對高超畫技的珍視。“肖像雖然處處損傷,蒙著塵埃,可是從臉上把灰塵抹掉,他就看出這是偉大的藝術家的手筆。肖像還沒有畫完;但筆力是令人驚奇的”[4]。三是畫家為高利貸者的“凝視”所震懾。“這雙眼睛更加炯炯發光地望著。……他感到一種不愉快的、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心情……”[4]他僅剩的幾個戈比也在畫店肖像的蠱惑下,莫名其妙地花了出去。“這樣,恰爾特科夫完全出乎意料地買了這幅古老的肖像,同時想道:我干嗎要買它?它對我有什么用?……他在路上想起了這交給店主的二十戈比是他最后的幾文錢。……見鬼!真叫人膩煩死了!”“真倒楣,見他媽的鬼!”[4]這兩次提到的鬼表明恰爾特科夫對莫名將剩余的錢花在買肖像上的憤怒,暗示了恰爾特科夫見到了真正的鬼(魔鬼),也為他以后的悲慘命運埋下伏筆。恰爾特科夫拿到錢之后,他的欲望通過金錢得到滿足,凝視由缺席狀態變為在場,與此相應的,他的靈魂將慢慢被魔鬼所腐蝕,成為魔鬼的替身。高利貸者的欲望也在此時得到滿足,獲得了永生,高利貸者的凝視看似消失了,但凝視已經完成主體的轉移,高利貸者通過畫家的眼睛注視著周圍的一切。高利貸者的凝視視域在這一過程中呈現擴大(從拍賣館到畫店,凝視的對象從富豪權貴到貧窮的下層人民)——縮小(從形形色色的人物中選中恰爾特科夫)——擴大(用恰爾特科夫的眼睛凝視其他的人物)的變化。凝視視域的變化展現凝視的力量、權力、欲望的同幅度變化,凝視的強大之處在于他的流動變化性。此后,在恰爾特科夫拿到金圓到他瘋癲死去的過程中,畫家對凝視的反應一共出現了三次。第一次是他拿到肖像中掉落的金圓后,態度由之前的懼怕變為坦然面對。第二次是他意識到他的才能在金錢的腐蝕下已經枯竭,流于庸俗,他對肖像感到厭惡、排斥,對那雙罪惡之眼感到恐懼、戰栗。第三次是他變得瘋癲、病入膏肓時經常夢見那雙可怕的眼睛,在他看來,所有人的眼睛都是高利貸者的眼睛。在這三次變化中,一開始表現了恰爾特科夫對凝視所帶來的權力、欲望和力量的臣服,并試圖通過金錢實現對權力、欲望、力量的擴張。凝視主體完成了轉移后,恰爾特科夫的眼睛也成為高利貸者的眼睛。在后兩次變化中,恰爾特科夫因為喪失繪畫靈感和自己低俗平庸的繪畫技能而痛苦沉思,在凝視肖像的過程中,實現了靈魂的復蘇,但悔之晚矣,他已經深陷欲望的泥沼無法自拔,最后只能在癲狂中死去。
四、結語
凝視作為權力、力量、欲望等要素的載體,把恰爾特科夫等從高利貸者那里獲得金錢的人作為征服和控制的對象。“看”與“被看”以及“凝視”與“被凝視”都不只是簡單的動作,背后都隱含著主客體關于深層的權力、力量、金錢的對抗和碰撞[7]。高利貸者在《肖像》中既是用視覺權力凝視他人的觀看者,同時也是被其他人觀看的被看者[7],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在凝視的視域下,高利貸者在死前用邪惡的靈魂、巨額的財富引誘人們走向墮落、毀滅;他在死前利用畫家將他的靈魂附著在肖像中,使自己的靈魂不滅,繼續用魔鬼的眼睛誘惑獵物。他用直擊人心的眼睛看出人們靈魂深處的欲望,無盡放大欲望,以金錢為餌,讓其一步步迷失其中,直到毀滅人們的靈魂,從而獲得永生。“眼睛”是高利貸者觀察世界、觀察他人的工具,金錢是他誘捕人心的手段,小說告誡人們要警惕金錢對藝術才能的腐蝕。
參考文獻
[1] 朱曉蘭.“凝視”理論研究[D].南京:南京大學,2011.
[2] 杜國英.彼得堡的“鼻子”和“眼睛”的現代神話傳說——果戈理的《鼻子》和《肖像》的另類解讀[J].名作欣賞,2011(33).
[3] 金亞娜.并非不可解讀的神秘——果戈理靈魂的復合性與磨礪歷程[J].俄羅斯文藝,2009(3).
[4] 果戈理.外國中短篇小說藏本[M].滿濤,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5] 戴錦華.電影理論與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6] Cavallaro D.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Thematic Variations[M].London:the Athlone Press,2001.
[7]? ?楊非.凝視與被凝視——凝視理論視角下《野草在歌唱》的視覺關系解讀[J].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11,33(6).
(特約編輯 孫麗娜)
作者簡介:宋翠蕓,溫州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