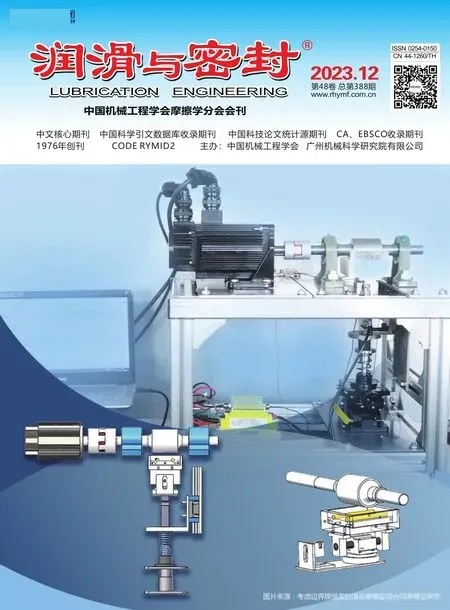考慮邊界膜強度的滑動摩擦副混合潤滑模型研究*
張盛為 嚴志軍 姜淵源 申子玉 郭 晨 徐久軍
(1.大連海事大學輪機工程學院 遼寧大連 116026;2.大連海事大學交通運輸工程學院 遼寧大連 116026)
內燃機、機床等機械系統的摩擦副在重載或啟停工況時,往往處于混合潤滑狀態[1]。混合潤滑狀態下界面間的載荷由油膜與微凸體共同承受,使其兼具流體動壓潤滑及邊界潤滑的特點[2]。對于流體動壓潤滑目前的研究已較為完善,但迄今邊界潤滑仍是研究不夠充分的一種潤滑狀態[3],邊界膜的存在使得滑動表面間的摩擦因數相對于干摩擦大大降低,摩擦副能夠保持較好的潤滑狀態[4]。然而,當邊界膜由于機械或溫度作用發生破裂時,微凸體接觸區發生固體與固體直接接觸,摩擦因數會發生階躍性突增,并伴隨著局部膠合和黏著磨損的產生。因此,考慮邊界膜作用的混合潤滑研究對于提高摩擦副使用壽命以及使摩擦副保持良好的潤滑狀態具有重要意義。
邊界膜破裂的原因十分復雜,對此前人進行過大量探索。早在1939年BLOK[5]提出了閃溫理論,認為邊界膜的破裂是由于表面溫度達到臨界值導致。1972年,CZICHOS和KIRSCHKE[6]對潤滑的集中接觸失效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在一定溫度下,不同的滑動速度對應的邊界膜臨界破壞載荷是不同的。隨后CZICHOS[7]在1974年又提出了失效面的概念。1994年,KELLY和BARNES[8]提出了考慮機械效應的熱模型,該模型認為邊界膜的破裂是由摩擦過程中磨粒等因素引起的非穩態熱導致。2000年,WANG等[9]從畸變能的角度對邊界膜強度進行研究,認為潤滑薄膜與基底的結合不僅會被高溫產生的熱能破壞,還會被剪切產生的變形能等其他能量破壞。2007年,WANG等[10]從邊界膜吸附熱的角度分析提出,邊界膜的覆蓋率與摩擦產生的熱量密切相關。2011年,AJAYI等[11]提出了絕熱剪切非穩態模型,依據邊界膜的軟化速率和硬化速率對邊界膜是否發生失效進行了判斷。2013年,LI等[12]通過將熱彈模型和熱穩模型耦合,對邊界膜破裂進行了模擬分析。2015年,WOJCIECHOWSKI和MATHIA[13]提出了膠合恒定先導模型,該模型同時考慮了流變性、表面形貌和接觸表層的物理化學性質對邊界膜的影響。2019年,許迪初[14]從邊界膜的生成率與去除率角度分析,提出了一種考慮邊界膜動態效應的邊界潤滑模型。

本文作者以摩擦副界面間滑動速度、膜厚、微凸體接觸壓力為主要參數構建邊界膜失效模型,并依據潤滑試驗結果對模型進行擬合,獲得模型參數;將該模型與流體動壓潤滑模型、粗糙峰接觸模型耦合,建立了一種考慮邊界膜強度的混合潤滑模型;通過實際摩擦副潤滑性能實驗驗證模型適用性。
1 邊界膜強度測試方法
1.1 試驗裝置
使用自制雙點接觸摩擦試驗機對邊界膜強度進行測試,試驗臺結構如圖1所示。試樣的安裝如圖2所示。

圖1 雙點接觸摩擦試驗機結構示意

圖2 試樣安裝示意
摩擦試驗機中上試樣為階梯軸,下試樣為兩黃銅圓柱試樣,上試樣圓柱面與下試樣圓柱面垂直相切構成兩點接觸;下試樣安裝于浮動支撐油盒內,油盒下連接浮動支撐結構,保證2個下試樣和上試樣均勻接觸;摩擦力通過安置在浮動支撐結構一端的摩擦力傳感器測量;施加于下試件支撐結構上的載荷可通過加載手輪調整,并由壓力傳感器實時測量。
1.2 試件準備
上下試樣參數以及試驗中潤滑劑相關參數見表1。上試樣為45鋼材質的階梯軸,階梯軸的首、末端與軸承構成過渡配合,加工精度為IT5,且其中一側的外端通過彈性聯軸器與電機相連。階梯軸中部圓柱面為試驗的工作面,直徑為50 mm,表面經過光整加工,并經過SiC砂紙(2 000目)和氧化鋁拋光液手工拋光。2個下試樣直徑為8 mm,選用H59黃銅材質,其表面經過光整加工。上下試樣的表面粗糙度采用TR210手持粗糙度儀測量,表面綜合粗糙度0.59 μm。試驗中潤滑劑選用CF10W-40潤滑油,試驗在恒定溫度下進行。

表1 試樣及潤滑劑相關參數
1.3 測試過程
在試驗進行前需將下試樣放在無水乙醇中用超聲波清洗;將下試樣安裝固定在油盒中,并向油盒中加入適量潤滑油保證下試件被潤滑油浸沒;潤滑油通過加熱電阻加熱,并將溫度控制在55 ℃;將試驗機調整至設定的轉速和載荷并開始試驗,待穩定后,測量各試驗工況下30 s內的平均摩擦力與平均加載力。完成一次測試后,需拆卸并重新調整下試樣接觸面后再進行下次試驗,每個試驗工況需重復 3 次測量以減小隨機性;每次試驗完成后清洗油盒并對試件和潤滑油進行更換。
2 邊界膜強度模型
2.1 邊界潤滑失效特征和規律
為了獲得邊界潤滑失效特征,以及載荷和速度對邊界潤滑失效的影響規律,采用上述試驗方法和規范,分別在滑動速度為0.1、0.3、0.5、0.75、1.0 m/s下,測量不同載荷對摩擦因數的影響,結果如圖3(a)所示;分別在載荷為20、40、60、100 N下,測量不同滑動速度對摩擦因數的影響,結果如圖3(b)所示。

圖3 摩擦因數隨載荷(a)與滑動速度(b)的變化
由圖3(a)可見,對應特定滑動速度,隨著載荷增加,摩擦因數存在突增現象,這反映了潤滑狀態的變化。當邊界膜破裂時,摩擦副間由于干摩擦導致摩擦因數急劇上升,因此摩擦因數的突增是邊界膜破裂導致的。從圖中還可以看出,隨著滑動速度增加,摩擦因數突增對應的特征載荷臨界值降低,當滑動速度為0.1 m/s時,加載直至170 N摩擦因數發生突增,而當轉速升高至1 m/s時,加載僅到80 N時摩擦因數就已發生突增,這表明滑動速度對邊界膜失效有明顯的影響。圖3(b)反映不同載荷下滑動速度對摩擦因數的影響規律,當載荷較小時(20、40、60 N),滑動速度的增加不會使邊界膜發生破裂造成摩擦因數的突增,而載荷為100 N時,當滑動速度增加至0.5 m/s時摩擦因數出現突然升高。這表明載荷較小時,由于油膜厚度較大,即使滑動速度較大,邊界膜也不容易破裂;而當載荷增大,由于油膜厚度較小,邊界膜更容易受剪切力作用而產生破裂。
2.2 邊界膜強度模型建立
綜合上述試驗結果,邊界膜的失效是法向載荷和剪切力綜合作用的結果,摩擦因數突增對應的工況反映了邊界膜破裂臨界失效點,邊界膜抵抗失效的能力可以用邊界膜強度表示。由于剪切力受滑動速度及油膜厚度影響,因此邊界膜強度可用含壓力、滑動速度及油膜厚度的函數表示。文獻[16]中提出的邊界膜強度模型對于微凸體間(簡稱pa-v模型)表達式為
pa=a×vb
(1)
式中:pa為微凸體接觸壓力,Pa;v為界面間滑動速度,m/s;a和b為常數系數。
2.1節研究結果表明,油膜厚度對邊界膜失效有顯著的影響,隨著膜厚降低,界面之間的剪切率和剪切力增加,邊界膜更容易破裂。但公式(1)中邊界膜強度僅和滑動速度相關,忽略膜厚的影響,故該模型不能反映界面之間的剪切率,難以和實際情況相符。據此文中針對表面點接觸條件下的邊界膜失效影響因素,提出改進后的邊界膜強度公式(簡稱pa-γ模型)為
pa=c×γd+e
(2)
式中:γ為界面間剪切率,1/s,γ=v/h,h為油膜厚度,m;c、d和e為常數系數。
為了獲得模型中的參數,針對文中2.1節摩擦試驗中試樣失效點對應工況,依據Hamrock-Dowson點接觸中心膜厚公式[3]與GREENWOOD和TRIPP[17]提出的粗糙表面接觸公式,得到不同工況下邊界膜失效時微凸體接觸壓力pa、界面間滑動速度v、膜厚h及界面間剪切率γ之間的關系,如表2所示。

表2 邊界膜失效時不同參數之間的關系
依據表2數據,利用Matlab對試驗數據進行擬合,選擇Power函數,分別得出pa-v型與pa-γ型邊界膜臨界載荷模型(強度模型):
pa-v:pa=2.592×107×v-0.683 9
(3)
pa-γ:pa=-1.057×108×γ0.151 9+9.418×108(pa>0)
(4)
依據2種模型對應的公式(3)和公式(4)得到邊界膜強度曲線如圖4所示。當摩擦副所處工況為曲線上方時,邊界膜發生破裂,因此上述模型可反映邊界膜的強度。對于pa-v強度模型,模型和表1數據之間相似系數為0.911 5;對于pa-γ強度模型,相似系數為0.997 8,表明所得pa-γ模型與試驗測試結果之間一致性更好。

圖4 邊界膜強度模型曲線
3 混合潤滑模型的建立
為了將邊界膜強度模型應用于實際摩擦副混合潤滑分析,將該邊界膜強度模型與流體動壓潤滑模型、粗糙表面接觸模型耦合,建立考慮邊界膜強度的混合潤滑模型。采用Reynolds方程作為流體潤滑基本模型,以高斯分布表征表面粗糙度,用邊界膜強度模型作為邊界潤滑和干摩擦轉化判據。
基于所建立混合潤滑模型,以徑向滑動軸承為對象進行模擬和驗證。徑向滑動軸承結構和參數如圖5所示。圖中,R1為軸頸半徑;R2為軸承半徑;c=R2-R1為半徑間隙;e為偏心距;Ψ為偏位角;W為外載荷;U為軸頸表面切向線速度;θ為軸承頂點為起點的周向坐標。具體的參數見表3。

表3 徑向滑動軸承模擬參數
3.1 基本模型
為了分析方便,將潤滑界面沿周向展開,x表示軸承周向坐標,y軸建表示軸承軸向坐標,z表示軸承徑向坐標,當采用柱坐標表示時,設x=Rθ,則徑向滑動軸承的Reynolds方程[18]為
(5)
式中:R為軸承半徑,m;h為油膜厚度,m;ph為油膜壓力,Pa;η為潤滑油黏度,Pa·s;U為軸頸表面切向線速度,m/s。
3.2 粗糙峰接觸模型
混合潤滑中接觸區域內的承載力由油膜壓力ph與微凸體接觸壓力pa共同承擔。文中采用GREENWOOD和TRIPP[17]建立的不確定模型表征微凸體接觸壓力,假設微凸體各向同性且高度服從高斯分布,選擇膜厚比λ=4(λ=h/σ)為微凸體是否發生接觸的臨界值,則界面微凸體接觸壓力公式為
(6)
(7)
式中:n、β分別為微凸體密度和曲率半徑;E為綜合彈性模量,Pa。
研究中設定微凸體接觸的臨界值為λ=4,即當膜厚比λ>4時微凸體不發生接觸;當λ≤4但邊界膜并未破裂時,此時邊界膜的摩擦因數μa通常在0.05~0.2之間[3];當邊界膜破裂時摩擦因數會急劇增加,摩擦因數設為0.5。因此,結合2.2節邊界膜強度模型,微凸體間的摩擦因數可表示為以下分段函數形式:
pa-v模型:
(8)
pa-γ模型:
(9)
對于作用載荷W,由動壓油膜和微凸體共同承擔,因此載荷為
W=Wh+Wa
(10)
式中:Wh表示油膜承載力;Wa表示微凸體承載力。
油膜承載力Wh在x、y方向上的分量分別為Whx、Why,則
(11)
(12)
微凸體承載力Wa在x、y方向上的分量分別為Wax、Way,則
(13)
(14)
對于摩擦力F,同樣也由兩部分組成:
F=Ff+Fc
(15)
式中:Ff表示動壓油膜內剪切應力產生的摩擦力;Fc表示粗糙峰接觸產生的摩擦力。
Ff及Fc依據公式(16)和公式(17)計算。
Ff=?τf(x,y)dxdy
(16)
Fc=?fc×pa(x,y)dxdy
(17)
油膜剪切力由Eyring模型求解,即:
τf=τ0arcsinh(ηγ/τ0)
(18)
式中:τ0表示Eyring應力,Pa;γ表示剪切率,1/s。
由公式(10)和(15)結果可得摩擦因數為
f=F/W
(19)
3.3 模擬過程和模型初步檢驗
對混合潤滑模型采用有限差分法求解。將求解區域劃分為等間距網格,運用超松弛迭代法求解油膜各節點壓力:
ph(x,y)(k)=ph(x,y)(k-1)+ω[ph(x,y)(k)-ph(x,y)(k-1)]
(20)
式中:ω為松弛因子,1<ω<2;k表示第k次迭代。
為保證迭代可獲得較好精度,并判斷計算是否可以停止迭代,制定以下油膜壓力收斂條件:
(21)
根據基本參數間的關系,采用Fortran語言編寫,具體計算流程如圖6所示。
為避免計算參數中的數量級過大或過小,定義量綱一化參數為:y0=y/b;p0=pc2/(6UηR);h0=h/c。其中R為軸承半徑,m;b為軸承寬度,m。
為了證明模型準確性,將建立的模型的計算結果與文獻[18]結果進行對比檢驗,兩者油膜壓力與油膜厚度結果的比較如圖7所示。

圖7 徑向滑動軸承油膜壓力、油膜厚度計算結果對比
通過與文獻計算結果對比,無論是壓力與油膜的分布形狀還是中間截面計算數值,結果都基本一致,初步說明了文中所建模型的準確性。
4 模型的實驗驗證
4.1 實驗設備和參數
采用自制針對實際軸瓦零件的摩擦實驗機,對混合潤滑條件下的摩擦學特性進行測試,以評價不同邊界膜強度模型的準確性。軸瓦摩擦實驗機上的摩擦副安裝和加載方式如圖8所示。

圖8 軸瓦安裝和加載方式示意
軸瓦摩擦實驗機中,與軸瓦配對的試驗軸由兩滾動軸承支撐,伺服電機將旋轉運動傳遞給試驗軸;軸瓦固定于軸瓦夾具中,采用液壓壓頭向下給該軸瓦夾具施加載荷;加載力由壓力傳感器采集,摩擦力通過電機功率消耗轉換獲得。
實驗中的潤滑油選用CF10W-40,初始載荷10 000 N,轉速100 r/min。實驗開始后首先在低載荷下磨合10 min,隨后逐級增加載荷(加載梯度為10 000 N),直至摩擦因數發生突增;記錄實驗過程中隨載荷變化的摩擦因數,實驗重復3次,取摩擦因數的平均值作為實驗結果。實驗相關參數如表4所示。

表4 實驗相關參數
4.2 實驗結果與模型評價
圖9所示為針對軸-軸瓦摩擦因數與載荷關系的實驗結果,圖中同時顯示基于pa-v與pa-γ邊界膜強度模型的2種混合潤滑模擬結果。

圖9 摩擦因數與載荷關系的實驗結果與模擬結果對比
由圖9可見,對于實驗結果,在加載力小于120 000 N,摩擦因數隨載荷增加緩慢變大,其數值均小于0.02;當加載力加至120 000 N,摩擦因數突然增加,數值約為0.05。結果表明,在混合潤滑條件下,當實驗載荷小于120 000 N時,多數微凸體接觸區的邊界膜未發生破裂,界面之間為流體摩擦和邊界膜摩擦為主,故摩擦副之間的摩擦因數較小;當加載力加至120 000 N,大量微凸體接觸區的邊界膜破裂,摩擦副微凸體接觸區域出現干摩擦,導致摩擦因數劇增。
此外通過對比可見,隨著加載力增加,實驗和模擬得到的摩擦因數均呈現相似的變化趨勢。pa-v邊界膜強度模型模擬結果對應的摩擦因數出現劇增的臨界載荷約為90 500 N,pa-γ邊界膜強度模型對應臨界載荷約為125 000 N,說明pa-γ邊界膜強度模型相較于pa-v邊界膜強度模型可更準確地反映邊界膜的破裂情況。上述分析也證實,文中所提出的混合潤滑模型可更準確地反映摩擦副在混合潤滑條件下的摩擦特性和潤滑狀態。因此,在對邊界膜強度進行分析時,剪切速率也應作為關鍵因素考慮在內。
5 潤滑狀態轉化特性和機制
在驗證考慮邊界膜強度的混合潤滑模型的準確性基礎上,進一步運用模型分析上述軸瓦零件在潤滑狀態轉變過程中的承載特性,模型參數設置見表4,與實驗工況相同。圖10所示為通過模擬得到的實驗工況下,界面間平均油膜厚度隨載荷的變化關系。在初始載荷10 000 N時,油膜厚度為4.0 μm,膜厚比λ小于4,此時微凸體開始發生接觸。因此,摩擦副在實驗過程中始終處于混合潤滑狀態。從圖中可以看出,當加載從10 000 N升至40 000 N,油膜厚度由4.0 μm迅速減小至1.5 μm;而當加載從40 000 N升至120 000 N,膜厚從1.5 μm減小至0.5 μm(對應膜厚比為0.44),減小速率較為平緩,這是由于當膜厚減小到1.5 μm后,微凸體開始承擔較大一部分載荷,減緩了油膜厚度變薄的趨勢。

圖10 界面間平均油膜厚度隨載荷的變化關系
圖11所示為模擬得到的在實驗工況下,摩擦副間微凸體接觸載荷占比隨載荷的變化關系。在載荷較小時(10 000、20 000、30 000 N),油膜厚度較厚,摩擦副載荷主要由油液承擔,微凸體接觸載荷占比不超過5%;隨著載荷的增加,微凸體接觸載荷占比迅速升高,從2.4%(載荷為30 000 N)增加到18.2%(載荷為120 000 N),這主要是因為隨著載荷的增加油膜厚度不斷減小,導致微凸體接觸數目與接觸面積增加,因此微凸體接觸載荷占比不斷增加。

圖11 微凸體接觸載荷占比隨載荷的變化關系
圖12所示為發生接觸的微凸體中邊界膜破裂率隨載荷的變化關系。可以看出,當載荷小于125 000 N時(未達到臨界載荷),邊界膜未發生明顯破裂,破裂率小于1%;當載荷達到臨界載荷125 000 N時,發生接觸的微凸體中有60%發生邊界膜破裂,邊界膜的破裂導致微凸體間產生干摩擦,進而使摩擦副處于較差的潤滑狀態。

圖12 邊界膜破裂率隨載荷的變化關系
圖13所示為摩擦力各分量隨載荷的變化關系。從模擬結果可以看出,當加載力小于125 000 N(臨界載荷)時,摩擦力只由流體和邊界膜產生,且隨著載荷的增加,邊界膜產生的摩擦力占比在不斷增加;當載荷升高至125 000 N左右時,由于邊界膜發生明顯破裂(破裂率為60%),總摩擦力從2 500 N升高至8 200 N,其中干摩擦分量為6 600 N,約占總摩擦力的80.5%,遠大于邊界膜和流體分量,因此邊界膜的破裂將導致摩擦力發生階躍性突增。

圖13 摩擦力各分量隨載荷的變化關系
6 結論
(1)提出了一種pa-γ邊界膜強度模型,該模型反映了邊界膜失效與微觀接觸壓力、膜厚、滑動速度的關系,更準確反映邊界膜失效機制,模型參數可從試驗結果獲取,更容易工程應用。
(2)建立了基于邊界膜強度的混合潤滑模型,該模型耦合了流體動壓潤滑模型、微觀粗糙峰接觸模型、邊界膜強度模型,通過與實驗結果進行比較,表明其可更準確地反映摩擦副在混合潤滑條件下的摩擦特性和潤滑狀態。
(3)在存在邊界潤滑的混合潤滑條件下,當加載力小于臨界載荷,邊界膜幾乎未發生破裂,摩擦因數隨載荷增加緩慢變大,其數值均較小;當加載力加至臨界載荷,邊界膜破裂,摩擦副微凸體接觸區域出現干摩擦,摩擦因數出現突然增加,表明該摩擦副由邊界潤滑為主的混合潤滑狀態過渡到以干摩擦為主的潤滑狀態。
(4)通過模擬研究滑動軸承潤滑狀態轉變過程發現,當加載力加至臨界載荷,界面間平均油膜厚度減小至0.5 μm(對應膜厚比為0.44),發生接觸的微凸體中60%發生邊界膜破裂,使得摩擦力中干摩擦分量達到80.5%,由此出現當載荷逐漸增加至臨界載荷時摩擦因數出現突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