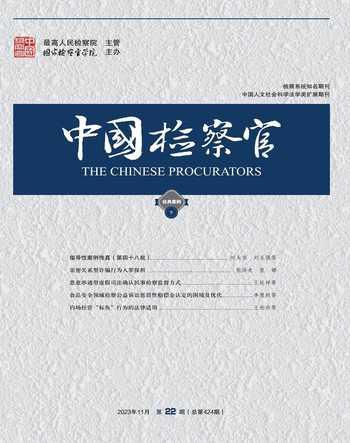親密關系型詐騙行為入罪探析
張澤龍 張娜
摘 要:親密關系型詐騙案件中被害人僅有對遭受財產損失危險的接受,無對遭受損失結果的接受。被害人基于自由意志自陷風險時,對于發生的危害結果應當自我答責。親密關系型詐騙案中被害人對親密關系的投資不具有“回報可能性”,行為人通過虛構親密關系,破壞被害人自我決定權的正確行使,行為人應當答責。只要虛構的親密關系實際上使對方不具有“回報可能性”,不需要再次虛構騙錢事由,也無需區分是主動贈予還是被動索取,針對這段感情的投資均應認定為財產損失。
關鍵詞:親密關系型詐騙 被害人承諾 危險接受 自我決定權 財產損失
親密關系型詐騙是指行為人虛構親密關系,使被害人產生對雙方關系的錯誤認識,借機騙取錢財的行為。以戀愛、交友為幌子借機攫取錢財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但在人際交往中,倚仗親密關系索取錢財的事經常發生。此類行為的罪與非罪具有模糊性,司法實踐對于案件的入罪路徑和數額認定都存在爭議,如何規范論證親密關系型詐騙行為構成詐騙罪亟待研究。
一、親密關系型詐騙行為認定之爭議
[基本案情]2021年4月,已婚的吳某(女,39歲)在拼車時認識了單身的龐某(男,32歲),吳某聊天中得知龐某為前女友花費20萬元,認為龐某“人傻錢多”,心生騙取其錢款的想法,遂虛構年齡,隱瞞已婚事實,欲與龐某戀愛交往。同年5月兩人確定戀愛關系,吳某多次表示想和龐某結婚,龐某陷入對這段戀愛關系的錯誤認識,對吳某的消費要求都盡量滿足,并主動贈予手機、冰箱等作為禮物。二人交往期間,吳某以各種真實或者虛假的理由向龐某索要財物共計12萬余元。同年10月,龐某發現吳某已婚事實,得知被騙后多次向吳某索要戀愛期間為其支付的錢款,吳某拒不退還。龐某聯系不上吳某后選擇報警,公安機關以吳某涉嫌詐騙罪立案并將其抓獲歸案。案件偵辦期間,吳某償還龐某經濟損失取得諒解。最終,吳某被法院以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并處罰金。
針對本案定性,實踐中存在不同觀點,有人認為,龐某的行為屬于贈予行為,所贈予的財物不應當認定為財產損失;有人認為,對親密關系的認識錯誤不屬于詐騙罪處分財物的認識錯誤;有人認為,必須在虛構親密關系的前提下再次虛構騙錢事由才屬于詐騙行為;還有人認為,龐某處分財物的行為與吳某虛構的親密關系之間具有條件性的因果關系,因此吳某當然構成詐騙罪。罪與非罪爭議的焦點在于,“行為人”使“被害人”陷入對雙方親密關系的錯誤認識,“被害人”以維持親密關系為目的實施財產處分行為,能否認定“被害人”存在財產損失并歸責于虛構親密關系的行為。
二、“結果接受”的解釋路徑
(一)本案存在“被害人承諾”
有學者從“被害人承諾”的理論出發,提出解決此類案件的思路:為維持一段親密關系而進行的財產處分,應當認為財產處分者存在“被害人承諾”。需要討論的是該承諾有效性的問題,如果承諾有效則阻卻犯罪成立。
與該案類似,司法實踐中將部分“酒托案”定性為詐騙罪。“酒托案”中,酒館招聘女性,以“談戀愛”“約炮”等理由,欺騙男性網友來酒館消費,以每杯酒水數十元至數百元不等的高價格騙取男性錢款,但是酒水品質正常,并無假冒偽劣。有觀點認為,在與“酒托女”赴約時,男性既在心理上確認了可能產生的高消費,同時也在行為上表現出對這種消費的默許。這種默許實際上是一種經濟上的“承諾”,暗示著他們愿意在會面過程中將財產用于支付高額酒水和娛樂費用。因此,這種認可實質上等同于對財產消費的承諾行為。[1] 同樣,在本案中,龐某為了早日結婚,對吳某的索財要求都予以滿足,龐某在給予財物時,無論是心理上還是行為上都具有自主性,客觀和主觀上都對自己處分財物這一事實有清晰的認識,這表明龐某允許吳某取得其財物,即龐某具有相應的“承諾”,如果承諾有效,龐某就不存在刑法意義上的財產損失,阻卻詐騙罪的成立。
(二)“被害人承諾”有效性的判斷
“被害人承諾”是一種阻卻違法性的正當化事由,得到被害人承諾的侵害行為不具有違法性。[2]“被害人承諾”除罪化需要判斷承諾的有效性。承諾有效必須滿足如下條件:符合承諾范圍、具有承諾能力、承諾對象適格、具有現實性的承諾、承諾無意思瑕疵。[3]本案問題之核心在于龐某的“承諾”是否滿足“承諾無意思瑕疵”這一要件。
“承諾無意思瑕疵”要求承諾的作出必須基于法益主體的真實意思,如果該承諾是在非真實意思情況下作出,則該承諾無效。案件中龐某受到欺騙,認為他和吳某之間的親密關系是真實的,在此認識錯誤狀態下作出的承諾,是否滿足“承諾無意思瑕疵”這一要件存在爭議。學理上一般認為,如果欺騙與最終受影響的法益具有關聯性,則屬于具有意思瑕疵的承諾,只有與法益存續有關的認識錯誤才是值得刑法關注的,這也被稱為法益關系錯誤說。如張明楷教授認為違法性的實質是法益侵害,故承諾的有效性判斷應當采取法益關系錯誤說。[4]周光權教授也認為,對于受欺騙的被害人承諾效力問題,總體上采取法益關系錯誤說是合適的。[5]
雖然何為“法益關系”較為模糊,但一般認為法益處分行為的社會意義或法益處分目的也屬于“法益關系”的內容。例如,在“移植腎臟案”中,醫生為了救助自己的朋友,欺騙某位母親說如果不把她的腎臟移植給她正在住院的孩子,孩子就會死亡;母親答應移植,醫生借此機會將腎臟移植給他的朋友。[6]如果否認法益處分目的是“法益關系”的內容的話,就會認為母親對于腎移植并未產生與法益本身(即身體健康)有關的認識錯誤,因此醫生無罪,但是這種結論難以為人們所接受。應當認為,母親對于處分自身法益的目的存在認識錯誤,進而影響了整個法益關系,故該承諾無效。
(三)本案的“承諾”因具有意思瑕疵而無效
本案中,龐某對于法益處分目的存在認識錯誤。在案件偵辦過程中,龐某曾多次表示如果知道吳某已婚,他絕不會為吳某花錢。龐某處分財物的目的是為了維持戀愛關系并締結婚姻關系,但是由于吳某的欺騙,該目的不可能實現,也即由于吳某的欺騙,龐某對財產法益處分目的具有認識錯誤。因此,龐某處分財產的承諾有意思瑕疵,該承諾無效,應當認為龐某具有財產損失。
總之,依照“結果接受”的解釋路徑,此類案件的被害人為維持雙方親密關系而處分財物的,應當視作被害人對處分的財產法益具有承諾。同時,被害人雖然具有處分財產的承諾,但是該承諾是受欺騙而形成的,影響了法益處分目的,即被害人所作的承諾因具有意思瑕疵而無效,應當認為被害人存在財產損失,行為人構成詐騙罪。
三、“危險接受”的解釋路徑
(一)“結果接受”解釋路徑的反思
上述“結果接受”的法理似乎妥善論證了親密關系下的詐騙罪問題,但如果對案件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被害人承諾”的解釋路徑仍然不夠妥當。以案件所涉及的詐騙罪為例,案件事實中確實可以找到被害人的“承諾”:龐某通過客觀行為與主觀意志表明其愿意讓吳某取得自己的財產,也即龐某作出“對方可以取得我財產”的承諾。值得反思的是,該“承諾”是否是對詐騙罪結果的承諾。
根據詐騙罪的基本構造[7],“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才是詐騙罪的最終結果,“行為人或者第三人取得財產”并非詐騙罪的最終結果。案例中龐某對于“遭受財產損失”這一點并未有承諾,其在意志上并非對財產損失結果的發生持希望、放任態度,而是反對、否定的態度。事實上,龐某所謂的“承諾”,是對“吳某取得財產”的承諾,這一承諾只是龐某對財產處分的同意,而非對財產損失的同意。
通過“移植腎臟案”與本案的對比更容易發現這一點。在“移植腎臟案”中,母親對于自己的腎臟會被摘取這一點是有明確認知與同意的,母親對于腎臟移植的生理意義也存在明確認知,因此母親存在對于危害結果的承諾。但是在本案中,龐某對于其整體財產法益受損這一事實不存在明知,也就不可能作出針對危害結果的承諾。
其實不難發現,任何詐騙罪都存在對“財產處分”的同意,詐騙罪正是因為行為人通過各種騙術獲得了被害人“財產處分”的同意才成為詐騙罪。也就是說,任何詐騙罪都存在“無效的財產處分承諾”,以此理論來論證親密關系型詐騙行為構成詐騙罪是缺乏可行性的,且邏輯等同于“因為這是詐騙,所以這是詐騙”。親密關系型詐騙與其他普通詐騙的區別在于,親密關系型詐騙并不需要再次虛構騙錢事由,而其他詐騙一般是直接虛構財產處分的事由。本案中吳某向龐某索要錢財時,大多沒有虛構錢款的使用事由,吳某索要微信紅包充值油費、還債都是真實事實。
總之,由于親密關系充滿不確定性,作為維持親密關系存續的感情因素又是法律無法審查的,親密關系中雙方的付出時常無所回報。針對親密關系的投資存在風險,社會生活中的理性個體對這份風險具有明確認知。因此,在親密關系型詐騙案中,被害人僅僅是對遭受損失危險的接受,而非是對遭受損失這一結果本身的接受。故而,正確的分析路徑應當是對被害人自擔行為風險的分析,即“危險接受”的分析路徑。
(二)“危險接受”的理論闡釋
所謂“危險接受”,指被害人在明知行為具有導致損害結果發生可能性的情況下,仍自甘風險支配或者參與到行為中。被害人雖然自甘風險實施行為,但是對于損害結果的發生仍持否定、反對態度。
危險接受與結果接受最主要的區別是,危險接受時,被害人只認識到了行為的危險,并沒有承諾實害結果的發生,沒有放棄自己的法益;結果接受時,被害人同意實害結果的發生,放棄了自己的法益。即使存在有效的“危險接受”,由于被害人并未放棄自身法益,被害人對危險的接受不足以直接阻卻行為的違法性,因此“危險接受”要阻卻行為的違法性,還需要借助深層次法理,即自我決定權。
所謂自我決定,“就是主體基于對自由的普遍承認和尊重而通過行為來決定和實現自己的自由,它是意志自由的客觀表現”[8]。當主體正確行使自我決定權去接受危險的時候,對于發生的危害結果就應當自我答責。[9]例如,在“注射毒品案”中,吸毒者讓他人將吸毒注射器借與其使用,吸毒者吸食過量導致身亡。[10]吸毒者對于吸毒的危險存在明確認知仍然注射毒品,表明吸毒者存在對于吸毒危險的接受,因此死亡結果應當自我答責。在“梅梅爾河案”中,狂風暴雨時乘客不顧船工警告,要求船工擺渡他們過河,最終乘客溺水身亡。[11]乘客對于暴雨中過河的危險存在明確認知且仍然要過河,表明乘客有對過河危險的接受,因此對于死亡結果應當自我答責。但是,當被害人未能正確行使自我決定權時,不應當自我答責。如果“梅梅爾河案”的事實是“有乘客要渡河,船工隱瞞雨天會翻船的事實,導致乘客做出渡河的決定而后途中翻船致死”,此時乘客自我決定權行使的前提就出現了錯誤,船工應當對其隱瞞事實導致乘客溺亡的結果負責。
(三)親密關系型詐騙的理論適用
1.對親密關系投資的前提:“回報可能性”
個體為了追求其所認為的高價值親密關系,自擔風險進行投資。個體針對某段親密關系的投資是渴望被回應的,也即個體進行投資的前提是該段親密關系事實上有回報的可能性。“回報可能性”就是正確行使自我決定權去投資該段親密關系的前提。如果對“回報可能性”這個前提存在認識錯誤,那么就不應當認定為主體正確行使了自我決定權,也就不應當要求主體自我答責。
如同證券、期貨交易行為,投資者進行投資的原因在于該證券、期貨是有可能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下為其帶來收益的。投資者作為理性經濟人,為了追求該份收益,在明知投資行為具有虧損風險的情況下仍然選擇投資,是其自我決定權行使的表現。此時,即使最終結果是虧空的,投資人也應當自我答責。但是,我國刑法之所以在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這一章節中,規定追究投資關系中第三人刑事責任的罪名,就在于這些行為的性質是誤導他人的行為,即這些行為破壞了“回報可能性”——作為投資者行使自我決定權的前提條件。例如刑法第181條規定的“誘騙投資者買賣證券、期貨合約罪”,該罪名打擊的行為是故意提供虛假信息等欺騙投資者做出錯誤決定的行為。投資者投資時,僅僅對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所帶來的風險具有承諾,其并未承諾放棄自己的財產法益任憑股票虧空。如果他人對投資者進行欺騙,使其在不明所以的情況下錯誤行使了自我決定權,該自我決定權帶來的損害就不應當要求投資者自我答責,而是應當追究欺騙者的刑事責任。
本案中,龐某之所以對該段親密關系進行投資,是因為龐某認為他和吳某之間的親密關系具有“回報可能性”。那么在親密關系是由吳某虛構的情況下,該關系就不具有龐某期待的“回報可能性”。也就是說,吳某虛構了事實,影響了龐某財產處分的自我決定權的行使,吳某積極促進龐某財產損失,此時雖然龐某存在對財產損失危險的接受,但是這份危險的現實化仍然需要吳某答責。
2.親密關系型詐騙中財產損失的認定
首先,司法實踐中對于本案行為構成詐騙罪是否需要吳某在虛構親密關系的基礎上再次虛構騙錢事由存在爭議。如在與本案類似的“劉某詐騙案”中,劉某(女)虛構身份,假裝與被害人孫某(男)熱戀,借此以各種理由索要錢財。劉某詐騙案的一審判決認為,在親密關系型詐騙案中,只有再次虛構騙錢事由才能構成詐騙罪,劉某向被害人索要100萬元用于理財和索要30萬元用于打造旅游資金賬戶的行為不應當認定為詐騙罪,因為劉某并未欺騙被害人。但是二審法院認為,一審的邏輯未將虛構親密關系與虛構騙錢事由的欺騙行為當做一個整體看待,被害人孫某正是因為劉某虛構了親密關系才愿意處分這些錢財,欺騙行為與財產損失具有直接因果關系。[12]
應當說,上述二審法院的思路是正確的,其認識到只要在親密關系具有虛假性的情況下,被害人處分的財物就應當被認定為財產損失。但是二審法院說理不充分,其仍然是按照條件說的邏輯進行論證,即戀愛只要有虛構成分,戀愛中所處分的財物就認定為財產損失,這樣容易模糊仰仗戀愛關系而索取錢財的行為罪與非罪的界限。應當說,只有在虛構的親密關系達到了影響被害人“回報可能性”的情況下,才能認定為詐騙罪。人類學理論認為,每個人都是天生的說謊者,人們在日常的社會親密關系中或多或少存在欺騙與隱瞞。仰仗戀愛關系而索取錢財的事例中雖然可能存在一定欺騙,但是維持一段親密關系本就是需要承擔風險進行投資的。健康的親密關系包括六個方面:了解、關心、相互依賴性、相互一致性、信任以及承諾。一般而言,最令人滿意的親密關系應當包括親密關系的六個方面。[13]按照危險接受理論,只要親密關系中雙方是真正健康地在維持親密關系,雙方是在相互正向加功,即使存在一些小的欺騙,也應當各自為風險現實化進行自我答責,這就排除了詐騙罪侵入日常生活的危險。
其次,在虛構親密關系的基礎上,如果欺騙者未主動索取錢財,被害人為了討好對方主動贈予財物,是否可認定為詐騙罪導致的財產損失也存在爭議。如“劉某詐騙案”中,辯護方提出抗辯認為,有的錢款并非是孫某基于錯誤認識予以處分,而是出于討好劉某父母的目的,該筆錢款應當屬于贈與,不應認定為詐騙。但二審法院最終并未采納該抗辯。一方面,孫某之所以做出“贈予”,是因為期待得到回報,該自我決定權行使的前提是贈予的“回報可能性”。劉某編造她父母是政府高官、在美國有房產等,在劉某的持續蠱惑之下,孫某才做出“贈予”行為,該行為不具有“回報可能性”,贈予的財物應當認定為劉某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而導致的財產損失。同樣,在本文案例中,龐某也曾為了討好吳某,向她贈予蘋果手機等物品,這些贈予的財物也應認定為財產損失。另一方面,在復雜的親密關系中,往往很難區分“索要”與“贈予”,親密關系中雙方經常做出虛假的意思表示,禮尚往來建立在暗示與猜測的基礎上,法律很難審查雙方當事人當時的真實所想,清官難斷家務事,因此區分二者并不現實。
總之,只要虛構的親密關系實際上使對方不具有“回報可能性”,那么不需要再次虛構騙錢事由,也無需區分是主動贈予還是被動索取,針對這段感情的投資均應認定為財產損失,欺騙方構成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