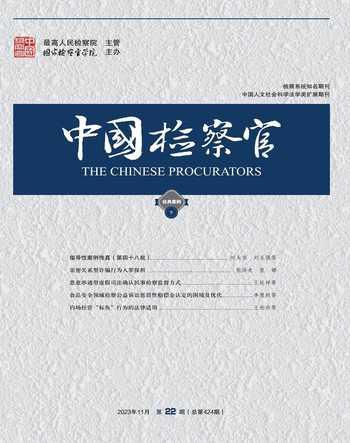明知是贓物而實施幫助變現行為的定性分析
于淳燁 劉軒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王某于2018年5月至2021年10月擔任某建筑公司采購部項目經理。任職期間,王某具有采購辦公用品的職權,但無對外采購鋼材的權限。自2021年3月至2021年10月間,王某利用網絡聯系他人,擅自偽造了本公司的一系列印章,以本公司的名義,先后與十余家鋼材經銷商簽訂購買合同,采取先供貨3個月,然后再付款的方式,大批量采購高于市場價格的鋼材。收到供貨后的當日或次日,王某再以遠低于市場價格的方式將上述貨物出賣。得到貨款后,王某除將其中一部分用于支付前期向經銷商采購鋼材的貨款外,剩余的錢款均用于個人開銷與揮霍。王某利用該行為如此反復達半年之久,后因無力償還拖欠的貨款,向公安機關自首投案。經查,王某拖欠部分經銷商的采購款達數百萬元。
犯罪嫌疑人劉某系某鋼鐵公司的銷售代表,在王某實施上述行為前便與王某相識。劉某與王某二人并未共謀實施上述行為。但在2021年3月至2021年10月間,劉某在明知王某利用支付賬期的方式套取變賣貨物的錢款后,仍多次為王某介紹不同的經銷商,使得王某得以從經銷商處購得鋼材。同時,劉某主動聯系王某,以遠低于市場價的方式收購王某騙取的鋼材,幫助王某將上述貨物及時變現,使得王某利用合同騙取貨物的犯罪行為得以為繼。然后,劉某再將收購的鋼材以略低于市場價格的方式賣給不同的經銷商,再將該經銷商介紹給王某,由經銷商將鋼材再次出賣給王某,以此反復循環。經查,劉某以上述方式支付給王某購貨款共計數百萬元。
二、分歧意見
對于王某利用偽造的公司印章,對外簽訂合同騙取貨物的行為,理論與實務中一般不存爭議,屬于《刑法》第224條規定的“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合同詐騙行為,成立合同詐騙罪。但是,對于劉某在明知王某利用支付賬期騙取鋼材,而仍為其介紹經銷商,并主動收購王某騙取的鋼材,幫助王某將騙取的鋼材變現的行為,究竟應當如何定罪處罰,在處理過程中存在三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劉某與王某成立共同犯罪,劉某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的共同正犯。該意見主張:雖然劉某與王某沒有就共同實施合同詐騙行為進行語言上的直接交流,但是劉某對王某利用支付賬期騙取貨物的行為是明知的,并且劉某積極為王某介紹經銷商,然后對王某騙取的貨物進行收購。說明劉某、王某之間已經通過相互間的行為,達成共同實施合同詐騙的犯罪故意。在不法利益的獲取上,王某將從經銷商處騙取的貨物以遠低于市場價格的方式出售給劉某獲取不法利益,劉某以略低于市場價格的方式將同批貨物轉賣給不同的經銷商賺取差價,然后劉某再將經銷商介紹給王某,由經銷商將同批貨物以略高于市場的價格出售給王某。劉某與王某之間彼此心照不宣、通力合作、各得其利。因此,劉某的行為成立合同詐騙罪的共同正犯。
第二種意見認為,劉某與王某成立共同犯罪,但是劉某不成立合同詐騙罪的共同正犯,而是成立合同詐騙罪的幫助犯。該意見主張:劉某只是向王某介紹了經銷商,并收購了王某騙取的貨物,并沒有參與到王某偽造公司印章、出具虛假合同等一系列騙取經銷商貨物的犯罪過程中。雖然劉某與王某沒有共謀犯罪的計劃和分工,但是劉某在主觀上對王某實施合同詐騙行為是明知的,并且劉某后續多次收購王某騙取的貨物,能夠證明劉某已經通過實際行動與王某形成了共同實施合同詐騙的犯罪故意。但是,劉某僅具有幫助王某完成合同詐騙的犯罪故意。因此,劉某的行為成立合同詐騙罪的幫助犯。
第三種意見認為,劉某與王某不屬于共同犯罪,劉某成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該意見主張:劉某作為鋼鐵公司的銷售代表,明知王某在較長的時間內,出售如此大批量的鋼材不合情理,很有可能是通過違法犯罪的方式獲取,仍然主動收購王某騙取的貨物,幫助王某以遠低于市場的價格與非正規的交易程序將騙取的貨物變現,避免王某騙取的貨物被司法機關追繳,并且劉某利用王某實施低買高賣的方式獲取不法利益。因此,劉某的行為成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劉某為王某介紹經銷商,主動收購王某騙取的鋼材,幫助王某將騙取的貨物變現,劉某的行為應當與王某成立共同犯罪,劉某屬于合同詐騙罪的幫助犯,具體分析意見如下。
(一)劉某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的幫助犯
1.劉某與王某成立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是指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原定由單獨的行為人予以實現,但實際上由多數人實現犯罪的情形。[1]按照學界通說,成立共同犯罪需要滿足三個要件:一是行為人為二人以上;二是共同的犯罪行為;三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就本案而言,劉某與王某均為具有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因此,案件審查的重點就在于判斷二人是否具有共同的犯罪行為和共同的犯罪故意。
首先,二人具有共同的犯罪行為。所謂共同的犯罪行為,是指各行為人的行為都指向同一犯罪,互相聯系,互相配合,形成一個統一的犯罪活動整體。[2]本案中,劉某與王某各自實施相應的行為,相互配合以達成實現合同詐騙的犯罪目的。其中,王某先后實施了偽造公司印章,假借公司名義與經銷商簽訂虛假合同騙取貨物的行為,而劉某則為王某介紹不同的經銷商,幫助王某可以利用偽造的印章和合同騙取經銷商的貨物,并且在王某騙取貨物后,主動收購王某騙取的貨物,幫助王某將騙取的貨物及時變現,使得王某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可以維系半年以上而不被發覺,這主要得益于劉某的行為在其中發揮的幫助作用,二人的行為彼此配合、缺一不可。因此,劉某和王某具有共同的犯罪行為。
其次,二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所謂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認識他們的共同犯罪行為會發生的危害結果,并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3]具有共同犯罪故意,也是在共同犯罪中實行“部分行為全部責任”的重要依據。在判斷各行為人是否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時,一個重要的因素在于審查共同犯罪人之間是否存在意思聯絡(或稱犯意聯絡)。意思聯絡是實現二人以上達成犯罪故意的紐帶。[4]通常情況下,意思聯絡的方式以明示的語言交流為主。但這并不意味著默示方式無法形成意思聯絡。實際上,在一些案件中通過行為來示意的默示的意思聯絡,也可以實現同樣的效果。例如,甲和乙在逛街時,不小心碰到行人丙,雙方發生激烈爭吵,甲從口袋里掏出一把刀遞給乙,乙用刀把丙捅傷,甲雖然沒有和乙進行語言交流,但在當時情境下,甲將刀遞給乙的意思很明顯,乙也立即明白了甲的意思,雙方之間就形成了共同的犯罪故意,甲不能辯說他沒有跟乙商量而不構成故意傷害罪。[5]本案中,劉某與王某之間也沒有直接的語言溝通,雙方也是通過彼此間的行為而實現有效的意思聯絡。首先,劉某明知王某并非建筑公司高管,王某也沒有對外采購鋼材的權限,不可能在一段時間內連續多次大批量購買鋼材,而且這些數量已經遠遠超出實際需求;其次,王某在獲取貨物后,或當日或次日便把貨物出售給劉某,王某實現了買貨與賣貨的無縫銜接,間接證實王某購買鋼材并非是公司所需;再次,劉某將自王某處收購的貨物以略低于市場價格的方式賣給其他經銷商,再將該經銷商介紹給王某,便于王某再次實施合同詐騙行為,在二人上述行為的多次循環往復間,二人已經通過實際行為實現了意思聯絡,劉某的行為為王某合同詐騙行為的持續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2.劉某成立合同詐騙罪的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
在我國刑法的共同犯罪體系中并沒有正犯、共同正犯及幫助犯的規范概念,但這不妨礙我們從理論上使用上述概念,進而應用到實務中并解決實務問題。共同正犯的概念是德、日等國的法定共犯種類,例如《德國刑法典》第25條規定:“自己實施犯罪,或通過他人實施犯罪的,依正犯論處。數人共同實施犯罪的,均依正犯論處(共同正犯)。”《日本刑法典》第60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的,皆為正犯。”[6]基于此,所謂共同正犯,就是以共同犯罪意思,各自分擔犯罪的部分,共同實現“自己的犯罪”的人。[7]而幫助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基于幫助的故意,以非實行行為加工于犯罪,使犯罪易于實施或完成的犯罪參與形態。[8]我國的共同犯罪體系屬于雙層區分制[9],在雙層區分制體系下,共同正犯屬于正犯的一種,而幫助犯則屬于狹義的共犯。關于正犯與共犯的區分,理論上存在主觀說、客觀說、犯罪行為支配說(或稱犯罪事實支配說)的觀點紛爭。主觀說認為,出于實施自己的行為的意思而進行行為的人是正犯;出于影響他人的行為的意思而實施行為的是共犯。客觀說認為,對結果的發生具有原因的人就是正犯;提供條件的人是共犯。犯罪行為支配說認為,出于實現構成要件的意思而有目的地根據一定行為來支配、控制因果關系,行為具有支配性的是正犯,反之,則是共犯。[10]筆者認為,主觀說的最大問題在于行為究竟是基于正犯的意思,還是共犯的意思,難以通過客觀證據合理驗證;客觀說則將是否實施構成要件的行為作為區分正犯與共犯的標準,但這難免會進一步引發如何判斷是否屬于構成要件的行為以及難以將操縱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這種未直接實施實行行為的人認定為正犯的難題。相比較而言,筆者支持犯罪行為支配說的觀點,目前該說已經成為《德國刑法》的通說。[11]本案中,對整個合同詐騙犯罪的進程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王某,因為王某先是偽造了建筑公司的印章,隨后又通過簽訂虛假合同的方式騙取經銷商的貨物,沒有王某的行為,合同詐騙根本難以完成。在這一過程中,劉某只是為王某介紹了經銷商,以便于王某騙取對方的貨物,顯然劉某的行為對整個合同詐騙的進程不具有支配作用。至于劉某收購王某騙取的貨物,幫助王某將騙取的貨物變現的行為,則屬于合同詐騙行為實施完畢后的不可罰的事后行為,雖然該行為具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作用,但已經無需再重復評價,其已經作為合同詐騙幫助行為的一部分而納入其中。
3.劉某不成立合同詐騙罪的片面幫助犯
在本案的處理過程中,有觀點認為雖然劉某的行為屬于合同詐騙罪的幫助犯,但劉某不是與王某具有意思聯絡的共同犯罪的幫助犯,而是單方面明知王某實施合同詐騙行為而為其提供幫助的片面幫助犯。因此,劉某的行為成立合同詐騙罪的片面幫助犯。
我國刑法第25條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因此,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須以行為人之間具有相互的意思聯絡為必要。幫助犯作為共犯中的一種,其存在以成立共同犯罪為前提。在我國現行刑法語境下,并沒有幫助犯的概念,幫助犯屬于起輔助作用的從犯中的一種[12],更沒有所謂片面幫助犯的概念。片面幫助犯屬于刑法理論中討論的概念。所謂片面幫助犯,是指單方的對于正犯的犯罪行為予以援助的情形。[13]就理論而言,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犯罪故意,客觀上實施了加功于正犯實行行為的幫助行為,具有刑事可罰性,因此成立相應犯罪的片面幫助犯。而在司法實務中,片面幫助犯也是客觀存在的。如甲得知乙某天將要去丙家殺害丙,甲便在乙實施入室殺人行為前,提前用萬能鑰匙打開丙家的房門,便于乙能夠直接破門而入實施殺人行為。該案例中雖然乙并沒有認識到存在甲的幫助行為,但甲不僅主觀上具有幫助殺人的犯罪故意,而且客觀上具有促進殺人的幫助行為,并且其行為已經達到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程度,該案例中甲的行為就是典型的片面幫助犯。但從現有立法層面來看,尚未認可片面幫助犯。也許有論者會提出不同的觀點,認為“兩高”已經通過司法解釋[14]的方式確認了片面幫助犯,即提供幫助行為的一方,在主觀上具有單向明知,即可依照共同犯罪論處。[15]本案也可以依據類似司法解釋的精神,認定劉某的行為成立片面幫助犯。筆者認為,片面幫助犯與共同犯罪的幫助犯最大的不同在于意思聯絡形式的差異,即前者是單向的意思聯絡,而后者是雙向的意思聯絡。因此,判斷劉某與王某之間意思聯絡的形式,就成為認定劉某成立片面幫助犯抑或共同犯罪的幫助犯的關鍵。前文已經論述了,劉某與王某之間通過默示的方式,通過彼此間的行為達成犯罪的合意,雙方對此都心知肚明,因而劉某成立共同犯罪的幫助犯但非片面幫助犯。
筆者認為,我國刑法總則明確規定了共犯必須具有雙向意思聯絡。盡管司法解釋就片面幫助犯先于立法從司法實踐層面進行了探索,但司法解釋不能代替立法,司法解釋只能針對特定的行為進行適用,不具有普適性。當依據片面幫助犯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時,應當以相關司法解釋的具體規定為前提。對于司法解釋尚未作出明確規定的,不能突破刑法總則關于共犯的規定,隨意擴大片面幫助犯的適用范圍。
(二)劉某的行為不成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我國刑法第312條規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成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根據本罪的罪狀表述,劉某的行為不成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理由如下:
1.劉某與王某就合同詐騙達成事實上的犯罪合意
區分上游共同犯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一個重要標志在于判斷行為人與上游犯罪人是否事先達成合意。如果在事先已達成合意,行為人就應當認定為上游犯罪的共犯;反之,則成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本案中,劉某與王某二人在王某實施合同詐騙行為之前,并沒有合謀如何處理王某騙取的財物。正如上文所述,在上述犯罪行為多次循環往復的過程中,劉某與王某對彼此之間在整個合同詐騙過程中的作用是心知肚明的,王某的供述也證實,劉某肯定知道這些鋼材的來路。試想,如果沒有劉某與王某相互間的共同合作,該犯罪行為將難以持續下去,而在本案中該行為前后持續了達半年之久,受騙的經銷商高達十余家,已充分證實劉某與王某已經通過各自的行為達成共同實施合同詐騙的犯罪合意,二人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
2.劉某已實際參與到王某合同詐騙的過程中
區分上游共同犯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另一個重要依據在于判斷行為人是否實際參與到上游共同犯罪的過程中。[16]在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案件中,通常是上游犯罪行為已經既遂,而將獲取的犯罪所得、所得收益交由行為人,由行為人通過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予以掩飾、隱瞞。本案中,如果從王某單獨的某一次合同詐騙行為來看,劉某均是在王某合同詐騙犯罪結束后,將王某騙取的財物進行收購再賣出,看似符合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構成要件,應當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責任。但從整體上看,王某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不是偶發的孤立事件,而是以同樣的行為方式反復、多次實施,持續達半年之久,直至完全無力償還拖欠的貨款后,王某才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而王某的行為得以持續,也得益于劉某在其中所扮演的“上下游中介”的角色,劉某行為的介入使王某合同詐騙的行為形成了完整的閉環。劉某并非在合同詐騙犯罪結束后才參與進來,而是一直在參與合同詐騙行為的實施。因此,從主觀要件上看,劉某收購王某騙取的貨物,實際上并不是為了掩飾、隱瞞王某合同詐騙所得,而是希望促成王某繼續實施合同詐騙,從而獲取低買高賣的不法利益。從客觀要件上看,劉某雖然沒有直接參與簽訂合同環節,但其在共同犯罪中只是與王某的分工不同,其收購再賣出、介紹經銷商等一系列行為,客觀上促進了合同詐騙犯罪的持續進行。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以合同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更能全面評價劉某的行為。
近年來,打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行為持續保持高壓態勢,越來越多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案件進入辦案視野。由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行為屬于事后幫助行為且行為人具有單方面明知即可,客觀上與共同犯罪中的幫助犯存在區分難題,如何準確區分共犯行為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行為,考驗著每個檢察人員的司法智慧與業務素能。合理界分共犯行為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行為,仍應從細節著手、從證據出發,綜合全案證據具體考量,具體而言:一是要區分行為人與上游犯罪人是否具有意思聯絡,聯絡的形式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二是行為人是否實際參與到上游犯罪的過程中并發揮作用,如果有,則應當認定為上游犯罪的共犯;反之,則應當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