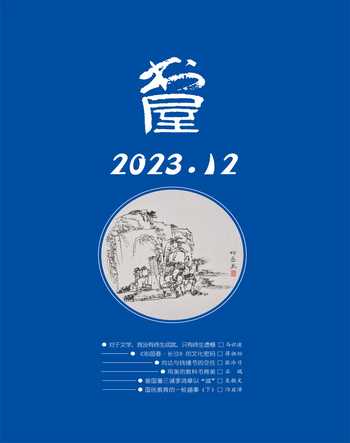營(yíng)一方“此心安處”
計(jì)緯
三株頂天立地的古樹,樹身離得不近,樹冠的枝葉卻連成了一片,遮天蔽日。它們應(yīng)該生在水邊,因?yàn)闃涓幱谢蚝苫蚱嫉乃参锔≈瑥臉溟g,可以看見遠(yuǎn)處有一條小船,船頭依稀坐著兩個(gè)戴草帽的人。畫面最左側(cè),題著“此心安處”四個(gè)字,鈐古璽式朱文“揚(yáng)之水”印章,下面一方圓形朱文印“董”。畫筆樸拙,書跡秀雅,這是董寧文(子聰)寫、揚(yáng)之水題的一幀小品。
此畫堪稱這里所選幾十幅董畫、揚(yáng)題之作的“畫眼”,“此心安處”四個(gè)字,更是所有題跋的文眼——也許就是這個(gè)原因,整本畫冊(cè)取名《此心安處》,副標(biāo)題“揚(yáng)之水子聰合寫小品”。
的確是一本與眾不同的畫冊(cè)。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yàn)槟腿藢の丁.媹D,題詞,直到設(shè)計(jì)、印刷,均耐人尋味。
畫,都是簡(jiǎn)筆寫意小品,筆墨潔凈,構(gòu)圖清爽;題,每幅也就四五個(gè)字,最多的十幾個(gè)字,清秀剛勁的小楷。副頁(yè)上,還都用印刷體完整地給出了題跋的出處,比如《此心安處》,一是蘇軾《定風(fēng)波》:“……萬(wàn)里歸來(lái)年愈少,微笑,笑時(shí)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yīng)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一是元好問《水龍吟》:“百年同是行人,醉鄉(xiāng)獨(dú)有歸休地。此心安處,良辰美景,般般稱遂……”慢慢體味,令人心靜神清。
每一幅都有這種耐人尋味之處。
兩棵樹,樹下一座茅亭,樹間一牙新月。題字“風(fēng)月俱閑”出自趙長(zhǎng)卿《眼兒媚》:“南枝消息杳然間。寂寞倚雕欄。紫腰艷艷,青腰裊裊,風(fēng)月俱閑。……”
一疊怪石,兩株菊花。題字“香噀西風(fēng)雨”出自吳文英《霜葉飛·重九》:“斷煙離緒。關(guān)心事,斜陽(yáng)紅隱霜樹。半壺秋水薦黃花,香噀西風(fēng)雨……”
一把巨型提梁壺,幾乎占據(jù)了整個(gè)圓形畫面,左下角五顆櫻桃,一枚小茶盞,右側(cè)題曰“應(yīng)自待月西廂”。語(yǔ)出周邦彥《風(fēng)流子》:“新綠小池塘,風(fēng)簾動(dòng),碎影舞斜陽(yáng)。羨金屋去來(lái),舊時(shí)巢燕,土花繚繞,前度莓墻……遙知新妝了,開朱戶,應(yīng)自待月西廂。最苦夢(mèng)魂,今宵不到伊行……”
一張正方形的紙,偏左上一只陶罐,種著離離青草,偏右下,一個(gè)瓷盤,盛著幾顆荔枝。題字“紅深翠窈”出自吳文英《瑞鶴仙·丙午重九》:“亂云生古嶠。記舊游惟怕,秋光不早。人生斷腸草。嘆如今搖落,暗驚懷抱。誰(shuí)臨晚眺?吹臺(tái)高、霜歌縹緲。想西風(fēng)、此處留情,肯著故人衰帽。? 聞道,萸香西市,酒熟東鄰,浣花人老。……追吟賦,倩年少。想重來(lái)新雁,傷心湖上,銷減紅深翠窈……”
淡墨涂下幾片參差的蓮葉,一紅一黑兩尾金魚搖曳其間。題字“何人輕憐細(xì)閱”出自周邦彥《華胥引》:“川原澄映,煙月冥蒙,去舟如葉。岸足沙平,蒲根水冷留雁唼。別有孤角吟秋,對(duì)曉風(fēng)嗚軋。紅日三竿,醉頭扶起還怯。? 離思相縈,漸看看、鬢絲堪鑷。舞衫歌扇,何人輕憐細(xì)閱……”
一幅荔枝的折枝小畫,題字“須插向,鬢邊斜”出自蔣捷《霜天曉角》:“……說(shuō)與折花人道:須插向,鬢邊斜。”
這一幅,有點(diǎn)讓人摸不著頭腦。蔣詞寫的是折花、插花,揚(yáng)之水讓人插荔枝,是筆誤,還是文人的瀟灑?都不是。
手邊恰有《開卷》2022年第十二期,刊有沈勝衣文《金果結(jié)腰間,銀荔生耳鬢》,寫的就是這幅畫:“水公大概是對(duì)古代曾流行簪戴荔枝飾物一事入了心,以致錄了那兩句貌似不相干的宋詞。”原來(lái)古代以荔枝為紋樣的裝飾物戴在頭上很普遍。作者引了揚(yáng)之水的著作《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中國(guó)金銀器》,感嘆“在此可見宋人一種獨(dú)特的風(fēng)情,男子腰間所系,女子頭上簪戴,到處都是金銀荔枝,仿佛讓這南國(guó)佳物生長(zhǎng)、結(jié)果于士人和佳人身上,相伴垂曳,端的好景”。讀過(guò)此文,再看畫的題詞,就能別有會(huì)心了。原來(lái)如此。
專業(yè)畫家是畫不出這樣的畫的,專業(yè)書畫家大概更題不出這樣的詞。
恰恰他們不是專業(yè)的書家畫家。他們是讀書人,他們都是編輯出身的文士、學(xué)者。揚(yáng)之水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就編《讀書》,出過(guò)幾本頗有影響力的書話作品,后來(lái)潛心名物訓(xùn)詁,不斷有著作問世。董寧文二十余年如一日,獨(dú)立編輯《開卷》,寫下十本《開卷閑話》,出版了八輯《開卷書坊》。
揚(yáng)之水的一手簪花小楷經(jīng)張中行先生推介,早就譽(yù)滿文林,那管既寫文章又寫字的筆伴隨她逶迤走過(guò)了幾十年,時(shí)間甚至超過(guò)她治學(xué)、做編輯的年齡。董寧文,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在皖南服役時(shí)就涉足書畫,算起來(lái)是資深畫家了。可見,他們并不囿于一隅,一條道走到黑,也不是心血來(lái)潮,半路出家。他們學(xué)有專攻,涉獵廣博;他們文事之余,寄情翰墨;他們的文事和藝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寧文這些年頗出過(guò)些裝幀、制作獨(dú)到的書,這一本也是。
二十四開的方開本,淡綠色絲質(zhì)封面,直包到封底,封面右上側(cè)是墨筆書名,左下側(cè)是一幅樹下美人的線描圖畫,線為黃色,字和畫都是長(zhǎng)方形,封底兩方朱紅色的印章,揚(yáng)的“棔柿樓”,董的“開卷樓”。畫大多數(shù)直接印在書頁(yè)上,題跋截出,單印為特寫,個(gè)別長(zhǎng)形的畫,印于宣紙,折一下,貼上。友人阿濤題寫的兩紙書名,也原樣影印,貼于書中。
揚(yáng)之水和子聰都是文人,所以文友多。文友多,文就多。書前書后的文章有六篇,唐吟方一人四篇:《讀揚(yáng)讀董》《〈開卷〉以外,丹青之間——讀董寧文的山水畫》《做藝術(shù)圓桌的寧文》《文心與藝心——寫在寧文海寧展前》,沈勝衣《宋人遠(yuǎn)意》,子文《含道映物澄懷味象》。《讀揚(yáng)讀董》,附了兩種手跡,一為硬筆橫行,一為毛筆直書。毛筆的那張也是宣紙影印粘在書后,唐先生的小楷勁秀而富有書卷氣,為此書增色不少。可能是怕文章過(guò)多,喧賓奪主,沈先生的那篇《金果》沒有收,如果收錄,是會(huì)給讀者很好的啟迪的。
一本書,這樣又附又貼,亂不亂?一點(diǎn)都不亂。一冊(cè)在手,大可領(lǐng)略統(tǒng)一之中異彩紛呈、厚重之下盡顯靈動(dòng)的韻味,這就又一次彰顯了文化、藝術(shù)的魅力了。
現(xiàn)實(shí)中能夠使人安心的去處越來(lái)越少,在紙面上有一方“此心安處”可去,也是極大的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