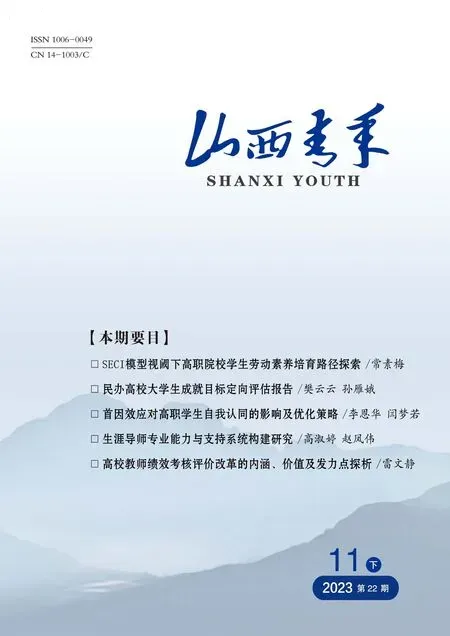民辦高校大學生成就目標定向評估報告
樊云云 孫雁娥
1.晉中信息學院,山西 晉中 030800;2.朔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山西 朔州 036000
一、問題提出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民辦高校的興起與建設還需更加注意內涵式發展。成就目標是以阿特金森的成就動機理論為基礎,在德維克(Dweck)能力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學習動機理論,是指成就行為的目的在認知(如對于情景的認識、成敗歸因)、情感(如焦慮)和行為(如學習策略、任務選擇和學業)等特征上的穩定趨向。[1]早期的研究者對成就目標進行了二分法和三分法結構分類,埃利奧特(Elliot)和賓特里奇(Pintrich)在邏輯推論和實證研究基礎上,形成了“掌握—成績”與“接近—回避”2×2的對稱結構。這一理論一經提出,就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在該理論的指導下,學者們已經開展了數量可觀的應用研究,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有關成就目標定向的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仍將是學者們積極關注的焦點話題,也將持續激發教育界與心理學界研究者的興趣與靈感,其研究對象也會逐漸延伸至不同背景的學生群體。新近一項實證研究進一步表明,大學生的成就目標與其創新精神關系密切,對成就目標的了解和評估有利于對其創新精神的培養。[2]本研究擬對民辦高校大學生群體的成就目標的實際水平進行系統考察,從而為大學生成就目標水平的整體提升提供參考。
二、研究工具和數據
(一)經驗數據
本研究的經驗數據來源于中部某省民辦高校的在讀本科生。J 信息學院屬于我國十大獨立學院之一,始終堅持以“完整的人”為培養目標,遵循“內涵建設、特色發展”的八字方針。本次研究數據來自2106 名本科生。其人口統計學特征如下:從性別分布來看,其中,男生為242 名,約占總數的11.5%,女生為1864 名,占總數的88.2%;從年級分布來看,本科一年級為953 名,占45.1%,本科二年級為599 名,占28.3%,本科三年級為328 名,占15.5%,本科四年級為226名,占10.7%;從擔任學生干部與否來看,學生干部為606 名,占總數的28.7%,非學生干部為1500 名,占總數的71.0%;從生源地來看,城市學生為481 名,占總數的22.8%,縣城學生497名,占總數的23.5%,鄉鎮學生167 名,占總數的7.9%,農村學生961 名,占總數的45.5%。
(二)研究工具及信效度檢驗
關于成就目標的測評工具來源于陳會昌譯著《人格心理學(第六版)》,[3]包括掌握—趨近目標、掌握—回避目標、成績—趨近目標和成績—回避目標四個維度,共12 個指標項目,每個維度各對應三個指標,每個指標按七分制計分,最低分計為1,最高分計為7。經內部一致性檢驗,整個量表的同質信度α 系數為0.904,四個維度的信度系數在0.706 至0.843 之間。遠高于0.7,顯示量表信度頗佳。[4]
三、研究結果
(一)本科生成就目標處于中等水平
樣本校本科生成就目標水平總體得分均值為4.85,高于理論中值4,標準差為0.95,高成就目標的學生占樣本總數的45.8%,還有20%學生的成就目標均值低于理論中值,目標水平明顯偏低。通過進一步分析發現,不同成就目標水平的學生,其學業成績明顯不同。那些成就目標越高的學生,其學業成績明顯越高,而成就目標越低的學生其學業成績也明顯偏低,該發現與其他研究的結果相一致,成就目標可以顯著預測學業成績。[5]總體看來,樣本校本科生成就目標總體水平一般,尚有較大提升空間。
(二)擔任干部的學生掌握趨近和成績趨近目標均值高于普通學生
高校學生干部作為大學生中的骨干力量,既是普通的受教育者,也是特殊的學生管理者和服務者,對于促進高校有效治理、濃厚校園文化氛圍、提升人才培養質量具有重要的作用。[6]因此,本研究從成就目標定向視角分析高校學生干部與普通學生之間的差異,具有較高的實踐價值。經過獨立樣本T 檢驗發現,本科生是否擔任學生干部的成就目標定向的得分均值差異具有顯著性(T=-2.173,P<0.05),擔任、不擔任學生干部的學生在掌握趨近目標(T=-2.704,P<0.01)和成績趨近目標(T=-4.066,P<0.001)兩個維度得分上均有顯著性差異,擔任學生干部的學生水平均顯著高于未擔任干部學生,在掌握回避目標和成績回避目標兩個維度得分的差異性不顯著(P>0.05)。數據表明,擔任干部的學生中有50.17%的學生具有高目標,而未擔任干部的學生中只有44%的學生目標較高,也就意味著不擔任干部的學生目標較低,距離高目標仍有較大的改善空間。無論是掌握趨近目標還是成績趨近目標,擔任干部的學生目標均值都較高。樣本中有65.6%的學生干部“其目標是獲取比大多數同學好的成績”,多數學生表示“即使很累,也會盡力去完成學習任務”,在學生干部身上發揮著很明顯的榜樣示范作用,帶著教師和普通學生的特別期待,學生干部具備高自信心和高成就動機,面對不同的教學環境和教學內容可以及時適應,因挫折感和失敗感而帶來的困擾也會進行自我調整,所以相較于不擔任干部的學生,學生干部無論是成績還是能力的趨近目標都較強。
(三)城市學生在掌握趨近和成績趨近目標的得分上均高于農村學生
有研究已經表明,不同生源地的大學生在人格特征、學習能力、就業取向及消費行為等方面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差異。[7]本研究主要分析來自不同生源地的本科生成就目標的類型和差異性。結果表明,成就目標定向在城鄉間存在顯著差異(F=3.181,P<0.05),主要集中于掌握—趨近目標(F=2.858,P<0.05)和成績—趨近目標(F=6.028,P<0.001)兩個維度,均呈現出城市學生高于農村學生的態勢。
在本研究低成就目標學生群體中,城市學生占22.78%,農村占比46.71%,無論是掌握趨近目標、成績趨近目標還是成就目標總值,生源地距離城市越近的學生目標均值越高。數據顯示,70.1%的農村學生即使覺得累,也依然會堅持完成學習任務,但會盡量逃避展現自己,對自己未來的目標定位也較為謹慎甚或模糊。75.5%的城市學生學習目標很明確,無論是能力還是學業成績都力爭上游,面對出現的失敗,會及時調整自己的學習策略,重新設置新的目標并為之努力,學習動機一直處于較高水平,不會陷入太多的自責和消極情緒中。
四、對策與建議
(一)強化本科生目標意識
高校校園環境為大學生提供的是多維文化氛圍,讓大學生有了更廣闊的發展可能性,校園環境中存在的文化交織、傳統與現代觀念的碰撞、集體要求與個性追求的差異,會使部分大學生產生自我定位上的迷惑與矛盾性。進入民辦高校的本科生對未來的職業地位和自身價值實現也存在迷茫和困惑。因此,民辦本科院校應有意識地培養大學生的學習目標,幫助學生做出清晰而準確的目標規劃,堅定成為合格而又優秀人才的信念,這在民辦教育中顯得尤為重要。對于本科生而言,在校期間要不斷完成學業任務和提升專業技能,不僅要設置近期內的目標,還要為未來的職業或升學選擇做出安排,學習什么內容的知識和技能,什么時間學習,學習的進度區間是怎么樣的等一系列的短期和長期目標,這些目標需要教師更多經驗和技巧的輔助,才能使得本科生可以更準確和更有效率地設置和實現。
(二)鼓勵更多學生形成掌握目標
以往研究表明,相較于相對功利主義的成績目標,具備掌握目標的個體更關注學習的過程,力求掌握新知識并提高自己能力,更有利于學生的身心發展。[8]因此,學校應重視引導更多本科生形成掌握目標,通過有效的教育干預以鼓勵學生積極選擇并參與到如大學生創業大賽、校園風采大賽等活動中,借此幫助本科生嘗試領會參與這些活動的意義,并理解其中所涉及的專業知識和掌握它所促進的專業技能,使學生專業素質、職業觀念、社會適應性等方面都形成特殊優勢,同時,喚起學生參與教育活動可以充實并增強自我的意識。此外,教師要多給予表揚性、鼓勵性評價,調整部分學生的回避型心態,逐漸樹立他們對自我能力的認同感和自信心。
(三)加強對學生的課下指導
良好的師生互動與生生互動,對于學生社交技能與學術能力的提升具有關鍵作用。提高本科生的成就目標水平,不僅需要教師在課堂上的積極指引,還需發揮教師在課下的引導作用。今后要加強教師對學生的課后學業指導和師生互動交流,充分滿足學生的不同學業需求,為學生解決疑難問題提供動力支持。建議學校建立健全師生溝通機制,將師生互動頻率納入教師考核范圍。另一方面,輔導員應該重視學生的立志教育和同輩群體的影響力。民辦高校的輔導員通過組織開展班級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積極引導學生不斷追求更高的理想目標,樹立遠大理想并確立堅定理想信念。在高目標指引下,學生才能不畏懼失敗和挫折,積極投入到學業中。同輩群體作為本科生在校期間最為主要的人際關系因素,充分發揮同輩群體中團結合作精神和同伴榜樣示范作用,依賴于群體的積極影響克服消極影響。
(四)增加學生干部經歷
本研究發現,學生干部兼備掌握趨近目標和成績趨近目標,會對學習動機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已有相關研究表明,擔任學生干部是一種教育過程,可以對學生的學業表現與某些能力產生積極影響。同時,也是高校踐行“立德樹人”教育根本任務的重要途徑。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高校中的學生干部往往是由少部分優秀的學生擔任,干部的積極影響促進學生的成績、能力與素質等方面繼續提升,“馬太效應”使非干部學生群體處于較弱勢的位置。因此,要建立多元化的干部任職機制,多為學生提供主動展現與提升自我的機會。總而言之,通過干部經歷的增加,可以促進本科生更加注重培養自身的能力,學生整體的心理素質和專業素質也能得到強化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