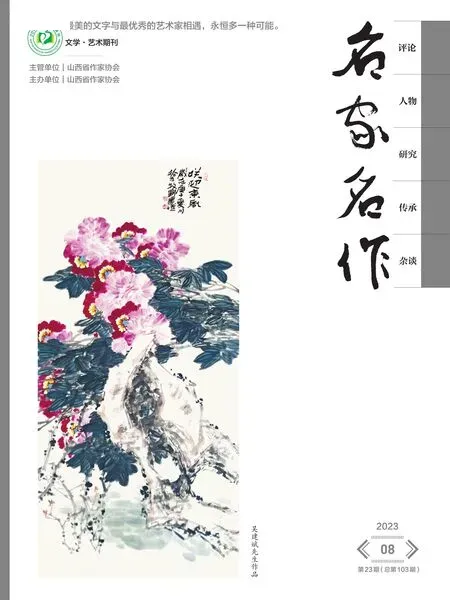后現代性與民族性的融通:國產動畫電影的娛樂化表達
潘廣宇
一、國產動畫電影的后現代性與民族性
弗朗索瓦·利奧塔認為“后現代即是對元敘事的懷疑”[1],后現代哲學的主要任務是告別統一的強迫觀念;闡釋有效的多元結構,并弄清多元性狀態的內在問題。后現代最顯著的特點是拼貼,即形象復制后的拼接、拼湊與任意組合形成了后現代主義的內在文本。隨著媒介文化的發展,后現代文化也呈現出商品化的表象,文化與市場不斷相連,并成為人們日常消費的一部分,這也消解了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的界限,使文化的商品價值得以實現。
后現代主義藝術遵循的是消費社會的文化邏輯,即藝術成為商品的文化邏輯,它看重瞬間感官的快感和震撼效果,這就與動畫電影本身的多元性、虛擬性、游戲性等特征不謀而合。
自動畫傳入中國,就帶著深刻的民族印記,從《鐵扇公主》到《長安三萬里》等作品,民族性一直貫穿國產動畫電影的發生與發展。動畫的民族性是指通過動畫作品展現本民族獨特的藝術形式和本民族獨有的氣韻與精神 。[2]中國早期動畫作品的民族性以形式探索為主,有水墨動畫、木偶動畫、皮影動畫等多種藝術形式,并產生具有獨特審美趣味的“中國動畫學派”。但隨著大眾審美心理的變遷以及外來文化的影響,部分創作者片面地認為古裝、歷史故事就是民族性的全部體現,不能與時俱進地發展民族性的創作風格,甚至一味地模仿美國、日本等國家的創作風格,使國產動畫創作落后于時代。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民族性是一個需要不斷被“他者化”和“時代化”的過程。“他者化”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之間的跨文化交流愈發頻繁,各種社會思潮與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矛盾,我們不能封閉或是一味模仿。在“他者”的影響下,要有選擇地借鑒優秀的文化元素,堅定民族性的主導地位;另外,傳統文化并不是一味地對歷史經驗進行積累,而是一種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選擇,需要經過“時代化”的檢驗。由此,過去的優秀傳統文化是民族性的必要體現,當下也可以產生未來可能繼承的“文化傳統”。
二、視覺元素的規訓傳承與非主流呈現
福柯認為現代社會是一所監獄,所有人都在接受“規訓”,現代社會中的個體行為、思想、訴求、身份認同等各方面的結果并不能完全自主,而是在各種微觀的權力系統中產生出來的。規訓的目的是“把他們保持在理想的能見狀態中,用監視體制包圍他們,將他們注冊登記,在他們之中構建一套累積、集中化的權力知識”[3]。而傳統文化符號的借用實際上是對大眾審美的一種“規訓”。
重意境是民族性中最顯著的特點,中國古代繪畫講究“詩畫合一”和留白,重視意境的刻畫,讓人回味無窮。《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山河社稷圖,畫中世界的天地山水如夢如幻,影片利用大量的遠景勾勒環境,使角色置身于合理的敘事空間,并使用留白的方式引人想象,讓特定的角色形象與藝術趣味相得益彰。
除了重意境呈現,傳統的民族符號也頻頻出現在國產動畫電影的創作中,《西游記之大圣歸來》中的反面角色“混沌”取自《山海經》,在未被孫悟空擊碎面具前,其形象是奇丑無比、臉色慘白的具象妖怪,創作者將傳統京劇中代表陰險奸詐的白色臉譜的文化符號融入角色塑造中,讓觀眾可以清晰地分辨人物定位。此外,很多傳統紋飾也都在國產動畫電影中有所體現。如《西游記之再世妖王》中的妖怪“元蒂”是完全虛構的,外觀造型上增加了三星堆青銅器上的饕餮紋,讓整體形象更顯兇悍。
無論是重視意境的審美習慣,還是對京劇臉譜、傳統紋飾等文化符號的借用,這些都來源于民族的文化積淀,奠定了影片民族性的基調。這無疑是民族基因的一種延續,當傳統文化影像符號再次出現在熒幕時,它會喚醒國民共同的情感記憶。與此同時,動畫創作者并非單純地沿襲傳統經驗,而是打破傳統二元對立的人物塑造方式,創作“非主流”的動畫角色。“主流”與“非主流”之間并無明確的邏輯分界。當“主流”與正面宣揚傳統社會價值觀念、大眾認可流行且產生重要長遠的社會影響等特點結合在一起時,“非主流”的特點就變得顯而易現:大膽挑戰即有社會傳統與規范,以此彰顯個性化。[4]
一方面是國產動畫電影中角色整體的反差性。《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的呈現一改以往作品中抽龍筋、扒龍皮而后割肉還父再重生的悲情人物形象,而是變成了帶著痞氣的頑劣少年,渴望被認可和關注。在小說《封神演義》中的申公豹與姜子牙為敵,而電影《姜子牙》中的申公豹被塑造成重情重義、憨厚老實,具有無私奉獻精神且甘愿犧牲自己的英雄形象,與傳統申公豹的形象形成鮮明的對比。
另一方面是國產動畫電影中角色的“審丑”特點。以《熊出沒》系列動畫電影為例。光頭強作為破壞環境伐木的反面角色,但其形象設計并沒有采用傳統認知中兇狠殘暴的符號表意。創作者將光頭強塑造成頭像倭瓜、眼珠突出、鼻子紅腫、有兩撇八字胡、四肢瘦小滑稽的男青年。這樣的設計使光頭強看起來又丑又萌,加入了喜劇效果,也讓很多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產生一種“生活不易”的情感共鳴,使其成為具有商業價值的經典反面角色。這類角色的設計并沒有完全遵循傳統的主流創作方式,惡人全部是線條刻板、身材肥胖、面目猙獰,正派則是長相俊美、身材高挑,而是采用“非主流”的策略,使觀眾有更豐富的審美體驗,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為我們呈現了角色塑造的更多可能。
三、傳統思想的解構與新倫理秩序的召喚
解構主義認為,經典思想主張走出“真理”體系的禁錮,其核心在于打破既有的、傳統的、固化的秩序,是一種反二元對立、反權威、去中心化的思維方式。結合德里達關于解構的論述,我們可以將“真理”理解為一種道統或秩序。“要解構一組對立就是要表明它原本不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是一種建構,是由依賴于這種對立的話語制造出來的,并且還要表明它是一種存在于一部解構作品之中的結構,而這種解構作品正是要設法把結構拆開,并對它進行再描述——這并不是要毀滅它,而是賦予它一個不同的結構和作用。”[5]而動畫電影作為一種后現代藝術,是解構傳統文化的最好方式。
以白蛇的民間傳說為例,白蛇傳說的故事主題一直以來存在爭議,如報恩說、愛情說、勸道說等,我國著名劇作家田漢編寫的《金缽記》中呈現了經典的“游湖、結親、酒變、盜草、上山、水斗、斷橋、合缽”等完整情節,此后的影視創作也都基于此展開。而電影《白蛇:緣起》的創作者將視角聚焦在前世,重視“緣起”的挖掘,“緣起”發生在阿宣的少年時光,阿宣正處于一種自由與秩序的典型博弈階段,他在一次次擺脫“人妖殊途”和“宿命論”的束縛中蛻變,與傳統文本中的許仙形象大相徑庭。
“后現代的創造既尊重無序又尊重有序,過度的有序和過度的無序都是與真正的創造格格不入的。”[6]這樣的顛覆性改編打造了更廣闊的想象空間,也反映了現代語境中社會階層矛盾、社會偏見的問題。這是對傳統文化精神內核的重構,凸顯了話語的時代性,符合觀眾的心理期待。中國神話故事和傳統文藝作品注重教化功能,“大陸電影傾向詩言志,以人文深度見勝”[7],動畫電影亦如此。一直以來,國產動畫電影都承擔著教育的作用,其在題材選擇與主題呈現上也重視民族美好品德的挖掘,傳達民族正向的思想、精神與觀念。
2023 年上映的《長安三萬里》在票房與口碑上均取得成功,并貫徹了“文以載道”的傳統思想,影片以唐代詩人高適的視角切入,來講述他與李白之間追求理想并不斷成長的故事。詩詞與動畫的融合喚醒了大眾蘊藏于內心深處的理想主義,并傳遞著樂觀主義精神。
近年來,國產動畫電影在創作過程中遵循著天人合一,追求和諧統一的理念,更注重挖掘人物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中的心緒和情感,強調故事背后的精神傳達。無論是《風雨咒》中犧牲自我化身妖獸的母親;還是《西游記之大圣歸來》中樂觀自由的江流兒;或是《大魚海棠》中湫的為愛奉獻……這些影片的創作都沿襲了儒、道文化影響下形成的民族心理,釋放出勤勞勇敢、樂觀向上、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等一系列民族美德,國產動畫電影對于民族母題的發揚也契合主流話語的時代需要。
四、他者沖擊下國產動畫電影的自我建構
“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現,可看見還是不可看見,可感知還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稱為他者。”[8]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國家、民族、價值觀的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超越自我文化的限制,影響著大眾的審美傾向。
《新神榜:哪吒重生》顯示了多種文化雜糅的拼貼表達,結合漫畫、嘻哈文化、朋克藝術等風格的藝術形式。各種文化的元素拼貼雜糅,不但毫無違和感,而且突出了畫面的視覺刺激與新鮮感,共同構建出嶄新的藝術美感。《十萬個冷笑話2》中戲仿的橋段層出不窮。凡人小金剛拿到創世神杖后心中的邪惡被無限放大,變成了邪惡的怪物,怪物的形象則致敬經典動畫《魁拔》中蠻吉脈獸的形象。《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管家與《哪吒鬧海》中的管家形象完全一致。這樣的拼貼與戲仿,都表達出傳統中難以表達的主題。人物被賦予大眾流行文化的審美傾向,用來諷刺或者表達新的思考,給視聽語言帶來更多可能性的同時也娛樂了大眾。
我們在借鑒西方藝術創作方法的同時也經受著挑戰,實際上,中國動畫的主體性更多地要從民族性出發,只有具備民族風格的作品才具備生命力。一方面,中國動畫創作應堅決摒棄庸俗主義民族化,堅持形式的多元化、創意化,在“他者”的影響下堅守民族性的主體位置。《大魚海棠》為我們打造了唯美的愛情故事,故事脫胎于《山海經》和《莊子》,卻運用了全新的視角,整部作品通過人族與神族少女之間的愛情、生死完成了對“天”神性的解構,面對“天”的壓迫,個體開始反抗并取得成效,以人本主義的關懷呼喚理性與道義。
另一方面著眼于現實生活可以為國產動畫電影添加更多活力。《昨日青空》將目光放在高中校園,講述了高考前夕高三學生的成長故事,雖然在形式上借鑒了日式的創作風格,但青少年題材符合時代特征,也是國產動畫電影的一次勇敢嘗試。而《雄獅少年》則是一部完全帶有民族風格的現實主義動畫電影,以中國傳統民間習俗——舞獅為切口,電影敘事包含留守兒童、個人成長、友情、親情等多個方面,影片中對于嶺南景觀的描繪也讓人身臨其境。2023 年上映的《深海》關注抑郁癥和重組家庭的社會問題,通過對主人公“參宿”一次奇遇的描繪,呼喚人們對友情、親情的珍視。這些影片有意識地希望擺脫“低齡化”的審美傾向,是一種勇敢的嘗試。
一直以來,中國傳統文學作品、民間故事等都是國產動畫電影重要的選題來源,建立民族審美主體也離不開對傳統文化的追問與挖掘。在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也應當放眼當下,民族性本位并不僅僅是對傳統形式的繼承,我們需要從中提取文化的內涵,讓更多人產生共鳴,以形成具有教育意義的道德力量,滿足觀眾對審美情懷的價值訴求。
五、國產動畫電影泛娛樂化傾向的得失
國產動畫電影在創作過程中融入后現代性特點,構建對異世界時空的展現、異世界故事的敘述和異世界秩序的幻想,可以滿足受眾對于充滿想象力的藝術作品的藝術欣賞和文化消費。文化的雜糅以及對傳統文本的解構、重構,可以使國產動畫電影跳脫出經典作品的桎梏,通過形象的迭代、關系的重塑以及旨趣的再造言說當代精神。與此同時,國產動畫電影的塑造也保持著對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對古典美學的繼承,使近年來國產動畫電影的民族性得以清晰地展現。中國傳統美學是當代國產動畫電影藝術的根基與靈魂所在,是其持續蓬勃發展的內在驅動力。但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并不單純是外在形式的繼承,更重要的是內涵與文化內核的繼承,過度的解構與改編是否還能代表傳統文化是我們必須要解答的問題。
動畫電影的創作往往表達了人們對現實的展現,以及對未來生活的展望。近年來,我國動畫電影的民族特性在對于民族文化和對生命價值的關照中多在呈現;在對當下的思考與對人的關注中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受眾的想象。但我們也不難發現過度追求動畫電影的商業化、娛樂化和奇觀化,有時會忽視動畫電影體現民族精神的功能與作用。因此,國產動畫電影的發展不應只追求娛樂和商業利益,在國產動畫電影主體性建構的過程中,可以添加多元化的文化元素,但不應當為了追求商業利益、迎合大眾而過度狂歡,摒棄對傳統美學的創新求索,否則會使國產動畫電影喪失民族文化的深厚根基和可持續發展的動力,進而淪落為面向低齡兒童的單純娛樂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