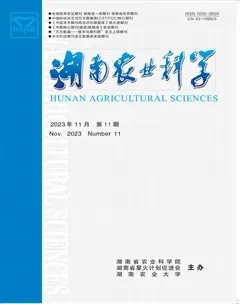不同種植模式對水稻生長發育與產量品質的影響
李恩宇,陳光輝,方希林,莫 旭,肖海強
(1.湖南農業大學農學院,湖南 長沙 410128;2.攸縣農業農村局,湖南 攸縣 412300)
長江流域是我國雙季稻的主產區,也是我國冬油菜的主產區,油菜種植面積和產量約占全國的85%[1]。在農村勞動力逐漸減少、雙季稻種植積極性不足的情況下,稻—油種植模式已成為農民節本增效的有效途徑,是南方稻田最常見的種植模式之一。同時,隨著國家馬鈴薯主糧化戰略的制定,馬鈴薯的種植面積正在不斷的增大,對糧食作物的結構調整產生了重大影響[2],稻—薯種植模式在逐步推廣,創造的經濟效益也在穩步提升。在不同種植模式下,前茬作物對土壤養分、理化性質等方面的影響是深遠且復雜的,直接影響后茬水稻的生長發育和產量品質[3-4]。研究設置稻—油、稻—薯、稻—冬閑這3種種植模式的大田試驗,比較不同模式下水稻生長發育與稻米品質的差異,探明種植模式對水稻生長發育、產量與米質的影響,以期為稻田種植制度選擇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地點及材料
試驗地點位于瀏陽市沿溪鎮湖南農業大學教學科研綜合基地,該區域屬于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土壤pH 值6.41,土壤有機質24.42 g/kg,全氮1.04 g/kg,全磷1.018 g/kg,全鉀8.39 g/kg,堿解氮101.15 mg/kg,有效磷60.41 mg/kg,速效鉀114.98 mg/kg。試驗水稻品種為隆兩優1377,油菜品種為湘雜油518,馬鈴薯品種為費烏瑞它。
1.2 試驗方法
采用田間小區試驗,隨機區組設計,3 種種植模式分別為稻—馬鈴薯(RP)、稻—油(RR)、稻—冬閑(RF)。對試驗田進行多次翻耕,盡量把土混勻,田間整平后分小區種植,每個處理3 次重復,試驗從2020 年開始連續進行2 a,小區處理不變,面積約200 m2,小區間做高、寬約40 cm 的田埂,并覆膜保證不透水透肥,確保各小區的基礎地力一致,且互不影響。水稻株行距為18 cm×25 cm,于5 月上旬播種;油菜用種量為4.5 kg/hm2,于10 月中旬播種;馬鈴薯用種量為2 250 kg/hm2,于12 月下旬播種,栽培措施均按照一般大田統一管理,馬鈴薯和油菜秸稈還田,水稻秸稈不還田, 2 a 水稻季的田間水分管理基本保持一致。
1.3 測定項目與方法
1.3.1 葉綠素相對含量 利用手持葉綠素SPAD 儀在水稻各關鍵生育時期(分蘗期、拔節期、孕穗期、灌漿中期、成熟期)測量水稻倒1、倒2、倒3 葉片,取平均值,每種模式隨機測10 株。
1.3.2 葉面積指數(LAI) 葉面積(cm2)=葉長×葉寬×0.75,葉面積指數(LAI)=每株綠葉面積×每公頃株數×10-8。
1.3.3 株 高 隨機選10 株,從水稻基部開始測量。
1.3.4 干物質積累 隨機選取10 株水稻植株分為莖、葉、穗3 個部分,殺青后,烘干至恒重,然后稱重。
1.3.5 產量及產量構成 按有效穗平均值取5 株進行室內考種,采取五點取樣法,連續取水稻50 株,脫粒后并稱重,計算平均每株實測重量,實際產量(t/hm2)=每公頃株數×平均每株實測重量。
1.3.6 稻米品質 水稻收獲后儲存3 個月再測量碾米品質、蒸煮品質、外觀品質。碾米品質:精選飽滿的稻谷100 g,用礱谷機測定出糙率,糙米率=(糙米重量/稻谷試樣重量)×100%;取20 g 新鮮糙米2份,用精米機碾出精米,精米率=(精米重量/糙米重量)×糙米率×100%,2 次測定結果誤差不超過1%。外觀品質:利用谷物外觀掃描儀(萬深SC-E)測定稻米長、寬、堊白粒率、堊白度、整精米率、透明度。蒸煮品質:膠稠度采用米膠延伸法,糊化溫度采用堿消值法,直鏈淀粉采用碘藍比色法測定。
1.4 數據處理
利用Excel 軟件進行試驗數據統計和處理,SPSS 軟件進行數據顯著性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種植模式對水稻葉片SPAD 值的影響
由表1 可知,不同種植模式下水稻孕穗期、灌漿中期和成熟期葉片SPAD 值差異顯著,2020 年和2021 年孕穗期均表現為RP >RR >RF;2020 年灌漿中期表現為RP 顯著大于RR 和RF,成熟期RF顯著小于RR 和RP;2021 年孕穗期、成熟期和灌漿中期均表現為RP >RR >RF,各處理差異均達顯著水平,而分蘗期、拔節期處理間差異均不顯著。隨著水稻生育時期的后移,各處理水稻葉片的SPAD值均表現為分蘗期到孕穗期下降、到灌漿中期上升、到成熟期再下降的趨勢。

表1 不同種植模式下水稻各生育時期的SPAD 值
2.2 不同種植模式對水稻株高的影響
由表2 可知,株高在前期增長較快,灌漿中期到成熟期稍有降低,這是因為前期養分主要供給營養生長,構建壯苗,以便為后期生殖生長打下堅實的基礎,后期水稻灌漿后,籽粒變重,植株有所彎曲。2020 年和2021 年,分蘗期RP 和RR 處理的株高顯著高于RF 處理,其他各生育時期不同種植模式下水稻株高的差異均不顯著,說明不同種植模式對水稻株高的影響不顯著。
2.3 不同種植模式對水稻葉面積指數的影響
由表3 可知,隨著水稻生育時期的推進,LAI呈先增后減的變化趨勢,在孕穗期達到最高。2020年拔節期,RP 顯著低于RR,RF 與其他2 種模式差異不顯著;2020 年和2021 年成熟期,RP 顯著低于RF,RR 與其他2 種模式無顯著差異;2 a 間3 種模式的LAI 在分蘗期和灌漿中期均無顯著差異。與2020 年相比,2021 年3 種模式的LAI 在孕穗期均有所增加,但差異并不顯著。

表3 不同種植模式下水稻各生育時期的葉面積指數(LAI)
2.4 不同種植模式對水稻地上部干物質積累的影響
由圖1 和圖2 可知,葉片干物質積累上,2020年孕穗期、2020 年和2021 年的灌漿中期均無顯著差異;分蘗期和拔節期,RP 均低于RR 和RF;從孕穗期開始,RP 葉片干物質積累最高;成熟期,2020 年RP 顯著大于RR,與RF 無顯著差異,2021年RP 顯著大于RF,但與RR 無顯著差異。

圖1 2020 年不同種植模式下水稻各生育時期干物質積累

圖2 2021 年不同種植模式下水稻各生育時期干物質積累
莖鞘干物質積累上,2020 和2021 年分蘗期、拔節期和孕穗期3 種模式均無顯著差異;灌漿中期,RP 高于RR 和RF;成熟期,2020 年各處理無顯著差異,但2021 年RP 顯著大于RF,與RR 無顯著差異。
穗部干物質積累上,2020 年灌漿中期3 種模式均無顯著差異,但以RP 最高,而2021 年灌漿中期RP 顯著高于RF,與RR 無顯著差異;2020 和2021年成熟期,RF 顯著低于RP 和RR。
總干物質積累上,連續 2 a 分蘗期均以RF 最高,其中2020 年與RP 有顯著差異;拔節期2020 年RR顯著高于RP,2021 年3 種模式無顯著差異;2020和2021 年孕穗期3 種種植模式均無顯著差異,但以RP 最高;連續2 a 灌漿中期均以RP 最高,其中2021 年顯著大于RR 和RF;連續2 a 成熟期均以RP最高,其中2021 年RP 和RR 顯著高于RF。水稻生育前期,地上部干物質積累RP 積累得較慢,但從孕穗期開始RP 地上部干物質積累逐漸高于RR 和RF。
2.5 不同種植模式對水稻產量的影響
由表4 可知,2020 和2021 年實測產量均表現為RP >RR >RF,每穗實粒數均表現為RF 顯著少于RP 和RR;千粒重在2020 年無顯著差異,但2021 年RP 顯著大于RF,與RR 無顯著差異;有效穗數在2020 年無顯著差異,2021 年RF 顯著少于RP 和RR;2020 和2021 年各處理結實率均無顯著差異。與2020 年相比,2021 年RP 和RR 處理均有增產,但RF 處理的產量有所降低。

表4 不同種植模式下水稻的產量及產量構成
2.6 不同種植模式對水稻米質的影響
由表5 可知,不同種植模式下稻米的碾米品質有所差異;其中,各處理的糙米率均在79.5%左右,差異不顯著;2021 年,RP 的精米率顯著高于RR 和RF,2020 年各處理的精米率雖無顯著差異,但以RP 較高;2020 和2021 年,稻米的整精米率均是RP顯著高于RR 和RF,碎米率均是RP 顯著低于RR和RF。

表5 不同種植模式下稻米的碾米品質 (%)
由表6 可知,不同種植模式下的稻米外觀品質也有一定差異;其中,整精米長和整精米寬并無顯著差異,但RP 的整精米長/寬均大于RR 和RF;2020 和2021 年,堊白粒率由低到高均表現為RR <RP <RF,其中2020 年RR 與RP、RF 差異顯著,2021 年3 種種植模式的差異均達顯著水平;2020 和2021 年,各處理堊白度均表現為RF 顯著高于RP 和RR;3 種種植模式下稻米的透明度均為2。

表6 不同種植模式下稻米的外觀品質
由表7 可知,不同種植模式下稻米的蒸煮品質也有一定差異;其中,2020 年RF 處理的稻米直鏈淀粉含量顯著高于RP 和RR 處理,膠稠度則相反;而2021 年RF 處理的直鏈淀粉含量顯著高于RP 和RR 處理,3 種種植模式間差異均達顯著水平,3 種種植模式的膠稠度表現為RP >RR >RF,差異均達顯著水平;2 a 間各種植模式下稻米的堿消值無顯著差異。

表7 不同種植模式下稻米的蒸煮品質
3 結論與討論
水稻葉片的SPAD 值是反映葉片葉綠素含量的重要指標,并且與光照和氮素密切相關[5-6]。有研究發現,冬季種植馬鈴薯,后茬水稻在灌漿后期水稻葉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降低幅度和丙二醛(MDA)含量增加幅度較慢,有助于延緩葉片的衰老,同時可增強光合作用和干物質積累,從而有效提高稻米品質[7]。有研究發現,稻—薯和稻—油均能顯著增加水稻產量,提高田間土壤養分的供應能力[8-9]。在該研究中,不同種植模式對水稻葉片的SPAD 值存在一定的影響,雖然在生育前期差異不顯著,但在孕穗期3 種種植模式存在顯著差異,而生育后期(灌漿中期與成熟期)均以稻—馬鈴薯模式的葉片SPAD 值最高,說明其葉片衰老較慢,能保持較高的光能利用率,光合作用積累轉運的干物質多,同時在水稻生育后期,稻—馬鈴薯模式的總干物質積累量以及穗部積累量是最高的,且均大于稻—冬閑模式,因此稻—馬鈴薯模式的千粒重較重,每穗實粒數較多,最終產量最高,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
有研究表明,不同的種植模式對稻米品質存在較大的影響。湯文光等[10]研究表明,稻—稻—薯、稻—稻—油、稻—稻—麥模式下稻米的品質均比稻—稻—冬閑模式下的好,具體表現在增加了水稻的糙米率、整精米率,降低了堊白度和堊白粒率。龔克成等[11]發現,稻—油能夠提高稻米的整精米率,降低直連淀粉含量。而也有研究表明,不同種植模式對水稻的外觀品質無顯著影響,但蒸煮品質和營養品質差異顯著[12]。這可能是水稻的品種和前茬作物的不同,兩者之間相互影響程度不同造成的。該研究中,稻—馬鈴薯模式下稻米的整精米率顯著高于稻—油模式和稻—冬閑模式,而稻—冬閑模式與稻—油模式之間碾米品質無顯著差異。這可能是因為前茬種植馬鈴薯土壤積累的養分較高,氮磷肥的增加能夠提高稻米的碾米品質。外觀品質中長寬比以稻—馬鈴薯模式最大,則該模式下的稻米顯得更長,稻—冬閑模式的堊白度和堊白粒率顯著高于稻—油模式和稻—馬鈴薯模式,說明前茬種植油菜和馬鈴薯能夠改善稻米外觀品質。稻—馬鈴薯模式的直鏈淀粉含量最低,膠稠度最高,而稻—油模式直鏈淀粉含量也顯著低于稻—冬閑模式,但3 種種植模式下稻米的堿消值無顯著差異,表明不同種植模式對稻米的蒸煮品質也存在一定的影響。綜合來看,稻—油模式和稻—馬鈴薯模式能夠不同程度地改善稻米品質,這可能是受水旱輪作的影響,病蟲害減少,土壤養分和物理特性得到改善,從而提高了稻米品質,而稻—馬鈴薯模式和稻—油模式之間的差異,是由于前茬栽培作物不同,導致栽培措施、田間土壤養分、秸稈還田成分等方面的差異,從而對水稻產生的影響不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