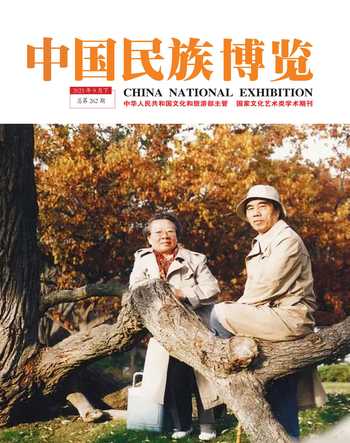魯迅小說建構的文學世界
李玉軍
【摘 要】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之一,其文學作品在五四時期影響深遠,而且在20世紀文學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于我國的思想啟蒙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創作的作品揭露了當時社會在的弊病,給當時的人們敲響了警鐘。《彷徨》作品的出現對當時社會的批判具有跨時代性,其中文字和人物的刻畫引發了人們的思考,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的發展意義深遠,也標志著現代小說進一步走向了成熟。時至今日,魯迅作品的文字與思想藝術對文學創作及創作研究仍有裨益。
【關鍵詞】魯迅小說;文學世界;小說賞析
【中圖分類號】I2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3)18—005—03
魯迅創作的作品思想深刻、題材多樣、人物形象典型,一直以來都是人們廣泛研究的文學對象。他創作的作品大都具有明顯時代特征,尤其是對作品人物的刻畫,性格特征鮮明,時代性強,淋漓盡致地展現了當時社會的生活景象。同時,作為杰出的語言大師,魯迅創作的作品創造了很多流傳至今的經典修辭表達方式,不同修辭手法的運用塑造了不同的作品風格。在《彷徨》中便運用了較多的細節描寫,對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題的揭示與情感的表達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他對生活觀察細微,刻畫的形象真實,這些都表現出了其卓越的文學才能,為后世留下了極為珍貴的藝術作品資源,豐富了現代文學的藝術寶庫。
一、《彷徨》的主要作品與創作背景
《彷徨》是現代著名的文學家魯迅創作的短篇小說集,共收有《長明燈》《祝福》《示眾》《在酒樓上》《肥皂》《傷逝》《高老夫子》《弟兄》《幸福的家庭》《孤獨者》《離婚》11篇小說。[1]其中,主要以《祝福》《示眾》《在酒樓上》《孤獨者》為經典小說代表。
《彷徨》是魯迅于五四運動后的新文化陣營分化時期創作,描繪了自辛亥時期到五四運動時期的真實社會生活,揭露了當時社會上存在的種種深層次矛盾,真切地表達了對民族生存的憂患與社會變革的渴望。《彷徨》展現了魯迅在這一革命探索的征途上心境,展露了當時自己的苦悶。同時,表達了自己堅決反對封建主義的不妥協精神。
二、語言的修辭手法
(一)摹狀
《彷徨》中的摹狀通常會隨著句子的語序產生變化。例如,在《祝福》中關于情態的有“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夾著煙靄和忙碌的氣色”。[2]“夾著煙靄和忙碌的氣色”本是定語應放置于“雪花”前,但考慮到如果定語過長會影響句子的和諧,以及為了打造更為逼真的背景環境,所以便調整了原本的句子結構。再如,在摹寫劇中人物四銘的舉止神態中,寫道:“他眉頭一皺,擎向窗口……”作者用簡練的語言刻畫了人物的形與神,側寫人物的內心與思想精神面貌。
(二)借代
《在酒樓上》的對話交談中有這么一句,“你教的是‘子日詩云么……你以為教的是‘ABCD么?”這里的“子曰詩云”是指舊儒學,而“ABCD”則是指英語,代表了新文化、新思潮。聯系該作品的寫作背景不難想到,這句話實則意指保守與激進、落后與先進的時代符號。兩處借代“辭約而旨豐”。[3]此外,還有《弟兄》中“小畜生”“悶葫蘆”等形象描繪,代指文中人物,突出刻畫了相應語境中人物的外貌形象。
(三)反復
反復主要是為了突出表達重點,以強化語義來抒發強烈的情感。在《彷徨》作品集中最常見的主要是間隔性反復。
1.突出重點,刻畫人物
在《祝福》中,有這么兩段重復文字的描寫,“頭上扎著白頭繩,烏裙……臉色青黃,但兩頰卻還是紅的。”“她仍然頭上扎著白頭繩,烏裙……臉色青黃,只是兩頰上已經消失了血色……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4]這里描寫的是祥林嫂第一次和第二次到四叔家做工的形象,相同的衣著打扮,但精神狀態卻完全不同。通過同一外在的反復描寫與人物精神狀態改變的鮮明對比,刻畫了艱難的現實生活對人物帶來的精神打擊。
在《在酒樓上》一段呂緯甫的自述中也出現反復手法的運用,如“無聊”便出現了六次,其他與“無聊”詞義相近的詞“隨隨便便”“敷敷衍衍”出現了四次,生動地刻畫了一個遭受挫折后自我頹廢的消極知識分子形象。
2.抒發情感,諷刺批判
在《傷逝》涓生的末尾獨白中,魯迅先生曾三次用到“新的生路”一詞。一方面,涓生作為一個正面人物,作者卻在描寫該人物時反復用到“新的生路”這一詞,表達了一個新青年強烈的熱情、上進心與勇氣。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矛盾體,涓生口號喊得越是響亮,越表達出了他內心的迷茫、脆弱與不負責任,“新的生路”一詞也隱含了為自己的不負責任和失敗尋找了一個高尚的借口,側面表達了魯迅先生的揶揄與反諷。在《長明燈》中也都有相應的體現。
三、人物形象的細節塑造
魯迅先生在刻畫小說人物時,語言文字的運用時常會讓讀者有一種文中人物或文中人物生活在自己身邊的感覺,讓讀者覺得自己并非是一個旁觀者,所以更容易引發讀者的自我反省。在《彷徨》中他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社會人物形象,這些人物代表正面卻難逃悲劇的現實生活,讓人同情。通過對這些人物的塑造,揭露了當時社會的時局情態。例如,在《祝福》中對魯四老爺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魯迅先生雖然對該人物著墨不多,但憑借著極少的語言,形象地塑造了一個冷酷、頑固的封建地主階級的形象。半幅對聯中魯四老爺幾次寫道:“祥林嫂被劫走……可惡,然而婆婆劫回……合理……”真實地再現了滿腹封建禮學,內心卻極其冷酷與無情的偽道士形象。
此外,在《祝福》中還成功塑造了祥林嫂這一善良、純潔的勞動女性形象,但同時也是受封建禮教殘害最嚴重,命運最慘的典型人物。里面這么一段人物形象塑造的文字描寫,“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木刻似的;一手提著竹籃……一手拄著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下端開了裂。”[5]這段運用了白描的藝術手法,語言簡練、質樸,內涵豐富,揭露了祥林嫂悲慘的命運。從祥林嫂臉上消盡的悲哀神色,再到比人還高的竹竿,且下端還開了裂,為人們展現了一個受封建禮教殘害的麻木的形象。一個“裂”字的細節刻畫,更是生動、傳神地為人們展現了一個身體佝僂,掙扎在死亡邊緣的乞討形象。這些臉部面色、神色、不趁手的開裂竹竿細節的描寫,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躍然紙上。這些在他的《肥皂》《高老夫子》《離婚》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描寫中都有體現。
四、語言的藝術性
在《彷徨》的小說作品中,魯迅先生擅長運用文字的描寫烘托環境,渲染氣氛,增添作品的社會生活氣息,藝術手法別具一格。通常在冷漠的情感表達下隱藏有熾熱的感情,在熱烈的情緒表達中又襯托有清冷,寓熱于冷又寓冷于熱,作品語言充滿了藝術性。例如,在《祝福》的一段文字中,就描寫到了過年外面傳來的炮竹聲音和火藥的味道及其火光,整個過年氛圍十分熱鬧,但在這樣熱鬧的場面中,祥林嫂卻一個人孤苦伶仃地站在寒風中乞討。一群人熱鬧的煙火和歡笑聲和一個人頂著寒風街邊乞討的對比,愈發凸顯了祥林嫂的孤獨。《在酒樓上》也有類似的描寫,如“鉛灰色的天,白皚皚的無精打采……微雪又飛舞起來了……”這段句子的描寫為呂緯甫出場的狀態埋下了伏筆。[6]文中呂緯甫遭遇困境,心中滿是苦悶,于是他開始沉淪,借酒澆愁,這段句子的描寫為人物的營造了悲涼沉郁的氛圍。再如,在《孤獨者》中,通過對渲染“靜”凸顯了魏連朵這一人物的孤獨,制造了無聲勝似有聲的藝術效果。在《傷逝》中通過對子君買狗時的萬般喜愛,再到子君離開后狗被扔掉又自己跑回來的描寫,用名叫“阿隨”的狗將歡樂與悲涼連接起來,引人感慨與深思,物是人非。魯迅先生通過對環境的文字描寫,表現了不同作品人物的心理活動,營造了一種真實、直穿人心的情感藝術效果。同樣,在《弟兄》的語句描寫中也都有體現。
五、鮮明的寫作風格
(一)人物變形中展露藝術真實性
在《傷逝》和《孤獨者》中,有這么兩段描寫:涓生“將真實深深藏在心……用說謊和遺忘做向導”;魏連曼死后,“他在不妥貼的衣冠中……合了眼,閉著嘴……冷笑著這可笑的死尸”,這些反映了當時社會環境壓力使得人物產生了扭曲的表現。通過變了形的人物形象的描寫,暗諷了當時社會的情形。
(二)簡練木刻畫般的文字風格
在《祝福》中,魯迅先生對于祥林嫂形象刻畫的文字描寫中寫道:“五年前的花白頭發,即今已經全白……只那眼珠間或一輪……表示他是一個活物。”語句質樸簡練,但筆筆都盡顯滄桑,字字刻畫入骨,讓人不由得為祥林嫂的遭遇與苦難感到痛心。此外,在《彷徨》作品集中,也有些回環與反復的簡練句子,極具凝定的韻律感。例如,在《傷逝》中有這么一段句子的描寫:“依然是這樣的破窗……這樣的窗前方桌……這樣的靠壁板床。”[7]雖然句式重復單調,實則是作者有意安排,展露了小說中人物凄愴的情感,文字風格頗具藝術美感。
(三)充滿著悲涼的現實感
魯迅先生的《彷徨》作品集中,寫作風格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和時代主義精神,極富“悲涼”的氛圍。這其中包括其小說人物形象的塑造,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命運的苦難以及凄慘的結局,都無一不烘托出了悲涼的氛圍,揭露了當時社會黑暗與落后的一面。尤其是在魯迅先生在運用文字描寫小說人物心理的流程時,底層人物被現實的壓迫的無力感油然而生,盡顯悲涼。
六、黑、白色文字的運用與主體情感的映射
魯迅作為現代白話小說的先驅人物,其在作品創作時有意將文體與文言語體劃分開,十分反感文言文中抽象、晦澀等文字弊病。所以,在他創作的《彷徨》小說集中,呈現了與以往小說完全不同的文字面貌,習慣以簡練的白話作為敘事語言。具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簡潔且有力的白描修辭手法的運用。在《彷徨》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刻畫方面,魯迅先生大都以白描手法塑造了性格鮮明的人物,這些人物特征的塑造與情節的連接,讓讀者可以對人物有一個更為直觀的感受,最經典的就是《祝福》里祥林嫂這一人物的塑造。另一方面是黑白色彩的運用。在魯迅先生的小說中,人物、環境等色彩運用較為豐富,但是強烈的黑白色對比卻是魯迅先生最常用和鐘愛的,這也使得其《彷徨》頗具樸素的韻味。
黑、白色的文字的描繪也側面描繪了主體的情感。黑色代表了勞動人民的苦難,暗含了作者的同情;白色代表了當時社會的被批判者,具有辛辣的反諷與揶揄意味。在魯迅先生創作的《彷徨》作品中,黑白兩色時常交織,營造了特定的氛圍,暗示了故事的發展,增添了小說的藝術魅力。在描繪具體的人物時,文字通常言簡意賅,但卻力透紙背。例如,魯迅先生作品《孤獨者》中的刻畫的孤獨的魏連殳等較為典型的“黑色”人物,從小說人物的描寫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其外在形象還是內在氣質,都透露著一種孤獨、叛逆、堅毅的反抗精神,是“精神界的戰士”。關于“白色”主要出現在場景的描繪與人物刻畫方面,例如,在《祝福》中頭扎“白頭繩”祥林嫂形象的刻畫,以及《示眾》中身穿“白色背心”的囚犯暴露在看客的目光下,描繪了“被看”的經典場景。[8]此外,在《彷徨》小說集中還有很多關于人物面色、須發等“白色”的描寫,或批判或憎惡,與之前黑色人物的描寫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些都映射了作者強烈的主觀情感色彩。
七、結語
《彷徨》是魯迅作品中一部藝術技巧精湛和思想內涵深刻的短篇小說集。在這部作品中的賞析中可以看出魯迅極強的社會觀察力與文學功底,感受到他對社會及國民的關切、對人性黑暗面的討伐。作品運用簡練的語言文字及修辭手法真實地刻畫了當時社會不同階層人物的形象,用諷刺、悲劇等寫作手法展露了人性的矛盾與扭曲,引發人們對當時社會現象的思考。同時,引導人們要保持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推動社會走向進步和發展。
參考文獻:
[1]劉玉鳳.悲劇性文化的藝術分析——探究魯迅《吶喊》與《彷徨》[J].文藝生活(下旬刊),2021(5).
[2]武子惠.魯迅小說《彷徨》中的修辭藝術[J].長江叢刊,2019(1).
[3]趙潔.“現代性”視閾下魯迅的靈魂書寫——以《吶喊》《彷徨》為例[J].名作欣賞, 2019(27).
[4]張童.論魯迅小說中的色彩意象——以《吶喊》《彷徨》《故事新編》為例[J].安徽文學(下半月),2018(6).
[5]朱文莉, 關樂樂.社會認知視角下《吶喊》《彷徨》中的人物命名藝術探究[J].新絲路:中旬,2023(2).
[6]范水平,曾巍.論魯迅小說敘事藝術的嬗變[J].宜春學院學報,2022(11).
[7]張佳瀅.“燈下漫筆”:《吶喊》《彷徨》中的“燈”意象研究[J].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22(3).
[8]王曉俠.以《吶喊》《彷徨》為例分析魯迅作品中的人物[J].江西電力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