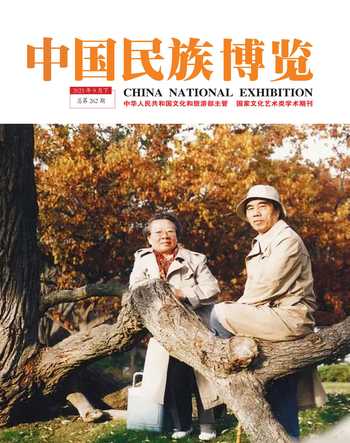瞻仰“邊界”:論當代音樂的藝術(shù)價值取向之迷思

【摘 要】“當代音樂”本身作為一個“進行中”的概念,其被預(yù)設(shè)的“邊界”往往是用以被“突破”而非用以“設(shè)限”的。本文選取兩種在當下具有代表性的藝術(shù)價值取向視野,即“中國敘事”與“人類世”的聲音圖景予以批評闡釋,并在此基礎(chǔ)上討論其“非普遍主義”的可能性追求。
【關(guān)鍵詞】當代音樂;價值取向;藝術(shù)邊界
【中圖分類號】J6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3)18—181—03
當代音樂藝術(shù)的邊界是一個復(fù)雜而多樣化的議題,它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個時代的藝術(shù)價值取向,并進一步影響音樂創(chuàng)作、音樂研究與相關(guān)衍生的音樂行為。有鑒于此,本文將從當代音樂的藝術(shù)邊界出發(fā):什么是當代音樂?可以為“當代音樂藝術(shù)”設(shè)界嗎?“邊界”對當代音樂藝術(shù)的作用何在?并進一步討論試圖打破這一“邊界”過程中的幾種音樂創(chuàng)作價值取向與可能性追求。
一、可以為“當代音樂”設(shè)界嗎?
“當代音樂”本身作為一個“進行中”的概念,即“當代”本身的“所指”就是作為一種隨時間流變而自然演進的過程,它將受到文化傳承、科學(xué)技術(shù)、社會影響、傳播媒介與個體創(chuàng)造力的影響,以各種樣態(tài)突破自身原有的設(shè)限。這讓“當代藝術(shù)”成為一個充滿創(chuàng)新與探索的領(lǐng)域。有鑒于此,若要為“當代音樂”設(shè)界,這一行為本身也同樣將充滿爭議:支持者認為“設(shè)立邊界”將有助于理論家更清晰地定義與理解當代音樂,而反對者則會認為由于當代藝術(shù)的自由與開放性,難以實現(xiàn)客觀而全面的邊界劃分,并將限制藝術(shù)自有的創(chuàng)造力。
上述爭議再次凸顯了“當代音樂”概念界定的復(fù)雜性,那么“當代藝術(shù)”或者“當代音樂”的邊界究竟在哪里?不妨以當代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主體(作曲家身份)對該問題予以轉(zhuǎn)化討論。當代音樂的作曲家在追求藝術(shù)價值取向之時,存在著這樣一種追求“獨創(chuàng)性”的主流共識,如賈國平教授所言:“因為所有的歷史經(jīng)驗都不能支持我們往下走……文化符號是一個有指向的標識,個人身份和個體的標識——既不重復(fù)歷史,又不重復(fù)當代他人的經(jīng)驗,創(chuàng)造屬于自我的經(jīng)驗。也將是音樂歷史由當下延續(xù)至未來的必然選擇”,換而言之,這一價值觀好比作為“當代人”創(chuàng)造屬于自己的音樂,則稱為“當代音樂”,這意味著他們對當代藝術(shù)的價值取向,事實上建立在創(chuàng)造個性“烙印”的基礎(chǔ)上,由個及彼、從微至著、以小見大,從而影響社會成為時代印記。
從這個意義上推論,所謂的預(yù)設(shè)“邊界”似乎往往用以“突破”而不是用以“設(shè)限”的。“邊界”雖然是一個中性詞,詞義被釋讀為“范圍”或“界限”,但隱約著“框定一個東西”的意蘊,例如“邊界感”一詞暗示著:“不要跑出這個范圍,不要侵犯他人”。但“當代藝術(shù)的邊界”在主體的自我解構(gòu)下,這樣的“邊界”已轉(zhuǎn)換成為一個自我“突破”的契機。因此,邊界可以被視為一個機會,音樂家可在其中挑戰(zhàn)和突破傳統(tǒng),以便開發(fā)新的創(chuàng)作。這種突破有助于推動當代音樂的發(fā)展,并將其引向新領(lǐng)域。
盡管如此,仍不可忽視“邊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邊界”的兩側(cè)劃分著“現(xiàn)有”與“未知”:邊界一側(cè)的“現(xiàn)有”領(lǐng)域是已被創(chuàng)造、可被認識、會被聽到的范疇,邊界的另一側(cè)的“未知”領(lǐng)域是未被創(chuàng)造、有待認識、可能會被聽到的范疇。當站在“現(xiàn)有域”,滿懷憧憬地“瞻仰”著邊界盡頭,凝視著另一側(cè)的“未知域”:作曲家是拓荒者、演繹家是開墾者、理論家是探索者……他們滿懷熱情,亦飽含迷思:另一側(cè)究竟有怎樣的聲音?這將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問詢,并將踏入“上下求索”的征途。
二、視野一:“中國敘事”的藝術(shù)價值取向
在尋找突破“邊界”的方法上,追求自身的音樂語言“中國化”是現(xiàn)當代我國作曲家一個主流的藝術(shù)價值取向,這同樣是作曲家群體尋找身份認同的體現(xiàn),選擇以“國別”作為宏觀的身份標識,并以此作為探索“微觀”音樂個性表達語匯的基石,通過選擇具有中國特色(古代、傳統(tǒng)、民族)的符號材料與文化密碼作為敘事元素,具體方式體現(xiàn)在尋找使用民族樂器、古曲音調(diào)、歷史故事等,以此跨越邊界探索“未知域”。
從理論家的視角,學(xué)界對中國當代音樂所反映出“民族主義”傾向的論斷也持一種多元的立場: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中國性”研究是國內(nèi)學(xué)界的基本共識;國際中,如《東亞當代音樂》主編吳熙淑(Hee Sook Oh)的觀點:“20世紀東亞的作曲家承擔(dān)了民族或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個人身份與國家或亞洲代表性之間的銜接是關(guān)鍵所在”,這即是一種對當代音樂中“民族性”價值取向的肯定。但國際上也不乏一些商榷的聲音,例如,德國漢學(xué)家芭芭拉·米特勒(Barbara Mittler)曾撰文《反對民族風(fēng)格:中國新音樂中的個人主義與國際主義》,并作出如下的論述:
聽眾不應(yīng)將中國音樂視為一種外來音樂或“他者”,而其本身在國際舞臺上就存有權(quán)利,并應(yīng)將其視為獨立于中國民族傳統(tǒng)之外的重要音樂。……中國音樂的“中國性”(中國特色)不應(yīng)被視為一種自然特征,而應(yīng)被視為個人選擇和發(fā)展的問題。所有中國作曲家都在創(chuàng)作自己的音樂(無論是否中國化),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不僅僅只是一種傳統(tǒng)。
這一論述反映了理論研究者在觀照創(chuàng)作現(xiàn)狀時,并不認同將“中國音樂”視為一種外來物,而應(yīng)當獨立平等地身處當代音樂的語境之中,因為在“中國新音樂”并不只是復(fù)述傳統(tǒng),對傳統(tǒng)的借鑒體現(xiàn)出的仍是當下的創(chuàng)作,但這并不應(yīng)該重新歸屬到某個民族文化中。此外,有更激進的觀點認為本世紀的嚴肅音樂正在遠離與單一種文化和民族的聯(lián)系,如沃爾夫?qū)?韋爾施(Wolfgang Welsch)提出了超越文化內(nèi)涵和邊界的“跨文化性”概念,認為“文化在人類社會本身是同質(zhì)的,而單一種的文化在全球時代不再有效,所有的文化都是混合、融合、混雜和不斷繼續(xù)變化中的”。這些從理論出發(fā),對于“中國敘事”作為藝術(shù)價值取向的合理性的異見,雖然有其合理性,但主要從對文化的認識與概念纏繞出發(fā),并不涉及實踐層面。
另一種可能商榷的弊端在于,盡管“中國性”與“藝術(shù)性”從理論上并不呈現(xiàn)對立的關(guān)系,然而在現(xiàn)實反映中卻又有容易造成之處,由于扎堆追尋“中國化”,在靈性不足的創(chuàng)作者的加工下,會體現(xiàn)為塑造藝術(shù)“刻奇”,使命題“喪失藝術(shù)底色”,并陷入文化認同的陷阱。就藝術(shù)價值取向而言,需明確“中國敘事”可作為一種“破界”手段,而非最終的目的與追求。另外,從作曲技術(shù)的“求新”,即對新音響、新技法的孜孜追求亦然,只是手段,絕非目的本身。
因此,當代音樂的藝術(shù)價值取向不應(yīng)只是復(fù)述歷史、加工歷史,更需探索“未來感”的聲音。盡管如克羅奇(Benedetto Croce)在《歷史學(xué)的理論和實際》中做出的著名論斷“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但當歷史作為“歷史”,其仍然會被后人賦予“雕塑化”的對待,即靜態(tài)的、需膜拜的。“藝術(shù)”可以作為藝術(shù)的藝術(shù),也不能只是藝術(shù)的藝術(shù),如當其被賦予社會價值,無論是如阿多諾(Theodor Adorno)所稱的作為“促進者”或是“反題”,它更需具與時俱進:當代的藝術(shù)能不能喚醒同時代的“感覺”,能不能喚醒時代的心聲?在當今社會一味模仿古代文人雅士的傷春悲秋,無論在技術(shù)上多么卓然,也存在一些虛偽性,如化用阿多諾式的犀利批判“好似精致的皮影戲”,或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評勃拉姆斯的用詞“資產(chǎn)階級的會客廳”,是相對缺乏能夠使當代人產(chǎn)生“共情”的,也可成為稍加反思為何“當代音樂”總是很難被欣賞的源頭。
三、視野二:“人類世”的聲音圖景
在跨越“邊界”作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目標下,在探索“未知域”的過程中,有許多當下迫切需要、并值得思考的話題,無論是文化命題到生態(tài)環(huán)境,從人類命運到寰宇蒼穹,藝術(shù)家仍有孜孜不倦的發(fā)聲余地。這些同樣也可以,并且已經(jīng)成為當代藝術(shù)價值取向的追求方向。
諾貝爾化學(xué)獎得主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在2000年首次提出地球已經(jīng)進入到“人類世”(Anthropocene)的紀元,盡管這一地質(zhì)概念尚未被正式認可,但已有許多地質(zhì)學(xué)家的關(guān)注與承認,并且已廣泛影響到生態(tài)美學(xué)與音樂藝術(shù)等領(lǐng)域。著名作曲家約翰·L·亞當斯(John Luther Adams)曾在《在“人類世”創(chuàng)作音樂:藝術(shù)家應(yīng)如何應(yīng)對生態(tài)危機時代?》一文中指出:我們必須思考“音樂究竟能否在與時事打交道的同時又與之分離?音樂能否與我們周圍的世界產(chǎn)生共鳴,同時又能創(chuàng)造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因為“音樂是具有激發(fā)人類意識、文化革新的力量”,并且要能實現(xiàn)這一目標所需的仍需要專注在“藝術(shù)本身”,這既提醒了在面臨生態(tài)環(huán)境巨變下,音樂家所肩負的責(zé)任與能力,能通過音樂聲音圖景喚起人類與世界的關(guān)系,從而采取行動幫助人們通過實踐改變世界。他的管弦樂作品《成為海洋》(Become Ocean)正是在人類世命題的思考下寫就,通過表達對存在的廣闊、深邃和神秘的潮汐的冥想,也希望喚起人們對隨著極地冰層融化和海平面上升,我們?nèi)祟惏l(fā)現(xiàn)自己面臨著可能再次成為海洋的前景的警惕。
在我國現(xiàn)當代音樂作品中,也存在與生態(tài)美學(xué)相關(guān)的藝術(shù)實踐,用藝術(shù)創(chuàng)作回應(yīng)人類世的時代呼喚,成為關(guān)注“人類世”聲音圖景的中國構(gòu)成。如著名作曲家譚盾的《地圖》取材于湘西張家界,而《水樂》的靈感源于鳳凰古城的沱江,這也體現(xiàn)了藝術(shù)家創(chuàng)建“人類世”聲音圖景的愿望,呈現(xiàn)出一種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學(xué)觀,使得音樂作品超越純粹藝術(shù)領(lǐng)域。
然而,這一藝術(shù)價值取向中,仍然存有諸多反思之處:因為藝術(shù)能刻畫現(xiàn)實、反映現(xiàn)實,卻不能直接觸及現(xiàn)實問題,藝術(shù)是否有足夠的感染力來促進行動,進而實現(xiàn)所規(guī)劃的理念?當代音樂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者是否足夠直接地回應(yīng)當代社會的挑戰(zhàn)?音樂作品是否能夠更深刻地觸及當下人們的關(guān)切和需求?這無疑值得更多的思考。
四、結(jié)語
當代藝術(shù)的價值取向到底需要什么?我們無法用普遍主義來討論它,正如無法用普遍主義來界定當代的音樂藝術(shù)邊界一樣,因為“一切普遍主義都包含著自身無法消化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潛能”,當代人無法替自己給出判斷、更無法預(yù)見未來趨勢,也只有通過不斷的嘗試與自我“批判”在曲折中前行:需要敬佩的是打破“邊界”的嘗試、對目的不明、安于現(xiàn)狀的鞭策,甚至是批判“過分越界”的聲音,正如恩斯特·布洛赫重構(gòu)并創(chuàng)造性闡發(fā)了馬克思的“自由王國”時的論斷:“最好的東西就是招致議論者”,正如邊界正矗立著被人們瞻仰,有待于被拓寬、有待于被破界。
參考文獻:
[1]Son,Mingyeong.Negating Nationalist Frameworks: Aesthetics of Unsuk Chins Musical Individualism in Twenty-First-Century East Asian Composition[J].Asian Music,2022(1).
[2]Mittler,Barbara.Against National S t y l e : I n d i v i d u a l i s m a n d Internationalism in New Chinese Music[A].In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at the 2003 Chinese Composers Festival[C].2008.
[3]汪行福.論馬克思的普遍主義[J].復(fù)旦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9(2).
作者簡介:陳蕓萱(1999—),女,上海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音樂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