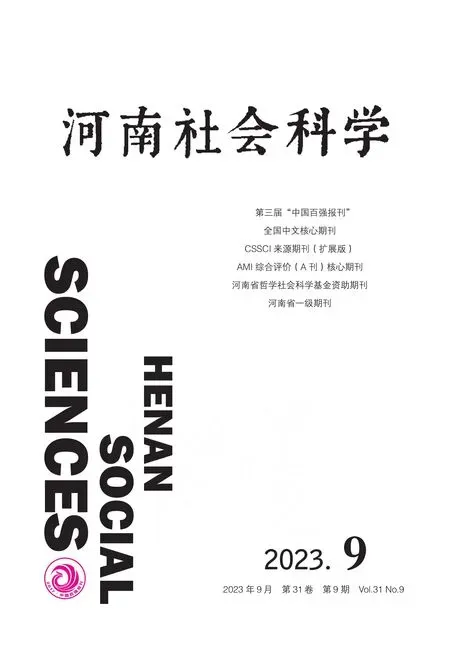伏羲敘事與中原學(xué)國家話語表達(dá)
尹全海
(信陽師范大學(xué) 炎黃學(xué)研究院,河南 信陽 465400)
2019 年2 月,《河南社會科學(xué)》開設(shè)《中原學(xué)研究》專欄,主持人李庚香把中原學(xué)學(xué)脈溯源至“肇始于伏羲的易學(xué)”。依靠歷史研究追尋與遠(yuǎn)古時代的直接聯(lián)系、完成中原學(xué)溯源是困難的;因?yàn)闅v史越向前看材料就越少,歷史記憶也越發(fā)模糊。為建立遠(yuǎn)古與當(dāng)下的聯(lián)系,1785 年,61 歲的康德建議:“在歷史敘述過程中,為了彌補(bǔ)文獻(xiàn)不足而插入各種臆測,是完全可以允許的;因?yàn)樽鳛檫h(yuǎn)因的前奏與作為影響的后果,對我們之發(fā)掘中間的環(huán)節(jié)可以提供一條相當(dāng)可靠的線索,使歷史的過渡得以為人理解。”不過,康德也承認(rèn),單憑臆測建立起來的歷史,“不能叫作臆測的歷史,只能看作單純的虛構(gòu)”[1]。看來,康德的建議有虛構(gòu)歷史的風(fēng)險。而歷史人類學(xué)研究,運(yùn)用文獻(xiàn)解讀與田野調(diào)查相結(jié)合的方法,既研究過去的建構(gòu)如何用來解釋現(xiàn)在,也研究過去是如何在現(xiàn)在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以至把過去和他們身處的現(xiàn)在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引發(fā)兼具歷史感與“現(xiàn)場感”的學(xué)術(shù)思考[2],則有可能為我們重新發(fā)現(xiàn)遠(yuǎn)古敘事的當(dāng)代價值提供一個思考方向。
一、伏羲敘事及其話語表達(dá)
伏羲是我國上古神話傳說中的人物,被尊為中華民族人文始祖。有關(guān)伏羲事跡的記載,最早見于《周易·系辭下》“伏羲作八卦”一事。《管子》《莊子》《尸子》等先秦文獻(xiàn)亦記有涉及伏羲的零星信息。成書于戰(zhàn)國末期的《世本》記載“伏羲制以儷皮嫁娶之禮”“包犧氏作瑟作琴”等,更為后世文獻(xiàn)廣為引用。自皇甫謐《帝王世紀(jì)》出,文獻(xiàn)所見有關(guān)伏羲事跡逐漸增加,但在古籍文獻(xiàn)中,《周易》《世本》《帝王世紀(jì)》仍是記載伏羲事跡的原初文獻(xiàn),晚出或后出者多為延伸性文獻(xiàn)。若除去上述文獻(xiàn)重復(fù)內(nèi)容,結(jié)合田野調(diào)查所得伏羲女媧遺跡及各種神話異文,我們大致可以整理出一個以地方性故事表達(dá)普遍性話題的伏羲敘事。
(1)伏羲女媧系中原神話傳說人物。文獻(xiàn)記載伏羲事跡所見地名,多在中原。如“燧人之世,有大人跡出于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犧于成紀(jì),蛇身人首,有圣德,都于陳”,“太昊帝庖犧氏,風(fēng)姓也,蛇身人首,有圣德,都陳”(《尚書正義》)[3]2-3,或“天皇伏羲都陳留”(《路史·后紀(jì)》)[3]2。雷澤,今河南濮陽范縣濮城;陳,今河南周口市淮陽區(qū)。盡管也有將雷澤注釋為今山東菏澤鄄城、將成紀(jì)注釋為今甘肅天水者,但甘肅省天水市和河南省周口市淮陽區(qū)“太昊伏羲祭典”,均于2006 年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民俗類,編號X-37)。
與此同時,中原大地上的伏羲、女媧遺存,如新密的伏羲山、女媧廟,淮陽、西華、項(xiàng)城、沈丘等地的伏羲女媧廟,南陽等地漢代畫像石中的伏羲、女媧交尾畫像等,不僅有跡可循,還有名有姓。女媧補(bǔ)天、摶土造人,洪水之后兄妹成婚等遠(yuǎn)古神話,流傳于正陽是“胡玉人與胡玉姐”的故事,流傳于桐柏是“盤古兄妹”的故事,流傳于淮陽則是人祖爺爺與人祖奶奶“捏土人”的故事,更似發(fā)生在隔壁鄰村的往事,真實(shí)而親切。商丘“兩兄妹”中的“混天老祖”和“混地老祖”,就是《莊子》中的“倏與忽”、《淮南子》中的“陰陽二神”[4]12。如此千姿百態(tài)的中原符號、美麗動人的中原故事,共同表達(dá)的則是盤古開天創(chuàng)世,洪水過后兄妹成婚,關(guān)乎人類起源的普遍性話題。
(2)伏羲女媧是中華民族“英雄祖先”。文獻(xiàn)記載伏羲事跡所見神名,如“太皞帝庖犧氏,風(fēng)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大人跡出于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犧于成紀(jì)。蛇身人首,有圣德,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太皞”[3]2;“太昊帝庖犧氏,風(fēng)姓也,蛇身人首,有圣德,都于陳”,“包羲亦號天皇”(《路史·后紀(jì)》)[3]2。文獻(xiàn)所記伏羲號曰天皇、太皞(昊)帝、百王先三種神名,按照孔子的解釋,“功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以至尊定神名,寓意伏羲是中華民族的英雄祖先、文化英雄和創(chuàng)始英雄,關(guān)乎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起源。
另據(jù)文獻(xiàn)記載,“華胥生男為伏羲,生女為女媧;伏羲鱗身,女媧蛇軀”,“女媧氏,亦風(fēng)姓也,承皰犧制度亦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為女皇。其末有諸侯共工氏,任知刑以強(qiáng),伯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次,故《易》不載。及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混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之號”(《禮記正義》《初學(xué)記》)[3]3。按皇甫謐的解釋,女媧承庖犧制度,雖為皇而不自為一代,與伏羲合稱羲皇。如今淮陽太昊伏羲陵稱“羲皇故都”,每年農(nóng)歷二月二至三月三舉行的“羲皇故都朝祖會”,蓋源于此。
(3)伏羲女媧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斯文鼻祖”。文獻(xiàn)記載所見伏羲的文化創(chuàng)造,如“庖犧作八卦,神農(nóng)重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申之,分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yuǎn)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jié)繩而為網(wǎng)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周易正義》)[3]3;“伏羲制以儷皮之禮”,“伏羲作琴”,“包犧氏作瑟”(《世本·作篇》)等[3]63。其中摶土造人、定姓氏、制嫁娶等,都是由伏羲女媧兩人共同完成的。文獻(xiàn)所記之伏羲、女媧創(chuàng)世尊神,民間神話中的兩兄妹,主人公都是一對青年的血緣配偶,他們共同肩負(fù)的是“開辟創(chuàng)世”和“再造人類”之重任。
據(jù)此可知,伏羲時代,應(yīng)該是伏羲、女媧時代,伏羲、女媧與神農(nóng)、燧人合稱“三皇”。對應(yīng)于中國新石器時代前期之裴李崗文化,距今9000—7000年;伏羲、女媧的文化創(chuàng)造活動,處于漁獵時代,早于炎黃農(nóng)耕時代。伏羲文化,應(yīng)該是伏羲、女媧文化,或羲皇文化,包括“開天辟地”“兄妹婚姻”“摶土造人”神話,在中原地區(qū)表現(xiàn)為三種神話的相互融合[4]15。因此,伏羲、女媧是早于炎黃時代,并與炎黃二帝并稱為中華民族的斯文鼻祖[5]。
據(jù)此,我們把伏羲敘事的普遍意義及當(dāng)代價值,理解為一種話語表達(dá)。其本質(zhì)是以隨處可見、親切可愛的地方性知識表達(dá)普遍性話語。伏羲敘事,對同樣以中原地方性知識為研究對象的中原學(xué)而言,或可作為表達(dá)國家話語及學(xué)科定位的思考方向。
二、中原及中華文明的全息承載地
中原一詞,有多重含義。作為地域中原,有廣義、狹義之別;在中國古代,中原還有“中國”“中華”“中州”“中夏”“中土”等稱謂[6]18,指的是文化中原或政治中原,也就是中原的文化含義或政治含義。中原學(xué)之中原,所要表達(dá)的學(xué)術(shù)話語,顯然是文化中原或政治中原;“天下之中”是最為準(zhǔn)確的概括。而“天下之中”,是指“普天之下”之地位,不是“東西南北”之方位。
關(guān)于中原的方位意義及其與中國、天下的關(guān)系,2016年4至6月,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學(xué)部委員劉慶柱先生,在與鄭州大學(xué)師生討論考古學(xué)與中原歷史文化時,認(rèn)為中原歷史文化,既是一門學(xué)科,又是一個大課題。至于中原文化,他認(rèn)為既是區(qū)域文化,又不是嚴(yán)格意義上的區(qū)域文化,因?yàn)闅v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代設(shè)置的區(qū)域叫中原,比如河南的簡稱為“豫”,山東的簡稱為“魯”,但沒有哪個地方叫“中”或者“中原”的。“中”是個方位,但把它具體化則是沒有“中”的。因此“中”既是東西南北中的集合體,又什么都不是;中原文化的關(guān)鍵是“中”,而“中”是相對于東西南北中整合在一起的[7]1-2。所以,中原的具體化呈現(xiàn)為地域中原,是具體方位;中原的抽象化則是文化中原或政治中原,可指代所有方位。
在中原學(xué)的話語體系中,中原的含義是指文化中原或政治中原,而不是地域中原。比如,2023年6月2 日,習(xí)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發(fā)表重要講話時指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具有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征[8];習(xí)近平總書記概括的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征,在中原地區(qū)都能找到具體、鮮活的“標(biāo)本物”。如連續(xù)性特征的河南例證、創(chuàng)新性特征的河南動力、統(tǒng)一性特征的河南標(biāo)志、包容性特征的河南現(xiàn)象、和平性特征的河南基因[9]。因此,如同劉慶柱所論“‘中’既是東西南北中的集合體,又什么都不是”一樣,在中國,除了中原,沒有一個地域空間能夠全息承載中華文明的所有特征。以中原歷史文化為其核心構(gòu)成和立學(xué)之本的中原學(xué),以中原文化為研究的中心內(nèi)容,以中原為研究對象,但植根其中的中原文化,尤其是中原歷史文化,絕不是一般的區(qū)域文化,而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根基和主干,是中華文化的根脈文化、主流文化、正統(tǒng)文化。源遠(yuǎn)流長的中華文化主要發(fā)祥于中原大地,中原地區(qū)由此成為中華歷史文化孕育、繁榮和發(fā)展的沃土[10]。中原學(xué)的研究目標(biāo)及價值追求,當(dāng)然也不能局限于地域中原。
目前所見,中原學(xué)關(guān)于“中原”的多重含義,如地域中原、文化中原或政治中原等,都有使用。中原學(xué)提出之初,突出的是地域中原,如2016 年李庚香正式提出“中原學(xué)”概念時說,本文提出的“中原學(xué)”主要從狹義上的中原(即河南)立論,因?yàn)橹挥泻幽先常M在中原文化圈的包圍中,河南最有資格代表中原和中原文化,同時輻射廣義上的中原地區(qū)。建設(shè)中原學(xué)學(xué)科,“意在整合各學(xué)科中的中原文化研究力量,引導(dǎo)中原文化研究方向,將多學(xué)科方法集中于中原文化的重大理論與現(xiàn)實(shí)問題研究中,從而拓展中原文化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構(gòu)建中原學(xué)“對于振興河南文化、重塑河南形象、提煉中原文化精神、引領(lǐng)河南經(jīng)濟(jì)社會建設(shè)具有重要意義”[11]。上述內(nèi)容,顯然是在地域中原范圍內(nèi)作狹義和廣義性界定。《中原學(xué)概論》的作者已經(jīng)開始思考并使用中原的文化含義,如在對中原學(xué)進(jìn)行學(xué)科界定時指出:“在中國,‘中原’是最高的,也是最大的地域、區(qū)域概念。”“中原文化既是一種地域文化、區(qū)域文化,又是中華文明演進(jìn)的重要源頭,具有地域文化、區(qū)域文化和國家文化、民族文化的復(fù)雜定位。”把中原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與國家文化、民族文化聯(lián)系在一起,已經(jīng)超出地域中原的含義。
中原學(xué)之中原,所要表達(dá)的學(xué)術(shù)話語是開放的,當(dāng)然不應(yīng)該局限于地域中原[12]。在文化或政治層面,中原不僅僅是最高、最大的區(qū)域概念,而且是維護(hù)中華文明5000 多年來從未中斷的核心政治理念。如1963年陜西寶雞出土的西周初年青銅器“何尊”銘文“宅茲中或”之“中”,即“天下之中”之“中”。《史記·周本紀(jì)》記載武王滅商后,在新都城選址時的對話:“成王在豐,使召公復(fù)營洛邑。周公復(fù)卜甚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這意味著國都就是國家的中心。《詩經(jīng)·大雅》還記有“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史記集解》解釋說“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把“京師”與“中國”對等起來。“中原”之“中”,即是在國家的地位,其文化意義和政治意義非同一般。中原學(xué)之中原,應(yīng)在中原地方性知識敘述的基礎(chǔ)上,提煉為國家層面的話語表達(dá)。考古學(xué)家劉慶柱就從國家“擇中建都”、都城之“擇中建宮(宮城)”、宮城之“擇中建殿”等,提煉出“擇中建都”“擇中立國”,是古代中國國家大一統(tǒng)意識的文化基因[13]。
三、中原文化及其對中國文化的獨(dú)特性表達(dá)
不是所有區(qū)域都能成為中華文明的全息承載地,但所有區(qū)域文化都可以對中國文化作出各具特色的表達(dá)。首先是由區(qū)域稟賦決定的各區(qū)域文化樣貌和人文精神,不僅是“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而且還是“吾土吾民鄉(xiāng)音難改”,如中原文化之厚重,為“華夏文明之源,炎黃子孫之根”;江南文化之靈秀,“人文淵藪地”“千山千水千秀才”;湖湘文化之革命精神,“我自橫刀向天笑”;閩南文化之敢拼敢贏,“愛拼才會贏”。其次是由歷史進(jìn)程決定了各區(qū)域文化特征和地位,即使是處于同一時代的各區(qū)域文化之間,對中國文化的具體呈現(xiàn)也各不相同。比如三代時期的中原地區(qū),不等于三代時期江南地區(qū),明清時期的華南地區(qū),也不等于明清時期的西南地區(qū)[14]。事實(shí)上,三代之前的中原地區(qū)、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江南地區(qū)、南宋至元的洞庭湖與鄱陽湖地區(qū)、晚明至清的西南地區(qū)、晚清至民國的東北地區(qū),所構(gòu)成的中國歷史序列恰好是一個前后相繼的歷史過程,在地域廣闊、區(qū)域差別明顯的中國大地上,各區(qū)域文化之間看似表現(xiàn)為穩(wěn)定的空間關(guān)系,而在長時段歷史進(jìn)程中,也會在變動過程中轉(zhuǎn)換為時間關(guān)系。
具體到中原學(xué)學(xué)術(shù)話語中的中原文化,如果說,中原的文化含義決定了中原地區(qū)能夠成為5000多年中華文明的全息承載地,那么中原文化的地域特征,則與其他區(qū)域文化一樣,都是對萬年中國文化各具特色的表達(dá)[2]。中原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中原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二者是地域與全國、部分與整體的關(guān)系,但就比較而言,中原文化是中國文化特別重要的組成部分[6]1。所謂“特別重要的組成部分”,首先表現(xiàn)在中原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根、主脈、主干文化,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組成部分,“主根、主脈、主干”就是中原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獨(dú)特性表達(dá)。《中原學(xué)概論》選擇中原文化的根源性特征,為中原學(xué)“文脈”溯源,選擇中原學(xué)術(shù)思想的領(lǐng)先地位,為中原學(xué)的學(xué)脈”溯源,即是以中原地方性知識對中國文化的獨(dú)特性或個性化表達(dá)。
《中原學(xué)概論》把中原學(xué)“文脈”演進(jìn)劃分為六個時段。其中,新石器時代是中原文化的萌芽階段,包括中原地區(qū)的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以及流傳于中原地區(qū)的“盤古開天”“女媧造人”“三皇五帝”“河圖洛書”等遠(yuǎn)古傳說。夏商西周是中原文化的形成階段,具體表現(xiàn)在夏、商、周前后相繼三個王國在中原地區(qū)的建立,及其創(chuàng)造的高度發(fā)達(dá)的“中國文明象征”的青銅文明、中國元典文化等。秦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原文化的發(fā)展階段,在中原地區(qū)主要呈現(xiàn)為中國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域外文化的傳入及其在中原地區(qū)出現(xiàn)的中國化趨勢。唐宋時期是中原文化的成熟階段,以文學(xué)藝術(shù)成就在全國的領(lǐng)先地位、宗教文化的傳播與融合、市民文化的繁榮為標(biāo)志;唐代東都洛陽、宋代東京汴梁,成為此一時期中原文化走向成熟的物質(zhì)載體。以此論之,中原學(xué)接續(xù)的是中原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根源性、獨(dú)特性表達(dá)。如若將中原學(xué)“文脈”追溯至元明清時期,中國文化中心和經(jīng)濟(jì)重心已經(jīng)完成了南移,中原文化在中國文化中的“軸心”地位已經(jīng)消失;把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當(dāng)代中原文化,如紅旗渠精神、焦裕祿精神等,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shè)中發(fā)出中原之聲[15],中原學(xué)雖可參與“中華民族第八次思想重構(gòu)”,但也會因忽視中原文化是對中國文化的獨(dú)特性表達(dá),而將中原學(xué)變成純粹是對“地方性知識”的描述,或《中國通史》教科書的地方性版本。
《中原學(xué)概論》把中原學(xué)“學(xué)脈”演進(jìn)劃分為七個時段。其中,先秦時期,在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百家爭鳴”中產(chǎn)生的中原諸子學(xué),如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之學(xué),以商鞅、韓非、李斯為代表的法家之學(xué)。兩漢時期,“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之后,以賈誼、晁錯為代表的中原經(jīng)學(xué)成就,以及洛陽經(jīng)學(xué)中心地位在東漢的確立。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xué)在中原的勃興,從何晏、王弼祖述老莊、首倡玄風(fēng),到“竹林七賢”著述清談、辯論“貴無”與“崇有”,代表一個時代的學(xué)術(shù)風(fēng)氣。隋唐時期,儒釋道在中原的三教融合及佛教中國化成果禪宗在中原地區(qū)產(chǎn)生的廣泛影響。宋明時期,理學(xué)發(fā)展史上的“北宋五子”中,除周敦頤、張載外,邵雍、程顥、程頤均在洛陽講學(xué)傳道,二程洛學(xué)影響所及宋元明六百年。以此論之,從中原諸子學(xué)、兩漢經(jīng)學(xué)、魏晉玄學(xué)、宋元明理學(xué)等,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精神和學(xué)術(shù)話語的學(xué)術(shù)思想,或創(chuàng)設(shè)于中原,或繁榮于中原,都是中原學(xué)的傳統(tǒng)理論形態(tài),而“二程理學(xué)”是其中典型代表。因此,中原學(xué)是“二程理學(xué)”的接著講[11]。在此意義上,中原學(xué)接續(xù)的是中原文化在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領(lǐng)域的領(lǐng)先地位。當(dāng)然,也有學(xué)者將中原學(xué)“學(xué)脈”延伸至肇始于伏羲的易學(xué),及軸心時代中原五子道學(xué)、中原理學(xué),接續(xù)馮友蘭“新理學(xué)”[15]。
《中原學(xué)概論》追溯中原學(xué)的“文脈”和“學(xué)脈”,所敘述的當(dāng)然是中原地方性知識,是中原文化的內(nèi)容,并不能因此而理解為是對中原文化的敘述,而是在中原文化的根源性特征和在學(xué)術(shù)思想領(lǐng)域的領(lǐng)先地位背景下,敘述的中原文化。所以,中原學(xué)之中原文化,所要表達(dá)的國家話語,是中原文化在中國文化發(fā)展中的根源性特征和在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領(lǐng)域的領(lǐng)先地位。
四、中原學(xué)及其一流學(xué)科定位
中原學(xué)的學(xué)科定位,在2016年中原學(xué)概念正式提出之初是非常明確的。中原學(xué),首先是學(xué)科,當(dāng)時提出建設(shè)中原學(xué)學(xué)科,意在整合各學(xué)科中的中原文化研究力量,引導(dǎo)中原文化研究方向,將多學(xué)科方法集中于中原文化的重大理論與現(xiàn)實(shí)問題中,從而拓展中原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中原學(xué),還是一流學(xué)科,“打造中原學(xué)一流學(xué)科”,就是為了“建設(shè)思想河南”。關(guān)于一流學(xué)科,《國務(wù)院關(guān)于印發(fā)統(tǒng)籌推進(jìn)世界一流大學(xué)和一流學(xué)科總體建設(shè)方案的通知》,雖已于2015 年10 月24 日印發(fā),但此時的中原學(xué)尚未樹立建設(shè)一流學(xué)科的自主意識,此時的中原學(xué)實(shí)際是中原發(fā)展哲學(xué)[11]。
2019年,李庚香發(fā)表《走進(jìn)新時代的中原學(xué)》一文,專題討論中原學(xué)的定位問題。他認(rèn)為,中原學(xué)是研究中原的學(xué)問,是研究中原的文化、文明,是研究中原經(jīng)濟(jì)社會生態(tài)發(fā)展的地方性知識體系。因此,中原學(xué)首先是“一門地方性學(xué)科,具有地域的特征和地域的形式”。同時,作者還特別強(qiáng)調(diào)“中原學(xué)是地方學(xué)術(shù),但又必須是國家話語、擁有世界情懷”,此論為至今所見最早提出中原學(xué)的國家話語問題。
其次,中原學(xué)因涵蓋古今,而具有“系統(tǒng)性”;中原學(xué)又因具有跨學(xué)科視野,而成為“一門綜合性學(xué)科”;更因中原學(xué)的本質(zhì)是實(shí)踐性,而“高度重視學(xué)以致用”[16]。當(dāng)然,系統(tǒng)性、綜合性和實(shí)踐性,應(yīng)該表達(dá)的是中原學(xué)的特征。與2016 年中原學(xué)概念正式提出之初時相比,在學(xué)科定位問題上,從一流學(xué)科轉(zhuǎn)向?yàn)榈胤叫詫W(xué)科,或者說中原學(xué)既是一流學(xué)科,也是地方性學(xué)科。同年,《河南社會科學(xué)》開設(shè)《新時代中原學(xué)學(xué)科體系之基礎(chǔ)理論構(gòu)建專題研究》,欄目主持人李庚香首度把中原學(xué)定位為“中國特色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中原品牌”,是一門新興學(xué)科[15]。中原學(xué)一流學(xué)科之定位更加具體而明確,但中原學(xué)的地方性仍是學(xué)界的主流,如2019 年《河南社會科學(xué)》《中原學(xué)專題研究》欄目,發(fā)表趙炎峰《中原學(xué)的合法性思考及其理論建構(gòu)》,主要討論的是中原學(xué)作為中原地方性學(xué)科屬性及其合法性問題[17]。2021年之后,中原學(xué)還被定位為“統(tǒng)領(lǐng)中原歷史文化研究的五方之學(xué)”,或“統(tǒng)領(lǐng)中原歷史文化研究的地方性知識體系”[18]。也有學(xué)者建議,把中原學(xué)納入國家推動的“新文科”建設(shè)[19]。
針對目前學(xué)界關(guān)于中原學(xué)的學(xué)科定位,如一流學(xué)科、地方性學(xué)科、中國特色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的中原品牌、中原歷史文化研究的五方之學(xué)、新文科等,本文認(rèn)為在國家話語表達(dá)上,中原學(xué)仍需堅持一流學(xué)科定位。為此須進(jìn)一步厘清:中原學(xué)研究內(nèi)容是中原地方性知識,但不是地方之學(xué);中原學(xué)是中國特色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中原品牌,不僅是河南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中原品牌,或當(dāng)代中原文化;“中國特色,世界一流”,是中原學(xué)國家話語最為準(zhǔn)確的表達(dá)。
中原學(xué)是中國特色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的中原品牌。目前中國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的最大現(xiàn)狀是,在學(xué)術(shù)命題、學(xué)術(shù)思想、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學(xué)術(shù)標(biāo)準(zhǔn)、學(xué)術(shù)話語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太相稱。因此,構(gòu)建充分體現(xiàn)中國特色、中國風(fēng)格、中國氣派的中國特色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學(xué)科體系、學(xué)術(shù)體系、話語體系,是當(dāng)代人文學(xué)者的使命和擔(dān)當(dāng)。其中,提煉標(biāo)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dǎo)國際學(xué)術(shù)界開展研究和討論,要從學(xué)科建設(shè)做起,每個學(xué)科都要構(gòu)建成體系的學(xué)科理論和概念[20]。中原學(xué)就是從中原歷史文化豐富內(nèi)涵中提煉出來的,反映中原風(fēng)貌、中國特色、時代特征和國際影響力的標(biāo)識性學(xué)科概念。所謂“中原風(fēng)貌”,就是中原學(xué)以“中原”為學(xué)科標(biāo)識,知識體系來自中原,從中原區(qū)域的、個案的、具體的事件研究出發(fā),敘述的是中原故事;所謂“中國特色”,中華5000多年文明突出特征唯有在中原足以全息呈現(xiàn);中國文化歷萬年之演進(jìn)與中原文化的發(fā)展軌跡呈正相關(guān),表明中原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縮影。正所謂“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國史”,中原學(xué)是中國特色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的中原品牌。
中原學(xué)是國家之學(xué)。“中原學(xué)是研究中原的學(xué)問”“中原學(xué)是以中原歷史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學(xué)科”等,一度成為中原學(xué)地方性學(xué)科定位的基本依據(jù)。于是在時間意義上,中原學(xué)是關(guān)于老家河南、出彩河南的地方性知識體系[21];在研究內(nèi)容上,中原學(xué)是統(tǒng)領(lǐng)中原歷史文化研究的地方性知識體系[22]。中原學(xué)是研究中原的學(xué)問,固然沒錯,但忽略了歷史時期的中原并非一般性的區(qū)域概念,中原地區(qū)是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形成的關(guān)鍵性區(qū)域[23],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擁有特殊作用和領(lǐng)先地位。中原學(xué)學(xué)術(shù)話語中的“中原”,是文化概念或政治概念,而不僅是區(qū)域概念,在此意義上,“中原”可指代“中國”,或“唯有中原最中國”。在此形成的區(qū)域?qū)W術(shù)文化,如先秦中原諸子之學(xué)、兩漢中原經(jīng)學(xué)、魏晉玄學(xué)、宋明理學(xué)等,是中國學(xué)術(shù)文化、國家學(xué)術(shù)文化[24]。因此,中原學(xué)敘述的是地方性知識,表達(dá)的則是國家話語。
中原學(xué)是一流學(xué)科。國務(wù)院統(tǒng)籌推進(jìn)的世界一流學(xué)科,包括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兩個含義。在此,我們先說“中國特色”,中國特色就是要回答中國要建設(shè)什么樣的世界一流學(xué)科,換言之,我們要建設(shè)的是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學(xué)科。中原學(xué)不僅源自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征的全息承載地,中原學(xué)的主要研究內(nèi)容更是對中國文化的獨(dú)特性表達(dá),最能體現(xiàn)中國特色,也最有可能建成中國特色的“一流學(xué)科”。再說“世界一流”,世界一流指的是“國際影響力”,在師資隊(duì)伍建設(shè)、創(chuàng)新人才培養(yǎng)、科學(xué)研究水平、優(yōu)秀文化傳承創(chuàng)新、成果轉(zhuǎn)化等方面,進(jìn)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河南省優(yōu)勢特色學(xué)科建設(shè)工程實(shí)施方案》的建設(shè)目標(biāo)是,到2024 年,5 個左右學(xué)科進(jìn)入國家“世界一流學(xué)科”行列①,《河南省特色骨干大學(xué)和特色骨干學(xué)科建設(shè)方案》的建設(shè)目標(biāo)是,到2023年,5個左右的學(xué)科達(dá)到國內(nèi)一流水平②,所指大概即“世界一流”。河南省特色學(xué)科“中原歷史文化學(xué)科群”“黃河文明學(xué)科群”、河南省特色骨干學(xué)科“炎黃學(xué)學(xué)科群”“甲骨文信息處理學(xué)科群”建設(shè)現(xiàn)狀,對中原學(xué)而言,既是契機(jī),也有挑戰(zhàn),更主要是契機(jī)。
五、結(jié)語
歷史研究,雖不能單獨(dú)依靠文獻(xiàn)建立起遠(yuǎn)古與現(xiàn)實(shí)的直接聯(lián)系,但結(jié)合田野調(diào)查材料提煉而成的,以地方故事表達(dá)普遍性話語的伏羲敘事,確實(shí)在中原學(xué)國家話語表達(dá)中依稀可見。比如中原學(xué)是關(guān)于中原的學(xué)問,敘述的是中原地方性知識,包括對中原學(xué)術(shù)思想的“接著講”、對中原歷史文化的“學(xué)科化”,但因中原不僅是一個地域概念,還是一個文化概念或政治概念,而且在文化意義或政治意義上,中原就是中國的國家在場,因此中原學(xué)是國家之學(xué),不僅是中原地方之學(xué)。中原學(xué)以中原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但中原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根、主脈,在中國文化演進(jìn)中擁有獨(dú)特身份,在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領(lǐng)域具有領(lǐng)先地位,中原文化不僅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更是對中國文化的獨(dú)特表達(dá),中原學(xué)不僅是中原之學(xué),還是中國特色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的中原品牌。打造中原學(xué)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中國特色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中原品牌,不僅是中原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之初衷,是應(yīng)該成為中原學(xué)不變的學(xué)科定位。
注釋:
①參見河南省教育廳等印發(fā)的《河南省優(yōu)勢特色學(xué)科建設(shè)工程實(shí)施方案》(教高〔2015〕1085號)。
②參見河南省教育廳等印發(fā)的《河南省骨干特色大學(xué)和骨干特色學(xué)科建設(shè)方案》(豫教高〔2019〕178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