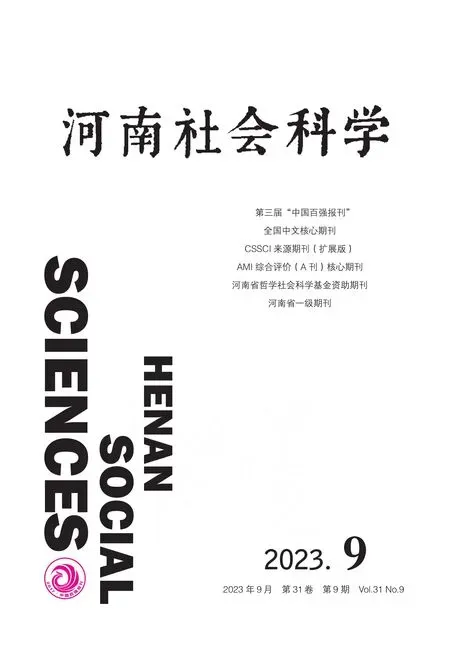數字場域中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構邏輯、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
翟月熒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 100091]
一、引言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關系社會長治久安和人民幸福。謀求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社會治理智能化”等具體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擘畫了一幅“中國之治”的社會治理藍圖,明確指出要“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同時強調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基礎上,要更加突出“科技支撐”[1]的重要作用。這表明中國社會治理已經走上了全新的數字化軌道。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驅動下,為了落實黨中央關于數字化建設的決策部署,許多地方在推進社會治理中不斷探索數字化建設的實現路徑,初步取得了互相促進的良好局面。
當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進入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建設相對滯后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風高浪急甚至是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亟須推進社會的結構性改革。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風險不斷積聚,社會治理的壓力與日俱增,人們已經不滿足于單一需求,而是向著越來越多元化的社會需求發展,這就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加強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成為提升社會治理效能、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構建良好治理秩序的必然選擇。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構建和發展可以從技術、制度、法規、政府治理等多方面來著手,其中技術維度是創新發展的重要保障。信息技術發展給社會帶來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為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了重要契機,為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提供了強大支撐。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具備強大的資源轉化能力,為社會治理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支撐。這些技術的使用為社會治理各主體提供了更加廣泛的可能性。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如何在數字化背景下充分發揮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潛能,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數字化背景下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建構邏輯
數字技術驅動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應從兩個方面來考慮,這里既包含了社會治理共同體的理論邏輯,又包含了社會治理共同體構建的現實邏輯。
(一)社會治理共同體的理論邏輯
“共同體”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相對于國家的重要概念。按照類型劃分,共同體包括了自然的共同體、虛幻的共同體、真正的共同體。從2012年“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到2019年“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提出,反映的是不同層面、不同領域社會治理的愿景。社會治理以“共同體”的形象出現,需要從理論層面進一步挖掘、理解。
第一,社會治理共同體基于共同合作的需求。雖然共同體概念的譜系較為繁雜,但學者對其核心觀念的理解大致可以歸于三類:基于自然傳承的風俗習慣而形成的相互依賴的情感共同體;共享種族身份或特定價值而彼此依存的權利共同體;基于特定的任務或目標而聚集并展開共同行動的任務共同體或目標共同體[2]。中國傳統人際關系形態的構成基本上以血緣、倫理、宗族為主線,這種人際關系往往通過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利益,形成相同的價值取向,即共同的觀念。這種從個人推及家庭,再從家庭推及國家的共同體理念一直是中國人所推崇的。可以說,“共同體”的提出更強調的是在社會生活的場域中達成一種相互幫助、相互合作的共同生活圈。當前社會所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日益增多,不確定性因素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將個體與社會割裂開來是不現實的,同時也為社會增加大量的不確定性。共同體的意義就在于通過彼此的融合、交流、合作共同抵御現實社會的風險,增強個體和社會的抗風險能力。共同生活提供了差異世界的和諧交往模式,推動了公共領域協助政治領域以實現問題的解決,這是自由與善的社會的基本條件[3]。
第二,社會治理共同體對社會分工、個體責任的思考。社會分工是超越一個經濟單位的社會范圍的生產分工,只有在彼此分工、相互聯系中才能為共同體社會打牢穩固的基礎。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用“職業團體”來構建個體與國家之間的聯系,形成“國家-職業團體-個人”三級聯結體系[2]。荀子主張根據人的社會性實行合理的社會分工。《荀子·王制》中提到“故人不能無群”,又提出“群而無分則爭”。由此可見,東西方都強調人在社會中的“責任”與“分工”,強調共同生活要各司其職,根據角色分工承擔相應的責任。將人的分工上升到社會治理層面,說明國家和社會的治理必然依靠群體協作中的分工來實現高效治理。尤其在現代社會,不同主體要根據各自的分工參與到治理的不同環節,分工已經成為一種絕對的行為規范,是各主體不可推卸的責任,是社會治理共同體得以可能的基礎。從“責任分工”的視角來看,社會治理共同體中的“人人有責”“人人盡責”對于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構建具有重要作用和意義。社會治理共同體中的責任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說:首先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責任,一個安全、有序的社會必然是人人相互負責,具有良好的人際關系的社會氛圍。如果人們相互之間的責任缺失就容易引發諸多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進而帶來社會的動蕩不安,那么社會治理共同體就更無從談起了。其次,在社會治理中強調社會是一個關系范疇,它依托于社會各主體的責任。在參與社會治理過程中多元主體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同時在各自的領域發揮著不同的作用。社會治理的效果取決于不同的社會主體責任履行的程度,而責任又是個人功能轉化為實現社會治理有效性的關鍵點。
第三,社會治理共同體基于共享目的的愿景。馬克思認為,共同體是人獲得全面發展的聯合體。這就意味著,人只有在共同體中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價值。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機會,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4]。這種以自由發展為價值核心的社會共同體,一方面強調了個體與社會共同體的關系實質,即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的統一;另一方面還強調了個體只有在社會共同體中其價值才能得以體現。可以說,現實社會共同體為個體發展、個體價值的實現提供了保障。換言之,在共同體中人才能真正地發揮其作為人的作用,即個體在共同體中的活動本質上既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也同時推動了共同體的發展。因此,在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是前提,“人人享有”是目的,個體在“享有”之中也進一步彰顯了自身的價值。
從“共同合作”這一基本生存模式再到明確的“責任分工”的進階模式,最終的目的是要達成“人人享有”的未來愿景,這就可以將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基本邏輯總結出來。社會治理是共同生活合作達成的共同事業,而這個“事業”則要依靠社會中個體的分工協作、責任義務來賦能建設,最終的目的是讓人人都能享有社會發展成果。“共同體”既是社會治理的工具,也是社會治理的目標,其目的都是要讓人人享有安定、和諧的美好生活。
(二)社會治理共同體構建的現實邏輯
社會治理是順應我國世情、國情的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也是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和根本走向,根植于社會變遷的過程之中。
第一,社會治理環境的復雜多變。隨著我國社會發展以及改革的不斷深化,原有的城鄉結構被打破,城鄉之間制度、規范、文化壁壘逐步消除,催生出巨大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潛力。城鄉社會結構的變化,帶來社會流動性的增強,帶動了社會系統從簡單化向復雜化的轉變。城鄉互動的頻繁性、資源要素的無序流動,導致社會沖突增加,對原有的社會運行結構產生沖擊,社會結構的復雜性大大增強,并對既有的治理機制和技術手段提出挑戰,社會治理環境的復雜性大大提高。尤其是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信息化數字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社會治理環境的復雜性,可以說,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社會問題。網上網下的同頻共振,人機交互更加深入,信息傳播方式、資源聚集程度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網絡謠言傳播和網絡輿情在技術的賦能下交互影響,社會問題的積累更具動態化和隨機性,社會治理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但是,猶如硬幣之兩面,數字技術在對社會治理提出挑戰的同時,對整合開發社會資源、突破現有治理體制的困境,以及為增強社會治理共同體治理復雜環境的能力提供了技術支持。
第二,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隨著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發展、社會的不斷進步、政府“放管服”改革的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程度不斷加深,社會治理主體已經由以政府管控為主轉向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多元主體如社會組織、企業、公眾等積極參與社會管理當中,實現了社會治理模式的轉變,使得社會領域呈現多元共治的局面。比如,社會組織通過承接政府職能和政府購買社會服務參與行業管理、公共服務、社區治理、公益慈善等多個領域,社會創新活動層出不窮[5]。企業家主體通過黨建引領、行業自治等方式協助黨政部門共同推動營商環境改善和市場化改革,積極參與社會共建共治過程[6]。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有利于社會資源的有效整合,提升社會治理的治理效能。但是,多主體之間的互動也將提升治理難度,進而對社會治理共同體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數字技術發展為多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平臺和渠道,更加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為社會治理開放的視野提供了便利,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治理主體的固有地位。與此同時,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也加劇了治理主體間的矛盾和沖突,為社會治理帶來了挑戰。
第三,社會治理過程的動態變化。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社會各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改革發展,可以說我們處在一個社會大變革、大轉型的時代。社會治理的過程要與經濟、社會、政府、技術的發展相匹配。同時,面對社會轉型期,相對應的文化、社會秩序等方面都會發生改變,對社會治理產生持續沖擊。這就需要在動態化的社會治理過程中,將相對靜態、單一的政府管理模式轉變為多主體的、動態的、開放的管理模式。網絡政務平臺等的發展將原來單向的傳達式的社會信息轉變為多向的互動式的交流,交互性和即時性顯著提高,在大數據和算法推送技術的加持下,精準服務成為可能。大數據實時更新、實時交互,極大推動了社會治理過程的動態化。自動決策、算法決策為政府作出精準行政提供了技術支撐。數字技術將數據的開發、協調、儲存等業務流程同步,并貫穿于社會治理的全過程。在社會治理的動態過程中,信息的即時傳播、及時反饋成為關鍵一環。大數據測算、人工智能場景模擬都為這關鍵一環提供了技術支撐。社會治理過程的動態化有利于社會機制的變化,進而推動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構建發展,但是應該注意的是,這也為社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戰。
第四,社會治理結果的不可預測性。現代技術體系的復雜性導致社會組織方式發生變化,使社會進程趨于復雜[7]。從社會環境的復雜多變到社會治理主體向多元化變化再到社會治理過程的日益動態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社會治理結果的不可預測性。現代社會本質上就是一個風險社會,專業化分工、管理科學化、技術進步等因素在推動經濟社會進步的同時,也顯著增強了經濟社會系統的脆弱性,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前所未有、難以預知的程度[8]。由于社會治理系統由原來的線性管理轉變為現在的網格化管理,社會的互動模式也由單一輸出模式轉變為多類型互動,尤其是技術發展又增加了人機互動模式,使社會治理結果的不可預測性又進一步增強,加之數字技術風險和決策偏差又進一步加劇了社會治理結果的隨機性。信息技術的發展使網絡信息的傳播成為影響社會治理結果的重要因素,數字技術更新了信息傳播的介質,社會輿論可以通過幾何式裂變快速抵達受眾,加之信息網絡、移動設備的發展,使網絡世界人人都有麥克風,一時間網絡謠言四起,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會治理的難度。隨之而來的數字鴻溝、算法黑箱等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社會治理的不確定性。利用數字技術在信息整合、大數據測算、算法推送等方面的優勢,可以有效化解社會風險,降低社會治理結果的不可預測性。
三、數字技術在社會治理共同體中的現實困境
理念是實踐的先導,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提出為社會治理提供了方向和指引。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戰略目標,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社會治理體系建設的內涵。然而,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一個需要長期探索的過程,存在很多現實問題。諸如數字技術內嵌社會治理程度不夠深入、數字技術治理的效能并未充分釋放、政府間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協作不夠深入等,這些都是社會治理實踐困境中的突出表現,未來之路道阻且長。
(一)協作困境與“新數字鴻溝”
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構建依賴于多部門的溝通、多元主體之間的協作、社會各種資源的整合以及各類技術共同發揮作用,唯有如此才能在高度復雜的社會治理環境中探索高效治理路徑。然而實踐證明,以上各元素均呈現出碎片化的特點,協作的緊密度不夠。首先,由于各政府機關之間涉及多部門的相互協作,橫向的部門協作難度較大。又囿于各部門之間有著各自的業務范圍和專業范圍,其分工也各不相同,各部門極易呈現“碎片化”狀態,難以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難以釋放部門合作間的強大合力。其次,在數字技術的賦能下,社會治理主體進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尤其是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數據,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社會治理各主體各自掌握數據資源,造成了大量重復數據的產生,各主體間所產生的數據不能進行有效的流動和交流,數據開放程度低,致使“信息孤島”“信息煙囪”產生,這些都是造成社會治理協作困境的重要因素。再次,由于各部門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容易造成各部門從自身利益出發,阻礙數據資源相互開放共享。數據資源的非共享性,減少了數據的利用價值,使社會治理多元主體的相互關聯性減少,限制了各主體之間的協同治理水平。
4) 設計罐底環形隔水圈。在罐底含水層以上設計隔水圈,消除罐壁和油品熱傳導對含水層的傳熱,儲罐沸溢模擬實驗證明,設計隔水圈后,火焰和熱輻射強度減弱明顯。
(二)制度建設相對滯后
信息技術的發展、數字技術浪潮的來襲,使政府等社會治理主體更傾向于依賴技術來決策,并以此提高社會治理效能。在社會治理過程中越來越重視技術的同時,制度的相對滯后又成為無法避免的新問題。制度滯后帶來技術與制度難以同步更新、無法達到高效配合等的問題都會影響社會治理革新的需求,從而引發社會治理的多方面困境。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元宇宙、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的普及和應用,網絡空間成為社會治理的又一領域,但是相對應的法律、制度、行業規則等都無法匹配現在數字虛擬空間的發展進程。這種大體量的虛擬空間,必然會加劇社會的動蕩,比如網絡空間中“人”的隱匿性更強,AI技術所帶來的網絡謠言的高仿真性等,都使社會治理的難度急劇增加,急需相應的法律、制度、行業規則來規范行業的發展。此外,大數據作為社會治理重要的戰略性資源,大數據的安全使用、個人信息數據的高效保護以及大數據的儲存、流通等都需要相關的制度保障,如果制度落后于技術發展,極易造成大數據使用秩序的混亂。加之缺乏規范的制度體系和完備的程序規則,協作治理和數據共享難以實現,從而社會治理的系統性、完整性就很難保證,極大增加了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構建阻力,使社會治理深陷困境之中。
(三)數字技術引發多樣態治理風險
數字技術是信息革命的前沿成果,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為社會治理帶來新的發展范式,但是社會治理風險也接踵而來,進而引發多樣態的社會治理次生風險。首先,數字技術驅動效應的發揮受到技術本身發展程度、技術嵌入社會治理程度的影響。尤其是技術嵌入程度會給當前社會治理模式與制度帶來一定的沖擊,導致社會治理效能的發揮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從而阻礙社會治理技術優勢發揮。而有效的社會治理也并不是數字技術加持的唯一結果,比如算法歧視、數字鴻溝等都會對轉型中的社會治理帶來風險和挑戰。其次,數據資源的非正確使用會帶來包括信息安全、算法霸權等后果。數據利維坦會導致數據獨裁,加劇寡頭統治的風險[9],加之社會治理主體間的利益沖突,加大了社會治理的難度。以目前技術發展的水平來看,由于認知的局限、技術的偏差,對于社會治理情況的解讀是有限的,尤其是精準匹配社會需求的能力還有待提升,由此來看對于社會問題的精準識別和社會需求的有效回應都大打折扣。再次,對于社會安全問題的挑戰日益增多,以數據泄露為主要表現的公共安全問題頻發,利用爬蟲軟件爬取大數據,對于信息安全有巨大的安全隱患,對網絡安全產生較大威脅。同時大數據的利用,對社會公眾的隱私形成比較大的威脅和挑戰。
(四)技術至上產生決策依賴
數字技術本身兼具賦能與控制的雙重功能,如果使用不當,技術有可能“被吸納”成為政府單方面管理社會的工具,日益淪為“控制社會的技術”[10],對于數字技術的片面強調,可能導致“技術至上”,從而引發公眾的價值迷失。數字化治理中存在過度依賴技術卻過于簡化社會和人的向度、忽視人的主體價值的問題[11]。值得注意的是,技術本身往往異化為社會治理的目的本身,其實它只是社會高效治理的一種手段。真正的“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的終極價值出現了迷失,在實踐中普遍存在以平臺建設的規格、數量等顯性的量化指標來判定治理效果的現象。由于配套設備的不完備等問題,數據平臺重復建設、運行效率低下的現象時有發生。更有甚者,數據平臺成為政府部門的擺設,造成資源的嚴重浪費。此外,算法歧視現象頻發,如算法背后隱藏的資本力量導致的算法不公現象、數字素養參差不齊等引發的數字鴻溝等。“信息繭房”的出現,有可能推動公眾的輿論發生偏離,從而忽視來自公眾的真實需求。“技術至上”的思維會在治理過程中過分強調技術的重要性,容易形成對技術的過度依賴,也容易造成治理主體只沉迷于數字技術所帶來的“虛幻快樂”的情緒之中,而忽略了數據背后的倫理和價值問題。過度強調技術導向,還有可能產生新的社會不公,導致在社會治理過程中不能形成多元治理的良性機制,也不利于社會治理共同體內部合作秩序的建立。
四、數字技術對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實現路徑
數字技術在促進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形成方面,依賴于社會治理過程對技術的吸納與對自身的調適,需要理念更新、制度變革、組織轉型、法治規范和倫理關切等多維度的協同支撐。數字化背景下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必須在明晰目標指向的基礎上,回應和化解社會治理中的現實困境,以包容審慎的態度不斷推進社會治理多元融合。
(一)協同治理與數字技術共享發展
首先,應建立社會治理的整體化思維,探尋協同治理有效途徑,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充分調動各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加強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的組織優勢,將社會治理的政策法規真正直插基層。政府部門要打破原有的“各自為政”的局面,打破部門間的“藩籬”,提升部門間聯動協調能力,積極提升社會治理各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其次,建立一體化協作平臺,充分共享大數據資源,挖掘大數據之間的動態關聯性并關注其動態演化過程,這些都是實現協同治理的內在要求。再次,提升公眾的數字化素養。一般認為,數字是信息的一種形式,因而數字素養是信息素養的組成部分,而信息素養被認為是信息時代普通公民應當具備的一種能力[12]。實現數字技術使用能力的大眾普及,尤其是縮小城鄉之間、老年人與年輕人之間的信息差,縮小甚至消除“數字鴻溝”是當前亟須解決的問題。綜上,在實踐過程中,需要采取試點先行、逐步推廣的模式,才能真正實現協同治理數字技術共享協同推進。
(二)構建線上線下平臺聯動機制
數字時代多平臺互動技術為社會治理共同體運行描繪了一幅美好圖景。數字政府平臺是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重要支撐,政府平臺通過不斷的轉型創新來提高自己的治理能力。構建線上線下互動交流平臺,一方面應打破固有思維,加強制度引導,平衡多元利益,圍繞大數據中心規劃打造“大聯動”治理平臺中心,建設智慧治理系統,在此過程中整合冗余平臺,構建橫向智能相同的綜合化平臺,同時在縱向監管上打破“藩籬”,建立聯動機制。另一方面,應建立各治理主體大數據中心,將大數據整合到信息采集平臺,并將采集后的相關治理數據信息進行高效反饋,采取實時監測、數據收集,通過大數據算法進行精準推送,使傳輸方與接收方形成良性互動,及時糾治治理中出現的問題,達到高效治理的結果。通過搭建供需平臺,實現服務變現,達到需求與供給的公開透明,促進服務就業增收。打造智慧治理共同體平臺,將各場景應用融入治理服務之中,促進政務信息共享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打造社會治理共同體。
(三)國家法律體系和制度體系的支撐配套
法律體系和規則制度體系的建立是為社會治理體系提供一套可供遵守的規范,通過合法性規制、形塑穩定秩序來提升社會治理的效能。技術創新為社會治理提供了更加可靠、更加先進的技術支撐,從而優化社會治理工具,推動社會發展。規則體系的適應性變遷本就是技術創新與應用的規范框架,能夠降低各方面對技術創新的阻力,為技術的創新應用提供合法性支持,也是技術創新應用于社會治理范疇的重要保障。同時,技術的創新為制度的變遷提供強勁的動力,推動制度建設的結構性優化。在數字化時代,技術與法律制度的同向推進、聯動發展是實現社會治理的有效保障。加快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明確各種跨部門協同組織的地位、設立條件、審批標準、設置程序、組織架構、職權責任、功能作用等基本事項,既可以為跨部門協同組織建設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據,也確保組織設立的科學性和合理性[13]。數字技術開發、應用的法律制度保障,是填補數字技術漏洞、提高技術水平、確保信息安全的重要保障。數字技術時代大數據、算法決策已經成為社會治理、公共決策的重要手段,加快出臺以數據和算法為基礎的政策法規,保證公眾對大數據和算法技術的公平享用,避免出現新的社會不公;對于智慧化決策,加快出臺人工智能相關法律法規,避免出現法律和倫理問題。總之,要減少技術創新的法律模糊地帶,動態良性的法規政策可以刺激技術創新的動力,持續推動技術不斷創新。在數字技術的應用中,不僅要關注技術本身帶來的社會治理效率提升,更應該加強技術應用的合法合規,注意對公眾的人文關懷和對技術的倫理規制,唯有如此才能探尋技術創新與社會治理的關鍵契合點。
(四)構建“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
五、結語
不可否認,數字技術下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是適應時代發展的現代化治理模式,其強調的是社會治理不同主體的協作能力提升和整體性治理功能的發揮。協作、信任、共識等構成了社會治理共同體的重要因素,數字技術的加持為培育社會治理共同體的要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為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提供了現實支撐。動態的制度建設配置、合理的治理結構、優化高效的智力資源等是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核心,是整體提高社會治理效能的關鍵。數字技術可以被看成一種技術支撐性治理架構,它將黨政機關、社會組織等各種主體納入社會治理框架中,注重從宏觀、中觀、微觀角度協同共治與增權式互動,強化主體兼容與功能互補的治理結構。在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中,體現的是技術賦能與制度的重塑,助推了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構建,凸顯了數字技術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的驅動作用。數字技術推動社會治理發展仍在繼續,將為社會治理提供更大的空間和更廣泛的可能性,特別是隨著社會治理重心下移,數字技術將與更多的具體主體、基層治理發生更加緊密的互動,進一步推動形成差異化的社會治理模式和實踐路徑,因此,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具有學理意義和實踐意義。更應該注意的是,數字技術推動社會治理共同體建構并不是簡單的線性結構,而是復雜的立體結構,因此不能在社會治理過程中過度夸大技術的重要性,應該具有更多的人文關懷和倫理規制。未來在探索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構建過程中,應更加注重“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價值導向,深度探索數字技術與社會治理的協同增效,為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建構貢獻更多的積極力量,為社會治理的結構優化、創新升級帶來更多的積極變化。
注釋:
[1]從“中國之制”看“中國之治”:解碼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EB/OL].(2019-11-06)[2023-06-25].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1/06/content_5449124.htm?isappinstalled=0.
[2]王亞婷,孔繁斌.用共同體理論重構社會治理話語體系[J].河南社會科學,2019(3):36-42.
[3]鮑曼.尋找政治[M].洪濤,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李云新,劉然.中國社會創新的特征、動因與績效:基于“中國社會創新獎”的多案例文本分析[J].公共行政評論,2016(4):147-170,209.
[6]何軒,馬駿.被動還是主動的社會行動者?——中國民營企業參與社會治理的經驗性研究[J].管理世界,2018(2):34-48.
[7]里克羅夫特,董開石.復雜性挑戰:21世紀的技術創新[M].李寧,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8]貝克.風險社會[M].何博聞,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9]唐皇鳳.數字利維坦的內在風險與數據治理[J].探索與爭鳴,2018(5):42-45.
[10]徐雅倩.技術、國家與社會:技術治理的現代面向及其反思[J].自然辯證法研究,2021(6):39-44.
[11]鄭磊.數字治理的效度、溫度和尺度[J].治理研究,2021(2):5-16,2.
[12]許歡,尚聞一.美國、歐洲、日本、中國數字素養培養模式發展述評[J].圖書情報工作,2017(16):98-106.
[13]劉培功.社會治理共同體何以可能:跨部門協同機制的意義與建構[J].河南社會科學,2020(9):1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