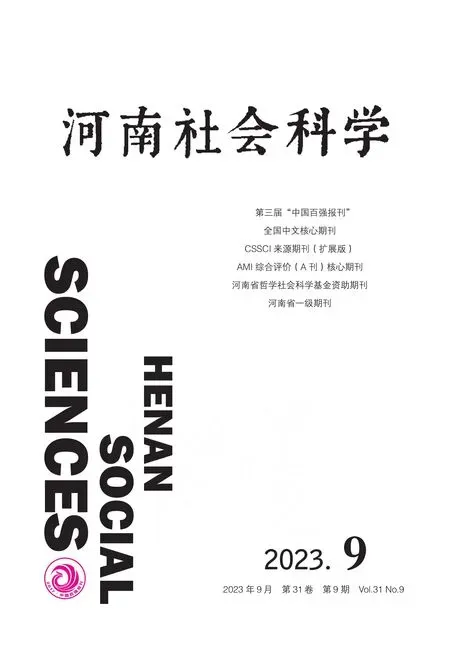群體行動中主事性的限制與擴充
賈 青
(1.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哲學院,北京 102488;2.中國社會科學院 哲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STIT邏輯對群體行動的刻畫
STIT邏輯是一種刻畫主事性(agency)的模態邏輯。STIT邏輯建立的基礎是將行動(actions)理解為一種具有主事性(agency)的事件(events)。這里所謂的主事性可理解為一種具有客觀性的意向性(intension),即行動者不但頭腦中要有一個想法或者意向,還要通過行動將這個想法或者意向實現出來。例如,行動者α在頭腦中有一個想法是“把窗戶打開”。如果這個想法僅僅停留在α的頭腦中,那么這就是一個意向性。如果α通過自己的行動確實把窗戶打開了,那α就通過自己的行動完成了自己頭腦中的想法,即α通過行動建立了自己與事件(窗戶被打開)之間的聯系,實現了主事性。基于此,我們才可以將主事性理解為行動者對事件的(完全)控制。因為主事性將行動從事件中區分出來,所以對主事性的刻畫才被視為一種對行動的刻畫,STIT邏輯才能被稱為一種行動邏輯。
STIT 邏輯對主事性的刻畫體現在句法和語義兩個方面。在句法層面,如果令α表示任意的行動者,A表示任意的語句,[·]表示任意的dstit算子(即連接行動者和事件的二元算子),那么任意的行動都可被表示為:[α]A[1]。在群體行動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將行動者α替換為包含多個行動者的群體G,因此任意的群體行動都可被表示為[G]A,其中G 是一個行動者集合且其中的元素多于或者等于2。
在語義層面上,STIT 邏輯的框架以BT(branching-time)框架為基礎構建。任意的二元組
在BT 框架的基礎上,STIT 邏輯的框架可被構造為一個四元組
上述語義解釋是對STIT 邏輯中dstit 算子的語義解釋。由于這一算子極有代表性,所以本文中我們都將以這一算子為例來說明STIT 邏輯的句法和語義。由上述這一語義解釋可知,一個單個行動者的行動為真(或者說單個行動者的主事性為真)當且僅當其在當下時間點的選擇保證了這一行動(具體來說是行動所導致的事件結果)為真且該行動不必然為真。
對于群體行動而言,STIT邏輯將群體行動區分為簡單的(plain joint)群體行動和嚴格的(strict joint)群體行動。兩類群體行動都強調要滿足行動者的獨立性條件(independence of agents),即要求不同行動者進行群體行動時不相互干涉,每個行動者仍然保持自身行動或者選擇的獨立性,不被其他行動者所影響。具體來說,如果用[G]aA表示簡單的群體行動、用[G]bA 表示嚴格的群體行動,那么在STIT邏輯的模型M 以及任意的時間歷史對m/h 下,某一簡單的群體行動[G]aA為真,當且僅當(1)Choice(α,m)(h)中,所有歷史上A 都為真;(2)存在一支歷史h1,使得A 在h1上不為真。也就是說,G 中所有行動者在時間點m 下的選擇都保證在歷史支h 上A 為真,但是A 并不是必然為真;在STIT 邏輯的模型M以及任意的時間歷史對m/h 下,某一嚴格的群體行動[G]bA 為真,當且僅當(1)[G]aA 為真,(2)對于G 中任意的非空子集F而言,[F]aA都不為真[2]。
由上述的語義解釋可知,無論是簡單的群體行動還是嚴格的群體行動都遵守決策論的要求,要求行動者具有獨立性。所謂嚴格的群體行動也只是要求群體行動所達成的結果A并不能由該群體中任意的一個小群體所達成。可見在群體行動的刻畫中,STIT邏輯并未說明主事性之間的相互影響或者作用。由于邏輯學中其他的行動理論(如PDL 等)對主事性的關注較少,因此也未能在群體行動的刻畫中注意到不同主事性的相互影響或者作用。
二、主事性的限制與擴充
在群體行動中,不同行動者之間主事性的相互交纏和作用是極為普遍的。例如α和β兩位畫家一起作畫。這種作畫可能有兩種情形:首先是兩位畫家各畫各的。無論是每人一塊畫布還是一塊畫布一分為二,兩位畫家的繪畫工作都互不打擾。其次則是兩位畫家一起畫一幅畫。畫家α將畫布染成淡紅色,然后畫家β根據α所畫的底色開始畫風景,之后α再根據β的風景畫開始點綴小昆蟲。這兩種情形中,STIT 邏輯只能幫助我們刻畫第一種,卻無法刻畫第二種情形下不同畫家之間的互動。
當然,在第二種情形下可以說,不管不同行動者之間是如何互動的,在上一行動者做完自己的行動(畫好自己的那一部分)之后,后面作畫的行動者在其當下所處的時間點上都是在完成自己的一個單獨的行動,因此無論是否考慮之前行動者的行動,當下行動者都是在憑借自己的主事性來完成自己的行動。這種說法沒有問題,但是卻忽略了不同主事性之間的相互影響,而這種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卻恰好是群體行動最大的特點之一。因此我們才需要將這一問題提出來加以解決。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作畫這一全體行動中,畫家α和β的主事性是一種相互限制的關系。例如,畫家α可能會畫小動物,也可能會畫小昆蟲,但是由于畫家β已經畫好了風景,所以α只能配合β已經畫好的風景來畫小昆蟲;而畫家β可能會畫黑色天空中的星星,也可能會畫淡紅色夕陽下的風景,但是由于畫家α已經畫好了淡紅色,所以β只能配合α已經畫好的淡紅色背景來畫風景。因此,兩位畫家在作畫這一群體行動中的主事性是一種相互制約、相互限制的關系。
除了這種相互限制的關系,不同行動者的主事性之間還可能是相互擴充的關系。例如大家通常所說的教學相長。老師幫助學生了解新的知識、擴充他的知識體系進而為其提供更多可能的選擇。例如,某種題型,學生原來只會兩種做法,現在經過老師的教導后會四種做法。與此同時,在與學生的討論和學習中也能讓老師了解自己知識體系的不足進而加以完善。例如,老師受學生啟發改進甚至修正自己之前的一些想法或者問題,進而改善授課方法、發表論文等。由此可見,在教師與學生構成的群體行動(教學相長)中,彼此都為對方提供了比原來更多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可以被刻畫為STIT 語義框架中的歷史進而為群體行動中的行動者提供更多可能的選擇。
當然,現實生活中的群體行動更為復雜,很少會出現僅限制主事性或者僅擴充主事性的情況,更多的情況是對主事性的限制和擴充在群體行動中并存。例如,群體行動的不同行動者中有的主事性被限制、有的主事性被擴充或者某些行動者的主事性先被限制后被擴充等。本文中,我們將以限制和擴充兩種情況為基礎,先進行一些簡單的刻畫,以期為后來的研究打好基礎。
對于群體的主事性或者意向性問題,主要有兩種處理方案:第一種是將群體的主事性視為一種“我們的主事性”(we-agency),即將群體行動理解為群體內部不同成員共同決議的結果,因此是群體中所有成員共同的主事性;第二種則是將群體的主事性視為不同于“我的主事性”(I-agency)的復合體,即將群體行動理解為群體中不同成員主事性的組合[3]。這兩種方案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對下面這一問題的回答上,即將群體行動的主事性視為一個整體還是不同部分的組合。本文中,為了更好地刻畫不同行動者主事性之間的影響和作用,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主事性之間的限制和擴充關系,我們將采取第二種處理方案。
三、動態方案的引入
由STIT邏輯的語義可知,無論是對單個的行動還是群體行動,對于主事性這一二元關系STIT邏輯都有兩方面的要求:(1)行動者在哪些歷史或者說可能性中進行選擇進而履行自己的行動。例如在上面的畫家作畫的例子中,畫家α可以將畫布染成淡紅色,也可以把畫布染成黑色、藍色等。這些都是不同的歷史,或者說可能的選擇。在這些不同的選擇中,畫家α的選擇或者說履行的行動就是把畫布染成淡紅色。(2)主事性所導致的行動不能是必然為真的。這是因為如果某一事件必然為真、必然會出現,那么不管有沒有行動者的主事性,這一事件都會出現,所以這一事件的出現也就跟行動者的主事性沒什么關系了,因此也就無法刻畫行動者與事件之間的主事性聯系。
可見在STIT邏輯的語義中,所有的歷史都是確定的,一個行動者在某一個確定的時間點上就是會面對那么多可能性。然而,由主事性的限制和擴充我們了解到,在群體行動中,由于其他合作者所作出的不同行動會導致行動者自身在某一時間點下所面臨的歷史是變動的:在行動者主事性被限制的情況下,行動者所面對的歷史會減少;在行動者主事性被擴充的情況下,行動者所面對的歷史會增多。因此,我們需要一個動態的方案來刻畫歷史的這種變動,進而刻畫群體行動中主事性的限制和擴充。這里,我們將引入動態認知邏輯(dynamic epistemic logic)中的方法來處理這一問題。
動態認知邏輯是一種刻畫知識(knowledge)和變化(change)的邏輯。動態認知邏輯是一類邏輯,其中還包含不同的分支,例如認知邏輯(epistemic logic)、信念修正(belief revision)、公開宣告邏輯(public announcements logic)等[4]。雖然這些分支在句法、語義以及公理系統等方面都不甚相同,卻都以多主體的克里普克模型(multi-agent Kripke models)為基本結構。動態認知邏輯致力于使用動態的方法刻畫信息(information)以及知識等的變化過程而不是單純的變化結果。
在動態認知邏輯看來,話語(discourse)可被理解為一個認知過程,說話(utterance)的意義(meaning)就在于改變交談中參與者所擁有的信息狀態。因此可以說,“意義”在動態邏輯中并不僅僅意味著真值,更多地應該意味一種更新條件(update condition),即由說話者所說出話語帶來的信息的改變。例如在課堂上,老師就是說話者,學生是這門課的參與者。在老師說話的過程中就會將新的信息或者說新的知識傳授給學生,由此改變學生原有的信息結構或者說知識儲備,這就是對學生原有信息或者知識的更新。
動態邏輯從創立之初就著重刻畫說話者和聽話者之間的互動交流對信息狀態的改變,由此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技術手段(例如模型的動態更新等)也強調刻畫說話者和聽話者之間的交流和互動以及這種交流和互動所導致的信息狀態的改變。所謂的說話,在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看來說話就是一種行動,說話者和聽話者之間的交流互動就可以理解為一種群體行動。相較于STIT 邏輯中的群體行動刻畫方案而言,動態認知邏輯中的技術手段更能幫助我們厘清不同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情況,因此,我們才需要引入動態邏輯中的技術手段。
以公開宣告邏輯為例,該邏輯的基本句法是在命題邏輯的基礎上增加知道算子K、公共知識(common knowledge)算子C 以及算子{·}得到的。對于系統中任意的合適公示φ和ψ,{φ}ψ就表示在宣告了φ之后ψ成立。由于動態認知邏輯的框架是以多主體的克里普克模型為基礎構建的,所以對于任意的模型M,其中應該包括三個元素,分別是可能世界構成的集合W、二元關系R 以及賦值函數v。相對于任意的模型M以及M中任意的可能世界w,{φ}ψ為真,當且僅當如果φ在模型M中以及可能世界w下為真,那么ψ在模型M|φ中以及可能世界w 下為真,其中M|φ表示將M 中的可能世界集W 限制為φ在其上都為真的可能世界構成的集合。
公開宣告邏輯中的算子{·}刻畫出了群體行動中不同行動結果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在STIT 邏輯中引入這種動態方案以刻畫群體行動中不同主事性之間的限制和擴充關系。
四、模型動態更新下的群體行動刻畫
如果以履行行動的時間順序為標準,那么群體行動可被分為兩類,即同時履行的群體行動和不同時履行的群體行動。所謂同時履行的群體行動就是指那種群體中所有的行動都同時履行的群體行動。例如上課時,所有同學都在相同的時間(段)上履行聽課的行動,這就是一個(學生聽課的)群體行動。除此之外,其他的群體行動都是不同時履行的群體行動。如果群體中的行動不同時履行,那么不同行動的履行時間必然會有時間上的前后差別。例如回答問題時,一個行動者先提出問題,另一個行動者再根據之前提出的問題進行解答,這就是一個不同時履行的群體行動。
在同時履行的群體行動中,行動者很難感受到其他行動者的影響或者制約。就算行動者感受到了,但是由于行動的同時性履行我們也很難在群體行動被履行的當下對不同主事性之間的限制和擴充做一個分析。但是在不同時履行的群體行動中,由于不同行動者在履行自己行動的時候都要受到之前行動的影響(群體中第一個履行的行動除外),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談論主事性的限制或者擴充問題就是必須的。本文中,不同時履行的群體就是著重研究的問題。
針對不同時履行的群體行動中主事性的限制和擴充,我們將使用歷史的動態化處理方案來刻畫。
在STIT邏輯原有句法的基礎上,我們增加算子{·}-和算子{·}+。對于任意的語句B以及任意的行動[α]A,{B}-[α]A表示行動[α]A被限制到那些B為真的情況下,{B}+[α]A表示行動[α]A被擴充到那些B為真的情況下。可見,{B}-[α]A和{B}+[α]A可在句法層面上被用來分別表示主事性的限制和擴充。
在STIT邏輯的原有語義中,任意的STIT邏輯模型M都是一個五元組
在STIT邏輯原有語義的基礎上,我們增加如下的概念。對于任意的語句A 和B,我們仍用HA表示A在其上為真的歷史的集合。除此之外,用H-B表示B在其上為假的歷史的集合。用HA∩B表示A和B在其上都為真的歷史的集合。用HA∪B表示A或B在其上為真的歷史的集合。同理,HA∩(-B)就表示A 和?B在其上都為真的集合,HA∪(-B)就表示A 或?B 在其上為真的集合。
在此基礎上,對于{B}-[α]A,其在模型M 以及時間歷史對m/h 下為真,當且僅當在模型M 以及時間歷史對m/h下,[α]A為真,且h屬于集合HB,即Choice(α,m)(h)包含于集合HA∩B且存在歷史集合HB中的歷史使得A不為真。其中,Choice(α,m)(h)就表示行動者α在時間歷史對m/h 下的選擇中包含歷史h的那一部分。
對于{B}+[α]A,其在模型M以及時間歷史對m/h下為真,當且僅當在模型M以及時間歷史對m/h下,[α]A為真,且h屬于集合HA∪B,即Choice(α,m)(h)包含于集合HA∪B且存在歷史集合HA∪B中的歷史使得A不為真。
由上面給出的句法以及語義解釋可見,不同時履行的群體行動中,主事性之間的限制和擴充都能夠被進行有效的刻畫。前一行動者履行自己行動后所造成的結果又是如何影響后面行動者的行動,都能通過這種歷史的動態刻畫方案來處理。
五、結語
通過引入新的技術手段,我們增強了STIT邏輯的群體行動刻畫能力。經典的STIT 邏輯只能刻畫同時履行的群體行動,在引入新的算子和語義之后,STIT邏輯增加了刻畫不同時履行的群體行動的能力。為了方便構建刻畫方案,我們對群體行動進行了簡單的分類。但是現實生活中的很多群體行動都會同時具有兩類群體行動的特點。例如行動者α先做一個行動,然后行動者β和行動者γ同時履行各自的行動,最后行動者δ再在之前行動(即行動者α、β、γ的行動)的基礎上,進行自己的收尾工作。這種情況比我們之前討論過的群體行動的不同情況都更為復雜,如何對這些復雜情況進行處理、給出合適的形式化刻畫方案甚至是構建形式系統并且證明系統的可靠性和完全性等工作,就是我們未來將繼續展開的相關研究。另外,針對同時履行的群體行動,雖然行動被履行的當下主事性的限制和擴充問題很難分析,但是行動被履行之后的時間點卻可被用來“回顧”之前群體行動中主事性的限制和擴充,這一點限于篇幅問題,本文沒有展開論述,還有待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