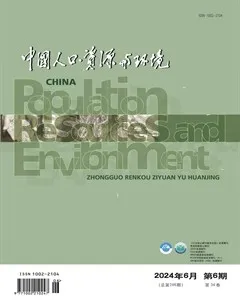環保法庭何以有效?











摘要 在推進環保法庭建設已經從司法政策被提升為國家政策的背景下,有關環保法庭的實際治理成效各方仍未形成共識,關鍵原因在于環保法庭提升地區生態環境治理績效的傳導機制不明。為此,該研究以能動司法理念為基本視角,提出法院與政府之間的“府院聯動”和由環境司法推動的環境議題“社會關注度”提升可能是環保法庭產生實效的主要方式,并進一步細化為“政府關注力度”“政府規制力度”“公眾關注度”和“媒體關注度”四條微觀路徑。實證部分運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實證檢驗了2011—2020年十年間135個中級人民法院環保法庭的設立對當地工業污染排放綜合指數的影響。研究發現,在控制其他影響因素的情況下,設有環保法庭的城市的工業污染排放比未設立的城市低11. 9%。中介效應模型估計結果表明,“政府規制力度”和“媒體關注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中介傳導作用。在發揮環保法庭環境改善功能的路徑中,政府的“行”勝于“言”,且媒體輿論場的作用大于民間輿論場。異質性分析表明,2015年前后國家層面一系列加強環境法治的舉措提升了環保法庭對于地方工業污染的治理效果,且環保法庭在經濟相對欠發達地區的作用更為明顯。就影響路徑而言,代表府院聯動的“政府規制力度”路徑影響較為穩定,而代表社會環境關注度的“媒體關注度”則體現出了較為明顯的時空異質性。據此,該研究的理論意義在于提示學界基于新時代能動司法理念,加強對環保法庭外部性的研究;政策意義在于,強調在堅持中央環境司法政策的同時,適度推動地區環保法庭的設立,優化環境司法制度保障,完善各方主體相協同的環境治理機制,尤其是加強環境司法中的公眾參與。
關鍵詞 環保法庭;能動司法;府院聯動;環境規制;媒體關注度
中圖分類號 DF823;F062. 2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4)06-0090-13 DOI:10. 12062/cpre. 20231201
2020年3月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共同發布的《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在高級人民法院和具備條件的中基層人民法院調整設立專門的環境審判機構”,這標志著因地制宜地推動環保法庭設立,從司法政策進一步被提升為國家政策。但是,盡管有來自國家層面的支持,理論界對環保法庭在環境治理中的實際成效仍未形成共識。區別于治理成效立竿見影的行政執法,司法常由于被動、中立的特性而被認為對社會治理作用有限[1]。雖然一些文獻證實,環保法庭的設立有效改善了其轄區內的污染治理情況[2],但仍有不少學者對此持懷疑態度,認為環保法庭解決環境糾紛的成效不及預期,治理優勢并不明顯[3-4]。造成這一分歧的重要原因在于,現有文獻對環保法庭影響地區環境的傳導機制研究不足。這使得一些學者對環保法庭的治理績效心存疑慮。在環保法庭已經被國家認可為中國現代環境治理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背景下,清晰地闡明環保法庭的作用機制已經迫在眉睫。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從強調司法與政府、社會有機協同的能動司法視角勾勒環保法庭影響地區環境治理績效的相關機制。
與現有研究相比較,本研究的邊際貢獻可能有以下幾點:①較為清晰地梳理與整合環保法庭對地區環境治理的影響機制,這是當前環境司法研究中,尚待填補之處。②為環保法庭的有效性提供新的證明思路,彌合法學與經濟學的認知分歧,一定程度上消解關于中國環保法庭實效性的爭論。③通過實證方法驗證環境司法能動協同現象[5]的存在,加深對協同治理在中國現代環境治理體系中重要作用的認識。
1 文獻回顧
有關環保法庭治理績效的討論,現有文獻大致分為兩種觀點。來自經濟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將環保法庭的設立視為準自然實驗,采用實證研究方法,證實環保法庭在地方污染治理中取得了多方面成效。范子英等[2]發現,環保法庭有效降低了工業污染物的排放,促進了地方環境污染治理。翟華云等[6]則證實,環保法庭的設置能夠有效地推動所在地區重污染行業上市企業進行環境治理,并發現了環保法庭成效的地區異質性,市場化程度更高的地區的環保法庭設置對促進企業環境治理更為有效。王鳳榮等[7]則關注到了環保法庭與企業綠色成長的關系,發現中級法院環保法庭的設立有助于推動企業的綠色并購行為。總體而言,社科學者就環保法庭所進行的實證研究,雖然數量不多,但方法嚴謹,結論可信度較高,幾乎一致性地證實,各地環保法庭的設立是中國環境治理近年不斷取得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
另一類觀點則以法學學者為代表,主要以經驗觀察和制度分析為方法,其態度上支持加強環境司法,但對環保法庭的現有成績卻普遍不甚樂觀。由于此類文獻較多,僅舉其中有代表性者述之。張式軍[8]基于觀察指出,多地環保法庭自成立以來,一直處于無案可審、“等米下鍋”的尷尬境地,他認為主要原因在于環保法庭受案范圍過窄且缺乏統一性規范。由然[9]則將環保法庭與環境行政規制進行比較指出,環境司法無案可審的原因在于制度運行成本較高,但激勵效果不足,因此相對治理優勢不明顯。上述學者有關“無案可審”的說法可能略顯夸張,但環保法庭“案件來源不足”也是觀察者的普遍共識[10]。現實中環境糾紛大量存在,但進入到司法程序的卻少之又少[11]。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在《環境資源審判白皮書》中公布的環境案件規模雖然看似達到了數十萬量級,但有學者指出,由于環保法庭采取審執合一體制,下級法院的環境案件統計中行政非訴案件比重過大,一些法院甚至占比近八成[12]。換言之,如果僅計算審判案件,環境案件的規模仍是相當有限的。總體而言,法學學者雖然看好環保法庭的未來發展,卻又認為其當下成效有限,形式意義大于實質意義,普遍存在著環保法庭受案源拖累,不能徹底發揮其治理潛力的憂慮。
上述兩種觀點的分歧,固然有因研究范式不同而產生的理解差異,但其關于環保法庭成效的見解沖突仍是顯而易見的。一個令人困惑的“謎題”是,為什么被學者普遍觀察到“無案可審”的環保法庭,卻又在其地區內產生了實際的環境治理績效?如果現有的實證發現是可信的,那么上述分歧表明環保法庭影響地方環境治理的機制很可能不限于對環境糾紛的司法解決,而是在案件審判之外另有路徑。這恰是現有文獻尚未闡明之處。
2 分析框架與研究設計
2. 1 基于能動司法的分析框架構建
長期以來,司法在國家治理中被視為一個邊緣且被動的角色。但近年來中國法院系統所提出的“能動司法”理念致力于探索一條不同于以往的司法參與治理路徑。司法能動主義的原初含義是指法院在適用法律審判個案時超出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直接回應社會演進現實。但中國法院所提出的能動司法理念與之不同,它更加強調法院要積極主動參與社會管理創新,通過一系列實踐策略融入國家治理體系之中,對完善社會治理發揮直接作用[13]。能動司法理念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法院的傳統角色定位,它要求法院本身是一個能動的治理主體,且愿意積極參與到社會綜合治理之中。而晚近興起的中國環境司法正是由能動司法理念所孕育的,作為其代表性成果的環保法庭從創設到推行都滲透著能動司法的基因,是司法主動回應環境污染現實的產物[14]。從現實來看,由于環境權與環境治理的公益屬性,以及環境法規范的儲備不足,坐等案件上門顯然并非良策,這就使得與傳統司法相較,環保法庭在治理實踐中必須具備更高的主動性與積極性。觀察當前環境司法的具體實踐,環保法庭參與環境治理大致可分為兩條主要路徑:政府路徑與社會路徑。前者主要通過環保法庭積極與當地政府合作開展環境聯合治理行動,即“府院聯動”而體現,后者則主要基于環保法庭設立所產生的社會影響而發揮作用。
首先,“府院聯動”機制是既有研究中被忽視的一環。“府院聯動”即法院與政府的聯系互動,近年來為法院系統積極倡導[15]。在當下環境司法現實中,其于現實有跡可循。一方面,在司法政策層面,最高人民法院近年來在多份環境司法文件中持續強調要強化能動司法,推動環境審判機構“做好與行政機關的協調配合”[16];另一方面,在司法實踐層面,下級法院已經普遍通過司法行政聯席會議[17]、司法建議[18]、信息共享[19]等方式與當地環境職能部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機制,一些地方法院和政府甚至共同出臺了環境治理文件[20]。這說明,當下法院已經通過“府院聯動”機制廣泛地參與到地區環境治理之中。
地方政府是環境質量的關鍵責任主體[21]。環保法庭對政府的影響可能存在兩個微觀機制——政府環境注意力與政府環境規制行動。二者分別代表了地方政府的“言”與“行”,與環境治理績效有直接關系。在既有研究中,學者多認可中央政府對環境議題的關注推動了地方政府環境注意力的提升,但對地方環境注意力與環境規制行動之間的關系仍存在爭論,而環保法庭設立與二者之間的關系更缺乏驗證。政府注意力理論認為,政府注意力驅動政府治理決策,調節政府在特定政策上的資源投入,對治理決策的執行結果極度重要[22]。王印紅等[23]基于對30個省級政府工作報告的歷時性分析發現,地方政府對生態環境的注意力受到中央的推動,總體上注意力強度逐年增加,但其增強并不必然導致相應的環境治理行動。張坤鑫[24]則基于地級市面板數據指出,在地方環境治理中,中央問責力度倒逼地方政府將更多注意力分配給環境議題,但政府環境注意力與政策執行力之間,并非線性相關。就環保法庭與二者關系而言,由于地方法院的人財物等資源主要仰賴地方政府供給[25],當地環保法庭的設立勢必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或默認。在設立溝通過程中,地方環保法庭可能從司法角度向政府提示地方環境污染的嚴峻性,從而觸動當地政府加強對環境議題的關注。同時,環保法庭的設立也為法院所倡導的環境治理“府院聯動”提供了組織基礎,強化了其聯動地方環境職能部門的組織抓手,這有利于法院與政府正式溝通機制的建立與加強,這從環境行政處罰的執行申請日漸成為環保法庭的主要業務中可以窺見一二。
其次,環保法庭對環境治理的社會傳導機制也尚未被充分研究。在社會治理中,社會監督是政府監督與司法監督之外的另一重要監督方式,構成了一種非正式的制度環境[26]。而輿論監督則是社會監督的主要呈現方式。環保法庭的設立不僅意味著地方環境治理體系的優化,而且對激發社會層面的環境輿論監督有潛在促進作用。大眾傳播學將社會輿論場區分為“媒體輿論場”與“民間輿論場”[27]。對于前者,環保法庭設立本身作為當地的公共新聞事件,勢必引起當地公共媒體的關注和報道,進而提升環境議題在公共新聞議程中所占的份額。對于后者,環保法庭為解決當地的環境污染頑疾而設,其對環境糾紛難題的解決潛在地提升了當地民眾的生態環境福祉[28],從而可能帶來更多的社會關注。
在輿論監督與環境治理的現有研究中,多數研究聚焦于公眾對環境議題的關注如何影響地方環境治理。此類文獻的早期研究發現,轄區內的居民抱怨會顯著地影響當地政府的環境治理偏好[29]。而晚近的研究則更為細致地展現出公眾環境關注度在改善城市環境污染狀況中的傳導機制[30],以及公眾對不同污染類型的關注偏好[31]。另外,少數研究注意到媒體關注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證實媒體關注,尤其是媒體對企業污染的負面報道會顯著增加企業的環保投資,起到了公司治理的作用[32]。需要指出的是,在議程設置理論中,盡管McCombs等[33]指出媒體能夠透過議題設置影響公眾關注,但有學者發現,二者在中國語境中并非總是一致,在一些事件中媒體關注議題與公眾關注議題也存在著相背離的現象[25]。因此,環保法庭的設置對公眾關注和媒體關注的影響不能一概而論,經由此二者的傳導機制也可能存在差異。
總而言之,政府與社會傳統上是地方環境治理的主要參與主體,但近年來能動司法理念指導下的環境司法主動參與地方環境治理實踐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作為環境司法代表的環保法庭既積極推動政府從“言”與“行”兩方面加強環境治理,也潛在地塑造著公眾環保意識與媒體議程設置(圖1)。綜上,文章提出以下假說。
H1a:環保法庭的設立能夠增強地方政府的環境注意力,從而對地方環境治理績效產生積極影響。
H1b:環保法庭的設立能夠增加地方政府的環境規制力度,從而對地方環境治理績效產生積極影響。
H2a:環保法庭的設立能夠提升當地民眾對環境議題的關注度,從而對地方環境治理績效產生積極影響。
H2b:環保法庭的設立能夠提升當地媒體對環境議題的關注度,從而對地方環境治理績效產生積極影響。
2. 2 研究設計
2. 2. 1 模型設定
自2007年始,環保法庭在中國各地市迅速發展。在本文2011—2020年共十年的觀測區間內,全國135個地級市中級人民法院陸續設立了環保法庭。這就為使用多期雙重差分方法評估環保法庭的影響提供了適合的條件。參照已有研究的做法[2,34-35],本文以多期雙重差分法(Time?varying DID)為基準回歸模型,首先估計環保法庭成立對于工業污染綜合指數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