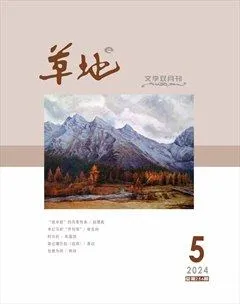父親是一棵樹
父親第一次揍我,是因為一棵樹。父親在門口的路邊栽下一排細細的水杉樹。頑皮如我,在父親走開后,拽著一棵樹開始搖晃,越搖越使勁,恨不得整個人都要拽在樹上。結果不言而喻,樹倒了,我在樹倒下的那一刻飛身離開。還沒走幾步,我的身子突然像被另一種力量拉起。我回過頭,看到的是父親嚴肅的表情。這是我從沒看到過的駭人表情。我想要逃離,卻被父親厚實的大手拉住。父親沉喝了一聲:“你在做什么?為什么要這么做!”我還沒來得及說話,就被父親拎到了那棵倒下的水杉樹旁,歪倒在地的水杉樹裸露的樹根上,還留有些許的泥土,和不久前澆過水后的根部的濕潤。父親一個巴掌打過來,我還沒來得及反應,很快伴隨著就是難以控制的哭聲。
我在哭,父親也不管我,去找了鐵鍬,把水杉樹原有的樹穴挖出來。澆過水的土濕濕的,挖起來并不吃力。父親將水杉樹重新種好,又填上干土,用鍬背拍打幾下。我的手還捂著眼睛,早已哭不出淚水,哭出的只有我虛張聲勢的喊叫聲。
父親又拎來了一桶水,水在他一搖一晃地走動之間,看起來像要潑出來,卻并沒有。
我還站著,看著父親取了水瓢,將水輕灑在又種下的水杉樹的根部,泥土喝到水,輕輕地陷落下去,噗噗地像呼吸。父親早已洞察到我在偷看,說:“要來澆水嗎?”我低低地應了聲:“嗯。”把捂住眼睛的手放下來,接過他手上的水瓢。小小的我喜歡玩水,就像眼前我給樹澆水,一瓢又一瓢緩緩地澆上去。很快,水杉樹的根部已經漫開了水,父親說:“給別的樹澆吧,它們也需要水。”我拎起剩余的半桶水,還有些沉,拎起來又放下,尋求幫助的眼神看向父親。父親說:“你用點力,再試試。”我用力去提桶,還是沒提起來,最后我幾乎是低身拽著把半桶水拉到了旁邊的一棵樹。半桶水很快澆完了,并沒澆上幾棵樹。我的眼神又看向了父親,父親說:“還想澆水嗎?”我點頭說:“想。”父親說:“那就自己去打水。”我拎著空桶,到了河邊,試著將桶斜放下去,桶加上桶里水的重量太沉,我拉不上來。不得不,我又重新把桶放下去,將水倒掉一部分。反復幾次,桶里還剩一小部分水時被我拉拽上來。過程中,父親一直站在我身旁,特別在河里取水時,父親就在我伸手之間的距離。這河有點深,每年夏天都會淹死幾個人。但在我幾次轉頭尋求父親幫助時,他又不容置疑地搖頭拒絕。
難以形容這半天我是如何澆完那排水杉樹的。母親從外面回來,看到一身臟兮兮的我,特別是衣服褲子都濕漉漉的還沾滿泥巴,簡直驚呆了。母親說:“你干什么了?搞得這么臟。”又說在旁笑嘻嘻的父親,“你是什么情況,也不管管!”父親朝我眨了眨眼睛,像我們之間的秘密似的,說了句:“不能說。”我也快樂地說:“不能說。”我早已忘記因為拉拽水杉樹被父親打得大聲痛哭的事情。
后來,我還悄悄地問過父親,“為什么要費那么大勁在路邊種樹,又不是種在我們家里。”
父親突然表情變嚴肅,說:“盡管不是種在我們家里,但在我們家門口,在我們生活的周邊,那也是和在我們家是一樣的……”
父親說了很多話,我認真聽著,又茫然地不知他在講些什么。
父親似乎看出了我的迷惑,笑了,說:“將來你會懂的。”又摸了下我軟軟的臉龐,剛剛被他打過的地方,說:“還疼嗎?”
我搖搖頭說:“不疼了。”緊接著又說:“我還要給它們澆水,讓它們快快長大。”
父親贊許地說:“你也要快快長大。”
父親干活的地方是一大片的灘涂,完全是由長江水沖積而成的泥沙地。這樣的灘涂之間,都不需要撒種子,連綿不絕一眼望不到盡頭的蘆葦就這樣自然地生長,這也許就是大自然的奇妙之處。對于這一切,我是新奇的,又是充滿無限向往的,甚至都不由得邁開腳步準備走向這一大片偌大的蘆葦地。
父親馬上制止了我,說:“那邊還不能去。”
我問:“為什么?”
“這里原先是江,這樣的土質還不足以讓我們放心地走下去,有可能像踩在淤泥里一樣把我們的腳我們的身體都吞沒。”緊接著父親又說:“淤泥你知道嗎?”
我點點頭,我看過一個電視劇,幾個在野外的探險人不幸踩在了一塊淤泥地里,越掙扎越下沉,后來幾個人都因此喪命了。
加之父親從未有過的嚴肅表情,讓我深感這個淤泥確實是足夠可怕的事情。
原先,我來這里覺得挺有趣的,還再三央求父親一定要帶我來。因為父親一直說,他在做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我看到了父親眼中的光,問他什么事情?父親說:“可以讓我們的國土可利用的陸地面積增大。”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問道:“為什么會增大,怎么又會增大呢?”父親又不回答我了。帶著這樣的疑問,我央求媽媽,一定讓我和爸爸去。母親說:“那里荒郊野外,有什么好看的。”但母親拗不過我,終于同意了,只是特意叮囑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我樂陶陶地跟隨父親來到這里,卻看到又是這樣的一種景象。這似乎不怎么好玩了。
父親還硬生生地說:“跟著我,一定不要亂跑。”
我點頭。
父親往前走,踩在腳下的土和我們住的地方的土有些不一樣。都是土,為什么會不一樣呢?我不懂。我也不敢問父親,父親剛剛兇巴巴的樣子嚇到了我。
一路上,碰上了父親的同事,穿著和他一樣的工作服,又都臉黑黑的,有點被風吹多了的老相。
他們說,“帶兒子來看看啊?居然都這么大了。”
父親回應著,“對,一轉眼個兒就高了。”
他們又說道:“和你以前拿來的照片完全不一樣了。”
“長長就走樣了。”
他們又說:“場長在找你,你趕緊去吧。”
父親說:“好嘞。”
我沒有吭聲,一直聽他們在交談,其實我想問,我有什么照片被父親帶來了這里?是小時候坐模型馬上哭鼻子的照片嗎?記憶中好像也就這張照片了。但我還是沒問出口,我怕父親又兇巴巴地瞪我。
父親帶我走過了他們在改造的一大塊田地,像豁然開朗般的景象。我還禁不住“呀”了一聲。那里堆放了很多的農具,擺放得都非常整齊有序,這讓我的好奇心一下又上來了。他們是怎么做到改造土地的?我其實很想親眼看到。但父親又把我帶進了休息的工棚里,一定要我不能出去。工棚里有父親給我準備的玩具和零食,父親說:“這些都是你的,別亂跑,不然什么都不給你。”
父親還反復說:“知道嗎?知道了嗎?”表情又變嚴肅起來。我點頭說:“知道了。”
走出工棚的父親和一個男人在說什么,然后父親和好幾個男人一起走進了那一大片的蘆葦蕩中,不對不對,父親不是說不能走進蘆葦蕩嗎?那他們怎么走進去了呢?
一排水杉樹,一大片蘆葦蕩,這些都是我小時候的深刻記憶。
接到母親打來的電話時,我剛開完一個重要會議,腦子有點蒙,拿起杯子準備喝口水時,電話就響了。母親說:“你趕緊回來吧,你爸又拿起鐵鍬,說要種水杉樹了。”
父親要種水杉樹,這還只是個小事。前幾天,母親急急忙忙打來電話,說都說不清楚,好不容易讓她慢慢講,才算聽明白——父親不見了!這好好的一個人,怎么就不見了呢?自從半年多前父親突然有老年性癡呆的癥狀后,他的許多行為都讓我們深感害怕,一個人默默地走出院子,走到大馬路上。這條我們家門口的路,早就從崎嶇不平的泥路變成了平穩又寬闊的柏油馬路,每天有無數輛車子快速開過,發出“轟隆轟隆”的急速呼嘯聲,而父親居然毫不畏懼地站在馬路中央,神情淡定地看許多年前他種下的那排水杉樹,如今都長成又粗又長的參天大樹了。好在鄰居趙叔看到,趕緊把父親拉回了院子里,很快就有一臺卡車疾馳而過,帶起了好大一股風。更嚇人的是父親經常會莫名其妙失蹤,母親明明把院門給鎖住了,她低身在院子里操弄蔬菜,等她沒多久起身時,發現院門不知什么時候被打開了,父親也不見了。父親肯定是找到了放在窗臺上的大門鑰匙,又悄無聲息地打開,再走出去的。母親著實被嚇出了一身冷汗,趕緊去叫鄰居趙叔、肖叔他們,大家也是一臉緊張,他會去哪里呢?不可能漫無目的地去找吧?母親突然眼前一亮,說,“肯定是去東灘濕地了”。母親說的東灘濕地,就是許多年前父親帶我去的蘆葦蕩。當然,那個地方早就不是蘆葦蕩了,后來經開墾后變成了魚塘、蟹塘,到今天已經成為城市最大的濕地公園,還是最大的候鳥棲息地。原本據說還有個方案,是要重新被開發,打造成為最高檔的集休閑旅游度假村為一體的一站式休憩區,后來不知什么原因被叫停了。
去往東灘濕地公園的路上,騎電瓶車的趙叔很快看到了一搖一晃高昂著頭慢慢向前走的父親。趙叔停下車,喊父親,“老傅,你去哪里?”
父親停下腳步,轉頭說:“你是在叫我嗎?”
趙叔說:“當然是叫你了,老傅,你連自己名字都忘啦?你這是去哪里呢?”
“哦,原來我叫老傅啊,我要去蘆葦蕩,剛剛場長叫人帶口信來,說讓我去上班。”父親說道。
早先時候還沒有東灘的說法,大家都簡易地叫那里“蘆葦蕩”。趙叔說:“誰讓你走那么慢,剛剛場長又讓人傳話來了,說今天要下雨,讓大伙兒休息一天,你不用去了。”
“是嗎?”父親抬頭看了眼天空,陰沉沉的似乎真要下雨,點頭說著,“我知道了。”
趙叔緊接著說道:“坐我的車吧,我帶你回家。”
父親看了眼趙叔的電瓶車,叉開大腿緩緩地坐上去。
晚上我到家時,父親果然已經回來了,一個人安靜地坐在桌子前,攤開的一副麻將牌,被他一枚枚地豎在那里,不是一直線的排列,而是很有規則,又有幾分錯落的排列。
我走到不遠處的母親身邊問母親,“爸又去東灘了?”母親說:“可不是嗎?還好他除了這個地方,別的地方也不會去。”嘆了口氣,母親又說:“你爸呀,喜歡和樹打交道,所以干了一輩子的灘涂開墾成農田,每天弄一身臭汗一身爛泥回來,他倒是樂在其中。”
我走到屋外,天空黑乎乎的,從屋子里照射出的燈光,隱約能看到院子里豎起的一排細細長長的小樹。前幾天還未曾見過,這無疑應該就是母親說的,父親又種的水杉樹吧?也不知道父親從哪里找來的這水杉樹,筆直矗立在我面前的樹,倒是方方正正、穩穩當當的。估計哪怕是來陣風,也不一定能立馬吹倒。但最好是不要起風,不然父親馬上會從屋子里沖出來,拿起工具給水杉樹打支撐。記得那年水杉樹種下沒幾天,就是一場呼嘯而來的暴風雨,父親不顧一切地沖到雨中,全身都淋透了,因為風雨而抖動著身子,卻仍繃著臉咬緊牙關將幾根木棍牢牢地豎在泥地里,榔頭用力敲擊下去,再用繩子為水杉樹做固定。后來水杉樹沒有一棵被刮倒,父親卻因為發高燒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
周末,我專程去了趟東灘濕地,父親曾經默默耕耘好多年的地方。這也是我第二次踏足這塊地方。小時候去過一次后,不知是父親不愿意再帶我去,還是我自己本身也沒太大興趣,后來就再沒去過了。在我稍大些時,開始了多年的在外求學生涯,更沒機會去那里了。一晃就那么多年過去了,時過境遷,父親退休,蘆葦蕩變成東灘濕地,時光真的是匆匆而過啊。
我把車停在了離大門口不遠的停車場,步行在東灘濕地轉了一大圈后,小時候對這一大片蘆葦蕩的印象已經找不到任何痕跡了,總覺得這里好大好大,比想象中的都大。以前這里只有蘆葦蕩,現在只在靠江水的位置有蘆葦蕩,大部分的地方都被種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水草綠植,之上是一條蜿蜒的漫長凌空木橋廊道,更類似于那種供游客觀賞游玩可以自由行走的場所。有無數只鳥兒從空中盤旋而來,或是在水草地里落下,或是在蘆葦蕩的頂端站立,也會探起身低下頭去輕啄,抬起頭時小嘴蠕動著,吃得是津津有味。我緩緩地行走,以期能捕獲更多腦子里的記憶,木橋、木平臺,和周圍牢固的木欄桿,都被打造得無比安全和井然有序,再不用像我小時候那樣,父親擔心我不小心掉入那塊蘆葦蕩中的泥潭中而拔升不起。
我無法獲知這一大片區域到底是有多大,就像我無法獲知這里停留了多少品類的鳥兒,更無法獲知父親在這里曾經灑下了多少汗水與青春……
從路邊走過的穿著一身工作服的保安,我不由得叫住他,“你能帶我去見你們這里的領導嗎?”
保安把我帶到了一棟管理房大樓,一個年紀和我差不多大的男人聽我緩緩述說我的父親在這里工作過,他原本平靜的表情突然變得波濤洶涌,不等我把話說完,他猛地握住我的手,非常激動地說:“你一定是傅萬樹傅師傅的兒子吧?”我愣了愣,很納悶他怎么知道呢?他接著說:“對,你不知道,我是當時場長的兒子,我們的父輩都在這里“戰斗”了好些年,我爸后來一直夸你爸,在蘆葦蕩干活時總是沖在最前面,手掘肩挑,開墾農田,挖溝造渠,筑堤壩,是干活的勞模。有一年,新筑的堤壩剛合攏,臺風突然來襲,為布置防范措施,你爸主動趕過來,忙了一天一夜沒合眼……我是畢業后來這里的,那時正好在搞東灘濕地的改建,我看著這里一大片一大片的蘆葦蕩被翻掉,一塊塊以前開墾下的田地得到保留,曾經的魚塘、蟹塘都被填埋,我很欣喜,因為我看到了施工設計圖紙,這里完全可以成為城市里的人來敞開呼吸快樂休憩的地方。意義還遠不止此,還可以成為候鳥的棲息地,有太多的鳥類,在飛過一眼望不到邊際的大海來到長江時,因為長時間的飛行體力不支,又得不到及時的食物補充而掉入海中,此時,鳥類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這里休息,我們也歡迎它們,像看見自己的好朋友們到來一樣。據不完全記錄,至少有三百多種鳥類,上百萬只鳥兒在這里遷徙停留。”
這個后來我知道了叫朱進的男人越說越興奮,臉上笑得如花兒般燦爛。我在為他做這一切可貴事情感到欽佩的同時,也暗暗明白,怪不得在濕地里的那些鳥類,看到我走過去時沒有任何驚慌,因為這里的人把它們當作了朋友,朋友之間是不需要害怕的。
朱進也和我談到了我的父親傅萬樹,時不時地會來東灘濕地,逢人就說這片蘆葦蕩里不能去,太危險了。這不由讓我有些汗顏。我說:“給你們添麻煩了。”朱進看了我一眼,“我并不覺得這件事麻煩,本來我也想找你。”他頓了一頓,又說:“我有一個想法,需要征得你的同意。”
我說:“你說吧。”
春暖花開時節,我又一次開車去了東灘濕地。停車場的保安早已熟識了我,不等我的車到,欄桿早早地高高豎起。我朝保安揮了揮手,表示感謝。
濕地的一處蘆葦蕩之間,搭起一大塊長長的親水平臺,底下是水,邊上是欄桿,頭頂是個可以遮陽,也可以擋雨的棚子。父親坐在棚子下的靠背椅上,好些年輕或年長的男男女女站著或坐著,饒有興致地在聽父親講述。父親說,“……當年這里可都是浩浩蕩蕩的長江水,不只是我們腳下的地方,其實圍繞這邊方圓幾公里的腳下土地,那時都是屬于長江的。江水不斷地沖積,泥沙在這里得到聚集,再堆積,慢慢地浮出水面,成為或高或低地淺淺陸地的雛形,與原有的土地連接在一起,鳥兒在這里停留棲息,這里再慢慢又長出了蘆葦,大自然就是這樣的神奇,人類并沒有在這里撒下種子,蘆葦就冒出來了,越長越多,越長越密集,成為了蘆葦蕩。看起來這里已經成為了陸地,我們就可以走進來了嗎?那當然是不可以的,因為這里的泥沙還沒經過翻整,如果貿貿然踩上去,很可能會陷下去,像踩在淤泥上,很危險……”
這就是朱進需要我同意的事情。不過這竟然給了我意外之喜,甚至說不可思議。父親原本已經有老年性癡呆的癥狀了,我站在他面前,他都會一臉茫然地問我,“你是誰?你怎么會在這里?”朱進請父親做專門的講解,講解好多年前,像他的父親、我的父親這樣一批人奉獻著他們的青春,不辭辛勞不顧一切地在這一片每年都在沖積增長的泥沙地上,開墾土地,讓一塊塊原本沒有價值的泥沙地,成為可利用有價值的田地,他們干著平凡其實又并不平凡的工作。他們在這里干了一輩子,開墾出了超過4000畝的農田。
父親一開始面對游客作結結巴巴地講述,時不時還停頓下,茫然地看一眼天空。但回憶的閥門就是這樣神奇。在父親緩緩地講述過程中,潮水一樣的往事止不住地往外涌,父親的話語也從生澀變流暢,臉上竟然也從蒼白變紅潤,甚至配合著還搖擺起手,像在打節拍。講到興起時,父親從位子上站起,對著不遠處奔騰翻滾的長江水,對著那一片隨風起舞的蘆葦蕩,像一名標準的演說家。
后來我咨詢了一位醫生朋友,說我的父親怎么一下子又恢復正常了呢?醫生朋友很細致地看了父親的病歷卡,他也表示出了驚訝,再三說:“這沒道理啊,真是不敢相信。”他后來跟我說,“通過回憶往事竟然能治療老年性癡呆,這堪稱是醫學界的奇跡了。”
東灘濕地管理公司每天會安排一臺車接送父親,父親的氣色也越來越好。父親開始能給母親做家務活了,還主動給我打招呼,“回來啦?”我說:“對,今天講得怎么樣?”父親像個指揮過千軍萬馬的將軍一樣,朝我一揮手,說:“挺好。”眼中綻放著若干興奮又激動的光芒。
父親還會從院子走到馬路上。馬路上依然車來車往,一輛輛車呼嘯著而過。我們已經不用擔心父親被車碰擦了。父親遠遠地看到車子開過來,他會馬上停住腳步。等看不到車子,父親再緩緩走過馬路。馬路的另一側,是父親許多年前種下的水杉樹,也是當年導致我挨打的水杉樹。這些水杉樹,已經高到一眼望不到樹頂了。
我走到父親身邊,說:“這些水杉樹,長得可夠快的。”父親點頭說著,“當初就這么短,這么細。”父親用手很清楚地給我比劃著。父親還指了指院子里那些細細長長的,他不久前種下的水杉樹,“它們,也會越長越粗,越長越高。”
我用力點著頭,又想起了什么,“蘆葦蕩,哦不,現在的東灘濕地,據說差點被建成了高檔度假村,后來不知怎么,又變成了濕地。”父親說:“不知道有沒有起什么作用,當年我聽說蘆葦蕩要變成高檔度假村,還給政府寫了好多信,反映我們的城市,除了鋼筋混凝土的高樓大廈,除了高檔度假村,也需要有讓人呼吸新鮮空氣的地方,更需要有讓候鳥停留棲息的地方……”
父親說得波瀾不驚,像在述說一件尋常事情,而此時,我已經驚呆了。
有一束陽光穿過水杉樹的樹葉之間,略顯斑駁地照在父親身上。我突然發現,穩穩站立在那里的父親,也像是一棵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