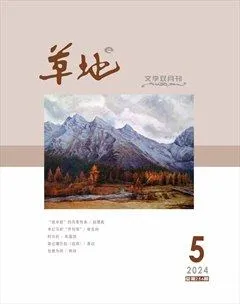比鏡像更豐富的川西以西
川西,一個蘊含深厚地理與文化底蘊的詞匯,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地理學概念,與川東、川北、川南遙相呼應,更為我們共同勾勒出四川這片廣袤土地上的多彩畫卷。
川西,顧名思義,四川的西部,對于地理學者而言,這僅僅是一個指示方向的詞匯,或許難以激起太多情感的漣漪。當這個詞匯跨越學科的界限,悄然融入文學作品的字里行間時,它便被賦予了生命,引領我們的思緒飄向那片遙遠而神秘的土地。
在文學的殿堂里,川西常常會加一個后綴“壩子”,而成為一個具有田園詩意的稱謂,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畫緩緩展開在我們的眼前。成都的繁華、樂山的秀美、德陽的古樸、眉山的溫婉、雅安的清幽……如同一顆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川西的大地上,散發著獨特的光芒。提及川西壩子,蓋碗茶、美女、美食、麻將,“少不入川,老不出蜀”,這些與川西緊密相連的詞匯自然躍入腦海,一種悠閑自得、慢條斯理的生活方式也接踵而來。
家琴的散文集《川西以西》,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這個概念在以往的地理學或文學作品中都鮮有提及,是對川西這一概念進一步的延伸與探索。
按照地理學的邏輯推斷,川西以西自然就是指成都平原以西的阿壩州、甘孜州等地。
一提起阿壩、甘孜,人們想得更多的應該是九寨黃龍,是四姑娘山,是稻城亞丁,是香格里拉……沒有翻開家琴的新書《川西以西》前,我眼前涌出的景象就是獨屬阿壩、甘孜的藍天白云,雄鷹翱翔;是高山聳立,綿延起伏;是大河奔流,浩浩湯湯;是山花爛漫,星空浩瀚;是飛揚的風馬,是靜穆的瑪尼堆;是寺廟傳出的晨鐘暮鼓是老阿媽口中喃喃的誦經……心中感念家琴將我生活了快六十年的川西以西寫進了她的作品,印成了書,留存下來。
翻開《川西以西》,一陣獨特的書香與我心中的感念融為一體。如同輕盈的白云在心頭升起,又如同拂面的清風從眼前飄過。
能讀書真好。能讀到自己想讀的書真好。
讀完《川西以西》,與其說她是一部散文集,不如說她是一部優秀的報告文學集。家琴以細膩的筆觸、真實的情感記錄了阿壩州這片廣袤大地上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在脫貧攻堅的浩大工程中,鄉村在國家的扶持下,在村民和各種幫扶力量的共同努力下,鄉村正從貧困的泥潭中掙脫出來,一步步走向富裕與繁榮。這部集子不僅讓我們看到了鄉村面貌的煥然一新,更讓我們感受到了那份來自內心深處的喜悅與自豪。
家琴曾給我說過她要寫阿壩州的一百個鄉村,因為在阿壩州,任何一個鄉村都是值得書寫的。《川西以西》實現了她的寫作計劃,全書分為《村人村事》與《涉水流經》兩大篇章。
在《村人村事》中,家琴捕捉了阿壩州鄉村的多樣面貌,從《云朵上的人家》中那漂浮于天際的村落,到《紅村日記》里記錄下的紅色記憶;從《梨鄉深處有人家》中彌漫的果香,到《夕陽余暉映草原》下牧歸的牛羊;再到《哈休的春天》里萬物復蘇的生機,以及《壤噶奪瑪村的夏天》中熱情如火的節日慶典,直至《遇見達格則》時那份不期而遇的震撼與感動……每一個故事,都像是一次心靈的旅行,引領我們穿越時間與空間,親身體驗那些平凡而又非凡的鄉村生活。
家琴六月去了西山,一個孟屯河岸邊理縣通化鄉的高半山村子,尋著浮云道,到了一個叫浮云牧場的地方,認識了浮云牧場的黃幺妹、余文正、楊志福、高波,品嘗到了浮云牧場正宗的農家菜老臘肉。
夜幕低垂,星光點點,家琴圍坐于農家的院落之中,眼前是瓜子散落、啤酒微涼、綠地如茵、柵欄輕繞、小徑蜿蜒、秋千輕蕩的溫馨場景。這些看似平凡的農家日常,在她的筆下卻化作了詩意的篇章,讓人仿佛能穿越時空,親身體驗那份寧靜與美好。《云朵上的人家》不僅是對一個村落的記錄,更是對一種生活態度的頌揚,一種遠離塵囂、回歸自然的向往。
曾有個喜愛文學的年輕人問我怎樣才能寫出好作品,還給我念了一段她所描寫的風景。從她的文章里我能看到優美的風景像一幅畫在我面前徐徐展開,畫里有聲有色,有形有景,你幾乎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文章就此止步了,我內心的期待并沒有出現。
怎么說呢?我是一個文學愛好者,也是一個寫作愛好者,雖然沒有寫出什么好作品,卻讀了很多好的作品,對好的作品也有一些體會。一部好的作品會有準確的表達,會有細膩的描繪,會有巧妙的構架,可以是現實的,也可以是浪漫的,可以是悲劇的,也可以是喜劇的。但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思想,思想有多遠,文學的路就能走多遠。如果家琴的文章止步于她所見的鄉村鏡像,自然是不能出彩的,她在西山村還聽到了浮云牧場興起的故事,浮云牧場的經營之道、經營現狀,更聽到了與浮云牧場相關的脫貧攻堅的故事,幫扶干部們的故事。這些故事放在浩大的脫貧攻堅工作中可能就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轉瞬即逝,但家琴看到了這朵浪花,并且把她原原本本地描述了出來,用“初識黃幺妹”“客棧的興起”“最真的守望”“楊福志的新生活”呈現給我們,讓我們讀到了平凡的村人村事中所蘊含的非凡的滂沱力量。
認識家琴主要是讀到她的詩歌作品集《卓瑪吉的風鈴》,后來讀到她的散文作品集《山里風》,再后來她又寫作了《蜀山之后》,正當我既驚異又羨慕她的寫作速度時,她的新作《川西以西》又來到了我手里。
《川西以西》是家琴無數次踏入鄉村,深入生活,對生活進行實地采訪和觀察后的真實描繪和敘述,展現新時代下的村人村事。這種真實性不僅體現在她對事件的描述上,更體現在她對人物性格、心理活動的真實把控與刻畫。
2022年盛夏,陽光熾熱而明媚,我們一行人從馬爾康啟程,懷揣著對文學的熱愛與對鄉村的向往,踏上了前往金川的旅程。此行,我們是為了參加由金川縣委宣傳部、金川縣鄉村振興局及金川縣文聯共同舉辦的筆會,一場關于鄉村、關于文化、關于夢想的盛會。路經周山,家琴要去周山采訪,我作為她的朋友陪著她去了。我們認識了周山村的支部書記羅爾伍,聽他講述了周山村的變遷,跟著他們參觀了村子最高處的卓斯甲土司的官碉、官碉下的寺廟、村子里的文化墻。離開周山村后我們按照筆會安排的線路參觀了金川縣正蓬勃發展具有典型意義的產業、文旅、村莊、田野。筆會結束前每到一處我也是心潮澎湃,想象也能提筆詩千行,筆會結束后,因為懶惰最終沒有寫出半個字。家琴則寫出了《梨鄉深處有人家》。
《梨香深處有人家》是一篇篇幅較長的文章,由“梨園深深”“周山村:向小康出發”“櫻桃紅遍甘牛社”“營盤山上的村莊”以及“馬奈,多元化的鄉村振興模式”五篇獨立而又相互關聯的文章組成。家琴以她獨特的視角和深邃的思考,將金川這個奔跑在脫貧奔康路上的地方,呈現得立體而全面。在她的筆下,金川不僅是一個充滿自然風光與人文底蘊的地方,更是一個充滿希望與活力的地方。每一個村莊、每一片田野、每一位村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書寫著屬于他們的故事與傳奇。
我們走的同一條路,參觀的同樣的景,聽的是同樣的故事,家琴用心用情地看,用心用情地記錄,讓我從她的文字里一點點回憶起那次筆會的一些細節來。我一邊讀一邊慨嘆家琴寫作的水平較之前又有明顯提升,慨嘆家琴作品中所具有的強烈的時代感,她能緊跟時代的步伐,關注社會熱點,讓更多的讀者可以了解到在脫貧的道路上金川的變化與時代的發展,感受到了時代的脈搏和氣息。
在《川西以西》這部作品中,家琴的視野更加開闊。她不僅描繪了金川的美麗風光,還將小金、馬爾康、紅原、壤塘、九寨溝、黃龍等阿壩州各地的風情一一展現。在她的筆下,不僅有壯麗的自然風光,更有感人至深的故事和鮮活的人物形象。她通過細膩的筆觸,將這些村莊的變遷與發展,以及那里人們的生活狀態,都生動地呈現在了讀者面前。
讀完這些作品,再回味家琴的話“阿壩州的每一個村莊都是值得書寫的”時,深以為然!她深刻的洞察力、敏銳的感受力及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將這些村莊的人物形象、事件場景、發展過程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在她的作品里看到了騰飛的木蘭,多彩的雙碉,還有透明的哈飄,洛威的村莊,久遠的柯盤,認識了這些村莊真正的守村人,字里行間盡是感染力和吸引力,讓我們不僅感受到了這個時代不斷豐富的物質,更感受到了這個時代人們正深刻變化的思想。
家琴最早寫詩,語言十分精練而富有詩意,隨著她對生活的認識與思考,她的作品中漸漸摒棄了華麗,卻又不失她本身所擁有的細膩溫婉,讓我們總能感受到一種獨特的韻味,一種融合集智慧、情感、精準、生動于一體的獨特表達。像清泉,潺潺流淌,像清風,徐徐而來,像細雨,潤物無聲,像陽光,溫暖大地,有時也像刀像戟,揭露社會的沉疴痼疾,非常成功又不露痕跡地將文學與新聞報道結合在一起。
報告文學兼具文學作品與新聞報道雙重性,報告文學是真實的、客觀的,報告文學又是生動的形象的。家琴的《川西以西》是對阿壩自然風光和人文歷史的生動描繪,猶如一面明鏡,映照出那些散落在阿壩州這片瑰麗土地上的鄉村,如明珠一樣正合著時代的節拍織成阿壩大地最美麗、最生動、最具有活力的社會肌理。
《川西以西》中的每一個故事都是平凡的,卻又能讓人感受到人性的光輝和溫暖。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體會到一種深深的感動和啟迪。
在未來的日子里,我們有理由期待家琴將用更加細膩的情感、更加深邃的思考、更加精湛的筆觸,記錄下生活中每一個值得銘記的瞬間。而那些即將誕生的作品,無疑將為我們揭示更多生活的真相,傳遞更多人性的力量,成為我們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