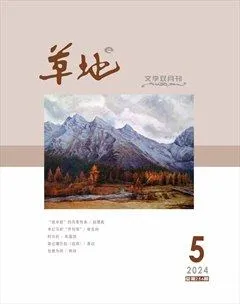時光機
一
大清早的,奶奶端了小簸籮過來。里面的小黃瓜頂花帶刺,番茄紅著圓臉蛋子。她照例不進籬笆院,似乎一進去就失了做婆婆的威儀。幾十年她記得那么牢,腳步拿捏得那么準。小白搖頭擺尾跑過來,討好地蹭一蹭老婦人黑臉綠幫的繡花鞋。老太太蹙起兩道細彎彎的淡眉,抬腳踢開小白。她探著身子把小簸籮放在黑籬門里的小網床上,轉身咳咳地走了。
小灶屋吞云吐霧。娘像一只被柴煙熏出穴的土蟬,也咳咳著鉆出來,她撩起圍裙擦著眼角嗆出的淚珠,努力張大眼睛四下里望。她剛才分明聽到了小白迎接熟人的動靜。可人呢?明亮的陽光晃得人眼花。她的目光落在網床的小簸籮上,心中倏然升起歡喜和柔軟來,細瞇瞇的眼睛放出喜悅的光。轉頭朝著爹爹喊:“早飯的菜有了!娘給送來的黃瓜番茄,新鮮地冒水呢。”
爹爹在打掃鴨圈。聽娘問話,卻不答言,只低頭暗笑。他早看見奶奶灰色的矮小身影拐進了西籬。娘還在那踮腳伸脖張望。軟紅舊衫子的婦人,身量小小,晨光里,尚未及夏日漂曬的臉兒,白生生泛著兩抹咳出來的胭脂紅,煞是生動。
爹爹撿拾出小半筐鴨蛋鵝蛋。小竹筐極小,仿佛只有爹爹的大飯碗那么大,那是鎮子上的姥姥編的。他喜滋滋捧到娘眼前,兩根手指捏起一顆巨大白鵝蛋,那蛋沾著新鮮落羽與鵝糞,在娘眼里卻是世間最美的鵝蛋。她眼里的喜悅撲出來,兩只手掌伸出去,像捧回一粒天鵝蛋,小心翼翼的。“大白鵝真是勤快呃,多讓人心疼!你看,你看!”她讓爹爹看那蛋殼上的一抹血跡,它彰顯著大白鵝下蛋時的費力與疼痛。
娘轉身喊小六丫頭。給奶奶送蛋去。每天早晨的頭一顆蛋,雷打不動地送到西籬去。奶奶不舍得吃。煙熏火燎的小灶屋窗戶,黃土剝落,凹陷出的窩窩,恰好嵌進去一只黃皮寡瘦的舊簸籮,千針萬線地重修舊補,里面的鵝蛋卻莊稼似的茂盛長出來。六丫頭知道,只要在小縣城里讀書的堂哥回來,小簸籮就立馬卸空了肚腹,一朝分娩似的。奶奶偏心,只心疼小叔和他的兒子們。六丫頭懷疑爹爹是奶奶當年討飯時撿來的,連累著東籬這一大家子都跟著不受待見。后來漸漸長大了,方知道奶奶不喜歡的是娘。可不是連帶著嫌棄娘生的兒女們?
奶奶偶爾來東籬門口,丟幾根菜園子里吃不完的蔬果,那也是提醒娘及時過西籬送蛋去。有時候,鵝屁股歇幾天,娘只好拿灰鴨與花母雞下的蛋來抵。奶奶便不高興,在自家矮矮的一圈籬笆里罵空:“果然是偷嘴的娘們黑了心的兒!哄弄老子么?惱上來給你們摔個七七八八蛋花黃......”每逢這時,娘不惱不急,敲著小陶盆給她的白鵝灰鴨花母雞喂食,小東西們討嬌地嘎嘎咯咯,娘的眼里都是寵愛。大白鵝長長的脖子,蛇一樣纏住娘的手腕,似有愧疚。娘拍拍鵝頭,柔聲細語:“大白呃,大白,今兒拌了厚厚的麩子,剁了新鮮的菠菜,吃了東西樹影里好生歇著去。”語態母愛充盈,像對我坐月子的三嫂。
爹爹蹲在石榴樹下抽著小煙袋,細瞇瞇的眼睛蓄滿笑意。其時,頭頂的小石榴青褐褐的,水嫩,正稠稠密密蕩秋千,似乎能聽到擠擠碰碰的叮當聲。榴嘴里深紅干皺的紅榴花,噙不住,吐下來,樹底下就落了一圈干松松的細碎花瓣,寂寂,安靜,惹人生憐。有一小朵猶猶疑疑落在爹爹腳面子上,他粗大的手指捻起皺皺縮縮的落花,不禁感嘆:“日子頭流水一樣快,攥都攥不住呃。轉眼,端午了!可不是,端午了。”他喃喃著,抬眼,陽光真亮!晃得人眼花。恍惚中,只見娘掀開鴨圈的柵欄門,走出來,裊裊的,笑容清甜,像幾十年前新嫁的模樣。
“看,鴨子們也不偷懶。除了送給娘,居然還剩下八九顆。腌起來呢?還是端午給孩子們拉拉饞?那墻根下的小壇子里,已有了小二十只呢。麥季子上也沒吃完。”娘手指輕輕扒拉著青皮蛋,語氣甜糯,商量著。
爹爹在鞋幫上磕了磕煙袋鍋子,立起身,探頭往娘手上看了看,陽光在牙
齒上開了花:“乖乖,這鴨蛋的個頭快趕上鵝蛋大了。真做活呃!下集我再多買些麩子去,不能虧了小東西們。”
籬笆下的牛耳朵,開了細小的黃花,碎碎的,小小的,羞怯怯藏在油汪汪肥厚的葉間,不仔細看,還真看不出來。爹爹的目光掠過牛耳朵,落在一蓬車前子上。恰好六丫頭卷著書本走過來,翻開泛黃的書頁,指給爹爹看:“這野草,可是不得了,在《詩經》里叫芣苢。三千多年前,就拿來做草藥用了。”爹爹瞇起細長的眼睛,彎下高大的身子,拿小煙袋在書上輕敲:“這倆字念啥?嗨嗨!多年不翻書本了,提筆忘字,好多熟悉的老伙計,都變成冷冰冰生面孔了!”
爹爹離我那么近,我嗅到他后脖頸處散發出的咸濕汗味,裹挾著濃濃的煙草氣。他頭上已有些許白發赫然入住。我心上一疼:爹爹老了,我還沒長大。那個叫時光的東西,有點不可愛了。
西籬的老婦人,何時歇了口,已經坐在老梧桐的影里了,膝頭擺放著小簸箕,俯著身子挑糧食。一只灰羽白翅尖的鳥,在她腳邊蹦蹦跳跳,歡喜撿拾她拋掉的稗子。光影里,灰衫的老婆婆,單薄,瘦小,像語文課本里的一副黑白插圖,蕭淡疏離。我突然覺得,離奶奶那么遠。
二
端午來臨時,田地里剛收過麥子。人和麥子一樣干癟。麥收季節里,勞動的艱辛和收成,用數學課本里的話說:不成正比。大地,像母親瘦瘠的胸,年年月月,營養不良,已經擠軋不出豐盈的乳汁,莊稼也嗷嗷待哺。經過麥季的農人,元氣大傷。近乎原始的收割農具,消耗掉了他們體內微薄的養分。一個麥季下來,爹爹面黃肌瘦,不,更確切的說是:黑皮寡瘦。
娘心疼極了。傍黑,燒了熱水幫爹爹擦背。暗影里,爹爹寬薄的后背,打麥場似的平,瘦骨嶙峋,像牛棚里疲憊不堪的老黃。娘嚶嚶啜泣。爹爹滿不在乎,朗朗笑著,說:“你看,你看,莊稼人不都是這樣子么?咱又不是高門大戶的白臉書生。再說了,日頭漂曬,一年無病,你可別小瞧了這一年一季的麥收,老中醫樟木爺爺常說:麥氣能逼出人一年的苦寒,不經過麥季的敲打,五臟六腑的寒氣出不來......這可有啥傷心的?”
歲月像把小錘子,把昔年清雋鮮生的爹爹,鍛造成了瘦骨錚錚的中年農夫。娘是看著爹爹,從青蔥到蒼老,被生活一步步篡改了模樣的,怎能不心疼而無奈!娘卻不太顯老,和爹爹走在一起,曾多次被生人誤認為是爹爹的大閨女呢。為此,娘憂傷,爹爹驕傲。娘顯著年輕,以至于讓奶奶不屑,甚至恨毒,平日里和親戚鄰居拉呱,故意大聲說給娘聽:“可不是長著一副狐媚樣子!天天嬌滴滴的,捻不動針,提不起線。人家是大小姐呃!鳳凰掉到雞窩里,老大(我爹爹)還不得當娘娘一樣供著?就差早晚磕頭問安了。”
娘之所以比實際年齡年輕十來歲,一半是因為人生得玲瓏嬌俏。她聲音裊娜,清甜,站在籬笆院里喚娃回屋吃飯,不見人,只聽聲音,竟惹得籬外走村串巷的貨郎小哥以為是誰家十六七歲的小大姐呢!直想著柴門討水,做那唐朝崔護,細探佳人。一半是因為爹爹,溫厚細膩。高高大大的男人,卻心細如絲,一副寬寬肩膀與胸懷,能擔起世間十分的柴煙,能遮蔽來襲的所有風雨。娘永遠是他身后的小女人。爹爹是一堵墻,卻在抵御奶奶的襲擊時,有些步履踉蹌,有些力不從心的小趔趄。他只能斡旋,只有巧費心思。因為兩個女人,都是他的至愛,他施展不了拳腳,生怕誤傷了誰。他的高大勇敢,在奶奶面前,瞬間塌方。
可爹爹是讀過書的,他不同于一般農夫,他有慧巧的心思,他護著妻子,又不誤傷親娘。他絕不是風箱中的老鼠,也不是熱鍋上的小蟻,他能游刃有余,舉重若輕。有時候,看爹爹在奶奶與娘之間周旋,突然就想起和村里小伙伴們常常玩的游戲,游戲的名字叫:老鷹捉小雞。爹爹是雄壯的大公雞,娘是扯著他后衣襟的小母雞,藏在他身后左躲右閃。爹爹則張開雙翅,左左右右,前前后后,敏捷地躲避著前方來襲者。不用說,奶奶就是爹爹對面那只老鷹了,氣勢洶洶,無時無刻不想著襲擊大公雞身后的小母雞。真有意思呃!只是,奶奶不夠高大,不那么彪悍,不那么兇惡。她只是妒,娘是長媳,娘咣地嫁進來,一下子就搶去了她的大兒子,她手捧奶喂養大的兒子呃!她一時還反應不過來,一時還接受不了。小叔就不一樣了,小叔是她的小兒子,等他長起來,娶媳婦,奶奶就有了足夠當婆婆的年齡與心理。面對小兒媳,她妥妥的,是婆婆,攢夠了一簸籮一簸籮的鵝蛋來當婆婆,當奶奶。其時,更重要的一點是,娘長得太俊美,小嬸長得太樸實。奶奶也是個喜歡穿繡花鞋的,站灶臺也不忘搽粉兒的,美人相妒嘛!從我能拿得動厚厚《詩經》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奶奶討厭我娘的原因了,娘就像《詩經》里的靜女,紅著臉兒躲在墻根等人,手里舉著一枝白茅或者紅色的草,美麗又文靜。娘是讀過書的,也曾是那殷實人家綠窗下的女兒。她不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只遵從自己的內心,卓文君似的叛逃,一株植物似的扎根在爹爹貧瘠的籬笆院里,她不覺得苦與累。生兒育女,粗茶淡飯,日日養鵝養鴨養雞子,還養了一條溫馴的土狗小白,那狗高大干凈,見人不咬,和氣得像鄰家兄長。
娘不侍稼穡好多年,插花子描紅也不精。似乎只會養禽種花。人家小菜園里垂垂蕩蕩,花紅柳綠的。她的小花園里,花香襲人,明明暗暗的,好不生氣。奶奶路過一回罵一回,罵她糟蹋土地,白眉赤眼的,小姐做派,不是過日子的人。奶奶的小菜園倒真是人勤地不懶,葳蕤茂盛,小叔他們兩家怎么也吃不完呀!頭后晌剛卸了半籃子,次日清晨又躥了小半筐。鄉下油金貴,炒菜費油,咔咔生吃又脹肚。咋辦?老太太捎信傳信地給女兒們,招呼來取蔬果,鎮上的姑姑們便隔三差五地來,沉甸甸肩扛手提了去。偶爾,老太太也垂憐東籬的兒孫,施舍幾根實在吃不完的瓜果,卻隔著籬笆投食,威儀的小腳步絕不越矩。娘便受寵若驚,惶惶不安,尋摸著四角空落的寒舍,欲投之以桃,報之以瓊琚。她窮得只有鵝蛋,哪有瓊琚!
三
端午節,一大早娘就在小灶屋里忙活開了。她是鎮子上楊大裁縫的三女兒,從小豐衣足食,大小節日都講究個儀式感,即使婚后日子貧窮,也盡其所能,隆重對待,決不潦草。清晨,紅蜀葵張開鮮嫩臉盤子,一朵朵噙香含露,在籬笆前曳曳招搖。花腹鳥的婉曲叫聲里,娘晨妝初好,軟紅的小布衫,烏溜的蓮蓬髻,鬢邊的紅蜀葵,面容明凈,眼神清寧。啪—半盆子茉莉花香的胰子水潑到木芙蓉下,空氣里彌散起淡淡的花香。木芙蓉結著碧綠的蕾,仿佛是待嫁的老姑娘,不禁催,倘若誰大力吆喝一聲,就會撲棱棱開出滿枝蝴蝶飛。娘站在廊檐下,手搭涼棚環顧籬笆院,宛如君王臨朝,滿院子生靈都是她的臣民。花花草草,雞鴨鵝鳥。老黃在棚下吃草,甩著鼻哨,十分愜意。新苫的芒草棚頂,跳躍著小魚似的陽光。小白撒歡,小孩子脾氣,舊籬門下里外穿梭,經線子似的。胖母雞被小白撞了個趔趄,咯咯噠,咯咯噠地驚怒個沒完。中年的花臉貓串門子,在西籬的矮籬笆上輕悄來去,碰到籬下紅蓼舉起的小紅臉,忍不住伸貓爪拍打一下。粉粉紫紫的牽牛花,扛著一只只明亮小喇叭,吹吹打打,辦喜事似的熱鬧。娘的一籬江山,歡實,朝氣,國泰民安。
娘在土黃盆中燙了白面,大灶膛里燃了干柴,鐵鍋底內倒了籽油,小陶罐里撈起白糖,炸糖糕。爹爹也咳咳起了床,先去淘草缸里撈一罩子青草,給牛棚里的功臣老黃添上。老黃抬起溫順的大眼睛,輕輕哞一聲,算是給主人問晨安。爹爹拍一拍大黃的腦袋,溫聲說:“老伙計,過罷了麥季,你可以歇口氣了。好好養養膘,秋季咱還得接著出力呃!”
小灶屋里,一只只焦黃酥香的糖糕撈在小竹筐里。娘喊爹爹過去,說是灶膛里火太盛,讓退出幾根劈柴。接著要炸油條了,不需要旺旺的火,細火瑩瑩著,就行。娘兩手油,汗水浸了眼,只好抬起手腕蹭一蹭粉膩膩的汗珠子。棗紅案板上,她切了一排溜細短的面條條,兩根指頭捻起面條條的兩頭,輕輕一擰,低低丟到泛著細碎油花的鍋里,兩根長長的竹筷子輕快扒拉著,面條條在熱油里輕盈翻身,蓬松舒展,一根金黃松軟的油條就成了。娘在當庭擺下了飯桌,六丫頭早流著細細讒涎坐到舊木桌前,端端正正等著吃。娘把小山似的兩只竹筐搬上飯桌,籬笆院里,香氣長了腳似的四處走,借著晨風裊裊扭出去,左鄰右舍顯擺去了。
我被娘攆起來,她拿竹筷子敲住探向竹筐的小爪子。她囑我把裝得冒尖的兩大碗給西院的奶奶送過去。又讓我送后別轉回,順道把后院她的兒子兒媳喊來。
我不情不愿往西籬走,剛轉過墻角,就低頭迅速銜起一塊糕,次次哈哈,燙得舌頭火燒火燎。做賊似的四下瞄,還好,只有那只花腹鳥站在奶奶家的籬笆上,歪著頭看我。我一陣羞惱,跺著腳轟趕,鳥一翅膀飛起,大驚小怪叫個不停,那鳥語一定是:“六丫頭偷嘴啦!六丫頭偷嘴啦!”這該打的鳥!
從奶奶家出來,空碗里躺了兩只粽子。那是頭天鎮子上的姑姑們送過來的,滿滿一簸籮躺在奶奶黢黑的灶臺上。我看著奶奶扒拉了半天,才挑出兩只小的,撂在我碗里。我討飯似的捧著碗往家走,心里憤憤不平:東籬大小六個孩子呢,兩只粽,讓人怎么分?還不夠塞牙縫的呢!哼,那么多粽子一定是留給小叔家的。我一頭拱進籬笆門。一抬頭,娘笑模笑樣地看著我,拿那花瓣似的柔軟聲調嗔怨道:“小六呀!小小年紀好迷瞪。快快放下碗,去后院喊你三嫂三哥來吃飯。油條糖糕要趁熱吃,涼了松塔塔的又水氣,失了味道。”
此時,娘已重新洗了臉,白潤潤的臉盤子眉黑唇紅。腰間的碎花小圍裙也解下了,她立在廊檐下,揚著細白的手臂吩咐我。她又換了短袖的月白衫子,那衫子是收罷麥新做的,對襟上盤著的松綠布扣,像一只只小蝶斂了翅。怨不得奶奶又妒又嫌,娘通體的古雅氣韻,哪里像鄉野村婦?那是人家做女兒時的富貴滋養出來的呀!與奶奶何干?娘今天特意戴了簪,晶晶的銀簪,在白稠的陽光里灼灼晃動,煞是嫵媚。娘看我張著嘴發愣,忍不住轉頭沖爹爹笑道:“朱先生,你看近來六丫頭是不是生了心事?時常發呆呃。”娘咯咯咯的笑聲,像夏日的冰棍兒,又涼又甜,撲面而來。我一激靈,回過神來。把兩只碗放在舊木桌上,折身就往外跑。
沿著布滿野花野草的細瘦小路,我往后院跑。三嫂家紅房頂的低矮屋子,像結在野花徑一端的紅果子。一路上,小蒼耳掛滿了褲腳,裸露的腳脖子麻酥酥的。小白在身前身后撒歡,也過節似的興奮。小東西瞎高興個啥?誰還舍得把端午的美味分一羹給它?娘照例會拿冷硬的雜糧剩饅頭,泡了刷鍋水,給它。只不過,今天的泔水里多了幾顆油星子罷了。小白不嫌棄,它會像往常一樣水汪汪的大眼睛望著主人們香噴噴吃飯,嘴里流著長長的涎水,卻一點不慍惱,一副忠仆的樣子。
早飯的糖糕與油條,一粒不剩,大家尚意猶未盡,端午的好滋味,仍在舌尖上纏繞。娘只吃了一點,就說飽了,在我們還狼吞虎咽吃得起勁時,就離開飯桌,開始泡花生,紅棗,大米,葡萄干,洗青青的葦葉,準備包粽子了。葦葉是頭天爹爹去野塘里摘來的。包粽子的一干食材,是鎮子上的姥爺打發小姨前幾天送來的。
半晌午頭上,娘把棗木案板搬到了石榴樹下,在一團婆娑的紅花青榴的影兒里,開始包粽子。她塵世間又一年隆重的端午節,在榴紅麥香中,喜眉喜眼地到來了!時光,搖啊搖,帶著俗世的香,帶著小民的愛。
歲月像把小錘子,把昔年清雋鮮生的爹爹,鍛造成了瘦骨錚錚的中年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