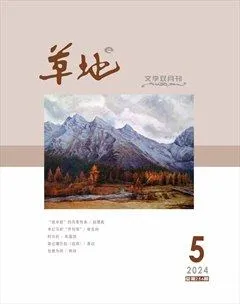也曾為師
一九八九年的鄉村,熱鬧又喧嘩。
一九八九年的鄉村中心校,學生多、老師多,地盤兒也多。十七歲的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了為期十年的鄉村教學生涯。
學校建在黃土高坡上,像釘子一樣嵌進黃土之中。校門外兩棵枝繁葉茂的老核桃樹從農人的田地越過土圍墻伸向校門,土圍墻只擋住了核桃樹的根部,核桃樹的大部分枝條經過上百年的努力,竄得跟五層教學樓齊平,形成一個巨大的天然樹傘,傘身遮住了大半個路面,傘柄處是一個小賣部。通往學校只有兩條通道,主干道從核桃樹下經過,另一條從柏樹下經過,兩條黃泥巴路在校門口相向完成交匯,同時被一把黑得發亮的大鐵鎖拒之門外。被拒之門外的還有附近三三兩兩的村民,他們或是來小賣部買點東西,或是在校門口抽上一支煙,順便透過小鐵柱焊接成的大鐵門向校內張望:學生的讀書聲,體育課上的哨音,學生投籃的命中率,甚至老師或者學生的著裝都會成為他們的話題,樂此不疲。
這所中心校的初中部招收金江、復興、德勝、五甲四個村的學生,小學部只收復興村的學生。初中生分住讀和走讀,小學生全部走讀。學校的周圍無一家企業,離學校最近的一家單位是鄉鎮府,除了一些年輕人晚飯后來學校打籃球,其他大部分時間互不往來。
這是90年代充滿著勃勃生機的鄉中心學校最為普通的模樣,但它們無一例外地會死在二十一世紀的春天,像一個逐漸發病的老人,起先是器官的慢慢衰竭,然后是意識的模糊,最后像一株枯死在秋天的小草,了無蹤跡。
那無疑是一個人口極度密集的年代,學校到處都是密密匝匝的人,我在這密密匝匝的擁擠中,成為了一名小學語文老師,成為小學語文老師那一年,我不滿十七歲。十七歲的我混跡在孩子們中間,與學生并沒有多少差別。丟沙包、踢毽子、跳繩、跳房,我也是鄉下長大的野孩子一枚,依舊保持頑劣的天性。與學生混太熟,他們漸漸就不把我當老師,不交作業、上課做鬼臉、有時還頂撞我,打掃衛生不徹底……。分管業務的校長長了一雙彎彎的笑眼:“七七老師,你今年幾歲了?”七七是我的名字,他們有時候叫我七七,有時候又叫我小七七,我是學校教師隊伍里年齡最小的那一個,而我的樓上住了一位跟我同名同姓的男老師,為了區別,老師們叫我小七七。我老實回答“十七”,集體辦公的老師們便“轟”地笑了起來。我尷尬得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分管領導刻意把揚起的唇角往下壓了壓。然后開始給我講如何管好班級、管好學生、提高學生成績,末了說:“學生和老師不要走得太近,必要時要收拾一兩個學生。”
所謂收拾,大概都知道意思。
當我頭一回揚起手中的教鞭時,我的學生以為我在跟他們開玩笑,笑嘻嘻地歪著頭看著我,我揚在半空中的教鞭不知道該如何落下,窘迫之時突然想起辦公室老師們的群嘲,我的臉莫名地燒起來,再看學生的眼神便覺得他們眼神里全是挑釁,手中的教鞭幾乎是不由自主地惡狠狠地落下。我的學生先是驚恐地睜大眼睛,后來仿佛才感覺到疼痛,再后來便“哇”地哭出聲來,看他“哇哇”大哭的表情里我竟聽出了許多不甘和委屈。
我對學生和自己的要求都越來越嚴格,不單是學生越來越怕我,就連自己想想也有點怕。漸漸地,我在與學生的距離中體會到了當老師的責任,也明白了自己的水平還差得遠,只要有空就去聽別的老師上課,每個單元考試之前讓學生自己定考試的分數,單元考試下來達不到分數的,便各種懲罰。操場上孩子們丟沙包時,一看見我便各自散開。
我再也沒有被叫到辦公室去過,學生再看到我時,眼里也充滿了恐懼和逃避,他們在學習上卻分外地努力了,在慣常的學期考試中,我所教的學科意外地得了學區第一名。年少的我,與學生之間隔閡的遺憾很快被紅艷艷的證書和微薄的獎金彌補,注重結果的獎勵堅定了我的教學方向,也導致我和學生之間更大的嫌隙。
一個夏日慵懶的下午,柳樹上的蟬鳴一陣接一陣,剛經歷地震,我們上課的地點從教室搬到了板棚里,無處消散的熱氣中,我正在為學生們上一堂試卷分析課。“同學們看看自己的卷面,干凈整潔的很少,有的卷面上的標點符號都飛到天上去了,勾勾劃劃、涂涂抹抹的連寫的什么都看不清……”“哈哈哈,標點飛上天了,飛上天了……”板棚的窗口上趴著一個高年級的男生,男生瘦瘦的臉,頭發朝天豎著,變腔變調地學我說話,眼神里充滿挑釁。我拿起教鞭作勢往教室門外走,男孩一溜煙地跑掉了。我再回到課堂,男孩又回來了,繼續“嘀嘀咕咕”地學我,我再去追,他又跑掉了。我沮喪地回到課堂,我的學生們臉上的各種表情還沒有來得及收住,竊竊私語卻中止了。我向全班發問,這男孩子姓甚名誰,學生們的眼神一下子齊刷刷地集中到班上的小女生身上。女孩兒名叫紅,長得清秀乖巧,上課卻總是不在狀態,清澈的眼神里全是懵懂,不管是未完成作業或者是考試成績不及格,為此沒少挨我的教鞭。每一回教鞭一舉起,女孩便先叫起來,眼里一直汪著的眼淚便“嘩嘩”地往下流。女孩兒躲避著集體的目光,像自己犯了錯似的低下了頭,不安地用雙手絞著衣角。有學生說,那男孩是紅的哥哥。
去紅家做家訪的那個下午,不到四點就放學了。我跟在紅的身后,紅一路磨磨蹭蹭,癟癟的書包灰溜溜地耷拉在她瘦小的身體上。書包上那些人工繡花明顯臟了,黑乎乎地看不出花朵本來的顏色。紅在我的催促下終于磨磨蹭蹭到了她家。柴籬笆圍著三間不大的土屋,紅怯怯地推開柴籬笆門,籬笆過處灰塵便揚了起來。天氣持續干燥,紅的父母去地里給麥苗灌水去了,等到太陽快落山才回來。他們肩上扛著鋤頭,一身灰塵,見到我,愣了一下。我自我介紹說是紅的老師,來做家訪。紅的父親忙著把肩上的鋤頭往墻上掛,母親忙著打開廚房的門去給院子里的雞舀水喝,他們都沒有空閑搭理我。院壩里的我像一個孩子似的沒輕沒重地說了紅的哥哥對我的挑釁和紅不努力讀書的事情,紅的父親都沒有聽完我說話,便憤怒地將已經上墻的鋤頭扔到地上,轉身從屋檐下取來鞭子,追著紅的哥哥就打,紅的母親并不敢去勸阻,只是罵罵咧咧地拴上圍腰進了豬圈,她的咒罵聲隨著她兒子的喊叫聲變得越來越大,先是說老天不公,地里不出莊稼,連年歉收。接下來說孩子不爭氣,吃了上頓沒下頓,早就不想讓他們讀書了。紅的父親使勁地打著男孩,男孩跑著跑著就不跑了,杵在他父親的身邊任鞭子在他身上起起落落,男孩倔強地昂著頭,咬著牙承受,實在忍不住了便悶吼一聲,然后眼神恐怖地瞪著我。頭一回做家訪的我被嚇蒙了,忘了自己是去做什么的,甚至自不量力地去拉開那條鞭子,卻被紅的父親一把推到了墻角,紅的母親見狀,又跟紅的父親大吵起來。院子里的雞停止了吃食,盯著這鬧哄哄的人群,莫名其妙。
我忘了自己是怎么走出那片柴籬笆的,只記得山邊的晚霞紅透了半邊天,而我卻十分茫然。
然而當新一天的曙光到來,我已然忘記前一天發生的一切。人就像打了雞血,又投入到熱火朝天的教學工作中,向老教師學習經驗,向同行請教,觀摩全國優秀教師的示范課……在不斷地嘗試和學習中愈挫愈勇,我所帶的學生每年全學區統考評比都穩居全學區第一,在全縣統考中也名列前茅。
在以學生分數為尺度考評教師的年代,我所教的班級平均分要超過同學科平行班老師所帶的班級平均分十多分,沒有人愿意辛辛苦苦教一年學生下來未得到任何鼓勵,還要扣自己的工資。考完試總有老師不相信自己學生的成績,去查卷,也有老師查我學生的試卷。無果后,再也不愿意跟我教同一年級的平行班,如果輪到了,便想方設法調另外的班級。十年,我用這樣的方式獲得一摞榮譽證書,那些紅艷艷的榮譽證書曾經是我的青春和驕傲,而現在看來,它們更像一個個傷疤記錄著我青澀的成長。
多年后的一個夏天,我在外地參加一個學歷培訓。讀私立幼兒園的兒子被老師體罰,電話那頭,兒子哭得泣不成聲,電話這頭,我也是淚流滿面,但我依舊小心翼翼地討好老師,生怕她會更加虐待我的孩子。整個下午,我沿著岷江河走了很久,心里的怨恨如同荒草蔓延,多年都不能釋懷。而想到曾經為師的我,十年間曾無數次這樣對待過我的學生,他們和他們的父母也和我一樣有過錐心的疼痛。
又過了十年,我以政府工作人員的身份回到了曾經所在的鄉鎮,與當地村社主任進行換屆交流談話,里面兩位村主任竟是我的學生。談完話竟問我,當年為什么對他們那么嚴苛?盡管江湖闖蕩數十年,我還是窘迫地低下了頭,像當年汪曾祺筆下的老師一樣訥訥。現在想想,真也不必!
那些曾經引以為豪的獎狀,我寧愿從沒有出現在我的人生中。
三十多年后,我再回到年輕時任教的中心學校,我成了一名作家。作為一名出過幾本書的寫作者,卻沒有一篇是關于教育題材的。我好像是為了彌補這個遺憾才又重回了學校,是選在學校沒有人的周末去的。越往前走越擔心遇見熟人,是真正的“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其實,大部分當年共事的同事早已各奔前程,許多人改了行,并在行業內風生水起。學校周圍并沒有多大的改變,老土墻還在,門口的大核桃樹還在,校園后頭四人合抱的古柏樹還在,校園里的古冬青樹還在,甚至校園,都還是三十年前的樣子。沒有了初中部,上千人的學校只有一百多名學生在校就讀。大部分教室空著,窗玻璃有雨水流過又被灰塵襲擊的痕跡,有的門窗都已損壞。立在教學樓前的操場上,人同校舍一樣寂靜到落寞。我在心里默數著自己曾經任教過的教室,一些傷感便不由自主地涌上心間。記憶中的教室里、欄桿上、過道里、食堂前全是學生,有的在讀書,有的在考試,有調皮蛋正將手里小半截粉筆往樓下漂亮女老師的面前扔……。樓道里的笑聲在耳邊回響起來了,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空。
食堂還在,顯然已經很久沒有使用了。看到食堂前粗大的塑料管,我的渾身頓時起滿了雞皮疙瘩,從這個水管里曾經很多回流出過泡得發白的死老鼠,水管連通的水池,是我們全校師生的生命之水。自有死老鼠從水管里流出后,學校里大部分老師便去山后的水溝里挑流動的水喝,水溝里的水時渾時清。挑水的路上還需要經過一位“瘋子”的家門口,“瘋子”傳說是一位才子,因愛受挫后回到了老家,也不住老屋,在老屋的門外搭一間草屋住,披頭散發,奇瘦。大部分時間在長長的白紙上狂草,寫下許多我們不認識的毛筆字,然后將那些字掛在樹枝上,陰風慘慘的樣子。我們去挑水,都要約上三五個人,生怕他會發瘋,但的確,十年的教書生涯中從未看到過他發一回瘋,心底有愛的人是善良的。
賣飯的木窗早已殘缺不全、油跡斑斑,顯然也是很久沒有使用了。我的眼前浮現出中午學生“搶”飯的熱鬧場景。“餓”依舊是學生時代的主旋律,一些學生把打飯菜的碗擱在書桌里,中午下課鈴一響便徑直從教室沖向飯堂,去得晚了便要排長長的隊,排在后頭的調皮蛋冷不丁使勁往前一擠,一些學生手上的碗或飯盒便落在了地上,招來一片指責聲。值周老師排查,大家便又相互保護。幸好每一個學生的飯盒或者碗都是鐵或塑料制的,經碰。食堂饅頭堿水時重時輕,有時發黃,有時發不開,鐵疙瘩一般。賣飯阿姨手中的勺子在菜盆里快速調配,不經意間有的同學碗里的葷菜便多一些,有一些同學便少一些。
住校生都是初中學生,他們大多從附近較遠的村子來這里讀書,有的每周還從家里帶一飯盒菜來學校,帶在飯盒里的菜大多是能放的,節約一周前幾天的菜錢。有的飯盒里裝一盒臘肉炒豆豉,則一周不用在食堂買葷菜了。在食堂打一盒白米飯,回寢室挖一勺子豆豉和肉捂到米飯下面或者把肉夾在饅頭中間便是一餐了。因此,總有老師把飯菜票勻一些出來給家庭條件不好的學生。食堂前的楊樹下,坐著吃飯的老師,大多學生便回到寢室吃飯,一些害羞的女生,得等到老師午休才出來洗自己的飯盒。
食堂寂靜,我卻仿佛聞到了飯菜的香味,眼前恍然出現一大盆一大盆的涼拌粉條、炒土豆片、炒蓮白,它們小山一樣堆在飯點前的窗口,或涼或暖的安慰彼時的慌張。
從食堂前的兩棵柳樹下往左拐,又有三間教室,這排教室背風,離主教區遠,那是我離開學校前因學生增多又依照地形修建的。我在這里接手了小學數學教學工作,這對于我而言,是一種打破慣性地挑戰,但畢竟是低年級的教學,所以有一些時間去整理教室前方自家的小菜園了,愛人在菜地種了紅的番茄、青的海椒,一小畦青蔥和芫荽,馬不停蹄的十年,在臨離開時才有了和它們認真對視的心情。
經過操場,耳畔又響起老校長“立正、稍息……”后的訓話聲,我的眼睛有一些潮濕。當年的老校長已經天人永隔,他是一名雷厲風行的人,在學校管理上有軍人做派,這所中心校在他的帶領下完成了許多個第一,比如全縣鄉中心校最早集體辦公的學校,第一個把全校幾百名住校生、一百多位教職員工集中起來跑步的學校,最重要的是許多學生從這里出發,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各種中高等院校,實現了自己脫離“農人”生活的理想人生……。把教育視為平生奮斗的事業的老校長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大概至死都沒有想到,當年轟轟烈烈人滿為患的學校如今寂寥成這樣。曾經一個村子至少有一所村級小學,每個稍大的鄉鎮都有自己的中學,到2000年后,幾個鄉鎮合并起來都難有一所學校了。學校早就沒有足夠的生源。家庭條件稍好一點的,都把孩子送到內地去讀書了,跑爸、跑媽已經成了高原特有的怪象。教師多了起來,多起來的教師再也不會像我們當年那樣抽打學生,他們和學生、學生家長做朋友,考試也不再統考和評分,曾經輝煌的教學成績不復存在。
風吹過古冬青樹,一些積葉便隨著風飄了下來。我的眼前隱約浮現大冬青樹上吊著的那面鐵皮做的鐘,厚,且有些凹凸不平。一根鐵棒就掛在鐵皮旁邊,敲鐘人敲鐘的聲音時大時小,有老師聽不見上下課鈴響,意見頗大。后來,便有了電鈴,電鈴的聲音又尖又細,能穿透學校的每個角落,甚至會覆蓋校外半里路的地方。遠遠地,我看見了當年的守校人,他早已不復當年雄姿,一派風燭殘年的樣子從校外的小道上往梨林深處走,甚至,都沒有側下頭看看這座曾經到處都是他的聲音的學校。
我立在古冬青樹下,父親曾經任教的藏寨中學也浮現在我眼前。那是一所消失得更早的,即將成為淹沒區的學校。校園屋頂上的舊瓦、老椽子都被取光,只剩下一些拆得七零八落的墻空洞杵在風中。學校大門只剩下一個泥筑的框架,左邊的半堵墻隱隱約約現著“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雨水和泥將墻面弄得斑駁不堪,教室里的那些黑板上依稀還有粉筆書寫的痕跡,屬于父親的粉筆早已隨著滔滔的江水流逝,為救自己的學生失去了年輕生命的父親,也一樣不會再有人記起。
古冬青樹的葉子輕輕落在我身上,仿佛是安慰,又好像是提醒。我的周圍空無一人,我的周圍全都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