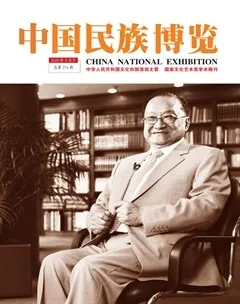清巫山嚴禁差役詐擾告示碑考
【摘 要】重慶市巫山縣騾坪鎮出土一通清代告示碑。通過科學技術修復和參考歷史文獻,還原碑刻原貌,精確釋讀碑刻銘文。并結合歷史文化背景,進一步解讀四川總督禁止差役下鄉敲詐勒索民眾訴訟費的原因。為考證清代基層治理制度、告示制度和司法訴訟制度提供了重要線索,尤其為理解清代四川地區訟獄繁興民情的形成有重要參考價值。
【關鍵詞】巫山;清代;差役;訴訟;告示
【中圖分類號】K249;D6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4)06—029—03
清光緒《巫山縣志》記載巫山民風:“簡詞訟、性淳樸” [1],但重慶市巫山縣騾坪七仙姑廟發現的一通清代嚴禁差役詐擾告示碑,卻告訴我們歷史并非如此。此碑記載了清道光十年仲夏月(1830年7月),官府為緩解官民沖突而禁止衙役下鄉敲詐勒索的通知,整篇文章初讀之令人感動,但隨著了解及研究的加深,發現這不僅個基層司法問題,應被當作縣鄉行政運作加以分析。
一、碑刻概況
2016年3月,七仙姑廟施工時發現一堆四分五裂的碑刻,后經縣文物管理所的科學修復,基本恢復原貌,現藏于巫山博物館。碑為青石質地,殘高104cm,寬74cm,文以楷書勒就,25行,殘留1030字。雖碑刻不少字脫落,但碑文所涉及重要內容的文字,基本可以認讀(圖1)。經查,該碑內容與四川省檔案館館藏文獻《道光十年三月初三日重慶府抄發川督告示》(以下簡稱“告示”)相同。
告示的撰寫者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四川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管巡撫事,世襲一等侯琦善。文中使用了大量的訴訟專門術語,大意如下。
四川省各地各級衙門的差役、書吏、衙役等辦職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利用訴訟人心理,巧立名目,強取豪奪,向民眾收取名目繁多的訟費的現象已經普遍存在,且屢禁不止,給當事人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為此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人也比比皆是。比如一旦發生盜竊案,差役不論案情輕重,必先探明當事人的家境,如果是富裕之家,就設法拉攏關系、收受賄賂,不去追兇破案,反而是謊稱有線索,多次到當事人家里甚至殃及周圍的人,然后在司法各個環節人為地設置種種障礙以索取更多的收入,平民百姓為了息事寧人,只好拿錢消災。

官府對此現象一是革除陋規、減少差役,二是密訪嚴查、嚴懲不貸,但更多的是期望通過對差役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希望他們設身處地,為當事人著想,秉公執法,切忌徇私舞弊。因此,特布告示以望各衙門差役等人員廣而告之,以此為禁。
二、清代巫山地方治理制度探析
清代,四川總督管轄四川省,領成都府、重慶府、夔州府等八府,巫山縣屬于夔州府[2]。縣級衙門是清朝對地方控制最基層的行政設置,治理職責由知縣承擔,下有衙役和胥吏。根據《光緒巫山縣志》記載:“劉從善,道光五年膺巫山,任民間詞訟,聽斷如神,案無留牘,邑無冤民,遂有劉青天之目。”“張炳,陜西進士,道光九年至道光十年任巫山知縣。清廉持己,勤慎奉公,民間訟詞。” [3]可知,道光年間的歷任巫山知縣均將民間訴訟作為政績的重點來抓,此碑即是道光十年時任巫山知縣的張炳在同年的仲夏月,將川督告示以刻碑勒石的形式保存至今。
(一)告示制度
中國古代在縣以下不設治,即朝堂派出官吏只到縣一級,縣以下的廣大農村實行自治。具有契約精神的告示碑便是地方自治最典型的表現之一。在清代,知縣通過告示向鄉村社會傳達國家的各項政策,表達官方基本態度。同時,鄉村社會權衡利弊,遵從“實事求是”的功利原則,將最關心的事件及最難解決的問題主動向官府申請頒發告示,要求國家權力的介入。
騾坪鎮位于巫山縣、巴東交界地,是重要的戰略要地[4]。場鎮北有當地村民募捐的“七仙姑”廟宇,香火十分旺盛。碑刻存放于村落神廟口,不僅是古代官道必經之地,各樣人馬過往頻繁,而且表明了其內容的神圣性。告示中提及朝堂令各州縣對裁減和留下的差役造冊進行公示、對嚴禁差役詐擾的做法進行公示,不僅僅是對差役的約束,更是為了讓深受其害的廣大鄉民知曉朝堂對此類擾民行為的重視程度。
以告示中主要提到的訴訟案件“盜劫”為例,便是當時巫山鄉民最關心的事情。此地盜賊興盛的原因,大概有三:一是社會動蕩不安,清康熙至道光年間,起義的農民軍和官兵在巫山連年激戰達16余場[5],嘉慶年間(1796年—1820年),白蓮教匪經騾坪逃竄至巴東,現境內鎮壓白蓮教時留下的大、小萬人坑[6],而且道光六年至七年(1826年—1827年),連續兩年發生夏秋大旱,民不聊生。二是人口復雜,地處川、陜、鄂交界地區的巫山,是人地關系交互的復雜帶,騾坪更是巴楚東西大道(歷代為連接成都至京師的驛道)上的一個關鍵節點、中轉站,“湖廣填四川”政策下,明代巫山人口密度約在3.78~11.34人/平方公里,至清嘉慶七年以后已猛增至48.88/平方公里[7],人口的過猛增長必然給當地管理、治安帶來不穩定因素。三是商賈云集,在嘉慶十八年(1813年)巴縣“團首牌甲條例”就指出:“川省地方五方雜處,匪徒最易跡。至渝城則更系水陸沖衢,商賈云集,奸盜邪淫無所不備。”[8]巫山由于豐富的山貨物產資源和“川鹽”的行銷,盜匪伴隨著商人經商、官員往來、鄉民日常流動等經濟繁榮局面而猖獗。可見,告示的政治實用性已表現得十分明顯,是清代實施地方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官民之間進行交流互動的一項不可或缺的工具。
(二)司法訴訟制度
告示中提及名目繁多的吏役,有胥吏,如書差、刑書;有衙役,如仵作、皂隸等;有雜役,如跟丁、轎夫等,他們濫設陋規為自己謀私利,或豢賊分贓,或設廳聚賭,或教盜誣報,或私開站寓濫押無辜,或聯結訟師搭臺訛詐,或把持行戶恃強抽分,或包庇匪人得規興販。清朝司法陋規為何嚴重?就必須結合清朝的司法制度及中央與地方可支配的稅收及衙役、書吏等人的收入來分析。
(1)清代國家立法的滯后性。受儒學影響,清代夢想實現“天下無事樂耕耘”的“無訟”社會,所以未對訟費作明確規定,即受理案件時的沒有征收標準。理論上,清朝的當事人參與訴訟勿需向衙門呈繳任何費用,然而在司法實踐中,訟費卻普遍存在。早在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陜西道監察御史程伯鑾,就曾向皇帝報告四川各地衙門在訴訟存在名目繁多的陋規,并建議官員革除陋規以至減少差役,降低民眾訟累[9]。到道光十年三月(1830年3月),四川總督琦善發布的告示相當于將十多年前程伯鑾的描述重復,表明在訴訟過程中當事人被衙門收取各種陋規以致敲詐勒索的現象,主要采用的是威逼利誘等理想化的“教化”手段,而不是折獄審刑。所以,整個清王朝根本并無制度上的創新來遏制陋規現象蔓延。
(2)清代地方財政的有限性。清代大部分從民間征收的錢糧賦稅收入轉變成了中央財政,留存于地方并供地方衙門開支的稅收少之又少。道光年間,巫山縣每年額征地丁銀、田房稅契銀、鹽稅銀、牙行帖稅銀、鐵稅變價銀可達4031.099兩[10]。但留給地方支配的數額非常有限,在這有限的數額中,最后用于支付衙役、書吏薪水的比例,則少之又少。巫山縣府正式在編的跟班、家丁、轎夫等人員為146人,年工資在3兩到8兩之間[11]。
(3)清代基層官吏的混亂性。清代知縣一般調任頻繁,而前文提到的衙役們卻相對穩定,實際掌握了官府的“實權”,才使得“例、吏、利”主導行政系統的運作[12]。按照周保明在《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中的估計,清朝時全國地方吏役人數當在兩百萬左右,其中大部分是白役[13]。通過比例可以推測,當時巫山縣還有臨時的白役至少在150人以上。而且無論是正式的還是臨時的吏役,不僅政治地位低下,而且工資低,養一身尚且不足,遑論家口。通過一張清光緒年間的訴訟賬單(表1)[14] ,可知訟案的案費和陋規不僅成為吏役們“額外”收入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衙門各房各班工作經費的主要來源。
所以,所以碑文中提到的各種奇特現象就可以理解了:官員則力圖減少訟案數量,因其政績考核的標準之一取決于他能否安定一方、爭訟漸少,以及審理案件效率的提高等;吏役們則是案件越多以及久拖不決則越有利于他們財源廣進。

三、結語
清代司法陋規泛濫,這同清代的封建性質、清中期后財政困難和衙役們微薄的待遇密切關聯,導致了吏治和基層司法的日益敗壞,促成了清嘉慶道光年間,四川“訟獄繁滋,甲于海內”[15]的地方民情的形成。以史為鏡,鑒往知今。我們深切感受到,自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堅持把黨建引領作為推動鄉村振興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與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充分融合,最終實現鄉村共治。
參考文獻:
[1][3][5][10][11](清)李友梁,等,纂.光緒巫山縣志[M].重慶:巫山縣志編纂委員會重印,1988.
[2](清)恩成修,劉德銓,纂.道光夔州府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1.
[4][6]四川省巫山縣地名領導小組編.四川省巫山縣地名錄[M].重慶:萬縣日報印刷廠,1983.
[7]藍勇,主編.長江三峽歷史地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8]四川省檔案館,四川大學歷史系.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下[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
[9]白瑞德.爪牙:清代縣衙的書吏和差役[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
[12]毛健予.清代的吏胥和幕賓[J].殷都學刊,1984(4).
[13]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14]鄭小春.清代陋規及其對基層司法和地方民情的影響[J].安徽史學,2009(2).
[15](清)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1.
作者簡介:張輝(1988—),女,漢族,山東泰安人,本科,館員,研究方向為文物研究、博物館展覽。